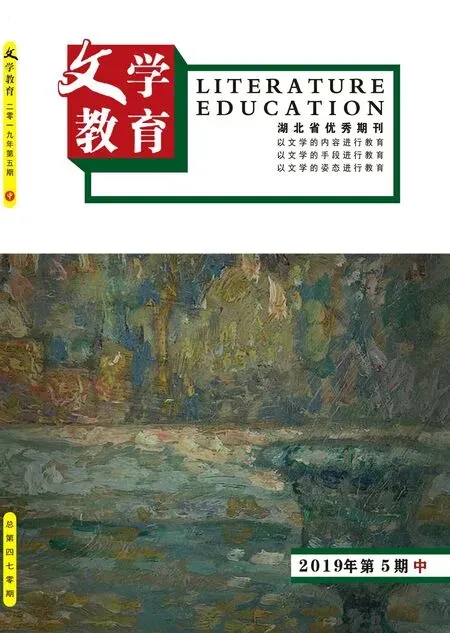淺析嚴歌苓小說中的女性形象
李 蓉
一.出國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嚴歌苓出國前所發表的小說數目較之出國后發表的作品數目是相對甚少,《蔥》是嚴歌苓發表的第一部作品,但由于當時文筆稚嫩、思想深度層次還沒有達到一個成熟的境界,在作品發表后并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和評論界的關注。隨后發表的幾部作品,也由于作者主觀化意識太強、敘事效果不夠強烈也未得到較多的關注。而她在出國前發表的最后一篇小說《雌性的草地》不僅反響熱烈,關注度高漲,而且為嚴歌苓之后所進行的創作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經驗,本小節將以《雌性的草地》為例來分析其出國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質。
(一)神性
《雌性的草地》故事背景發生在七十年代、文革動亂的背景下,一群年輕的女知青被放置在中國西北莽荒的大草原上,組成一個神圣而有莊重的集體——女子牧馬班,在惡劣的草原氣候和環境下牧羊軍馬,將美好的青春和珍貴的生命奉獻給這片草地,直到犧牲。故事從小點兒這個有偷竊、亂倫等不良行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馬班開始,她年紀雖小,卻有著各種騙人的技巧使得自己可以在女子牧馬班生存下去,同時,以她自己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有著莊重而有殘酷的使命的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所有人。嚴歌苓寫過很多關于雌性的作品,她以自身作為女性來深愛著雌性這個生物體,她也曾對“雌性”做過這樣的解釋:“它包含女性的社會學層次的意義,但更含有的是生物學、生態學,以及人類學的意義,把女性寫成雌性,這個容納是大得多,也本質得多了”,可以見得,她對這個概念的深層理解。
在女子牧馬班有一個超越人性的存在——沈紅霞,沈紅霞的人性已然超出了人性本身,因為她在艱苦的環境和卑微的團體中讓它獨自升華為神性。她是在那個殘酷壓抑時代下的犧牲者,在荒涼的草原上她用常人不理解的人性去征服了紅馬和女子牧馬班的所有人,她的人性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完美,這體現在她與紅馬的每次爭斗上。紅馬是草原上最珍貴和最難以馴服的馬,沈紅霞不顧自己的安危來馴服紅馬,使紅馬可以由她支配,她寧愿被紅馬拖到皮肉綻開、血絲模糊甚至生命垂危,也不愿用輔導員叔叔交她的方法來馴服紅馬,她深愛著紅馬,但為了集體的榮譽和紅馬的責任,卻還是一次次的送走紅馬。同時,在相處方式上,她在女子牧馬班這個集體中往往都是沉默寡言的,但她的行為卻給其他人最大的威脅,人們常常從她簡單的一個字或一句話中來猜測她所要表達的意思,她容不得對這個集體榮譽的一絲損害,在馬群走失之后,她犧牲掉了自己的睡覺時間來完成她所認為的偉大使命,她用她升華的神性去壓抑任何損害這個集體的行為。這種人性是底層苦難人民的善良激發出的神性,也是一種對正常人性扭曲之后的結果。
(二)扭曲的情感
女性歷來以母性著稱,母性顧名思義是母親之性,這是一種歷來為人所贊頌的人性,在《雌性的草地》一書中無論是女性還是母性都以一張扭曲的面目存在著,有變態母性的牧馬班班長柯丹,也有扭曲性欲的小點兒。而正是有著這樣變態的柯丹才有了怪異的孩子布布,正是小點兒扭曲的性欲才有了不合乎倫理道德的姑父與侄女之間的亂倫,這種扭曲的造成拋去人物自身存在的問題,主要還是時代和環境造成的悲哀,在西北莽荒的大草原上,女子牧馬班的女性不再被公正地視為女性。她們工作的艱辛程度超過一般男性,不僅遭受到馬粗糲的對待,而且還要忍受情欲的折磨。而一切雌性的本能擴張都是情欲,生活在復雜社會背景中的女性不僅擁有著雌性的本能,還有著對倫理道德的遵循和對于美好心靈世界的向往,由此往往掙扎在情欲與倫常、肉欲與愛情的爭斗當中。小點兒就是深陷在這種矛盾中的典型,她和姑父之間不堪的情欲就是源自于兩性之間的本能性吸引,但卻違背了最基本的倫理綱常,輩分的差別使她感到害怕,但她卻無法拒絕情欲帶給她的享受,“每回他驚險地潛越病女人將她抱在懷里時,她都推他,同時又不撒手的要他”。但人畢竟是有意識,有情感的動物,當小點兒選擇離開這個骯臟的環境去神圣的女子牧馬班生活,來躲開情欲的糾纏時,本能的欲望卻使她無法無視身體的貪念。即使逃離到荒涼的草原上,她還是不斷與姑父相遇,繼續掙扎在矛盾當中,直到姑姑在兩人合謀般的目光中死去,倫常與情欲的持續戰斗才得以停歇,這罪惡般的情感才得以結束。
二.出國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嚴歌苓的《少女小漁》、《天浴》、《第九個寡婦》、《金陵十三釵》、《一個女人的史詩》等多部出國后作品被相繼成功搬到熒幕,從而使一位旅美作家走進人們的心中,得到海內外文學界的空前關注和熱議,獲得各種文學獎項。她筆下的女性形象也在這些作品中大放光彩、豐富多姿,但書中的這些女性地位基本大多處于社會的最底端,如蒙昧無知但卻單純善良的村婦王葡萄,日本戰后遺孤多鶴,知識青年下鄉的文秀,遠赴海外被迫成為妓女的扶桑,秦淮河花魁趙玉墨,在父輩成分問題影響下參軍的小穗子等。
(一)率性的情欲
王葡萄是嚴歌苓筆下女性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她是一個單純善良的人,但在守寡后并沒有安分守己,因抵不過肉體的渴望,一次次和琴師、孫少勇、史家兄弟等幾人嘗歡,幾乎每一次歡愛都是在王葡萄的主動下開始的,并從中得到了極大的樂趣,她沒有感到一絲的羞恥,也沒有感到一分的丟人,反而更多的是對情欲的歡快。這種索求同樣出現在其他女性身上,她們的第一次都是在半推半就中開始的,并且從此一發不可收。蘇菲被歐陽萸吸引后,巧巧在眼鏡男的誘導下,甚至孫麗坤在發現徐群山的女兒身后,都沒有任何對貞操即將失去的羞恥和恐懼之感,而是享受這種情欲偷歡帶給她們的樂趣,并且主動地配合著他們。情欲必然存在,但是如此赤裸地表達而不是隱藏,讓這些在許多方面遭遇性別歧視和壓制的女性顯得格外真實和動人。這也讓我想起了《白鹿原》中那些同樣渴望情欲卻要么放蕩要么壓抑最后都成為悲劇的女人,不同于這些女人,嚴歌苓筆下的女性并不是用身體來取悅男人或者擔負生育機器的職責,而是真心享受情欲帶來的快活,并且對激情過后可能帶來的災難毫無顧慮,對一切因此到來的災難坦然接受。
(二)無奈的生存
《扶桑》是嚴歌苓出國后發表的代表作之一,扶桑的形象正是作者對于所有和她一樣的外來人命運不幸的同情和無奈,但又比作者本人多了一份麻木,她用精湛的語言描寫出了一個讓人感到痛心的扶桑形象。當扶桑被二三十個男人拖進馬車的簾帳后面的時候,她沒有喊救命,也沒有罵他們畜生,而是安靜地對著虛無一次次張開身體,同時用牙狠狠咬下一顆顆紐扣。當她把所有紐扣帶回自己的房間,放進一只空粉盒,關上盒蓋,晃了晃,聽它們沙沙的撞擊聲時,她是多么平靜。不能說她的眼神中沒有恨,但是連她自己都感受不到自己的怨怒和仇恨。她沒有絕望,甚至沒有屈辱之感。或許是她在夾縫中遭受了太多的苦難,而多年的妓女生涯也讓她喪失了僅有的一點自尊和羞恥心。在無數個正常人選擇死而放棄生的時候,她有她的執著和不放棄的精神,在這艱苦的環境下努力的生存了下來。扶桑驚人的遭遇或許成就了她強悍的免疫力,但是嚴歌苓筆下其他經歷相對簡單的女性,依然存有這種讓人費解的力量。還有在異國夾縫中生存的小漁,為了與男朋友江偉可以長期居住在美國,不僅無私地犧牲自己和糟老頭假結婚,而且用她的善良感化了老頭,她面對恥辱和苦難始終保持著東方女子那種特有的母性——善良、質樸、無私。而這些女性對恥辱和生存的免疫都是為了能夠在夾縫中生存下去,也表達了作者對她們的同情以及對一切不公正因素的控訴。
三.地域和時代背景
隨著嚴歌苓遠赴海外,她的寫作角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盡管還是千篇一律的抒寫女性形象,但這時的女性形象特質卻發生了質的變化,不再是一些不完美和殘缺的女性,更多的是一些人物形象鮮明,性格豐滿的女性,如王葡萄、小漁、扶桑等。即使王葡萄和小點兒所處的時代背景是一樣的,但人物的性格卻是大不相像,比起小點兒作為女性時的扭曲人格,葡萄的性格雖然潑辣、頑固,但更多了些柔情和人情味。再比如出國前作品中的小點兒和出國后作品中的小漁,她倆是在不同時代背景和不同地域背景下,作者創造出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在艱苦的國內背景下,作者創造出來的逐漸喪失女性身份的這些女性是對制度和社會的譴責和批判,使女性身份得到重視的呼吁。而出國后,作者所面對的是一個擁有著多元的文化背景的國家,人文關懷意識強烈,女性身份不像國內一樣卑微,作者的責任從提倡重視女性地位轉而到對東方女性魅力的弘揚,是為了讓這些在邊緣中生存的女性向中心靠攏所作的努力,也使東方文化更好的在西方世界得以傳播,和西方文化相互取長補短達到融合相處。總之,這種由眼界的開闊和西方人文關懷意識帶給作者心靈的慰問下的成熟戰果,便是由社會意識、地域變化和作者心境開放下造成的女性形象特質的改變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