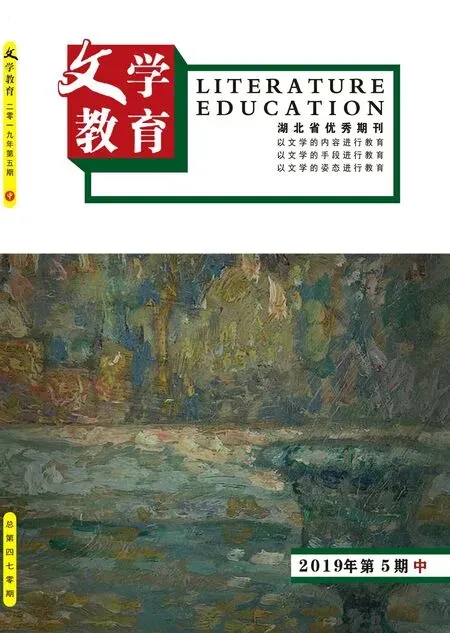從《周易·大過卦》看過與惡的關系
吳易恒 龔曉康
關于《周易》的內涵,孔圣下過結論:“潔靜精微,《易》教也”,由此見《周易》之深。從善惡問題來看,《說文》將惡解釋為過。從大過卦看,過又有多個層次。由于古今對惡的定義繁多,各家不一,故需界定惡的范圍,再進行進一步分析與比較。
一.對惡的界定
惡之界定基于先秦儒家之惡。荀子認為:“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嘩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荀子認為惡即是用偏激、兇險的行為造成混亂,包括違反了社會的規定的行為。而惡的來源上荀子認為是對欲望的追逐,荀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如不節制則造成危害。但“好利”又是人之先天的本能,由此荀子認定了惡的定義并要改變人之自然本性。
在《論語·堯曰》中有“四惡”的概念:子張問如何是四惡?孔子進行了回答:一“不教而殺謂之虐”即缺乏仁義之心;二“不戒視成謂之暴”則是魯莽、急功近利;三“慢令致期謂之賊”即是輕慢、高傲;四“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則是貪欲、私欲。
總結下來,惡分三個層次:本能之惡,即人的欲望、私欲,也就是貪和欲,是出于自然的本能,先天具有的。放縱之惡,是對這種本能的欲望的向往,不加以節制、引導則會無限增長,即是放縱。行為之惡,從思想上的逐欲延展至行為上的逐欲并造成危害。
二.大過卦中過的含義
《說文》:“惡者,過也”。但過在大過卦中有多層含義,故對《大過卦》進行分析。
2.1 陰陽之過
對照今本周易與《馬王堆帛書周易》如下:
今本: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初六:藉用白茅,無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九三:棟撓,兇。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
上六:過涉滅頂,兇。無咎。
帛書本:
初六:籍用白茅,無咎。
九二:楛楊生荑,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九三:棟撓,兇。
六五:楛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
尚九:過涉滅釘,兇。無咎。
對比可見,今本周易為大過卦,帛書本為泰過卦,《說文》:“天大,地大,人亦大。凡大之屬皆從大”,泰字古字形為夳,顯然泰字從大,是大的延伸意。段玉裁:“后世凡言大而以為形容未盡則作太。”他認為泰和太相同,都是對大的形容,因此泰和大都是對此卦所指之物限度的形容。大過卦四陽二陰,陽爻貫穿中間,陰爻退居首尾,中間四陽過盛,故泰和大即是指陽勝于陰。棟為梁柱,指代陽之義;撓是彎曲,指代過多之義,棟撓就是指陽之發用過于強盛,打破了陰陽平衡,故有陰陽之過的含義。
大過卦中還描述了陰陽之過的具體表現: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
今本是稊,帛書本是荑,荑就是荑草,即初生嫩芽,代表陰陽調和。即指雖有年長或剛強之人,能以陰柔方式來調和,便會和諧。但孔子《象》中說:“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二者相處過程中有難度,老夫屬陽,為強陽;女子屬陰,為弱陰。陽過盛,弱陰無法完全調節,必有陰陽不調。故《象》言:“棟橈之兇,不可以有輔也”。
九五則是枯楊生華,即老樹開新花。九二為嫩芽,代表生機,九三為華,花開終消亡,故不長久。九五即為老婦少夫雖相互調節,然而華而不實。孔圣《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丑也。”正因為這種陰陽協調之間的不平衡,使得象征陽屬性的這根梁柱不斷傾斜,陽屬性的不斷過度,最后發展到上六已是河流滅頂之災的卦象。故大過卦中的過包含陰陽之過的含義。
2.2 準則之過
準則是限定事物的一種標準。事情超過原有的標準,必造成危害。大過卦開始即是梁彎房殞,即說明行為不可超過的準則。但又利有所往,這由于九二和九五的中間都是陽爻,貫通無阻,故亨通。但《彖辭》提醒:“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即說大者太過,陽剛過盛,因此開頭與末端皆弱,只有位置適當才是亨通。另外即使達到了上六的兇險之境,也要守住內心的準則,所以《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在險惡中實現君子人格,做到不懼、無悶。
在初六時同樣要遵守準則。初六:“籍用白茅,無咎”。籍有兩意,一馬融認為:“在下曰藉”,指籍是居于下位的,侯果:“以柔處下,履非其正,咎也”;二《說文》:“藉,祭藉也。”即是將籍作為祭祀時鋪在地下的草墊,用這樣的方式作為對祭祀對象的尊敬。因此這里籍一指初六之低,居于下層,爻位不正,二指小心謹慎,與祭祀時的禮教規范相符,即內心敬重與行動和禮。因此在陰陽不得位時,須如祭祀時一樣,向內謹慎恭敬,向外合于規范則無災。因此過包含準則之過的含義。
2.3 極限之過
《說文》認為頂即到達巔峰、極限。大過卦中極限有兩個方向:一即將越過,二已經越過,即九三和上六。九三與九四相似,九三主梁隆起,九四棟梁彎曲。棟梁無陰爻輔助,太過剛強則彎曲,并到達極限而垮掉。九三另一解釋為陰爻在首尾,則陰陽不能調節,故終將達其極限而衰落。九四說主梁向上隆起,這是由于九四與初六陰爻相對應,初六小心謹慎、符合標準的行為能調和剛強之災害。
上六為已經超過了極限。上六:“過涉滅頂,兇。無咎。”河流過頂,超過的事物所能承受的極限。程顥認為上六之災是由于過于剛強以及小人之禍,越過了能接受范圍的極限。過涉有三意:一是如程顥所說是由于行為做事過于剛強,水代表小人,有小人之災。二過是對水的形容,指環境達到了生死的極限,由于大過卦是說澤滅木,毀壞了樹木的生長。三是認為上六處于頂峰,上卦是兌卦,所以指水,九二至九五剛強不止,缺乏謹慎、過于自負,急于過河,必被淹沒。依三種解釋都可以看出這里有超過了極限的意思。
三.過與惡的比較
以上總結出過的三個含義,即陰陽、準則和極限,通過這三層含義來與之前界定的惡進行比較。
3.1 陰陽一體與得失有別
將陰陽之過與本能之惡進行比較。陰陽具有指代性,都是一個屬性或一類事物的概括,也是上下概念的延伸。上下概念才是統攝陽與陰、天與地、生與死、得與失等概念的,上和下概念之間正如陰、陽需要調和,相互協調。人的求欲之本性可作為對陰陽某一邊的追求,所以荀子認為的人的自然本性正是出于對得和失的分別,即欲得而患失。但從大過卦來看,惡的過程和結果都是由于上下之間即陰陽之間的不平衡,《易》有“生生”,便是對陰陽調和、生死相續,上下和諧一體的追求。因此過與惡的區別就在于過是基于陰陽一體、生死一體的陰陽不調;惡則是對上下概念經過分別后的患得患失。從過和惡所呈現的表面現象來看,過打破了陰陽的平衡;惡打破了社會的平衡。因此過需被調和,故九二、九五能生芽與花;惡需被改造,故荀子言圣人作偽善以教化之。
3.2 目的不確與善惡一致
將準則之過與放縱之惡進行比較。兩者在發動處有一定差異,惡的過程和目的都是為追求欲望。準則之過則是由于陰陽不調、剛強居中而越過了一定的準則,其目的可能屬惡,亦可能屬善,目的性不明確。過與惡的相通點就在于都越過準則并且造成危害,兩者的相反方向都是君子,也就是面對不同的境遇都會堅守準則。所以過與惡在善惡觀上是一致的,符合、維持準則即為善;越過準則,造成危害即為惡。因此,準則之過的出發點、目的并不明確;而在善惡觀上,過于惡是一致的。
3.3 殺身成仁與尚有余地
將極限之過與行為之惡進行比較,惡是逐欲與放縱的行為,并造成危害,也正如“四惡”所提到的這四種行為,其還是超過了一定的標準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關鍵還是屬于越過一定的范圍。過與之對比結果則更加極限,過是以及達到了極限或即將達到了極限的行為。惡所造成的后果、過錯還可以改正,即使是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還是可以修復。但過有可能發展到了最頂端的位置或者接近頂端的位置,最終不得不在物質上以殺身成仁或在精神上必須獨立不改。因此從這里比較,過比惡更加兇險,惡的程度是可有大小的界定,而過則越過了極限,并且惡是可以改正或緩解的,而過發展到頂點,這是無法改正的。也就是說過的結果上更絕對一些。
四.結論
經過對比可發現,過與惡的關系即是惡歸于過之中。原因有三,一在于大過卦中提倡的是陰陽一體的,而惡已經又進行了進一步的分別。二過的目的、指向是不明確的,這種不明確反而是沒有經過分別、理解之前的對事態變化的直觀反映,與后天設定的惡形成了一種對比。惡的行為源頭是逐欲和縱欲,目的性強,而過的源頭,是由于陰陽不調,目的性不明確。三在結果上,過的結果也比惡更寬大。過的已經呈現出超過極限之后所發現的現象,而惡并沒有討論到惡發生至極限頂峰的時候,因此惡與過相比,惡的內容更狹窄,是對過各個方面的縮小,而過的范圍更大,其中所蘊含的內容更廣。因此得出二者的關系;惡是過的下位概念,過是惡的上位概念,過中包含了惡,惡歸于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