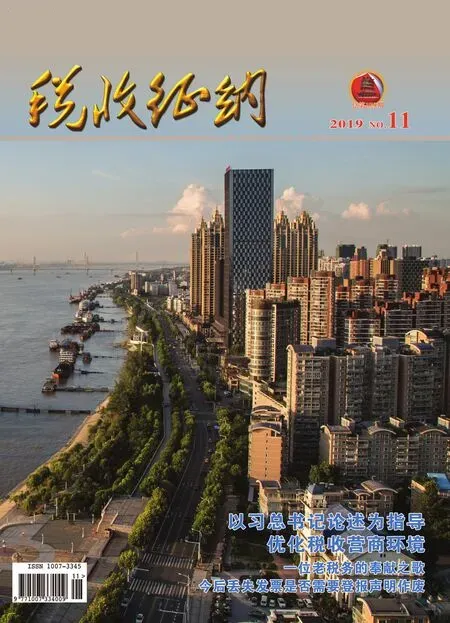曹操的屯田與租賦
彭安才
曹操是國人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三國演義》首篇就以汝南術士許劭之言,稱其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從此戲臺上曹操的扮相總是白臉,其實,真實的曹操既有“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遠見;也有運籌帷幄出奇制勝的軍事智慧;還有興屯田修耕植,治理租賦的經濟策略,正是這些成就了他的傳奇人生。
固本培源興屯田修耕植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曾經被朝廷行文通緝的曹操逃回家鄉(xiāng)陳留,散家財,舉義兵,聚眾五千余人。在出兵征討青州黃巾軍時,設奇謀制勝得降卒30萬人,難民男女百萬人。從此,青、兗二州為其根據地,派部下棗袛組織難民及淘汰下的士卒墾荒造地種莊稼,養(yǎng)蠶植麻織綿布,試行屯田經營,以解決軍隊吃穿問題。他及時采納了謀士治中從事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三國志卷一》的建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從洛陽迎接漢獻帝及百官遷都許縣(許昌)。漢獻帝冊封曹操為大司空,武平侯,負責管理朝政,取得了政治上的優(yōu)勢。
據《三國志卷一》記載,身為丞相的曹操決心蕩平群雄,結束戰(zhàn)亂,讓百姓安居樂業(yè)。他效法秦人重視農耕以及孝武屯田西域的經驗,聽取并采納了羽林監(jiān)棗袛的“科取官牛,為官田計”的“分田之術”。任命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棗袛為屯田都尉,全面負責屯田及租賦管理。頒布《置屯田令》“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同時號令各地州縣設置田官,專職司農積谷,負責征收租賦及倉儲管理。以難民集中屯田為民屯,稱“典農部民”或“屯田客”;軍隊墾荒種地為軍屯,稱“士家”,即“秋冬習戰(zhàn)陣,春夏修田桑”。
由于任峻統領各地屯田有方,“所在積谷倉廩皆滿,……軍國之饒”。《魏書,任峻傳》所載,連年戰(zhàn)亂和災荒,老百姓流離失所,死亡無數。就連散布在各地的軍閥及黃巾殘部也因饑荒無糧而“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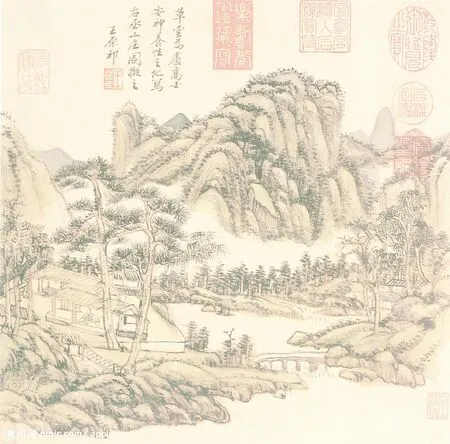
曹操及時興屯田修耕植,極大地解決了軍隊的糧草供應問題,軍心穩(wěn)定,戰(zhàn)力加強。按史書上講,曹操之所以能戰(zhàn)勝攻取,兼并群雄,曹氏功臣中棗袛,任峻當居首列。可見“一日無糧軍心散”之重要性,屯田耕植對保證軍事勝利有很大作用。
公平稅負整頓租賦秩序
曹操與袁紹的官渡之戰(zhàn),出奇制勝以少勝多。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徹底掃除袁氏殘余,統一了北方。漢獻帝封曹操領冀州牧,從此長江以北廣大地區(qū)皆曹操管轄。由于袁紹統治北方“重斂于民,民皆怨之”,加之多年戰(zhàn)亂,地荒人稀,人民極其貧困。為醫(yī)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給民休養(yǎng)生息,及時調整租賦政策。頒布免河北租賦的法令“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即免去河北地區(qū)一年的租賦。同時,對其他各地鄉(xiāng)村自耕農頒布《收田租令》,“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及逋藏匿罪人,為捕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fā)。郡國守相明檢查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曹操頒布的征收租賦的法令,明確指出了租賦不公平,就會引起社會的不安定。實行公平租賦就要重法打擊豪強兼并田地,禁止豪強或富戶將自己應納的租賦強加給下民代交。審配是袁紹的重臣,其宗族也屬于懲治之類。法令同時規(guī)定租賦按每戶田地的畝數定額征收;按戶定額征收絹、綿。規(guī)定了地方官吏的檢查責任。這樣的征收租賦政策,相對于袁紹的“重斂于民”則是輕多了。
曹操力矯漢末的弊政,推行打擊豪強,奪回他們強占的大量土地,以“分田之求”給弱民以田地。恢復了農業(yè)生產,緩和了階級矛盾。同時,為了確保租賦收入,由官府組織自耕農民及屯田生產者,興修水利灌溉工程。在關中,河北修建成國渠;疏導高梁河,修建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地萬有余頃。”這些水利建設工程,實現了旱澇保豐收,變水害為水利。對發(fā)展農業(yè)生產,保障租賦收入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