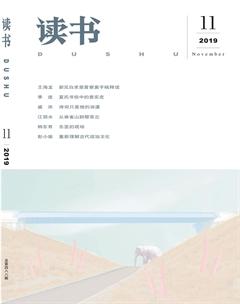詩詞只是他的消遣
盛洪
北宋熙寧四年(一0七二)元月,趙宋皇室為在皇宮歡度元宵節,準備購買花燈四千多盞。因數量較多,市場供貨有限,遂又下令,禁止商家賣給他人,并要求減價收購。蘇軾聽到后“驚愕不信,咨嗟累日”,最后決定上書皇帝,勸他收回成命。
這份上書被稱為《諫買浙燈狀》。在其中,蘇軾說道,知道陛下一心要效法堯舜,“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更何況這只是為了取悅后宮。雖是為了盡孝,“然大孝在乎養志”。而賣燈的小家小戶,本小利薄,“衣食之計,望此旬日”。他們指望在元宵節前將花燈賣出,掙回薄利,為一年的生計墊底。“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如果減價的原因是認為花燈并無太大用處,那又何必買呢?如“惡其厚費,則如勿買”。所以,“臣愿追還前命”。
讓皇帝收回成命,這種要求是否太過分了呢?當然比較難。但蘇軾在奏議中給出了一些榜樣。如唐太宗曾遣使向涼州都督李大亮索要他的名鷹,但遭到拒絕。唐太宗卻很贊許,“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唐明皇遣使到江南購買水鳥,遭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對,就召回使者;后又詔令益州制造一些奢侈品,宰相蘇許公竟不奉詔。還有就是李德裕,他是唐朝重要政治家,最后官至宰相。他在浙西任職時,有一次皇帝下詔要當地打造銀具二十件,紡織綾緞兩千匹,他上書極力勸阻,皇帝只好作罷。蘇軾接著說,如果內有如此臺諫數人,外有如此地方大員數人,則買燈這件事,或“必須力言”,或“必不奉詔”。為什么?因為有如此陛下“聰明睿圣,追跡堯舜,而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如果再不向皇上提意見,那就是瞧不起他,不把他當明君,“臣罪大矣”。
能從字里行問感受到,除了該說的恭敬話,蘇軾此文極為嚴厲。即使是恭敬話也不是白給的,必須要有值得恭敬的品德相配,那就是“從諫如流”。那么這篇奏議的效果如何呢?查了一下《宋史》,似無記載。大概此為小事,且并未發生,所以不記。不過,從蘇軾后來的奏章來看,宋神宗接受了這個批評。后面這個奏議現在稱作《上神宗皇帝書》。在一開始,蘇軾就講,他一直等了十幾天,卻沒有反應。于是“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顯然,宋神宗接受了他的意見。不過蘇軾確實認為,這只是件小事。只不過這件小事將要引出一件大事,這就是他的這篇《上神宗皇帝書》。
皇帝既然改錯,就該表揚,“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又來了一番恭維,然后話鋒一轉,“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有這么一個從善如流的皇帝,我怎么能辜負你呢?如此一來,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向你提意見了。這也符合蘇軾本人的原則,也是他父親蘇洵提出的原則,即最好的諫議是能夠被接受的諫議。這還要看對象如何。“蓋未信而諫,圣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原來《諫買浙燈狀》只是一個火力偵察。既然神宗接受了取消買燈的建議,就說明他是可諫之人,鼓勵提意見。“許而不言,臣則有罪。”于是就可以提出更重要、更大規模的諫議:“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買燈者矣。”后面才是重點。
第一件事說的是,宋朝立國百余年,負責財政稅收工作主要由三司負責,一直由三司使、副使和判官等人完成,并無大的問題。但現在突然在三司上又設置了一個“制置三司條例司”,增加內務官員六七個,外出使者四十余人。斂財的龐然大物,不僅增添不少耗費,更是向世人宣示要大斂其財。這給了那些“小人”以口實,“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貴”。即使辯白也無用,因為設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就是鐵證。如果否認,就像趕著鷹犬到森林,卻說不是去打獵,拿著漁網到江湖,卻說不是去捕魚一樣。要想消除這些對皇室斂財的誹謗,“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只有取消這個疊床架屋的機構,才能平悠悠眾人之口。
接著蘇軾更從立法程序角度否定此事。他說:“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后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也就是說,如果不遵行立法的正當程序,就是一個惡法。所謂“中書”,是指三省六部中的中書省,是專門替皇帝擬詔的地方。雖是奉旨擬詔,卻可以提出意見并駁回,這被稱為“封駁”。即使通過了中書省,還有一個“門下省”,如果有問題也可駁回。唐朝時,皇帝擬的詔書抬頭,就是“門下”,就是直接讓門下省審察之意。在宋代,中書和門下已合為一省。過了門下關,詔書還要由宰相附署,如果宰相有意見,也過不了這一關。這種制度一直到明朝都有保留。如頑劣的正德皇帝想下旨以“平定寧王叛亂”為名到南方游玩,怕內閣不附署,就以“威武大將軍”的名義發。因而,蘇軾這里所說“中書”,應是指這一整套政府決策的制衡機制。
強勢的皇帝有時能夠繞過這種“中書”體系,如武則天時期的“斜封官”。這反過來也說明,中書省的人也有意區別。走正當程序的,則用中書省黃紙朱筆正封任命敕令;而走側門的,則以墨筆斜封敕令示之。在明朝,這種“斜封官”叫“傳奉官”,即不經吏部考察,皇帝私相授受的官員。這些斜封官或傳奉官經常位子不穩。武則天死后,數千斜封官被罷免。明朝也如此。如明憲宗時罷免了五百傳奉官;明孝宗罷黜了三千余傳奉官;世宗時,又盡斥前朝傳奉官三百多人(張薇:《明代的監控體制——監察與諫議制度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137頁)。蘇軾在這里所斥責的事情,大概是王安石與神宗私下決定的,因怕群臣反對,所以不走中書正當程序。
如果走中書的正當程序,將會如何?蘇軾說“無乃冗長而無名”,即走程序的時間會很長,最后可能無疾而終。但這是一件好事,“智者所圖,貴于無跡”。比中書正當程序更廣義的立法程序,還可從《尚書》中看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決策之前還應聽取官員和民眾的意見,如果大多數人贊成,則此決策應是好的決策。“如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兇。”此事已進行了一年多,也可以從眾人的態度來判斷。連宰相都不愿做這種斂財之事,外邊的議論更多,應知這個決策存在著嚴重問題。實際上,派出官吏到地方斂財干預,本來就不是正路。蘇軾回顧了漢代、南朝劉宋及唐代時皇帝派員到地方的劣跡,說他們“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追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
第二件事,是有關官府雇用民夫。唐代稅制,已由租庸調改為兩稅法,實際上是將其中租調合并,與庸并稱“兩稅”,并以唐大歷十四年(七八0)應稅數額為基數。其中本已包含雇用民夫的費用。宋代繼承其制。但現在又將雇用民夫單列,要求增加庸錢。蘇軾說:“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朝廷不應再法外加稅。更重要的是,從制度角度看,這是一個惡劣的先例,“萬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謊”。這是一種思考制度的長遠眼光,“圣人之立法,必慮后世”。看到一個端倪,就會聯想到以后可能出現的最壞情形,將其從根上制止。這與現代制度經濟學的看法頗為一致。布坎南說,制度安排要考慮最壞的情形。因為如果制度不能防備最壞的人,好人就會受到打擊,整個制度也就會瓦解。
第三件事情,就是青苗法。這在當時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青苗法,表面上看一則是為了在青黃不接之際接濟貧苦百姓,二則是為朝廷籌資,目的是為北伐西征籌措軍餉。蘇軾指出,這種制度一旦實行,有幾方面的弊端。首先是,這種制度要求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借貸經營,這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性質,使其具有營利性。因而青苗法不僅成為政府官員的硬性任務,而且也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就可以借用政府的強制性手段將貸款分配給民眾,雖然朝廷“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即使是老百姓自愿請借,也一般是窮困人家,如果出現荒年,就面臨還不起錢的窘境,被迫逃亡;與他們連坐的富裕鄰居就要受到牽連。雖然借貸利息名義上低于民問的高利貸,但由于官府的強制性,沒有通融延期的靈活性,借貸條件實際上更差。
青苗法的第二個弊端,就是與常平法爭資源。宋時各地都有常平倉,即政府糧庫。其功能是:“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也就是說,常平法是以少量儲備糧食通過影響糧食市價來解決荒年糧貴的問題,是一種政府有節制且有效的介入市場的方法。而青苗法的資金是建立在出售常平倉儲糧基礎上,再用所得資金借貸百姓的。如此一來,常平倉就沒有了平抑糧價的糧食資源,常平法的功能就被廢止了。“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誰救其饑?”沒有常平倉糧食平抑糧價,一千戶以外的人家誰來救濟?因而,“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
類似的,就是實行均輸法排擠了民問商業,問接地也減少了政府收入。均輸法本要“徙貴就賤,用近易遠”,朝廷原來的發運司就增加了商業功能。如此一來,“豪商大賈,皆疑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而蘇軾深知“商賈之事,曲折難行”,要先期付款買入商品,再等賣出才能收回資金,才能獲得利潤。而官府買賣,先要設置相關官吏,建立機構,成本已高,而由于壟斷或官錢不計費,賣價可低,“則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此法雖然可能有些許所得,但“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均輸法所獲利益,會被商稅的損失所沖抵。蘇軾做了一個比喻:“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看到這里,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蘇軾這番議論是在王安石新法時的“現在進行時”批評。這不僅有巨大的政治風險,而且新法的全部問題還沒有充分展現。然而從后世對這段歷史的評價來看,這也許是對新法最早的系統性批評,并且內容大體正確,為后世所接受。如汪圣鐸在其所著《兩宋財政史》中說:“推行新法的結果,非但沒有減輕農民負擔和疾苦,反而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和疾苦,故而往往危害了生產的發展。”如青苗法就使“官吏從中作弊勒索勢不可免”,“故而一般說,青苗錢‘蓋名則二分之息,而實有八分之息”(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版,62頁)。關于均輸法,汪圣鐸干脆大段引用蘇軾《上神宗皇帝書》相關段落,并說“均輸法行后不久就無聲無息了”,與均輸法類似的市易法則“所收不補所費”,實則財務性虧損。
所以總體而言,王安石新法并未達成它的目標,即增加國家賦稅收入。據汪圣鐸的《兩宋財政史》,表面上看,青苗法每年增收約二百萬貫,免役法增收三百萬至四百萬貫,市易法增收約一百萬貫。但正如蘇軾所預見的那樣,這是以損害其他收入為代價的“成果”,就如同把牛賣了換來的羊。實行新法以后的熙寧十年(一0七七),宋朝廷的田賦收入僅為天禧五年(一0二一)的81%,減少了約一千二百五十二萬貫石匹兩束;其中糧食收入為一千七百八十九萬石,僅為天禧五年的55%(汪圣鐸:《兩宋財政史》,49-52頁)。熙寧十年的商稅收入為八百零五萬貫,僅為慶歷年(一0四一至一0四八)的41%;榷酒收入一千二百九十七萬貫,僅為慶歷年中的76%。新法所增收入不敵商稅和榷酒收入的損失,更遑論主要稅種田賦的損失。一頭牛都沒有換來五只羊。北宋經濟經王安石這樣一折騰,變得貧弱,也為北宋的滅亡埋下了種子。
到這里,我們回想起蘇軾所說“壞商稅而取均輸之利”,則會驚嘆他的超凡的判斷力。其實,這沒什么了不起,只是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及“不與民爭利”的一貫傳統。不過在蘇軾這里并不是死記硬背經典所得,而是內化于心的精神。他對政府介入民間經濟有著本能的警惕,對商人群體的經濟權利高度尊重,對平民百姓哀怨的深切同情,使他能夠敏銳地看到問題,并用他那個能作出傳誦千古的詩詞的頭腦,冷靜地分析問題,并找到癥結。盡管人們印象中蘇軾是一個絕頂聰明、恃才傲物之人,但他對政府所需人才卻是另一種要求。他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說,官員宜清靜淡泊,忠厚老成。這樣可以為政寬簡,與民休息,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則。他用此原則要求自己,也用這一原則衡量別人。王安石等新黨人物的作為,自然在否定之列。
如果從政府的功能定位來看,蘇軾所提官員之標準,卻是極為確當。因為政府只應做守夜人,保證民眾的基本的公共物品,即安全、秩序與公正,而無須過于有為。蘇軾說:“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腐,老成起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精明強干者雖然能迅速有效地完成政府工作,卻可能傷害了社會。他贊揚曹參謹慎而不干預司法和市場;贊許謝安,他被譏“清談廢事”,笑著回答說:“秦用法吏,二世而亡。”蘇軾說,只看到“吏多因循,事不振舉”,就要苛察以矯正,“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當我們想到蘇軾在任杭州知府時也曾修建西湖蘇堤,就知道他所說的,并非不做有利于鄉里的公共工程,而是反對以政府的名義侵入社會邊界,做本來應該由市場和家庭做的事情。
蘇軾反對苛察官員也似乎獨樹一幟。理由是:“大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貪垢,至察無徒。”人無完人,如果政治領導人過于計較別人的缺點,就沒有追隨者了。如果“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茍免”,這就不是朝廷的福氣,也不是皇上的愿望了。而不計較于小節,“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只是用人要強調“歷試”,“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以賈誼為例。有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是感嘆漢文帝不用賈誼。但在蘇軾看來,他才氣過人,然早年說要把匈奴變成漢的屬國,有點少年輕狂,漢文帝讓賈誼輔佐長沙王,是有意歷練他。“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心自悔其說,旋之晚歲,其術必精。”他的早夭實屬意外。
治國中比用人更重要的,就是基本價值觀。蘇軾說:“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在這里所謂“道德”與“風俗”,就是最基本的精神價值,以及由此價值奠基的社會秩序與經濟政治制度。貧與富,強與弱,只是一個社會的物質外表。如果只追求表面的財富而損害基本精神價值,實際上就損害了一個國家的根本。而表現為“強”的武功,也許會帶來災難。蘇軾舉了一些例子,包括隋文帝統一天下,武功了得,但房玄齡很早就看出隋朝不會長久;漢元帝建立了超越武帝、宣帝的武功之后,不久就出現了王莽篡漢。“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
風俗中之重者,就是諫議制度。蘇軾本人就擔任過中書合人,曾有封駁的經驗。蘇軾說:“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圣人過防之計。”與秦漢和五代對比,蘇軾高度肯定了宋代的諫議制度,說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宋朝廷就沒有問罪于任何提意見的人,有時會有輕微責罰,但很快又重用。“許以風聞,而無長官。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批評到天子或宰相,天子臉色凝重,宰相則可能辭職待罪。他知道“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而這是一種“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的制度安排。有這種制度化的批評機制在,朝廷的一些錯誤,出現一些奸臣、權臣,可以用言辭抑制;否則“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朝廷紀綱,孰大于此?”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制度嗎?
而如果對臺諫意見不予理睬,甚至壓制臺諫制度,則會破壞這一制度的功能,打擊天下提意見者。“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臺諫制度廢止,就可能執政為私,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如果執政為公,“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如果平常不讓別人說話,則臨危之時還能要求別人守死節嗎?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子同而不和。”蘇軾舉例說,周公、召公都是圣賢,“猶不相悅。著于經典,兩不相損”。另一個例子是講東晉王導,每次請賓客,“舉坐稱善”,但王述卻不高興,“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王導“亦斂衽謝之”。即使君子之間也有不同,為什么要求一種聲音呢?
到這里,我們看到了蘇軾這篇奏議最重要的內容,那就是要保持一種制度,堅持一種原則。這個制度就是臺諫制度,這個原則就是要有不同聲音。這時,蘇軾已經不是在抽象地討論原則,而是現實地面對重壓。這就是來自王安石的破壞。與之相比,新法還只是一個政策之爭。王安石的更大錯誤是打擊御史,摧毀臺諫制度。他要將彈劾他的幾名御史投入監獄,只是在司馬光等人的強烈反對下,才改為流放。他罷黜呂公著等御史領袖,而將未中科舉的諂媚之人李定扶為全權御史,并將反對此任命的三個御史免職。“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達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臺的人,三名是皇宮中的諫官。”(林語堂:《蘇東坡傳》,百花文藝出版社二000年版,114頁)可想而知,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所集中批評的,正是王安石對諫議制度及這個制度之基礎的毀棄。
然而,“蘇東坡上書之后,如石沉大海”(林語堂,120頁)。三個月之后,蘇軾不能再忍,又上一書,現稱為《再上皇帝書》。蘇軾的言辭似乎更為直率和犀利,目的就是督促皇帝改弦更張,廢止新法。他引孔子的話:“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告訴皇帝,改過更讓人敬佩。近來有更多的議論傳了過來,更坐實了新法的問題。但滿朝文武畏不敢言,蘇軾自己的上書又“不足以感動圣明”。退休的宰相大臣、地方長官都說不便,而朝中原來支持新法的諫官也開始批評。在這時神宗下詔,只是嚴禁強制分配青苗貸款,并非廢除新法。他很失望,比喻為小偷想改過,但又不想全改,宣稱以后一個月只偷一只雞。他又批評神宗想將新法再在西北三路試行,比喻為醫生明知是毒藥,還要以人的生命試驗。“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
進而,蘇軾引《尚書》,“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治道就是天道;而“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就有亡的危險。古今朝廷存亡,依賴于四種人,即民、軍、吏和士。得罪其一,就有亡國危險。而實行新法,“一舉而兼犯之”。“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于此者乎?”皇帝之所以沒有覺察,是因為內外有諂諛之人,蒙蔽圣聽。蘇軾在上一奏章中說過,他在陜西察訪時,看到“愁怨之民,哭聲振野”,但“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為樂”。這樣的事“自古如此”。不然,秦二世為什么不知道山東的反叛呢?這次他又警告皇帝:“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
蘇軾連發三箭,效果如何?從大的歷史看,王安石最終下臺,新法廢止,應與蘇軾的努力不無關系;但又不是他一個人的努力,還有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韓琦、富弼等重量級人物,還有他的弟弟蘇轍等。應該說,這是在宋朝的制度結構下,在諫官文化傳統的大背景下的綜合結果。具體看,制置三司條例司在成立的第二年,就被取消,其職能并人中書省;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都在元豐末、元祜初(一0八五至一0八六)被罷止。所以北宋暫時避免一亡。但由于從熙寧二年(一0六九)開始到元祐初年(一0八六),新法畢竟已經實行了十七年,對北宋社會造成了深重的損害。舊黨上臺后,還要面對新法帶來的經濟衰落的后果,同時面對契丹和西夏的壓力,在去除新法的斂財手段后,一時無力籌措御邊的資金,造成新黨及其新法復辟。
關于蘇軾心心念念重中之重的臺諫制度,他不僅用言辭來捍衛,而且付出切身的代價。當蘇軾在奏章中說“白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時,他可能沒有料到的是,他竟是第一個例外。這就是他所遭遇的烏臺詩案。蘇軾一貫公開反對新法,新黨之人一直在找機會整他。有一次神宗對司馬光說“似乎蘇軾人品欠佳”,司馬光回答說,這大概是王安石煽動的誣告吧(林語堂,121頁)。這次則是被王安石扶上臺的御史中丞李定所陷害。所以蘇軾極為諷刺地被自己維護的臺諫機構所傷害,并且罪名也是有宋以來很罕見的,用搜集來的詩文斷章取義,以定誹謗朝廷之罪。幸虧在底線上,神宗站穩了腳跟,他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蘇軾逃過一劫,但臺諫制度受到重創。雖然王安石罷相,新黨下臺,但這種打壓批評,在臺諫部門安插親信用于黨爭的做法卻被沿襲下來。到了后來蔡京專權時,對不同意見的打壓到了瘋狂的程度,竟編制“元祜黨人籍”,對黨人一律“永不錄用”,并禍及子孫,不讓他們參加科考和留在京師。宋徽宗用他獨特的瘦金體親筆書寫了“元祜黨籍碑”。由于忌憚蘇軾、秦觀、黃庭堅等人的文名,還焚毀了他們的文集,甚至砸毀刻有蘇軾詩文的石碑。從崇寧元年(一一0二)到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共十二年的時間,不僅重行新法,使國力進一步衰弱,而且嚴重破壞了臺諫制度所應起到的政治平衡和制約作用。僅僅又過了十六年,北宋亡于靖康之變,徽、欽二宗成了金人的俘虜。
在傳統中國,也有人以蘇軾在政治上多有挫折,而貶抑他的政治成就,然而蘇軾卻把這些挫折看成他的政治貢獻的結果。他在晚年《題金山自畫像》中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黃州、惠州、儋州是他的三個流放地,他卻視作功業之所在,不正是一種“求仁得仁”的心態嗎?在他自己看來,他并非徽宗欽定的元祜黨人,他堅守的原則是超越黨派的。他在司馬光等舊黨人物掌權以后,又反對盡罷新法,提出不應是新黨提出的政策就要廢止。他以他的行為表明,他只服從天道,而不是黨派的政治利益。正是因為蘇軾勢孤力單,王安石通過破壞臺諫制度而用于黨爭,舊黨也用同樣的辦法報復新黨,北宋王朝才在黨爭中滅亡;也正是蘇軾以其一己之力堅守的“臺諫風旨”,因其正確性而生存下來,為宋的復興奠定了精神基礎,成為南宋初年的顯學,延續了宋朝一百多年的生存。而又以宋朝在中國歷史中的輝煌存在,而成為中國政治精神的寶貴遺產。
在今天,誰都知道蘇軾是一個天才詩人,但鮮有人知道他在政治制度和原則上的貢獻要更為重要。當我想找一本有關的書時,發現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仍是唯一的讀本。林語堂自述,他當年飛往美國時,帶了大量“有關蘇東坡的以及蘇東坡著的珍本古籍”。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蘇東坡傳》仍是那樣內容豐富和深刻。幸好,《蘇東坡全集》為我們提供了比當初林語堂先生占有的更全面的資料,讓我們在家中就能輕松一覽蘇軾一生的全部文獻,全景把握他的思想精神。蘇軾這個千古風流才子為中華文化貢獻的,不僅是激揚豪放的詩篇,而且是深刻凝重的政治思想,以及他為捍衛這種原則的身體力行,面對沉重打擊的淡定心力,超然于黨派的臺諫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