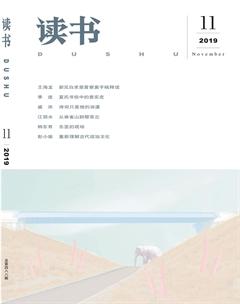休謨之死
徐志國
一七七六年夏天,休謨在愛丁堡他的新居永遠地離開了人世,他在愛丁堡的朋友們為失去這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友人而痛惜。亞當·斯密因需要照顧生病的母親而不能守在休謨身邊,但是他與休謨以及負責照顧休謨的醫生和家人保持著密切聯系。斯密除了關心這位即將失去的最親密的朋友之外,還承擔著協助休謨完成其自傳的使命。休謨的去世不只牽動著親人和朋友的神經,遍布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休謨的敵人也在此時屏住了呼吸,關注著這個享有盛名的宗教懷疑主義者會以一種怎樣的心境離開世界。
為什么休謨之死會引起人們如此密切的關注?這誠然是因為休謨在思想界的巨大影響力,正如對休謨持有偏見的托馬斯·杰弗遜感嘆休謨的《英國史》在北美殖民地的影響力:“這一本書(《英國史》)削弱英國憲政的自由原則的力量超過最偉大的軍隊。”不過,休謨之死受到關注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原因。作為一位著名的無神論者走向生命終點,休謨的表現本身就有著宗教哲學上的價值,因為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可以拿休謨的表現來證明各自的立場。休謨一生不喜歡爭論,對反對派的狂怒處之泰然,只是遵循經驗主義的原則表達他對世界的理解、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是以平靜、樂觀,甚至幽默的方式離世的,這在客觀上對他宗教觀點上的敵人一一宗教正統論者構成了沖擊。這種沖擊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他的敵人在失望之余變得有些氣急敗壞,對已故的休謨發動了更猛烈的詆毀。作為休謨最親密的朋友,斯密也因為負責向公眾介紹休謨去世的情況,經受了他一生中的最大責難。
要理解圍繞休謨之死所發生的各種故事需要我們從休謨的人生理想——做一個成功的“文人”(Man of letters)說起。我們常常稱休謨為一個哲學家,實際上自年輕時開始,休謨的夢想不是做一個學院派的哲學家,而是一個以學習和交流為志業的“文人”。在啟蒙時代,“文人”這詞包含著探索普遍知識(general learning)和進行思想交流的雙重含義。文人與學院派哲學家的主要差別在于,后者的興趣主要在于認識和闡明有關現實世界的“真理”,文人的欲求則更為廣泛,一個文人不僅希望探究世界的普遍知識,而且還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引領公共話語,獲得現實的影響力,改變人們對于公共事務的看法。
在休謨的心中,雖然闡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構成的原理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被人們接受,同樣也是一種失敗。當他發現他所構想的具有“劃時代”革命性的著作《人性論》由于過于“深奧”,無法在公眾中引起反響時,就果斷地放棄了這一成果,稱之為“年輕時代不成熟的作品”。休謨認為這本書的錯誤不在內容,而在表達方式,于是對其中的認識論和道德論部分進行了改寫,以一種公眾更易于接受的明快式語言加以表達。人們發現休謨在政治哲學方面有很深刻的思想,但是休謨從來沒有寫出一本如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或霍布斯的《利維坦》一樣的政治理論著作,他的政治論著是由一些短小精悍的時政論文構成的,論文之間缺乏直接的相互聯系,沒有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要探究休謨的政治哲學,只有將他的《人性論》《英國史》以及他的宗教著作和這些政治論文結合起來思考才能一窺其中的奧秘。休謨不但沒有一部完全系統的政治理論著作,他甚至沒有像斯密和盧梭等人那樣有一個完整的政治理論著作的規劃。休謨的這種做法并非緣于他的疏忽或懶散,而在于十分關注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被公眾接受、如何才能對人們的觀念產生實質的影響。基于《人性論》的失敗,他認為深奧的、純粹解剖式的著作并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休謨選擇做一個文人與他從小所生活的家庭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休謨一七一一年出生于一個貴族之家,剛出生父親就去世了。他和一個哥哥、一個姐姐由母親獨自撫養長大。雖然家庭背景較好,可是根據當時歐洲的長子繼承制度,父親留下的絕大部分財產都由哥哥來繼承,休謨只能獲得其中極小的一部分,這意味著休謨只能夠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獲得生活的來源。休謨在學生時代就發現,自己內心占統治地位的激情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其他任何職業都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厭惡,立志要將一生獻給文學,并努力訓練自己的文學才能。休謨有著強烈的自信心,他不愿意像霍布斯和洛克等哲學家所做的那樣,為獲得生活來源而依賴或服務于某一個大人物。為了在有限的財產支持下寫作《人性論》,年輕的休謨移居到法國一個生活成本不高的小城一一拉福來合,并且嚴格自律,以極其節儉的方式維持獨立的生活。斯密曾講過休謨年輕時省錢的一個例子。休謨常到一家小酒館吃飯,但他從來不給侍者小費。不過侍者并不生氣,因為休謨總能將他們逗得哈哈大笑。斯密強調休謨的“這種節儉,不是基于貪財,而是出于對獨立的熱愛”,即使在生活最嚴苛的時候也并沒有影響到他的仁慈與慷慨。中年之后,休謨的《政治論文選》,特別是《英國史》等著作的成功使他獲得了大量版稅收入,生活變得寬裕乃至富裕。休謨自豪地說他從書商中獲得的版稅收入“大大超過了英格蘭以前所知的任何一位作家”。
經濟上的獨立只是休謨成為一個精神自主的文人的必要條件。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文人還要保持思想的客觀中立,不能依附于任何黨派和流行的思想體系,只能從社會的公共利益出發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面對外界的批判和壓力時,無所畏懼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在《英國史》中,休謨自豪地宣稱“在所有的歷史學家當中,唯有我既不在乎當時的權力、利益和權威,又不在乎大眾偏見的叫喊”,最能夠以一個中立的身份來評判各派的主張。令休謨沒有想到的是,《英國史》最早出版的一卷——從詹姆士一世繼位到查理一世被殺——受到了各方面的猛烈攻擊。尤其是輝格黨攻擊他竟膽敢“給查理一世和斯特福德伯爵一灑同情之淚”。考慮到輝格黨在國家和思想領域所處的主導地位,休謨對輝格黨的批判必然會觸怒社會中大量有權勢的人物,但休謨不為所動,在他后來對斯圖亞特王朝兩卷的一百多處的修訂中仍然堅持自己的原則判斷,每一次都更為偏向托利黨人的立場。
休謨選擇做一個文人而不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家也與他的哲學認識論有關。在休謨看來,人類的行為是受“信念”統治的,若想推動社會進步,就需要通過某種方式影響和改變人們的“信念”。為了推動社會秩序的進步,必須要改變人們錯誤的公共意見——休謨稱之為迷信,他讓人們認識到何為真正的公共利益。休謨認為,一個脫離實踐和社交,只關注抽象的理論構建的學者缺乏對社會的影響能力,無法引導公眾信念的改變。休謨發現歷史著作是一種傳達觀念、引起人們關注的有效途徑,于是在完成一些短小精悍的政治論著之后,就開始六卷本的《英國史》的寫作。休謨也十分重視作品的可讀性,在去世前長達十多年的時光中,他除了偶爾受邀從事一些行政事務之外,主要的工作就是修訂他已經出版的著作。有趣的是,休謨并不認為這種修訂工作很枯燥,而是和寫作本身一樣充滿樂趣。在朋友中問,休謨有著強烈的幽默感,很善于通過巧妙的方式處理與他人觀點的分歧。
休謨將各種迷信看成他一生最大的敵人,他相信迷信對良好的社會秩序和人們的幸福是有害的。在各種迷信當中,休謨又將關于宗教的迷信看成最具破壞性的一種。宗教派系具有強烈的原則性,使得家庭、社會政治分裂成為互不相容的群體,在人們之間最難實現相互妥協。休謨對宗教的批判包括對宗教的社會學批判和認識論批判。在《宗教的自然史》當中,休謨探討了宗教的起源,認為它本質是一種迷信,起源于原始人對外界環境的不了解而產生的恐懼。作為一種迷信,宗教無論在道德上還是政治上都是有害的,特別是以基督教為代表的一神教,它比西方古代的多神教更具壓迫性,更容易在人們之間造成分裂。休謨說:“坦白地說每一種宗教在道德上都是有害的。”關于宗教的認識論批判,休謨在《自然宗教對話錄》這本書,以及“論自殺”“論神跡”“論靈魂不朽”等論文當中,以經驗主義哲學為基礎,對宇宙設計論、正統宗教論等有關上帝存在的論證進行了批判,認為它們在邏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休謨對上帝存在的懷疑和對宗教的道德與政治批判自然會引發正統派的圍剿。英國一六八八年的憲政體制雖然在政治上確立起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不過這并不能保證人們在社會領域寬容多元的價值觀念。在啟蒙運動時期的蘇格蘭,政治和宗教事務主要掌握在蘇格蘭長老會手中,雖然出現了威廉·羅伯特森(WillianRoberterson)、亞歷山大·卡萊爾(Alexander Carlyle)、休·布萊爾、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為代表的一些溫和派成員,但是持宗教正統主張的蘇格蘭大眾黨仍然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就社會氛圍來說,人們普遍對無神論者有著深深的敵意。休謨曾先后申請愛丁堡和格拉斯哥大學的教職,都因為他的無神論傾向而沒有成功。基于當時的政治形勢,連作為朋友和老師的哈奇森都不認為休謨是合適的人選。在宗教的正統派看來,宗教是人類道德的基礎,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道德上必定是一個惡棍,一個無神論者沒有資格成為大學中的道德哲學教授。宗教正統派學者、哈伯丁大學教授詹姆斯·貝蒂(James Beattie)強烈批評休謨哲學,他認為休謨對宗教的攻擊是在試圖“推翻這僅有的人類幸福的基礎”。休謨毫不退縮,他相信人類的道德并不需要宗教作為基礎,一個無神論者可以是一個有著高尚美德的人。休謨對自己一生的辯護,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榮譽,更是在啟蒙思想的戰場中捍衛內心的哲學信念。
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休謨對疾病和死神的態度是現實的和積極的。他對病情采取積極治療的態度,直至去世前一年還尋求各種方式治療。他到倫敦找醫生看病,并且到巴斯(Bath)溫泉小鎮嘗試用洗浴來治療。當休謨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就著手準備自己的后事。為了讓世人了解自己,休謨寫了一個簡短的自傳(“My ownlife”),簡要介紹自己的一生。他將一生概括為“熱愛文名”和“性格樂觀”,除了自陳獲得經濟獨立和具有樂觀的性情之外,幾乎沒有夸贊自己,更多的是著作的失敗。為了避免被他人說成是追求虛榮,他的自傳主要涉及他的學術生活,并聲明他的這些說法都很容易得到證明。在宗教正統派看來,當一個人走向死亡時,將會面臨上帝的審判,不虔敬者必然會在神的面前瑟瑟發抖,對自己一生的行為表示懺悔。休謨十分清楚這些人在他死后一定會采取各種方式來攻擊自己,他以經驗的、可證明的方式向世人描述自己的真實生活——這種生活,休謨認為可以經受住最嚴格的道德檢驗。
作為休謨最親密的朋友,斯密是一個比休謨更為內斂和謹慎的人。斯密更期待過一種平靜的生活,他曾勸說休謨不要因為盧梭的攻擊就公開自己和盧梭的往來信件,理由是這會打破休謨所擁有的平靜生活。就其本意來說,斯密不想與宗教正統派直接沖突,無論在《道德情操論》還是在《國富論》中他都沒有正面表達自己的宗教觀點。斯密甚至沒有答應休謨的一再請求,在休謨死后出版他的《自然宗教對話錄》。然而,作為休謨的密友,斯密理解休謨一生的雄心與渴望,知道休謨在死后會遭受到各種各樣的非難和攻擊。為了維護這位密友的榮譽,斯密覺得有責任向世人介紹休謨在去世前的想法和行為,請求休謨允許他完成其自傳的補充部分。斯密對休謨去世的描述寫于他給休謨的出版商兼朋友威廉·斯特拉恩的一封長信。在休謨去世后,此信與休謨自傳合成一個小冊子很快公開出版。
在這封信中,斯密寫道,當休謨從倫敦返回愛丁堡之后,他已經十分清楚地知道留在世上的日子已經不多了。不過,雖然休謨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變得更為虛弱,休謨愉快的性情卻沒有一刻消沉,他像往常一樣為他的新版著作進行修訂和閱讀,并興致勃勃地與身邊的人一起談話和娛樂。在他面前,朋友們在談話時不需要將他當成一個即將離世的人而有任何顧忌,休謨為此很高興甚至以此自夸。斯密曾經用一段動人的語句描述休謨的一生——用斯密的傳記作家伊恩·斯姆普森·羅斯(Ian Simpson Ross)的評價來說,這些句子也許是斯密一生中寫得最好的一段話:“這樣,我們最優秀的、永遠也不會被忘記的朋友去世了。……他的性情看起來,請允許我這樣表達,也許比我所認識的任何其他人都更為平衡。……總的來說,我認為他,無論是他的生前,還是直到他去世,已經在人性的弱點所能允許的范圍內,最大可能地接近成為一個具有完美的智慧和美德的人。”斯密知道,他對休謨的這種描述,休謨的敵人絕不會同意,但他不為所動。
休謨去世三年以后,斯密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一封我認為是完全無害的、關于我們剛辭世的朋友休謨的信件,帶給我比我所寫的《國富論》對整個英國商業體系的攻擊更多十倍的狂暴攻擊。”宗教正統派對休謨和斯密的攻擊實際上反映出他們內心的恐瞑,休謨用他的一生證明了美德并不需要以宗教為前提。塞繆爾·杰克遜·普萊特(SamuelJackson Pratt)在《對休謨的生活和著作表示抱歉》中寫道:“大衛·休謨死了。正統派的支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被這一事件動搖。”休謨就這樣在朋友的眷戀和敵人的嘲諷攻擊中去世了。回顧休謨的一生,可以說休謨完全實現了他年輕時代就確立的做一個“文人”的夢想。終其一生,休謨從未對自己在思想上的發現和創見有所懷疑,但他十分渴望自己的著作能夠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因此在自傳中不斷地強調自己著作的不成功。按照休謨的描述,他的《人性論》“出版時就死掉了”,《人類理智探原》“完全被忽視了”,《道德原則研究》“來到這個世界沒有人關注和看到”,《宗教的自然史》出場“更加昏暗”,《英國史》第一卷被“斥責、不贊同甚至是嫌惡的叫喊聲充斥”,而關于都鐸王朝的兩卷的“叫喊聲”“幾乎等同于對關于斯圖亞特歷史的反對”。《英國史》中關于早期英國的兩卷“只是被容忍,或者取得了可容忍的成功”。在休謨的觀念中,只有他的《政治論文選》和《英國史》關于斯圖亞特歷史的第二卷一經出版就獲得了人們的接受。實際上,如果我們仔細審視,就會發現休謨對自己著作的出版慘狀的描述有一些夸張。正像丹尼斯·拉斯姆森(Dennis Rasmussen)所問的:“如果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如此不成功,他為什么變得那樣的富有和著名?”詹姆斯·哈瑞斯(JamesHarris)也同樣持這一觀點,在他看來,休謨的著作實際上都取得了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作家所夢寐以求的成功,他年輕時作為一個“Manof letters”的理想完全實現了。
縱觀休謨的一生,他是一個能夠給自己也給他人帶來快樂的人,他的個性獨立、溫和、樂觀,很容易與人相處,能夠感受友誼。休謨還是一個對自己和對社會有用的人,依靠版稅的收入獲得了經濟獨立,并以一位哲學家的身份啟蒙人們的思想觀念。休謨贏得了朋友的愛和尊重,與斯密的友誼更是他一生幸福的重要構成之一。雖然休謨在思想上有很多敵人,但是他不曾被這些狂暴批判擾亂心境。他堅信自己是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因此能夠以一種無比坦然和安寧的心境離開這個他所享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