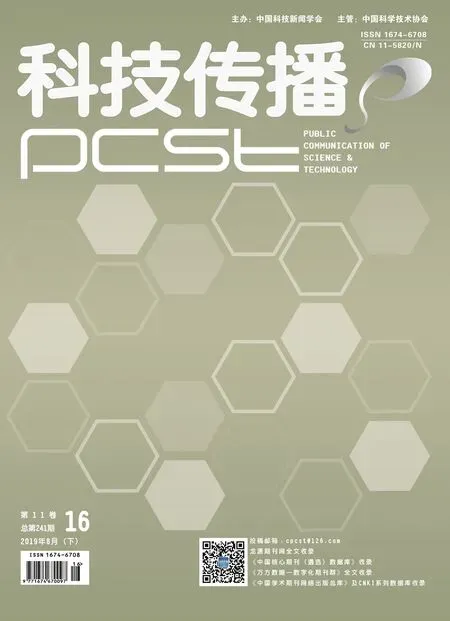論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法律屬性
——以“自然孳息”定性的合理性為研究視角
許純純
1 問題的提出
人工智能在著作權(quán)中起初僅是以載體的形式出現(xiàn),用以輔助創(chuàng)作與傳播。在創(chuàng)作行為上,并不存在著作權(quán)法上的創(chuàng)作行為,無法產(chǎn)生達到獨立產(chǎn)生著作權(quán)的法律效果;在傳播行為上,日益豐富了傳播途徑與傳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為著作權(quán)法對相應(yīng)的著作權(quán)人權(quán)利做出了更為完善的規(guī)定。換言之,人工智能在著作權(quán)的影響更多的是發(fā)生在非創(chuàng)作領(lǐng)域。然而,由于人工智能的不斷升級更新,它在著作權(quán)法中起到的作用逐漸發(fā)生變化,如今已經(jīng)介入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可獨立完成創(chuàng)作,初步顯現(xiàn)出智力創(chuàng)作的痕跡,這不禁使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面臨新的挑戰(zhàn)。但是對于這些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作品定性與權(quán)利歸屬,現(xiàn)行法律無任何規(guī)定,學術(shù)界與實務(wù)界尚未形成統(tǒng)一的看法,產(chǎn)生了大量的著作權(quán)法律爭議。倘若不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定性與歸屬進一步進行明確,極有可能會沖擊我國的現(xiàn)存著作權(quán)制度體系,甚至導致海量的“孤兒作品”應(yīng)運而生。
2 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可版權(quán)性的理論困境
2.1 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背離著作權(quán)法的立法價值
現(xiàn)代著作權(quán)法的立法價值自始至終都在于:給予權(quán)利人對作品的法定專有權(quán),以此鼓勵和支持作品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通過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立法本意可以得出結(jié)論,著作權(quán)法的核心乃是利益平衡理論,確認和分配知識市場的利益是其重心之一,而尋求作品的來源并非其最終目的。利益平衡理論強調(diào)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立法目的、功能以及整體的制度體系均應(yīng)立足平衡知識產(chǎn)權(quán)權(quán)利人的專有利益、與社會大眾權(quán)利相關(guān)的私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等多元利益之間的均衡關(guān)系。[1]由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并非自然人創(chuàng)作的產(chǎn)物,倘若以溯及主體作為判斷標準,則不難得出結(jié)論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不屬于作品,亦無法得到著作權(quán)法的保護。
2.2 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不具有著作權(quán)法意義下的獨創(chuàng)性
根據(jù)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以創(chuàng)作物是否符合作品的構(gòu)成要件為前提,進而確定著作權(quán)法是否應(yīng)對其進行保護。通說認為,作品的構(gòu)成要件包括四要件:具有獨創(chuàng)性即原創(chuàng)性;是思想或情感的表達;其形式表現(xiàn)必須為法律所認可;具有可復制性。[2]據(jù)此可知,倘若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在構(gòu)成形式上符合相應(yīng)的標準,亦即通過充分運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使其創(chuàng)作物以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方式表達其內(nèi)容,并以符合法律的形式予以表現(xiàn),就基本上達到了作品構(gòu)成要件的要求。從上文分析可知,作品對溯及主體也沒有過多的要求,基于此,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作品性。但由于其缺乏獨創(chuàng)性,故關(guān)于其是否具有思想和情感的表達卻仍存在不少非議。
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體系亦認為,作品是創(chuàng)作者思想和表達的體現(xiàn)。依據(jù)思想與表達的二分法理論,法保護的是作品的表達并非是思想本身。從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作過程來看,其創(chuàng)作物的產(chǎn)生過程依賴于機械式的智能程序,并非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行為。
2.3 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創(chuàng)作主體不契合著作權(quán)法的立法文義
作品是一種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表達,因此通說認為它應(yīng)以人的思想于感情為基礎(chǔ)。根據(jù)該理論,作品的權(quán)利也應(yīng)歸屬于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構(gòu)成的著作權(quán)人。這一觀點使得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缺乏法律主體地位,人工智能無法因自己的創(chuàng)作物享有法律賦予的權(quán)利更無法承擔法律規(guī)定的義務(wù),其亦不可能作為當事人出庭,即使其出現(xiàn)在法庭,也不存在法律上應(yīng)有的實際意義。
此外,著作權(quán)法的目的之一是激勵創(chuàng)新,所以它賦予了作者在有限時間內(nèi)的壟斷權(quán),此舉的最終目的是增進社會整體福利。在現(xiàn)今的創(chuàng)新驅(qū)動發(fā)展模式下,這一基本原則在著作權(quán)法規(guī)則的解釋與拓展中依然需要被遵循。至于應(yīng)否賦予人工智能以壟斷權(quán),關(guān)鍵還是得考慮此舉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競爭與保護之間的平衡關(guān)系。實踐中,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會使得部分著作權(quán)主體的差別化日益減少,從而導致作品內(nèi)容趨向同質(zhì)化,這對傳統(tǒng)著作權(quán)的保護產(chǎn)生了一定的沖擊,創(chuàng)作物的內(nèi)容不排除出現(xiàn)新一輪趨同性的可能,作品的獨創(chuàng)性即原創(chuàng)性會大大降低。而此番現(xiàn)象均對給予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著作權(quán)保護的正當性做出了否定[3]。
3 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定性為自然孳息的合理性
將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定性為孳息,繼而通過民法對其予以孳息的保護,有利于給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一個合理的法律地位,解決現(xiàn)存的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保護的困境難題。
3.1 作為民事對象具有可保護性
如今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暫時尚未大規(guī)模的涌出,但是當下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日新月異,正是由于其不斷發(fā)展,所以可以預測在不久的將來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可能會掀起新一輪的法律挑戰(zhàn)。倘若當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數(shù)量增多到一定規(guī)模時,現(xiàn)行法律依舊不給予定性與保護,那么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的詩歌、音樂和繪畫等創(chuàng)作物可能會對人類作品產(chǎn)生沖擊。畢竟在相同條件下,理性的人一般都會選取制作成本較低還與人類作品實質(zhì)區(qū)別不大的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面臨這種情況,一般作品的作者及其權(quán)益難以得到充分的保護與滿足,可能致使其創(chuàng)作積極性不斷降低,而這可能又會導致與之相輔相成的傳播產(chǎn)業(yè)也會面臨困境甚至走向衰弱,此種結(jié)果很明顯是與著作權(quán)法立法之初強調(diào)推動文化事業(yè)發(fā)展與繁榮的目的背道而馳。由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難以納入著作權(quán)法制度進行調(diào)整和規(guī)范,但倘若不明確其定性與歸屬,則難以對其展開保護和司法救濟。如果一直將其至于法律空白地帶,那么極有可能對我國的現(xiàn)存著作權(quán)法等相關(guān)制度體系造成沖擊,亦會造成海量“孤兒作品”無處安置的局面。由此可見,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進行保護具有必要性與合理性。
3.2 契合自然孳息的構(gòu)成要件
我國現(xiàn)行的民法立法尚未將孳息的概念進行詳細地規(guī)定,但是民法理論界基本上認同孳息即原物的出產(chǎn)物或原物的收益這一觀點,根據(jù)其屬性進行分類,可將其分為法定孳息與自然孳息。法定孳息是由他人使用原物而隨之產(chǎn)生的,[4]但人工智能是通過對資料收集、整理并自行加以運用從而產(chǎn)生創(chuàng)作物,其并不符合法定孳息的定義。而自然孳息的判定則為:其一,該物是否以獨立物的形式存在;其二,該物是否為經(jīng)過加工而產(chǎn)生的新物;其三,該物是否為埋藏物。據(jù)此分析,第一,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一旦產(chǎn)生便與產(chǎn)生作品的軟件程序相分離,獨立成為一種創(chuàng)作成果;第二,人工智能通過算法對信息進行加工、整合形成新物;第三,其顯然不屬于埋藏物。故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契合自然孳息的構(gòu)成要件。不可否認,此種認定具有一定的擬制性,畢竟傳統(tǒng)的自然孳息往往以有體物的形式存在。但當下將其定性為孳息是相對而言最為貼切的。
3.3 利于節(jié)約我國的立法、司法資源
出于保護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相關(guān)權(quán)利人的目的,當下部分人工智能水平較高的發(fā)達國家,正著手對著作權(quán)法進行立法修訂,使得應(yīng)對具體的問題時能夠有法可依。但從我國的司法實踐出發(fā),如果設(shè)立新權(quán)利,其涉及面不僅廣而且較為復雜,通過設(shè)立新權(quán)利的形式解決新問題則極有可能因為制度尚未成熟而引發(fā)更多的問題。面對基于社會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新事物,最好的應(yīng)對方法便是對現(xiàn)有的法律資源進一步深入挖掘和優(yōu)化整合,充分利用現(xiàn)有法律和法理的合理部分加以解決[5]。而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其性質(zhì)符合民法中關(guān)于孳息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因此,將其定性為自然孳息,不僅有利于解決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定性的困境,也有利于進一步明確相關(guān)的保護范圍以及提供侵權(quán)解決機制。綜上所述,故關(guān)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立法不必脫離現(xiàn)有立法而單獨再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進行定性。
4 結(jié)語
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不具備創(chuàng)造性思維,而人的靈感以及個性,正是作品創(chuàng)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但其不斷發(fā)展使得現(xiàn)行法律體系受到?jīng)_擊,也為現(xiàn)行法律體系帶來新一輪的挑戰(zhàn)。因此,將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定性為自然孳息并通過運用自然孳息的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進行規(guī)范和調(diào)整,以期更好地應(yīng)對當下因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發(fā)展而導致的保護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