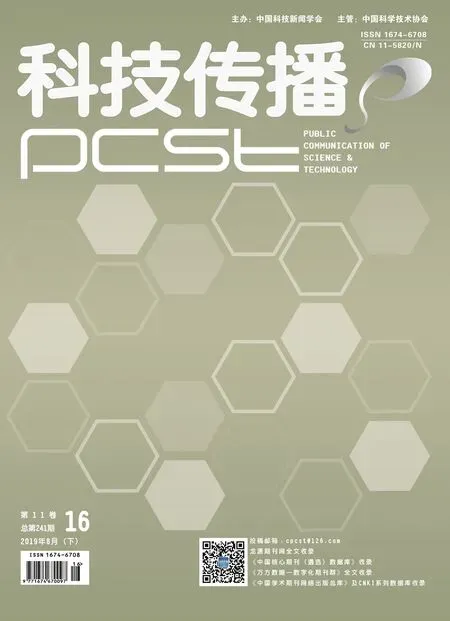人工智能技術在公共圖書館導視中的應用
——以南昌大學圖書館為例
郝琳琳,胡紅忠
公共圖書館這種信息聚集區和人群高度集散區,傳統的導視系統已經很難滿足人們的需求。人工智能技術在導視系統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該技術可以彌補傳統導視系統的不足,使得導視系統更具有靈活性。
1 公共圖書館導視系統的特點
公共圖書館的導視系統有著它自身的特點。從公共圖書館自身角度說,一方面它是一個高度集中各類信息的場所,另一方面公共圖書館信息的快速更新也對公共圖書館導視系統的實際應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從外部因素上,公共圖書館是人群高度集散的場所,這就使得公共圖書館的導視系統要滿足它自身的內部需求和外部人群的需求。
2 公共圖書館導視系統普遍存在的問題
導視信息傳達不暢,導視系統的首要用途就是向用戶傳達信息,但就目前許多圖書館的導視系統來看,導視系統并沒有發揮到指導用戶尋路的目的;導視系統設計同質化,導視系統的設計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應使導視系統的設計融入到相應的環境中。然而,現有公共圖書館的導視系統并未與公共圖書館的空間有任何關系;導視系統設計形式單一,傳統的導視系統仍停留在普通的設計形式上,給用戶單一視覺上的信息傳達,但是并沒有考慮到所有人群。例如,隨著時代的變化,老人群體對文字及圖形符號的理解也和年輕人逐漸產生差異,并且導視系統中的字體過小,圖形符號設計過于復雜,也會影響老年讀者對導視信息的識別性。以上問題都是傳統導視系統設計中存在的共性問題。
3 人工智能技術在導視系統設計中的應用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交互手段越來越多。人類由一個物理現實世界逐漸走進虛擬世界,相比個人用戶端,智能端的應用更具靈活性。無論用戶所處何種環境,只需借助智能端App 即可找出目標位置;AR 技術,是一種實時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角度后,通過電腦將相應的虛擬圖像附加上去的技術。這種技術可以把虛擬世界融到現實世界并進行互動,最終做到將虛擬和現實同時顯示出來,通過虛擬圖像彌補了現實世界的不足之處,能夠讓用戶產生沉浸式體驗。
4 空間導視系統設計整合
本章節以江西省南昌大學前湖校區圖書館的導視系統為例,對現有的空間導視系統進行優勢整合分析。總平面布局索引圖位于圖書館借閱室外,人體工程學相關研究表明,人體主體視覺區域位于水平視線高度以上20cm,而索引圖位置處于人體水平視線高度以上40cm 至60cm 區間水平,從而導致沒有產生示能。此外,導視牌位于圖書館借閱室內部,同樣地,并未起到與用戶交互這一作用,導致用戶錯過這相關信息,從而使用戶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尋找相關圖書資源。圖書館一樓至四樓屬于流動書庫,每層樓均有不同專業方向的書籍。借閱室外僅有A4 紙打印的小標識用于指示用于所處樓層,樓梯間無燈光,也無其他導視系統。進入借閱室后,每個書架上均有用于標注書籍類別的導視牌,但由于書籍的更新使得導視牌內容需發生不定時的變化。然而經調研發現,導視牌上的許多信息是由圖書館管理人員手動填寫的。此舉不僅影響了導視牌帶給用戶的美感,且諸多信息也會隨著紙張和顏料的老化而逐漸模糊不清。縱觀圖書館借閱室一樓到四樓的導視系統,涵蓋了筆者在第二節所述的公共圖書館導視系統的問題。在理論和技術的支持下,筆者針對南昌大學圖書館導視系統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次優勢整合,并探索創新形勢下的公共圖書館導視系統設計。
5 南昌大學圖書館導視系統設計構想
導視系統應建立在南昌大學圖書館公共環境設計中。基于此原則,筆者認為首先要將導視系統融入到整個內部環境中。其次考慮用戶在圖書館內部的行為模式和流線圖,使導視系統發揮其最大限度的巧能性特征。最后運用技術手法賦予導視系統新的生命力。最終使得圖書館內部導視系統在具有功能化的同時也具有藝術化。并突破以往中規中矩的平面導視系統,探尋多維度的空間導視系統以帶給用戶的多種感官體驗。
首先門口舊有的導視牌換成信息亭,在交互界面上顯示樓層的各功能區域及分布。信息亭的使用能夠方便用戶對圖書館整個空間布局產生宏觀的把握整體概念。信息亭就像放大的手機屏幕一樣,存在讀者內心的內隱記憶就能夠發揮作用,在讀者無意識的情況下就已經完成了與信息亭有效交互過程,其操作方式和用戶與手機交互有著一致性,因此能夠產生示能。用戶可以進行滑動、點擊、上拉等操作,點開想要尋找的隱藏信息。相比導視牌所傳遞的有限信息,在大數據時代信息亭傳遞的消息可以是無限更新的,并且根據每個人上傳的信息,大數據進行分析運算,得到屬于每個用戶獨一無二的閱讀喜好信息,可以更加人性化地服務讀者。然而,信息亭可供人數觀看是有限的。基于此不足,筆者認為可以利用手機客戶端的App,只要用戶進入圖書館區域并且將手機連上圖書館的內部網絡,App 便可以像電子地圖一樣帶領用戶找到目的地路線。針對樓梯走廊這一空間,因為原導視系統沒有燈光,因此要加入光源設備。筆者認為可以利用空間投影技術,當用戶走近時可以通過聲控開關,并且打開空間投影,投影隨之可以顯示樓層指引,所有信息都是隨著用戶的行動發生著變化當用戶靠近時,附近的墻面會通過投影顯現,從而達到指示的作用。互動的導視系統能夠帶給用戶耳目一新的感官體驗,同時隨行動而出現的提示方式,使觀眾幾乎不可能錯過每一個指示路口的信息。就圖書館閱覽室內部而言,每個架子上的標簽可以用電子觸摸顯示屏替換,此屏幕能夠給讀者一個示能,然后讀者根據顯示屏上的意符,進行搜索圖書信息等操作。當讀者尋找書籍資料的時候,電子屏可以顯示出目標書籍的具體位置,從而給予讀者及時的反饋。這一模式的導視系統便于讀者應用的關鍵是人們對電子顯示屏操作的固化,是基于習得性電子顯示屏操作的一個概念模型。因為圖書館的圖書流動性很強,上述導視系統的設計能夠及時給予讀者最新的信息以及最人性化的關懷。
6 結束語
目前我國關于導視系統研究的理論,對于公共圖書館導視系統的應用研究在我國的導視系統設計中仍較為少見 。筆者以南昌大學前湖校區圖書館為例在公共圖書館導視系統優化方面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是本研究僅論述了人工智能圖書館幾種可能形式,然而當今交互導視系統的發展已經逐漸成熟起來,大大豐富了現有導視設計的形式。交互設計可以通過人工智能使設計中的各元素均能與用戶產生聯系并力求使用戶獲得最佳的交互體驗。在“萬物互聯”的情況之下,人工智能通過對用戶交互行為模式的分析、用戶心智模型與感知認知邏輯的推理,以及用戶體驗與評價緊密結合,從而產生交互的前饋與反饋,最終影響交互設計方法,達到人性化的設計,更好地滿足用戶心理和生理上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