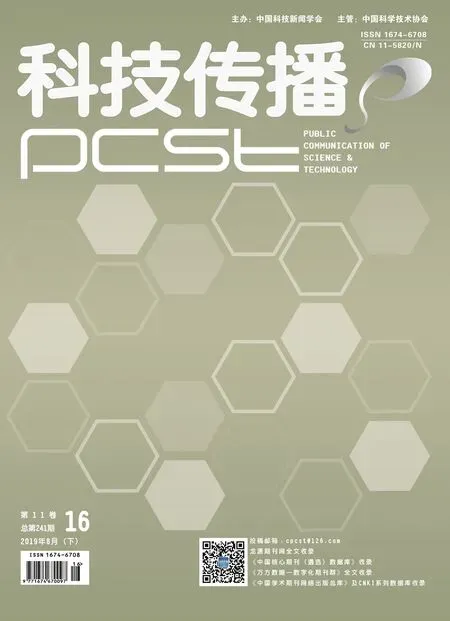管窺《杜甫韻文韓國漢詩接受文獻緝考》中的編輯元素
代景麗
眾所周知,編輯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各個環節相互聯系、制約和促進,具有嚴密的整體性,而作為每一個具體的環節又有相對的獨立性。在編輯《杜甫韻文韓國漢詩接受文獻緝考》的過程中,筆者即對其從結構章節的設置、內文編校、裝幀設計以及印制工藝等各個環節進行了先由部分而及整體,后由整體而及部分的統籌思考。下面擇編輯元素之一二環節,加以簡單介紹。
1 開本選擇及輔文設計
先來談該書的開本選擇問題。書籍的開本及成書的體式,往往體現著責編的基本素養。初見此書雛形,煌煌千余頁的體量,加上作者執意要成一書,費神思量開本問題儼然大有必要。版心大小直接決定著每頁所排字數多少,從而間接影響書脊的版式設計及封面的整體風格,所以對其細加斟酌實屬必要之舉。經過數次與作者溝通,起初達成的出版意向是簡體橫排,165×238 專著開本,但考慮到書稿為詩歌形式,且為杜詩韻文,我大膽建議作者采用繁體豎排,改換184×260 的開本形式。這樣一則會增添古色古香的味道,盡量保留杜詩的時代韻味,二則也會適當消減成書的厚度,減少后期圖書裝訂過程中的麻煩。看似簡單的開本、體式的調整,實際上增加了后期編校中的諸多問題,但好在我用一顆職業編輯的耐心與信心戰勝了當時所謂的困難。再說有關輔文事宜。恰切的圖書輔文可以對圖書正文起到補充、完善的作用,有時甚至具有畫龍點睛之效。沈先生的這部專著就涉及封面、書名頁、內容提要、作者簡介、凡例、跋、附錄等。對于封面文字,作者提供了幾幅書法家的墨寶,結合書稿內容及書法體式風格,最終選擇了黃震云先生的書名題字。同時書名頁的設計也與此書法色調保持一致,即將整個封面背景做黑白處理,既有與封面整體上的統一,又有獨屬于書名頁要素設計的雅致。內容提要和作者簡介,是對此書此人的高度凝練化表述,從某種層面上說,對圖書的營銷也會具有一定的宣傳效果,對其應甚加重視。沈先生博學又有專攻,人生經歷尤其豐富。對于這樣的古代文學大家,我酌從其教學科研及著述成果方面加以闡述,學歷背景、社會兼職其余情況均統不計。該書的內容提要,我遵從精煉而有文采的編寫原則,盡量做到簡略中的詳盡。先生為人低調,對于序和跋,不請業界泰斗級人物為之,全由其受業弟子寫就,恰與該書的舒朗清爽之貌相互契合,盡得古人高居其位而不居功的神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對于凡例的加工,本著引導與補充的原則考慮,將其分條羅列,眉目清晰,對于讀者迅速理清全書行文脈絡及閱讀難點大有助益。經過這樣妥善的處理,輔文既自成一體,各自承擔相應文本職能,又與內文內容交相呼應,極大地提高了圖書的閱讀美感及便捷性,達到了圖書輔文從屬于正文而又高遠于正文的現實功效。
2 內容編校
談及內容編校,雖已年逾兩載,但卻恍如近在眼前。不得不說,那是一段痛苦而美好的時光,因其極苦而今則變得極甜,頗耐回味。初接排完版的書稿,我著實嚇著了(八百來頁),或許是我入行太淺,從未策劃過如此大體量的圖書。但我有堅定的信念,憑著自己多年來古文知識的積累,一定可以啃下這塊“硬骨頭”。初接此稿,尚是隆冬之際。一校下來,發現在繁簡體轉換的過程中,對于異體字的處理,出現了很多矛盾點。于是我果斷將其列為專項檢查點之一,并就“發”“斗”“臺”等問題與作者進行了反復溝通,第一時間將校對結果反饋給他,最終根據詩歌的具體內容做了確切的統一處理。在二校中,校對編輯提出書稿中詩人注文是否加句讀的問題。我結合書稿的內容,認為在史料價值方面的體現之一即是該書可為學界提供較為恰切的杜甫韻文在韓國彼時的接受樣態,如若不加句讀,讀者接受起來會頗感吃力,也較容易引起解讀方面的誤解,這當然不是我們愿意看到的。基于此種考慮,我與沈先生進行了深入溝通,他雖覺得這一小小的改動會大大增加其校對的工作量,但考慮到于學林的接受之便,先生還是欣然同意添加句讀。由此可見,作為杜甫研究的一大學者,先生是何等的用力與盡力!作為責編,我也一次次被先生一絲不茍的敬業精神而深深感動。后經先生三個來月的思考與查閱,注文內容句讀分明,意思明確,全稿也舒朗起來,言其“一改定乾坤”,或不為過。當然,后來在四校、五校中又發現了由“又”“右”等引起的背題、同姓詩人的排序、書名號的部分缺失以及相同詩人的詩文重復等問題,這些“炸彈”的拆除,有效地提升了書稿的內文質量。
3 裝幀設計
談及此書的裝幀設計,我感觸頗深。清晰記得當時作者對于封面的基本要求:首先,必須要有杜甫的畫像;其次,水墨色調。乍一看,似乎很切題,相信這也是很多人選擇的程式化封面。我雖不認同先生的本初設想,但我也沒有即刻打消他參與設計的積極性,這一次,我想用事實說話,“逼”先生自退。因為有時尊重作者原初的想象力也可以激發編輯加工中的創造力,這是編輯智慧的來源之一,切不可切斷。于是我讓美編按照沈先生的“理想圖”,做出一幅封面;又按照我與美編的設想,做出了一幅云紋封面效果圖(黃底白字),將其一起發給了作者。很快,電話打過來了,沈先生先是對自己的“設計”自責了一番,說自己思維太固化,看似切題,但效果遠不如從“遠”入題更傳神。這恐怕就是不解一字,盡得所欲的最好說明了吧?當然,后來我們在封面題字、封面襯紙及作者照片等方面看法也不盡相同,后經先后數次出校樣,最終我們的意見達成了一致。但也不得不說,這也是頗為坎坷的。因為作者認為封面要將其所能想到的亮點元素比如內容簡介、宣傳用語等均體現在有限的封一、封四之中,而封面布局最忌滿,滿則固,固則死,這也合乎古人“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哲學思維。但我也不否定作者的提議,他是想把圖書的亮點都表現于“門面兒”上,無可厚非,原因在于他不太了解出版,但對于他的參與意識我還是極為贊賞的,相比那些將書稿一交了之的態度,我還是更欣賞前者,畢竟編輯與作者是在共同創造著精神產品,兩者不能截然分離。總之,與作者、美編幾經磨合,我對設計之美,留白之韻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會,雖然我們常言“條條大路通羅馬”,但對圖書的裝幀設計而言,有且只有一條最恰切而簡潔的羅馬之路,這便是經由編輯直覺上升到藝術直覺的主觀注意。
4 印制工藝
圖書印制質量,在某種程度上關乎整個出版環節的成敗,也是連接圖書編校與發行的關鍵一環,對此不可不尤加重視。在印制此書之前,我先是對比了北京新華印刷廠、長春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等五六家印廠,對他們的印刷質量、紙張情況、成本、運輸以及時間等做了全面考慮,最后決定選擇就近印刷。在紙張、工藝等相較不大的情況下,選擇本地印刷一則時間上較有保證,二則可以節約運輸成本。選定了印廠,我還是不太放心,尤其是對紙張,我決定親自到印廠確認一下。畢竟每批紙張的克數雖固定,但有時難免還是會有色度上的稍許差異,這也是我堅持去“目測”的基本考慮。對于封面用紙,我看后選擇了250 克銅版紙,采用起鼓工藝,并對成書做附膜處理;對于內文,采用黃度較高、光滑度較好的80 克道林紙,這就契合了本書的古雅氣質。事實證明,我這樣的選擇是合乎出版選紙規范的,因為一本書的用紙,要充分考慮書稿的內容、印制成本以及成書效果。沈先生的這部學術專著,以詩歌為綱,串聯起杜甫韻文在韓國的接受樣態,偏古雅之風,選用泛黃的紙張既能在閱讀中保護讀者視力,又能增添復古典雅之韻。
5 結束語
著名作家巴金曾說:“作為編輯工作者,應當把自己看作這塊園地的園丁,你們做的不僅是介紹、展覽的工作,你們還有將‘萌芽’培養成樹木的責任。”作為圖書百花園中的一名園丁,我愿將雨露之情傾心播撒在每棵幼苗之上,古木參天是我們的夢想,但我深知,這得源于當下對圖書幼苗的點滴呵護,始于一個字、一頁稿、一本書。做到這些,編輯之路定繁花似錦,樹蔭連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