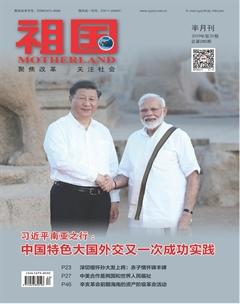鄉村振興戰略視角下看鄉土信仰的社會作用
贠蒙琳
摘要:在具有時代前瞻性與引領性的鄉村振興戰略的視角下,從歷史性、整體性與主體性的視角出發發掘鄉土信仰的社會作用,以楊凌示范區的典型村廟為例闡述鄉土信仰在精神層次與行為層次上的文化振興意義,展現其在新時代與鄉村振興目標的耦合,期待更好發揮鄉土信仰的積極意蘊。
關鍵詞:鄉村振興 ? 鄉土信仰 ? 村廟 ? 社會作用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統籌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鄉村振興要求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振興,其中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鄉村文化振興與鄉村振興的多重價值目標耦合”,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固本之道”、“鑄魂工程”與“應有之義”,但同時,文化振興在迎來機遇的同時,也面對來自國家、社會及個體在思想認識與實踐發展中的諸多挑戰,可能存在被誤解、被輕視及被破壞的風險。
一、多維視角下的鄉土信仰
(一)歷史性的視角
鄉土信仰的發展伴隨著世代累積的經驗與實踐,深深植根于我國歷史傳承下的多樣地域、多元民族與獨特鄉村,具有綿延不絕與古老厚重的歷史底色。
以楊陵示范區周邊的聶村金仙觀為例,20世紀以來,金仙觀同樣經歷了歷史的起起伏伏,從20-30年代廟會普遍的鼎盛,到50-70年代的低迷期,政府將以廟宇為依托的民間信仰活動視為封建迷信予以取締,廟宇被拆、神像被毀、廟會停滯。改革開放后,隨著村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與政策的寬容,民間信仰開始回暖,廟宇的重建也隨之興起,金仙觀從名不見經傳的小廟,發展成八社共建的典型村廟,其供奉的主神“聶云霄”更是歷經神話的演繹與縣志的認可,以每年三次大型廟會的蓬勃氣勢擴大其影響范圍與發展潛力。如聶村的發展軌跡一道,每個地方的社會文化史都經歷了廟宇建設與禮儀文化的變革,在此過程中也積累了無數的民間經驗與智慧,前仆后繼了精英們的經營與引領。
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上述對鄉土信仰所具有的文化歷史價值的充分認知,有利于充分意識到保護文化的延續性和社會的有序性的重要性,從而更珍視鄉土信仰所攜帶的中華文化的寶貴文化遺產與根脈,它們是中華文化不斷生長的豐厚文化土壤。
(二)整體性的視角
鄉土信仰雖然主要發生在鄉村的場域中,但我們不能割裂地去談鄉村。其一,對于民間信仰的文化價值,要把握其與經濟、政治、社會等的關系。其二,尊重鄉土信仰完整獨立的運作機制及文化體系,不能簡單地以外部性眼光加以評判。在以楊凌示范區的典型村廟為例的調查中,村民們的信仰是很豐富的,有信佛的,也有信鬼的,也有信各種自然的精靈的,不僅有儀式、祭祀、禮儀,還有巫術的各種活動。這些信仰很多是跟社會問題、心理問題和人的身體疾病有關系的,這些鄉村的問題是鄉土信仰經久不衰的現實基礎,但問題根源的查找不能局限于鄉村,而要反思城市化、現代化與資本化的運作是否造成了城鄉的斷裂與分化。在更大的圖景中,以鄉村振興的目標導向尋求個性基礎上的共性,梳理鄉土信仰各具特色背后所具有的共性機制與功能。
(三)主體性的視角
“回到自己的文化語境當中,才能真正看到中國的傳統。”他者化的眼光有可能矮化鄉土信仰自有的邏輯體系和內在關聯性。在鄉土信仰的發展過程中,鄉村的禮俗秩序和倫理精神被不斷發揚,普通人的參與感與主體性也得到激勵。建立在尊重與自信基礎上的文化認同,才更具有個性,才能真正滲透進農民的日常生活中、鄰里之間的親疏禮儀中,也融匯在日常的生產過程中,而不是流于政策推行洪流下的模式化產物,更不能淪為“社會建設的試驗場、資本擴張的生意場、政治角力的戰場與落寞文人的懷舊地”。
二、鄉土信仰的作用
(一)鄉土信仰在精神層次上的慰藉功能
1.鄉土信仰是鄉村凝聚力的源頭活水
以進香為例,它是指“信眾到外地的廟宇參拜,可以是個人行為,也可以組團前往,或者由當地廟方發起。”桑格瑞表示,“參加進香基本上就是一個分享靈驗故事的聚會,香客們相互交換自己的神奇體驗,開啟友好的交談。通過這些交談,香客們找到對自己宗教體驗有共鳴的聽眾,并從中學習別人使用的詞匯和表達方式。換句話說,進香為朝圣者提供了一個公共場合來確認他們信仰的正確性,以及他們生活的宗教意義”(Sangren , 2000 :91)。進香是圍繞鄉土信仰延續的一個重要的儀式,其中香火是信眾們參拜時所必須的物品,一般來說,一座廟的知名度越高、在信眾心中越靈驗,其外在表現通常是香火的鼎盛,信眾們不會與某個廟會建立制度性的聯系,他們與廟會的關系是自由而疏松的。通常信眾們會在農歷的初一 、十五到廟里進香,并在大殿中拜神,每逢大型的廟會活動時,再進行更加復雜、隆重的進香與拜神儀式。在與進香一道的諸多儀式被詮釋與外化的過程中,人們通過表達和實踐處在一個聯系更加緊密的社會關系網絡中,這對于維系村民彼此的生活秩序、乃至整個村莊共同體的凝聚都具有重要的整合作用。不論男女老少,都能在集體的狂歡中各獲娛樂體驗、情感滿足、矛盾紓解與自我認同需求。
普通民眾的信任與捧場也為無償的廟管會組織者們帶來了與傳統鄉紳類似的社會尊重與敬畏,促成了德高望重者們威望在村內其他公共事務上的延伸,從而減少村內沖突、增強社會控制,為鄉村治理與凝神聚氣帶來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
2.鄉土信仰是鄉村道德規范的現實載體
鄉土信仰中涉及的儀式多按照長幼輩分次序舉行,無疑是對道德教育的重申。人們出于功利的、現世的目的,到廟里燒香敬神、捐物捐力,同時也在期待神明的保佑,以獲得寬恕與庇佑。鄉村社會成員們普遍對禮序、神明和權威的敬畏,增強了集體成員內部的認同感,維持并強化了傳統文化的優良價值體系,使得“由地緣認同、血緣認同和信仰認同形塑的內生秩序”地位更加穩固,“核心就在于修復了鄉村的社會秩序和信仰體系。”
3.鄉土信仰是追溯鄉愁的儀式投射
儀式的舉辦建構了一種共同的美好記憶。當儀式活動結束之后,儀式現場的熱鬧逐漸淡去,重歸日常生活的族人依然反復品評與回味儀式的過程。
以武功鎮松林村土地廟為例,每年陰歷二月初一和初二是土地爺的廟會,其中二月初二是正會,二月初三是文昌爺的廟會。日常每月的初一、十五,來自外村的或者本堡的人會來此地敬爺。學者林美容提出“信仰圈”的概念,如果某個廟會的知名度與靈驗度都較高,建廟者可以在原廟的基礎上,采用分香的形式另建新廟。原廟和新廟,或者也稱為祖廟和子廟就構成了一個“信仰圈”,即“以一個神或其分身為信仰中心,區域性的信徒所形成的信徒組織,也可涵蓋沒有具體區域性祭典組織的區域性信徒的分布范圍,或是某一神抵的區域性勢力范圍。”金仙觀作為屬于八社的大廟,在民間傳說與廟會儀式上都與其他小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神話故事中,以轉世的形式將多個村廟串聯起來。據說,金仙觀供奉的是西北救世菩薩即三霄的二轉世,她轉世投胎到聶村的聶守仁員外家,自出世以來哭泣不止,靈山老母撫摸她后她便停止哭泣,靈山老母隨后帶她上靈山修煉成西北救世菩薩。楊陵周家村供奉的大霄的第三轉世;王家廟供奉的是二霄的第三轉世;松林村的火星娘娘廟供奉的三霄的第三轉世,火星娘娘就是封神榜里的火靈圣母。在儀式形式上,則體現為密切的互動與交流。據會長介紹,土地廟是金仙觀取水儀式的必經之地,從聶村金仙觀出發到西觀山取水,途中需在土地廟的二水關駐足敬神,后返回金仙觀。在民間傳說與廟會儀式的加持下,村民的娛樂活動也如火如荼的展開,每年都有村民自組織的自樂班前來助興,為自樂班的老人及看客們帶來節日的意義。
可以說,鄉土信仰是一種全民狂歡、超越一般意義的理性與經濟行為的社會活動,遵循狂歡、熱鬧和快樂原則,是一種社會的、奉獻性的廣場化活動。在當地人心目中,一年一度的廟會是重要程度比肩春節的節日,他們生發出自豪感與認同感,也在儀式的傳承中推舉出無數個剪紙巧手或是手藝能人,無形與有形的文化符號作為情感連接的方式,給幾代人帶來共同的關于鄉土信仰的記憶。
(二)鄉土信仰在行為層次上的實用功能
1.鄉土信仰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巨大的文化資本
傳統鄉村社會,最具有特色的,就是系統性的禮儀系統、完整可追溯的歷史文脈,如碑刻、廟宇。在民俗活動的演繹中,能夠吸引老中青少各個年齡段的村民前來,并與外界的人交流慶祝,編織出新的社會網絡,帶來了新的社會資源,不僅在文化層面創造了本土文化和異質文化競相表演的機會,也在人才方面吸引了本地精英的駐留,緩解了鄉村人才流失的問題,更為鄉村與外界的雙向認同打開了窗口,為后續諸多社會資源的落地創造了潛在的可能。
2.鄉土信仰是對分散社會資源再整合
以在楊凌示范區的典型村廟的田野調查為基礎發現,廟管會作為祭祀活動的草根組織團體,并不具備嚴格的科層組織,而偏向于更加扁平化的機構設置,分管財務、后勤、宣傳等工作,在一年一度的廟會中,則由廟管會人員和自發的一部分群眾承擔起接待香客進香和食宿、安排外來的娛神團隊、記錄布施與公布明細、維持治安與保持衛生等工作。在廟會等大的祭祀活動結束后,自發群眾與部分廟管會成員會自行解散,回歸他們原本的務工、務農或照料家庭的世俗生活中。
以武功鎮上營東村的文昌廟為例,據會長介紹,在武功縣還叫有胎縣的時候,據傳說唐朝時此地就有文昌廟,李世民生于武功,其母在其求學期間前來求功名。后漢朝的蘇武(武功人)在北方立功,此地才改名為武功縣。后自改革開放以來,文昌廟先后經三次重建:最初為土堆堆(原廟的遺跡);后在原址上建小廟并塑像;再后建大廟并塑像;最后一次歷時一年多,于2013年建成現在的文昌廟,主要靠群眾捐款修建,個人捐款最大數額為兩三千元,主要向本村、上營西、北、南堡及周邊村落籌款。三次修建均由三位會長及副會長主持,資金、材料、工具等均是群眾自愿捐款,匠工自愿前來參與修建工程,主要開支集中在建廟材料的購置、建廟人員的工錢和塑神像上。在廟址修建的過程中,傳統鄉紳的帶領作用與普通民眾的貢獻行為得以結合,彰顯了廟管會這一自發組織在人員調配、資金籌集與事項統籌等方面的民間智慧。
雖然廟管會這一組織在實踐過程中不具備官方授予的權力,但是它仍然能夠履行其社會職能,并在實踐與互動中尋求良性的運行模式,這樣自下而上、因地制宜地鄉村治理實踐探索,正適應了村民與鄉村的自我發展需求與主體性地位,在動態調試中尋求環境、秩序與服務的三重保障,最終為因地制宜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兼具特色與源頭的民間方案。
三、結語
在鄉村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與新的文化意識沖擊的境況中,如何在鄉村振興與文化振興的話語導向下發掘與完善鄉土信仰的社會作用,一方面需要黨和國家對鄉土信仰繼續本著對鄉土信仰活動“保護、管理、引導、服務”的理念,積極強調“宗教治理”應該向“社會事務和公共事務”方向轉化傾向,從而逐步走向法治化、規范化、社會化的治理;同時需要社會力量如廟管會、鄉村自組織的貢獻,發揮村民的創造性智慧與經驗,從而推進鄉村自治發展。一方面也需要以一種與時俱進的眼光看待鄉土信仰的存在問題,清醒地認識到鄉土信仰中封建糟粕的部分、廟管會等草根組織管理體制的落后、廟會開展時安全與生態問題的顯露等。在曲折中前進,于人文關懷的寬容中不懈探索更加開放包容的社會文化機制。
參考文獻:
[1]吳理財,解勝利.文化治理視角下的鄉村文化振興:價值耦合與體系建構[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1):16-23+162-163.
[2]鄧小南,渠敬東,渠巖,等.當代鄉村建設中的藝術實踐[J].學術研究,2016,(10):51-78.
[3]盧云峰.超越基督宗教社會學——兼論宗教市場理論在華人社會的適用性問題[J].社會學研究,2008,(05):81-97+244.
[4]陳進國.中國鄉土信仰如何走向善治[J].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03):115-120.
[5]羅士泂,張世勇.儀式實踐與村莊社會整合——以江西省泰和縣東塘村的“上燈”儀式為例[J].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15,(04):71-78.
[6]王習明.對農村民間信仰的幾點思考——以關中等地農村老人“朝廟子”現象為例[J].中國宗教,2008,(02):66-68.
[7]孫敏.民間信仰、社會整合與地方秩序的生成——以關中風池村廟會為考察中心[J].北京社會科學,2017,(01):109-118.
[8]索曉霞.鄉村振興戰略下的鄉土文化價值再認識[J].貴州社會科學,2018,(01):4-10.
[9]林美容.臺灣的神明信仰[J].閩臺文化交流,2010,(01):82-88.
(基金:省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支持項目(2018
03004),作者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