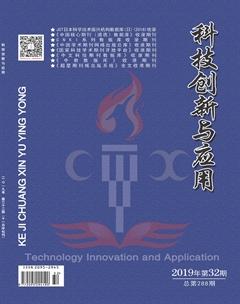科研誠信治理的國際經驗探析
徐巍
摘? 要:科研誠信是科技創新的基石。通過對科研誠信科學內涵的辨析,回顧了我國學術界對于科研誠信治理的經驗與成績,比較了美、英、韓、澳等國科研治理的不同層次探索,提出了“政府型治理體系”、“非政府型治理體系”、“多學科治理體系”與“學術立法治理體系”四種模式,結合我國國情提出了科研誠信治理的國際經驗借鑒。
關鍵詞:科研誠信;科研誠信治理;國際比較
中圖分類號:G32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2945(2019)32-0074-03
Abstract: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is the cornerston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research integrity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academic circles in our country are reviewed the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 of the governan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scientific research to explore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ance, put forward four models--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non-gover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multidisciplinary governance system" and "academic legislation governance system", combining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integrity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科研誠信是科技創新的基石。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加強科研倫理和學風建設,懲戒學術不端,力戒浮躁之風。“加強科研倫理和學風建設”這一表述也是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2018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著力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科研誠信建設新格局,以優化科技創新環境為目標,以推進科研誠信建設制度化為重點,旨在營造誠實守信、追求真理、崇尚創新、鼓勵探索、勇攀高峰的良好氛圍。
1 科研誠信的科學內涵辨析
科研誠信,也被稱為科學誠信或者學術誠信。美國學術誠信研究中心將學術誠信定義為:即使在逆境中仍然堅持誠實、信任、公正、尊重和責任這五項根本的價值觀。2007年,科技部聯合教育部等五部委,建立科研誠信建設聯席會議制度,成立了科學技術部科研誠信建設辦公室,并于2009年編寫《科研誠信知識讀本》,其中定義科研誠信為:“科研誠信也是指科研工作者應實事求是、不欺騙、不弄虛作假,必須恪守科學價值準則、科學精神以及科學活動的行為規范。”《讀本》中還指出,科研誠信涉及四個不同層面的問題:(1)防止科研不端行為(偽造、篡改和剽竊),通知重視和治理科研中的不當行為;(2)制定和落實一般科研活動的行為規范準則以及生命倫理學研究中的相關規章制度;(3)規避和控制科研中由于商業化所引發的利益沖突,同時注意來自政治、經濟發展等方面壓力對科研的影響;(4)強調與科研人員道德品質和倫理責任相關的個人自律,同時關注科研機構自律、制度建設和科技體制改革。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科技界和學術界就開始關注科研道德問題。1981年,鄒承魯院士等人聯名致函《中國科學報》,建議開展“科研工作中精神文明”問題的討論,在科技界引起極大反響。20世紀90年代后期,不少學術期刊和主流媒體開始就學術規范、學術道德等內容,并就此開展廣泛討論。同時,相關政府部門、學術機構和社團組織也逐步設立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專職機構,并出臺有關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的規章制度。1996-1998年,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先后設立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負責組織和領導學部的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工作。之后,教育部(2006年)和科技部(2006年)也先后成立了各自的科研誠信管理部門。1999年底,科技部、教育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中國科學聯合印發了《關于科技工作者行為準則的若干意見》。2006年底,科技部發布《國家科技計劃實施中科研不端行為處理辦法》,標志著科研誠信治理與體制化建設的初見成效。
2 科研誠信治理的國際比較
世界各國對于科研誠信治理在實踐上進行了不同層次的探索,有的針對治理模式的創新、有的針對治理結構的建構、有的針對治理路徑的探索,下面具體概述。
2.1 美國——政府型治理體系
美國科研誠信的治理中主要存在兩種主要力量,一個是由科研人員組成的科學共同體;另一個則是由議會、政府部門等政策制定者組成的政治共同體。1941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批準建立科學研究與發展局,標志著二者合作的“分離模式”的誕生——由政府向科研人員提供資金,科研人員通過科研創新和科技產出為政府提供科研成果,用于軍事或其他領域。基于此種模式,科學共同體在科研誠信治理上占據主導位置,不僅對科學共同體內的成員進行科研誠信的監管,同時掌控科學研究的有效產出。相反,政治共同體的作用則僅限于為科學共同體提供資金以及對于科研產出的評判。隨著20世紀70年代被稱為美國科學界“水門事件”的 “薩默林老鼠免疫案”和“耶魯醫學院事件”的發生,“分離模式”下政治共同體不參與科研誠信的監督的弊端也逐漸顯現。由此可見,分離模式不適當地夸大了科學共同體在科研治理中的作用,而將政治共同體排除在科研治理之外,這使得美國學術界無論是在科研不端問題上還是在科研創新和成果轉化問題上都面臨挑戰,同時也為“合作模式”的誕生提供了條件。
20 世紀80年代開始,二者的合作關系從二戰時期的“分離模式”逐步轉變為“合作模式”。由此,通過“科研誠信辦公室(ORI)”、“技術轉移辦公室(OTT)”等邊界組織實現了政治共同體和科研共同體的密切合作[1],并通過相應的立法和機構保障提供有效的運行機制。大衛·古斯頓在《在政治與科學之間:確保科學研究的誠信與產出率》中提出,科學共同體與政治共同體之間存在委托代理關系,科研誠信與產出率總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持久利益之所在。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公眾也有權參與到科研誠信治理中,因為無論是科研失信行為還是科技成果的轉化都可能涉及到公眾的切身利益[2]。
2.2 英國——非政府型治理體系
20世紀90年代起,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率先出臺《關于科研不端行為指控調差的政策和程序》[3],這也標志著英國建立科研行為指南和科研不端行為規則的開端。此后,英國研究理事會、維康信托基金會、政府科學辦公室、科研誠信辦公室等多家機構紛紛出臺《捍衛良好科學行為》、《良好科研行為指南》、《科學家通用倫理準則》、《科研不端行為調查程序》等多項政策。由此可見,區別于美國以政府為主導的科研誠信監管體系,英國采取了典型的非政府主導的治理體系。英國自上世紀末著手治理學術不端以來,歷經了二十多年的發展,形成了以《維護科研誠信協議》為核心的三重治理結構:科研機構支持和監督其科研人員;基金組織引導和監督科研機構;科研誠信辦公室和其他輔助組織支持三者活動[4],構建了以協商為主的多中心治理結構。相比于美國以政府監管機構處理科研失信行為的模式不同,英國則構建了學術機構主導的、以協商為主的多中心治理結構。
英國非政府型治理體系的優點在于明確了各部門的分工和職責,強化協商溝通,形成了有機統一的治理框架,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重復建設和業務冗余,有利于學術工作和科研治理的溝通與協作。此外,通過接受多種渠道的監管,有助于增強科研誠信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構建了多方聯動的學術生態治理體系,增強了社會公眾對于學術群體的信心和期望,同時也極大地減少了政府在治理科研失信行為所帶來的不必要的行政管理負擔。
2.3 韓國——多學科治理體系
2005年12月,韓國爆發了“黃禹錫案”。2006年1月,韓國政府取消黃禹錫“韓國最高科學”稱號并免去其一切公職,最終于2010年判決黃禹錫有期徒刑18個月,緩期2年執行[5]。以“黃禹錫案”為轉折點,韓國逐步啟動了科研誠信治理模式的制度建設。針對韓國自身學術界存在的成果至上的學術風氣、等級分明的師徒關系、落后封閉的實驗室文化等弊端,主要以借鑒歐美的科研誠信治理經驗為主,通過政府積極主導相關政策法規的制定,在科研誠信治理上也取得一定成效并形成本國特色。
2007年韓國教育部借鑒了美國《科研不端行為防范法》,出臺《科研倫理保障準則》。此準則相比于歐洲國家指南性政策不同,沒有突出科研失信行為的預防和教育等自律手段,而是一部具有強制性的法律法規,對于科研失信行為的審查和出發程序進行了詳細說明。隨后韓國科技部發布了《科研倫理保障準則指南》,對科研誠信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即:在整個科研過程中,不存在疏忽或錯誤知識以及偽造、變造、抄襲等科研失信行為,確保科研成果的客觀性和準確性。2015年,韓國教育部重新修訂了《科研倫理保障準則》,將科研失范行為的邊界擴大至項目的涉及、執行、結果報告和成果發表等多個環節。此外,韓國教育部和韓國研究基金會共同出資成立了韓國大學科研倫理委員會,還在多個學科領域內都頒布了相應的科研誠信行為規范,包括:《學術振興法》(人文社科)、《科學技術基礎法》(理工科)、《生物倫理安全法》(生物醫學)和《著作權法》(文學藝術)等,旨在建立以大學為中心、多學科層級的科研誠信治理共同體[5]。至此,韓國構建了依托人文社科、理工科、生物醫學、文化藝術等四大領域的,統一科研誠信法律框架下的多學科層級的科研誠信治理格局,充分考慮到不同學科特點的差異化分層治理模式,針對學科特征對科研失信行為實現了個性化監管和處置,從而有效地開展了專業化的科研誠信教育。
2.4 澳大利亞——學術立法治理體系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于2007年發布了由國家健康和醫療研究理事會、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作為澳大利亞核心科學基金機構,會同澳大利亞大學聯盟共同起草的《負責任的研究行為準則》。該《準則》作為科研誠信行為的指南,在約束科研人員和科研機構應當遵循的原則和規定的基礎上,針對違反該準則的不端行為提出了明確懲治方案。只要是違反了《準則》,即使是很小的一部分,也要退還來自撥款機構的全部資助。2010年4月,澳大利亞科技部成立了科研誠信委員會,次年初發布了《澳大利亞科研誠信委員會章程》,明確提出科研誠信委員會作為一個獨立組織,負責審查各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內部章程,對各單位的科研失信行為進行程序性監督。此外,參考英國科研評估系統,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建立了本國的科研評估系統,包括:學科評估、資助類型評估和管理政策評估[6]。評估后每年定期發布的《年度評估報告》不僅用作評價各機構及學科科研能力,更是作為爭取各級科研機構經費投入的重要指向性文件。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通過立法的形式,利用法律手段規范科研人員、科研機構的學術行為,強化科研過程參與人員的法制意識,建立了國家層面的宏觀監管制度。澳大利亞的部分大學還設立了預防教育,通過設立課程,科研誠信討論會,入職培訓等等手段來全方面有效地預防科研不端行為的發生。
3 科研誠信治理的經驗探析
第一,明確監管機構責任。當下,我國科研誠信治理體系尚未完善,存在多頭管理的弊端,務必應從機制體制入手,明確各監管機構的責任。例如,在2018年3月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完善科研誠信管理工作機制和責任體系。其中,科技計劃管理部門要將科研誠信要求融入科技計劃管理全過程;教育、衛生健康、新聞出版等部門要明確要求教育、醫療、學術期刊出版等單位完善內控制度;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協要強化對院士的科研誠信要求和監督管理;地方各級政府和相關行業主管部門要積極采取措施加強本地區本系統的科研誠信建設;從事科研活動的各類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是科研誠信建設第一責任主體,學會、協會、研究會等社會團體要發揮自律自凈功能。
第二,加強科研誠信立法。科研誠信治理體系的構建,一方面要積極宣傳倡導,開展多種形式的知識普及和專業教育;另一方面更應該通過立法的形式從根本上進行強制管理。不但需要科研人員弘揚科學精神、恪守誠信規范,以共同的理念和自覺的行動開展自律監管,更要通過法律強制手段規范科研人員與科研機構的科研行為,堅持預防與懲治并舉,堅持自律與監督并重,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保持對嚴重違背科研誠信要求行為嚴厲打擊的高壓態勢,嚴肅責任追究。建立終身追究制度,依法依規對嚴重違背科研誠信要求行為實行終身追究,營造潛心研究、追求卓越、風清氣正的科研環境,形成中國特色科研誠信監管體系。
第三,建立治理信息系統。目前,科技部已會同中國社科院建立完善覆蓋全國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科研誠信信息系統,對科研人員、相關機構、組織等的科研誠信狀況進行記錄。重點對參與各級科技計劃(項目)組織管理或實施、科技統計等科技活動的項目承擔人員、咨詢評審專家,以及項目管理專業機構、項目承擔單位、中介服務機構等相關責任主體開展誠信評價。切實做到全覆蓋、共聯動,借助信息化技術手段,推進科研信用與其他社會領域誠信信息共享,加強科研誠信信息跨部門跨區域共享共用。
第四,保障科研人員權益。全面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推進分類評價制度建設,清理科研四唯(“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將科研誠信狀況以負面清單的形式,作為各類評價的重要指標。徹底告別人才量化指標體系,釋放科研人員主觀能動性和科研內驅力,形成中國特色科技評價體系。從根本上走出科研評價與科研導向的困境,樹立正確的人才評價使用導向,從根本上避免與物質利益簡單、直接掛鉤。堅持評用結合,加大對青年骨干優秀科研人員的扶持力度。秉持遵循科學研究的客觀規律,建立對科研機構的中長期評價制度和動態管理,引導科研人員樹立正確的科研價值觀。
參考文獻:
[1]胡金富,史玉民.美國研究誠信辦公室:歷史演變、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12):47-51.
[2]解本遠,賀曉慧.美國科研治理模式的演變及啟示[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05):68-74.
[3]劉學,等.英國科研誠信體制建設的經驗及啟示[J].科學管理研究,2017,35(06):110-112+116.
[4]馮磊.英國學術不端治理體系的結構及特點研究[J].高教探索,2018(05):69-74.
[5]李友軒,趙勇.“黃禹錫事件”后韓國科研誠信的治理特征與啟示[J].科學與社會,2018,8(02):10-24.
[6]王濤,夏秀芹,洪真裁.澳大利亞科研管理和監督的體系、特點及啟示[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4(11):8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