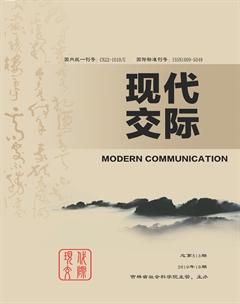《王佛脫險記》與《神筆馬良》異域性對比
王儒鈺
摘要:異域性不單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以同一民間傳說為原型所重構的作品可具有不同的異域性。從人際關系角度對比分析了《王佛脫險記》和《神筆馬良》各自的異域性,并分析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作者的寫作目的不同。尤瑟納爾以法國文化的他者身份重構古代中國文化,基于積極的角度體現異域性;而洪汛濤基于社會主義思想的他者身份重構封建文化,批判封建文化。
關鍵詞:異域 ?王佛脫險記 ?神筆馬良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9)19—0132—02
對于異域的想象向來是文學創作中的重要主題之一。借助對于“他者”的不同幻想程度的描寫,作家在差異性中構建一個想象的異域,反照自己的母文化,同時重新構建自己的母文化。然而,許多研究對于“異域”采取了狹義理解,將“異域性”等同于空間的、地理的異域性,等同于對外國、異民族的描寫;但對于歷時的、歷史性的異域性注重不足,對于作家以本民族不同時代的文化背景的作品(比如當代人寫的以古代為背景的小說),一般沒有足夠重視其中的異域性。本研究認為,同一民族的文化和社會是歷時性的,即使是以本民族文化背景的文學作品,因為歷史條件,作家所處的時代和作品背景的所處時代也會產生異域性——故事的世界對于作者也同樣是“他者”文化。
本研究針對上述不足,對比分析兩篇脫胎于同一民間傳說原型、分別由中外作家創作的短篇小說——法國作家尤瑟納爾的《王佛脫險記》和中國作家洪汛濤的《神筆馬良》,兩篇小說的故事世界對于各自作者的時空都具有異域性。《王佛脫險記》是基于一個道家傳說的再創作(柳鳴九,1987)。它敘述了被皇帝逮捕的老畫家所作的畫突然活了起來、畫家進入畫中世界得以逃生的故事。《神筆馬良》是洪汛濤基于民間傳說創作的寓言童話(李學斌,2011)。敘述了擁有神筆的馬良讓貪婪的皇帝進入畫中世界,從而得以脫險的經歷。本研究選取1955年原始版本,從人際關系角度對比兩者的異域性,并解析造成這兩者異域性異同的原因。
一、兩者人際關系的異域性對比
異域是作者出于各種動機被重新建構的概念,而非模仿。張隆溪(2002)認為,異域更多的是一種審美體驗和再創造。作者的動機和自身經驗對于異域性的形成的作用,比作為基礎的“異質”文化本身的作用更大。洪汛濤作為寫作于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作家,封建制度下的古代中國文化對于他而言是一種異質文化,因為他并非耳濡目染,而是從經過了他人建構的書本中學習得到來,并且經過社會主義思想的過濾;而尤瑟納爾也并非古代中國文化的一分子,她在自己的法國母文化的經驗基礎上反觀中國古代文化。人際關系是根植于文化系統個體間互動的模式和準則,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成分部分,集中體現兩者異域性差異。
《王佛脫險記》中的人際關系的異域性具有兩極化的特質——雖然有帝王絕對專制所導致的壓迫和服從,但更有基于中國傳統人際倫理重構的和諧溫情一面。皇帝和林、王佛之間的關系,以及皇帝和士兵之間的關系是冷色調的,在皇帝面前,“士兵們像女人一樣發起抖來”,這是因為皇權的角色權威對作為權力結構最底層執行者的“士兵”的絕對壓制。但是這種冷酷的人際關系絕非作者構建的重心,作者想象中的古代中國人際關系仍然是以暖色調為主。作者敏銳捕捉到了中國文化中“師徒”這一特有的倫理概念,描寫弟子林心甘情愿地跟隨師父漂泊卻毫無怨言,體現林如何按照中國傳統的師徒倫理居于這種關系的一端:“林沿門乞食來供奉師傅”,這是古代中國賢哲游歷天下時弟子的經典侍奉之舉;對于師長的言談,“林總是謙恭地作出認真聆聽的樣子”。這種“謙恭”聆聽的狀態出于東方傳統的尊師重道,是道德而非制度。而當林聽到皇帝決計殺死師父時,他捍衛師長的反應極其果決,“畫家的徒弟林就從腰間拔出一把缺了口的刀子撲向皇帝”,這舍生取義更是源于中國傳統中對于師長“視之如父”的態度,面對“父”,“子”為之獻身也在傳統觀念中顯得合情合理。這些根源于中國文化的師生關系的特質,和作者的母文化大相徑庭;西方文化中的師生關系從古希臘時代起,就重視辯證思維和相對平等,對于對師長的絕對謙恭并不重視,因而,林的那種“謙恭聆聽”的態度和對師長視之如父的精神,是作者從法國文化這一“他者”身份出發,力圖重構一個她心中的典型的“尊師重道”的古代中國文化的結果,她重構的是一個放大了中國傳統人際倫理中暖色調的一面。
與之相反,《神筆馬良》中的人際關系異域性則是單極化的重構——作者認識到封建制度的專制性和等級秩序,構建了一個冷酷而森嚴的社會,沒有《王佛歷險記》中的暖色調。這里的人際關系是臉譜化的基于金錢的關系,以至于主角馬良無法建立起真正的師生關系——學館的教師看見馬良出于經濟上的弱勢地位,甚至斥責他“窮娃子想拿筆,還想學畫?做夢啦!”,然后將他無情地趕走。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里的師生關系是缺位的,因為被金錢和權勢異化的倫理不允許有高于金錢的關系存在。而故事中的皇帝可以隨意命令馬良作畫,“馬良不肯去,他們把他拉去了”,皇權對于人身自由的踐踏被赤裸裸地暴露了。這里,作者并沒有構建一個“父子”式的傳統東方式的師徒關系或者平等的人際關系,而是構建了赤裸裸基于金錢和權勢關系的人際倫理。這些異化的倫理對于寫作于20世紀50年代的提倡共有和平等的社會主義時期的作者,是一個異域。
簡而言之,《王佛脫險記》中的人際關系既有專制壓迫,又有人際之間和諧溫情的一面,充滿了作者對于中國文化中和諧一面的積極的異域想象;而《神筆馬良》中的人際關系則只有被封建制度所附屬的金錢關系和權勢關系所扭曲的冷漠一面,來源于作者對于封建文化的壓迫人性的負面的異域想象。
二、兩者異域性差異的根本原因
兩者異域性差異的原因是寫作目的的不同。
尤瑟納爾的寫作目的是表達對于古代中國文化的欣賞之情,并且在構建古代中國這一異域的同時,反觀自身的母文化。她以法國文化這一“他者”身份觀察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對于古老東方文明中恭敬與和諧的人際倫理的向往。她藉此來表達對于20世紀初期西方世界過于物質化的反觀。
與之相反,洪汛濤的寫作目的是基于社會主義視角的諷刺和批判封建制度。洪汛濤和封建文化之間有著很遠的心理距離,他深受反對金錢關系和等級制度的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封建時代的中國對于他而言是倫理被金錢和權勢所扭曲的“異域”,因此對等級森嚴的封建思想持批判態度,對迷信金錢和權勢的統治者進行諷刺。
三、結論
《王佛脫險記》和《神筆馬良》基于同一民間傳說,但是在人際關系方面異域性上差別巨大。《王佛脫險記》構建了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諧溫情的人際倫理,而《神筆馬良》基于金錢和權勢的異化的人際倫理這種差異來源于作者不同的寫作目的;基于法國文化的尤瑟納爾表達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贊賞,而基于社會主義思想的洪汛濤表達對于封建文化的批判。
本研究對比了兩部作品的異域性并且揭示了原因,有利于文學研究者更深入地探索中國民間傳說在國外作家和中國作家筆下的差異,也有利于跨文化對比研究。但是,本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因為僅從一個角度異域性開展研究。對于以后的研究,可以從異域性理論入手,深入探討異域性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基礎。
參考文獻:
[1]柳鳴九.尤瑟納爾研究[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2]李學斌.原型結構及其文學意義——洪汛濤經典童話《神筆馬良》的當代解讀[J].蘭州學刊,2011(2):204-206.
[3]張隆溪.異域情調之美[J].外國文學,2002(2):70-74.
責任編輯:趙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