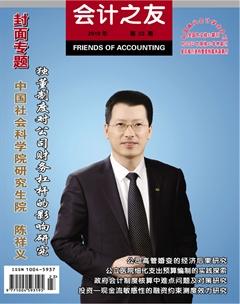企業戰略差異度與稅收規避
周蘭 唐潔寧
【摘 要】 文章以2008—2017年滬深A股上市企業為樣本,分析企業戰略差異度對稅收規避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戰略差異度越大,稅收規避的激進程度越高,即戰略差異度導致的融資約束與管理層私利動機將激勵企業采取更激進的避稅行為;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中戰略差異度對稅收規避的影響更加顯著;稅收征管強度的提升使得企業避稅成本增加,管理層尋租空間減小,從而抑制戰略差異度對稅收規避行為的激勵作用。研究結果拓展了既有文獻對稅收規避影響因素的研究,也為戰略差異度是否影響企業財務決策行為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經驗證據。
【關鍵詞】 戰略差異度; 稅收規避; 產權性質; 稅收征管
【中圖分類號】 F27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9)23-0087-06
一、引言
稅收規避在各個時期、各個國家均普遍存在。企業試圖通過合理避稅手段降低稅負,將原本上繳的現金部分留存于企業內部,從而降低對外部融資的依賴[ 1-2 ]。而管理層為了攫取更多私人利益,很可能利用避稅活動中復雜且不透明的交易或事項做掩護,導致企業內部代理成本增加[ 3 ]。企業如何避稅日益受到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關注,成為國內外的研究熱點。大量研究發現,股權結構、高管激勵及公司治理等因素都會影響企業的避稅行為。但關于稅收規避的影響因素研究,已有文獻并未得到一致結論。同時,已有研究側重關注企業微觀層面的特征與避稅行為之間的關系,卻鮮有文獻從企業戰略層面分析避稅程度的影響因素。
企業戰略是企業實現持續發展和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為了建立不可復制的資源,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占據獨特地位,越來越多的企業采取偏離行業常規的戰略。管理層需要根據戰略變化調整經營活動和財務決策,所以不同的戰略定位將會直接影響企業的財務特征和財務決策行為。已有文獻表明,差異化的戰略將導致更嚴重的內外部信息不對稱[ 4 ]、更高的融資成本[ 5 ]以及更高的現金持有水平[ 6 ]。那么,企業稅收規避行為作為財務決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否也會受到企業戰略特征的影響?本文試圖從戰略差異度①視角出發,考察企業戰略特征對稅收規避行為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不同產權性質和不同稅收征管環境下,企業戰略差異度對稅收規避所起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既可能減輕企業的負擔,提升股東財富[ 7 ],也可能增加代理成本[ 3 ],損害股東價值。因此,如何合理籌劃并降低企業稅負對企業非常重要。而避稅決策作為企業經營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可能受到企業戰略定位的影響。戰略定位作為企業戰略實施的基礎,是基于企業整體而制定的決策。管理層需要根據企業戰略變化調整經營活動和財務決策,以期獲得長期發展和競爭優勢。因此,不同的戰略特征將會影響企業稅收規避的動機和能力。本文將從以下兩個方面具體分析企業戰略差異度對稅收規避行為的影響。
第一,由于偏離行業常規的戰略通常未經檢驗且背離行業經驗和智慧,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需投入更多的成本進行探索與創新,從而有更高的融資需求[ 8 ]。然而,偏離行業常規經驗的戰略導致企業經營風險增加[ 9-10 ],合法性與合理性降低[ 11 ],顯著提升企業獲取外部資源的難度和成本[ 5 ],使得企業不得不依賴內部現金流,從而激勵企業采取稅收規避等內源融資方式。一方面,稅收規避是企業節約大量現金流出的一種重要途徑,可以將原應上繳的現金部分留存于企業內部,降低企業對外部融資的依賴[ 1-2 ]。較高的戰略差異度下,企業經營業績和現金流的波動更為頻繁[ 12-13 ],企業更需要增加現金儲備以預防資金流斷裂的風險。另一方面,隨著企業面臨融資約束程度的增加,稅收規避所節省的現金流出的邊際收益顯著上升[ 14-15 ]。同時,相比于削減研發費用或廣告支出等節約現金支出的方式,稅收規避對企業的長期經營業績和發展潛力的不利影響更小[ 1 ]。因此,戰略差異度較大的企業更愿意采取激進的避稅行為,從而緩解融資約束導致的資金壓力,更好地應對經營過程中的風險。
第二,戰略差異度加劇了企業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4,16 ],降低了稅收規避的風險和成本,同時也引發了代理沖突,從而提高管理層采取激進避稅行為的動機。一方面,當企業戰略偏離行業常規水平時,外部利益相關者難以理解和評估企業的經營決策模式,無法依據行業平均水平準確判斷企業經營狀況[ 17 ]。隨著戰略差異度的增大,企業信息透明度降低,稅收征管部門將更難發現企業的避稅行為,企業避稅的成本顯著降低,這將促使企業稅收規避的動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加,外部投資者在業績評價中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往往將短期業績波動歸結為管理層的無能,由此引發的代理沖突將促使自利的管理層進行在職消費、盈余管理等機會主義行為。管理層采取激進的避稅決策不僅可以保留更多的現金流來攫取私利,而且可以為其機會主義行為提供掩護[ 2 ]。因為稅收規避往往涉及專業的稅務籌劃技術,一般的非專業人士很難洞悉其機理。為了避免被稅務機構發現,管理層會采用復雜且不透明的交易或事項以掩蓋其避稅行為[ 3 ],這些交易活動將會增加企業經營結構與財務的復雜性和模糊性。因此,企業戰略差異度較大時,出于自利動機,管理層采取稅收規避的激進程度越高。基于上述分析,較大的戰略差異度將會增加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據此,提出假設1:
H1:企業戰略差異度越大,稅收規避的激進程度越高。
在我國特殊的金融體系下,由于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政策傾斜,非國有企業獲取外部資金的難度遠大于國有企業,因此面臨更高的融資約束[ 18 ]。基于這一現實背景,在采取偏離行業常規戰略的企業中,非國有企業通過稅收規避緩解資金壓力的動機更為強烈。此外,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往往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督,他們更重視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與個人職業生涯前景[ 19 ],一旦激進避稅行為被發現,管理層需要承擔政治成本和聲譽風險。基于政治前途考慮,管理層更傾向于服從上級政府的指令,并約束自身機會主義行為,因此戰略差異度對企業稅收規避行為的影響在國有企業中更弱。綜上分析,與國有企業相比,非國有企業的避稅程度更高,因此戰略差異度對企業稅收規避的影響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加明顯。據此,提出假設2:
H2:相對于國有企業而言,非國有企業中戰略差異度對稅收規避行為作用更加顯著。
稅收征管作為政府稅收政策以及稅務稽查的集中體現,在改善公司治理的過程中發揮著外部監督的作用[ 20 ]。稅務征管部門可以通過檢查公司賬目掌握其生產經營等各方面信息②,從不同方面印證企業的真實經營狀況。隨著稅收征管力度的提升,稅務征管部門發現企業稅收規避行為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從而提高企業避稅活動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企業面臨戰略差異度帶來的融資約束,避稅成本的上升仍會抑制企業采取激進稅收規避行為。與此同時,一旦信息不對稱,滋生的管理層利益侵占行為被稅務機關發現,管理層不僅面臨經濟處罰和股東的訴訟,而且會遭受職業聲譽損失。所以說,對于戰略差異度較大的企業而言,若所在地區的稅收征管力度增加,管理層尋租的空間減小,利用復雜的稅收籌劃技術等手段掩蓋避稅行為的可能性隨之降低,從而抑制管理層的激進避稅決策。據此,提出假設3:
H3:地區稅收征管強度越大,企業戰略差異度與稅收規避的正相關關系越弱。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我國2008—2017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我國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新的企業所得稅制度,稅率、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以及稅收征管等方面與之前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因此,為了確保稅收規避度量的前后一致,本文選擇2008年為樣本的研究起點,所使用的財務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名義稅率來自WIND數據庫,各地稅收收入、行業產值、進出口總額以及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在具體的樣本選擇過程中,筆者進行了如下處理:(1)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ST、PT等財務狀況異常的公司;(3)剔除所得稅信息披露不完全、當期所得稅費用小于等于零以及名義稅率為0的樣本;(4)由于我國西藏自治區的稅收優惠政策免除了企業的地稅,為了確保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剔除西藏自治區的樣本;(5)剔除其他數據缺失的樣本。經過篩選,最終得到15 742個有效樣本。同時為了避免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的水平上進行了Winsorize處理。
(二)主要變量設計
1.稅收規避的衡量
Hanlon和Heitzman[ 21 ]的研究梳理了國外文獻中衡量企業稅收規避的主要方法,目前廣泛采用的有兩類:一是基于有效稅率的度量,二是基于會計—稅收差異的度量。由于我國稅收政策同國外有較大區別,國內上市公司享受著廣泛的稅收優惠,各自的名義稅率也不盡相同,使得有效稅率無法準確反映企業的避稅程度。為了提高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借鑒國內外文獻的做法,采用Desai和Dharmapala[ 22 ]提出的消除應計利潤影響后的會計—稅收差異,這一指標在會計—稅收差異的基礎上考慮了盈余管理的影響,通過控制操控性應計來分離盈余管理行為導致的會計—稅收差異。具體估算過程如下:
BTD=?琢TACC+?滋+?孜 ? (1a)
TA=?滋+?孜 ?(1b)
其中,BTD=(稅前會計利潤-應稅收益)/期初總資產,應稅收益通過所得稅費用和企業適用稅率估算得出;TACC為經上期總資產調整后的總應計利潤,總應計利潤為凈利潤減去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的差額;?滋+?孜即無法用應計利潤解釋的那部分會計—稅收差異,用于度量企業進行稅收規避的程度,記為TA。
2.戰略差異度的衡量
本文所指戰略差異度,即企業戰略偏離行業平均水平的程度,借鑒相關學者的做法,從以下六個維度來衡量企業戰略差異度:廣告投入(銷售費用/營業收入)、資本密集度(固定資產/員工人數)、固定資產更新程度(固定資產凈值/固定資產原值)、研發強度(無形資產凈值/營業收入)、管理費用效率(管理費用/營業收入)、財務杠桿[(短期借款+長期借款+應付債券)/所有者權益賬面價值]。每一個指標均反映了企業戰略的一方面,六個指標共同反映了企業的總體戰略。在指標計算過程中,考慮到我國企業較少單獨披露廣告宣傳支出和研發支出,參照葉康濤等[ 16 ]學者的做法,本文分別采用銷售費用和無形資產凈值來近似替代。具體計算方法如下:(1)按年計算出每個行業中各企業的六個指標值。(2)求出每個指標值與當年行業平均值的差額,再將差額除以標準差進行標準化之后取絕對值,得到企業在每個維度上偏離行業平均水平的程度。(3)計算出每個企業標準化后六個指標的平均值,即得到戰略差異度的指標DS。
3.稅收征管的衡量
本文借鑒曾亞敏和張俊生[ 20 ]等的方法,采用各地實際稅收收入與回歸模型估計的預期稅收收入之比來反映當地稅務機關稅收征管的強度。具體估計模型如下:
其中,為各地區當年末稅收收入除以當年國內生產總值;IND1和IND2分別代表各地區當年末的第一產業產值和第二產業產值;OPEN表示各地區當年的進出口總額,反映了各地區的開放程度。通過模型回歸的系數,可以計算出各地區當年的預期 。然后,用實際的 與預期的 的比值表示稅收征管強度(TE)。最后,本文根據稅收征管強度的中位數,將樣本企業分為高低兩組,比值高于中位數TE取1,否則取0。
(三)模型設定
為了控制稅收規避的各種影響因素,本文設置了如下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資本密集度(PPE)、無形資產比例(INTANG)、存貨密集度(INVENT)、盈利能力(ROA)、成長能力(Growth)以及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irst)。同時,模型中控制了行業和年度虛擬變量。綜上所述,本文涉及的主要變量定義如表1。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從全樣本來看,TA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均接近于0,標準差為0.027,說明樣本企業存在稅收規避行為,且各企業間稅收規避的激進程度存在差異。戰略差異度DS的平均值為0.614,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1.76和0.189,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戰略差異度整體水平較高,其中個別企業經營戰略與行業常規模式相差較大。稅收征管強度TE的平均值為0.405,標準差為0.491,表明我國稅收征管力度普遍較小,且各地區之間的征管強度存在較大差異。描述性統計反映樣本企業其他方面基本分布特征與同類研究大致相同。
(二)相關性分析
表3列示了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檢驗,從表中可以看出,稅收規避的度量指標與戰略差異度變量顯著正相關。這一結論初步表明,企業經營戰略很可能影響其避稅行為,但確切結論還需要通過多元回歸進一步驗證。此外,控制變量的相關系數基本低于0.5,表明模型設定不太容易出現多重共線性的問題。
(三)多元回歸結果分析
通過控制影響稅收規避的其他公司特征及行業、年度屬性,本文進一步進行嚴格的多元回歸分析來檢驗企業稅收規避激進程度是否會受到戰略差異度的影響。表4列示了戰略差異度對稅收規避行為的影響,以及在此過程中與產權性質、稅收征管強度的交互關系。
表4中第(1)列報告了戰略差異度對稅收規避激進程度的回歸結果。本文采用TA衡量企業稅收規避的激進程度,該指標與戰略差異度的回歸系數為0.003,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在控制其他相關因素下,企業戰略差異度越大,稅收規避的激進程度越高,這一結論支持本文的假設1。其他控制變量的結果與現有文獻基本一致。
表4第(2)列中,將DS與State交乘,研究稅收征管對戰略差異度與激進稅收規避行為間關系的影響。可以發現,DS×State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非國有企業中,戰略差異度和激進稅收規避行為正相關關系更強,結論支持假設2。由此表明,當企業面臨戰略差異度帶來的較高融資約束水平時,非國有企業通過稅收規避緩解資金壓力的動機更強烈。
表4第(3)列中,將DS與TE交乘,研究稅收征管對戰略差異度與激進稅收規避行為間關系的影響。可以發現,DS×TE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企業所在地區稅收征管的力度越高,企業戰略差異度和激進稅收規避行為正相關關系越弱,結論支持假設3。由此表明,稅收征管不僅提高了企業的避稅成本,而且降低了管理層利用激進避稅行為來獲取私人利益的可能性,從而抑制企業激進的稅收規避行為。
(四)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以下檢驗:(1)為了避免企業個體變量遺漏對結論的影響,采用固定效應回歸的方法驗證結論的穩健性。控制了企業個體之間的差異后,檢驗結果與前文一致。(2)由于廣告投入和研發強度兩個維度的數據無法直接獲取,利用銷售費用和無形資產凈值進行替代可能對本文結論產生影響。筆者借鑒Tang等[ 12 ]的方法,剔除這兩個維度,重新構建戰略差異指標。檢驗結果支持前文結論。(3)借鑒Manzon和Plesko[ 23 ]的方法,利用經上年總資產調整后的賬面稅收差異衡量稅收規避的激進程度重新檢驗,該值越大表明企業實施稅收規避的可能性越大。筆者對實證部分的所有內容采取新的指標進行回歸分析,研究結論保持不變。
五、結論
本文以2008—2017年滬深A股上市企業為樣本,研究了企業戰略差異度對稅收規避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1)企業戰略差異度與稅收規避行為的激進程度呈顯著正相關關系;(2)企業戰略差異度與稅收規避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3)企業所在地區的稅收征管強度越大,戰略差異度與稅收規避激進程度的正相關關系越弱。通過更換替代變量和估計方法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發現上述結論仍然可靠。
本文的研究不僅豐富了有關企業戰略和稅收規避的文獻,而且深化了對稅收征管治理效應的理解。本文的結論表明,企業在進行合理的稅收籌劃時,應當更關注自身的經營戰略,以便應對戰略差異可能導致的融資約束問題。同時,鑒于企業戰略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稅收規避策略,稅務機構等監管方應對企業的戰略信息予以更多的關注,并加大稅收征管強度,充分發揮公司治理的外部監督作用,從而更好地保護投資者利益,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EDWARDS A, SCHWAB C, SHEVLIN T.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cash tax savings[J].Accounting Review,2016,91(3):859-881.
[2] 后青松,袁建國,張鵬.企業避稅行為影響其銀行債務契約嗎: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考察[J].南開管理評論,2016,19(4):122-134.
[3] 葉康濤,劉行.公司避稅活動與內部代理成本[J].金融研究,2014(9):158-176.
[4] CARPENTER M A. The price of change:the role of CEO compensation in strategic variation and deviation from industry strategy norm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26(6):1179-1198.
[5] 王化成,張修平,侯粲然,等.企業戰略差異與權益資本成本:基于經營風險和信息不對稱的中介效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7(9):99-113.
[6] 李高波,朱丹.戰略異質性與現金持有:基于預防動機的實證檢驗[J].東岳論叢,2016,37(8):81-99.
[7] MCGUIRE S T,WANG D,WILSON R J. Dual class ownership and tax avoidance[J].Accounting Review,2014,89(4):1487-1516.
[8] 孫健,王百強,曹豐,等.公司戰略影響盈余管理嗎?[J].管理世界,2016(3):160-169.
[9] SYDNEY F,DONALD C H. Top-management-team tenure and ?organizational outcomes: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3):484-503.
[10] HILLER ?N ?J, HAMBRICK ?D ?C. Conceptualizing executive hubris:the role of (Hyper-)core self-evaluation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4):297-319.
[11] DEEPHOUSE D L. To be different,or to be the same?It's a question (and theory) of strategic balanc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2):147- 166.
[12] TANG J, CROSSAN M, ROWE W G. Dominant CEO,deviant Strategy,and extreme 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role of a powerful board[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1,48(7):1479-1503.
[13] 陳收,肖咸星,楊艷,等.CEO權力、戰略差異與企業績效:基于環境動態性的調節效應[J].財貿研究,2014(1):7-16.
[14] FAULKENDER MRONG W.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y and the value of cash[J]. Journal of Finance,2006,61(4):1957-1990.
[15] 王亮亮.金融危機沖擊、融資約束與公司避稅[J].南開管理評論,2016,19(1):155-168.
[16] 葉康濤,董雪雁,崔倚菁.企業戰略定位與會計盈余管理行為選擇[J].會計研究,2015(10):23-29.
[17] 何熙瓊,尹長萍.企業戰略差異度能否影響分析師盈余預測:基于中國證券市場的實證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8,21(2):149-159.
[18] LU Z, ZHU J, ZHANG W. Bank discrimination, holding bank ownership,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2,36(2):341-354.
[19] 張琛,劉銀國.融資約束與民營企業稅務自利行為研究[J].經濟管理,2016,38(3):113-123.
[20] 曾亞敏,張俊生.稅收征管能夠發揮公司治理功用嗎?[J].管理世界,2009(3):143-151.
[21] HANLON M,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 [J].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10,50(2-3):127-178.
[22] DESAI M,DHARMAPALA D.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79(1):145-179.
[23] MANZON G B,PLESKO G A. The 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and tax reporting measures of income[J].Tax Law Review,2002,55(1):176-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