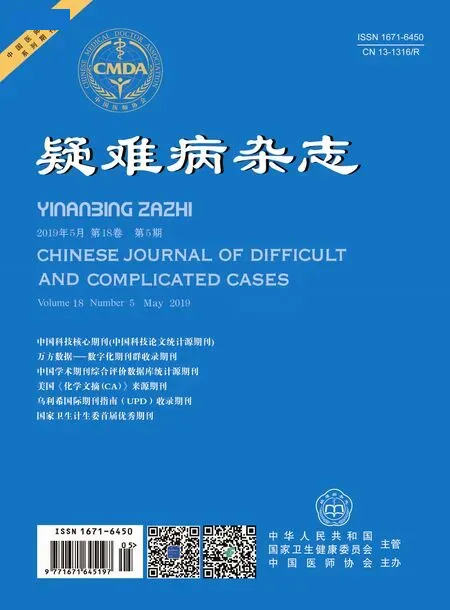自噬及其在腎纖維化中的作用研究進展
吳承,朱少明綜述 程帆審校
腎纖維化(renal fibrosis)是由各種致病因素導致的腎臟結構進行性損壞和功能逐漸喪失的病理生理過程,是所有進展性慢性腎病(CKD)發展為終末期腎病的共同途徑。其特征為細胞外基質(ECM)在腎小管間質中過度沉積。腎纖維化的發病機制是初始損傷后發生的一種失敗或適應不良的腎臟修復過程,它涉及腎臟中幾乎所有細胞類型的相互作用和協調[1]。腎纖維化是一個很難逆轉的病理過程,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自噬(autophagy)是細胞通過形成自噬體和自噬溶酶體對細胞質組分進行降解的過程。自噬除了具有分解代謝功能外,還是細胞對應激的一種適應性反應和保護機制,在各種疾病包括纖維化疾病的發病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近年來,多項研究證明自噬在腎纖維化疾病中起作用[2-3],根據細胞或組織類型和病理狀態,自噬可以促纖維化或抗纖維化[4-5]。這些研究表明誘導自噬可能參與腎纖維化的腎保護機制,但其相關調節機制尚未明確。因此,研究自噬及其在腎纖維化中的作用對于尋找腎纖維化的有效治療靶點尤為必要。
1 自噬的概念及分類
自噬指細胞在各種應激條件下,通過形成雙層膜結構的囊泡(即自噬體),包裹細胞內損傷或變性的細胞器、蛋白質以及入侵的病原體等物質,并運送到溶酶體中進行降解的生物學過程。其過程大致分為誘導、核化、自噬前體的延伸、自噬體的成熟等4個階段,它的典型特征是在細胞質中形成自噬體。自噬分為生理條件下的基礎自噬以及應激條件下的誘導型自噬[6]。生理狀態下,細胞通過自噬降解損傷、變性、衰老和失去功能的細胞、細胞器及各種生物大分子,實現細胞內物質的分解代謝和循環利用。病理狀態下,自噬作為細胞的一種保護機制可以清除入侵的病原體,并可保護細胞免受毒性物質的損傷。根據功能和細胞內底物進入溶酶體的途徑不同,又可將自噬分為巨自噬(macroautophagy)、微自噬(microautophagy)、分子伴侶介導的自噬(chaperone-mediated autophagy,CMA)等3種主要類型[7]。巨自噬是研究最為廣泛和深入的類型,通常所說的自噬即指巨自噬。微自噬是指直接通過溶酶體膜隨機突出和內陷吞噬細胞內容物的一種非選擇性降解過程。分子伴侶介導的自噬是由分子伴侶蛋白如熱休克蛋白70(HSP70)識別含有特定序列五肽基的可溶性蛋白底物并與之結合,然后經過單獨跨膜轉移將這些底物運送到溶酶體內降解,但不能降解細胞器,此類型自噬只存在于哺乳動物細胞中,而且具有高度選擇性。這3種類型的自噬雖然具有形態上的差異,但都達到了將內容物轉運到溶酶體降解和循環利用的目的。
2 自噬過程中的分子機制
2.1 自噬的誘導 自噬的全過程受自噬基因(autophagy-related genes,ATGs)和自噬蛋白(autophagy-related proteins,Atgs)的高度調控。自噬蛋白在哺乳動物細胞中表示為ATGs,在酵母菌中表示為Atgs。細胞在內外某些不利因素如缺氧、饑餓、受損蛋白質蓄積、高溫、細菌入侵等的誘導下,其平時處于抑制狀態的自噬過程被啟動[8]。目前發現有30多種自噬基因,其中與誘導自噬密切相關的是ULK1復合物(ULK1是ATG1在哺乳動物細胞中的同源蛋白)。ULK1復合物在正常狀態下與雷帕霉素靶蛋白復合物1(mTORC1)結合,當細胞受雷帕霉素作用或缺乏營養時,ULK1復合物與mTORC1解離而活化[9],或當細胞處于其他應激狀態時通過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被激活[10]。活化的ULK1使ATG13和FIP200磷酸化,形成ULK1/2-ATG13-FIP200復合物,將其他自噬蛋白轉運到吞噬泡組裝位點(phagophore assembly site, PAS),并在此生成新月形的自噬前體膜[11]。
2.2 自噬前體的核化 繼自噬蛋白之后,下一個被募集到PAS的是含有ATG14的磷脂酰肌醇三磷酸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PI3K由PIK3C3/Vps34、PIK3R4/P150和Beclin-1組成,其主要通過與Beclin-1相互作用的蛋白質發揮調控作用,參與核化過程[12]。跨膜蛋白ATG9和液泡膜蛋白1(VMP1)在核化階段發揮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形成自噬前體膜所需的原料主要為線粒體、內質網、高爾基體的膜和質膜。ATG9在介導這些供體細胞器為自噬體前膜的形成供給原料過程中起關鍵作用[13]。VMP1則通過其ATG結構域與Beclin-1的BH3結構域相互作用,將PI3K募集至自噬前體膜[14]。同時,活化的ULK1使Beclin-1和ATG14L磷酸化來增強PI3K的活性[14]。PI3K將磷脂酰肌醇(phosphatidylinositol,PI)磷酸化轉變成磷脂酰肌醇三磷酸(PI3P)[15],從而使自噬前體膜經過核化成為杯狀結構的吞噬泡(phagophore)即自噬前體。
2.3 自噬前體的延伸 自噬前體的延伸需要2個泛素樣(ubiquitin-like,UBL)蛋白系統的參與。第1個泛素樣蛋白系統是ATG12。ATG12在E1激活酶ATG7和E2結合酶ATG10的作用下依次與ATG5和ATG16結合形成ATG12-ATG5-ATG16復合物[16],該復合物與吞噬泡膜特異性結合,促進吞噬泡的延伸。第2個泛素樣蛋白系統是LC3。ATG4將LC3前體切割成LC3-I,最初存在于細胞質中。隨后LC3-I依次與ATG7和ATG3結合,并由這2種自噬蛋白加工處理,然后與磷脂酰乙醇胺(phosphatidylethanolamine,PE)耦聯,形成脂質形式的LC3-Ⅱ。LC3-Ⅱ結合于自噬體膜上,直至自噬體與溶酶體結合,是自噬體膜的特征性標志[17]。另外跨膜蛋白ATG9的轉運能力和多聚化對自噬體的形成是必需的,在自噬前體膜的延伸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8]。
2.4 自噬體的成熟 自噬前體在延伸的過程中不斷包裹胞漿中的受損蛋白質及異常細胞器,最終在邊緣融合成為密閉的自噬體(autophagosome),自噬體再與內涵體或溶酶體相互融合,成為自噬溶酶體(autolysosome)。該過程中,自噬體向溶酶體的轉運依賴于微管,而自噬體與內涵體的融合需要VTI1B蛋白的參與[19]。紫外線抵抗相關基因(ultraviolet radiation resistance-associated gene,UVRAG)蛋白可以與PI3K復合物結合,并可以激活GTPase RAB7,GTPase RAB7可以促進自噬體與溶酶體的融合[20]。自噬溶酶體形成后,其中包裹的內容物被溶酶體水解酶降解,生成新的氨基酸、脂肪酸、核苷酸等小分子,供機體重新利用[11]。
3 自噬的調控
自噬是一個高度保守的過程,由許多不同的調節因子控制。在介導自噬的多條信號通路中,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Beclin-1、P53作為它們的交叉點,對自噬的調控起關鍵作用。mTOR是一種絲氨酸和蘇氨酸激酶,由對雷帕霉素敏感的mTORC1和對雷帕霉素不敏感的mTORC2兩種功能性多蛋白復合物組成,在調節細胞生長、蛋白合成、代謝和細胞死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1]。mTOR的上游是PI3K-Akt-mTORC1途徑,其最顯著的特征是調控細胞增殖[22]。Ⅰ型PI3K是一個信號傳感器,它接收上游生長因子信號,并通過3-磷酸肌醇依賴性激酶1 (PDK1)促進Akt(蛋白激酶B)的磷酸化。Akt磷酸化后可激活mTORC1,并最終抑制自噬。mTOR的下游是ULK復合物,由Atg13 、ULK1/2和FIP200組成,這些組分都是啟動自噬體形成所必需的[9]。在正常代謝條件下,mTORC1使Atg13磷酸化,阻止ULK1、ULK2和FIP200的結合,從而抑制自噬。在機體能量缺乏時,AMPK被激活,從而抑制mTORC1和激活ULK復合物,啟動自噬體的形成[9-10]。ULK1復合物的調節信號對自噬的進展是至關重要的,這些信號啟動Vps34與自噬啟動子Beclin-1結合,形成Beclin-1復合物。Beclin-1復合物募集其他ATG蛋白定位于自噬前體膜,促進結合位點的形成和自噬蛋白的結合,并驅動自噬體形成的早期步驟。Beclin-1的功能可被不同的結合配體抑制或激活,例如被Bcl-2抑制和被UVRAG激活[23]。此外,腫瘤抑制蛋白P53在細胞發育中具有多種調節功能,包括誘導或抑制自噬。P53在自噬中的作用是位置依賴性的[24],位于細胞核內的P53通過激活靶基因(如DRAM)誘導自噬,而位于細胞質中的P53則以細胞周期依賴性方式抑制自噬,但其抑制自噬的機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4 自噬與腎纖維化
腎纖維化是腎臟遭受內外多種致病因素的刺激,發生固有細胞損傷和大量膠原聚積,造成腎實質硬化和瘢痕形成,最終導致腎功能完全喪失的一種病理生理改變。其發生機制的主要特征是細胞外基質(ECM)的異常沉積[1]。在進行性腎臟疾病中,無論初始病因如何,腎纖維化是終末期腎病(ESRD)的共同途徑。在體外和體內研究中已經表明,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的上調在腎纖維化的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其中TGF-β1是其最豐富的同種型,已被確立為腎纖維化的中樞介質[2]。TGF-β1可通過Smad3依賴性或非依賴性機制誘導細胞外基質(如Ⅰ型膠原蛋白和纖維連接蛋白)的產生,也可通過抑制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和誘導MMP的天然抑制劑即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劑(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TIMP)來抑制細胞外基質的降解[3]。最近研究表明,TGF-β1可調節自噬,而自噬可調節與腎纖維化相關的信號通路,如腎小管間質纖維化、腎小球硬化和糖尿病腎病[25-26]。在腎纖維化中,TGF-β1是一種具有雙重功能的多效細胞因子,既能誘導膠原蛋白合成,又能誘導自噬和促進膠原蛋白的降解[2]。膠原蛋白合成和降解之間的平衡對于維持組織穩態至關重要。并且,TGF-β可以通過PI3K/Akt激活mTOR通路,因此它可能對自噬起激活和抑制的雙重作用,這可能取決于特定的細胞類型和環境[3]。有研究表明,自噬的上調和下調都可能影響腎纖維化的轉歸和發展[4,27]。由此可見,自噬對腎纖維化的作用可能是多方面的和細胞特異性的。
5 自噬在腎纖維化中的作用
5.1 自噬抗腎纖維化的作用與機制 自噬可抑制腎纖維化,并且是維持腎臟和系膜細胞中細胞外基質穩態所必需的。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自噬抑制腎纖維化的機制主要是通過促進活性TGF-β1和Ⅰ型膠原蛋白(Col-Ⅰ)的降解[2]。TGF-β1是腎纖維化的有效誘導劑,可誘導細胞外基質的產生,包括膠原蛋白和纖維連接蛋白,其過度生產和逐漸積累是腎纖維化的標志。同時,TGF-β1也是自噬的重要誘導物,在體外培養的人腎近曲小管上皮細胞(HK-2)中,TGF-β1誘導自噬體的積累和自噬蛋白LC3的轉化,從而促進成熟TGF-β1的降解來抑制腎纖維化的進展[28]。并且,LC3介導的自噬可降解腎小管上皮細胞(RTEC)中的成熟TGF-β,從而減少TGF-β分泌并抑制由單側輸尿管梗阻(UUO)和腎損傷誘導的腎纖維化。此外,自噬蛋白Beclin-1亦有助于防止腎臟中膠原蛋白的過度沉積[28]。在腎纖維化的發展過程中,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系膜細胞(MC)。在腎損傷和進展性腎病過程中,系膜細胞進行增殖并產生過多的細胞外基質,膠原蛋白是細胞外基質的主要成分,Col-Ⅰ是與纖維化相關的主要類型。TGF-β1誘導的腎小球系膜細胞自噬,可通過降解細胞內Col-Ⅰ減少細胞外基質的產生和防止不溶性前膠原蛋白的過度積累[5],從而抑制腎纖維化。另有研究發現,自噬還可保護腎小管細胞免受環孢霉素A(CsA)誘導的凋亡[29],明顯減輕腎功能障礙。除腎小管細胞外,腎損傷過程中誘導的自噬可保護系膜細胞免于凋亡,說明自噬不僅可保護上皮細胞,也可保護間充質細胞。此外,在自噬的調節因子中,mTOR抑制劑抗纖維化作用的相關研究表明,雷帕霉素抑制mTORC1信號通路對糖尿病腎病具有較強的腎臟保護作用[30-31]。但mTOR抑制劑抗纖維化作用的機制主要是由于其對自噬的間接誘導作用,還是由于其抗增殖活性,目前尚存在爭議。
5.2 自噬促進腎纖維化的作用與機制 自噬不僅可以抑制腎纖維化,也能促進腎纖維化。例如,在UUO導致的腎纖維化小鼠模型研究中,持續激活腎小管細胞自噬促進腎纖維化[4]。自噬促進腎纖維化的機制主要是通過誘導腎小管萎縮和分解[32]。在腎纖維化中,自噬和腎小管萎縮的聯系最初也是在單側輸尿管梗阻的動物研究中提出的。研究表明,自噬在阻塞的腎小管中被激活,表現為自噬體積聚、Beclin-1表達增加和LC3-Ⅰ向LC3-Ⅱ的轉化[4]。這些變化伴隨著自噬溶酶體的增加和活性增強,進一步表明在阻塞的腎小管中誘導的自噬增強。伴隨著自噬,在阻塞的腎小管中也誘導了腎小管細胞凋亡。重要的是,腎小管萎縮的發展與自噬和凋亡呈時間依賴性,提示自噬可能與細胞凋亡協同作用,誘導腎小管萎縮和腎單位喪失[4]。在類似研究中,Koesters等[33]通過在腎小管中過表達TGF-β1的四環素控制的轉基因小鼠模型研究發現,TGF-β1的持續表達在腎小管細胞中誘導自噬,具有自噬特征的腎小管塌陷,細胞碎片填充殘留腔。這些變化與廣泛的腎小管周圍纖維化有關。這種退化變性的細胞其細胞核顯示正常染色,未見表示凋亡的TUNEL染色陽性。總之,這些結果表明自噬是TGF-β1誘導的腎纖維化中腎小管萎縮和分解的主要原因。除該機制外,另有研究表明,雷帕霉素激活自噬可誘導促纖維化信號傳導級聯效應[34];而不受雷帕霉素直接影響的mTORC2/Rictor信號通路是TGF-β誘導的肌成纖維細胞活化的重要下游分支,該通路的激活高度促進腎纖維化的進展[35]。此外,通過TGF-β的正向前饋機制起作用的活性氧(ROS)是細胞應激中自噬的有效激活劑,其主要通過抑制mTOR介導的途徑起作用[36]。這表明自噬可通過激活非Smad信號通路(包括ROS的產生)促進纖維化。但是,自噬在腎纖維化中的病理生理學影響仍需要進一步研究來闡明。
6 展望
自噬作為細胞在應激狀態下的一種適應性反應和保護機制,在機體許多生物學過程中起重要作用。自噬的失調是導致多種疾病包括腎臟疾病的發病機制。已有研究表明,自噬失調與腎纖維化疾病密切相關,并支持自噬是一種細胞保護機制的觀點。自噬是腎損傷中應激適應性反應不可缺少的機制,通過清除蛋白聚合物和受損細胞器,以及負向調節和防止腎臟中基質蛋白的過量積累,促進細胞存活和抗纖維化。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自噬促進腎纖維化。自噬在腎纖維化發病機制中的作用可能是多方面和復雜的。基于目前關于自噬在腎纖維化中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在未來的研究中,有必要進一步加深對自噬的機制和生理功能的認識,確定自噬是否可能成為預防或減輕腎纖維化發病機制的有效治療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