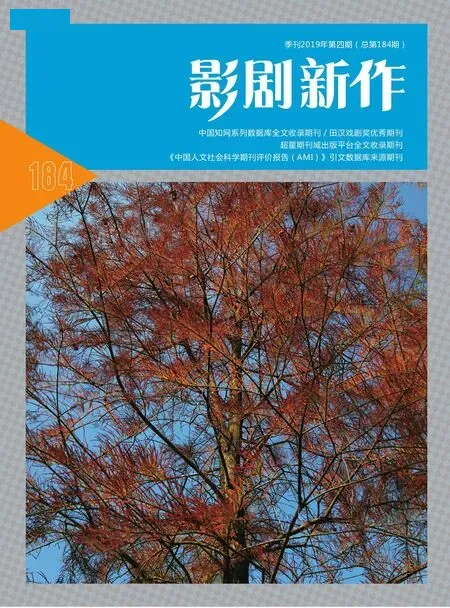從多媒體舞臺劇《華山美少年》看對傳統神話的現代敘述
陳燕華
陳燕華:江西省藝術研究院
責任編輯:吳建軍
沉香劈山救母是一個有著悠久敘述歷史的神話故事,其早期雛形來自于唐代《廣異記》“華岳神女”篇,講的是華岳三娘與書生私自結合的愛情故事;至宋元時期這個故事的情節進一步豐富,一方面加入“劉錫趕考”“落弟”“高中”以及“招婿”等反映時代特點的情節,另一方面還加入兩人之子“沉香出生”“繼母楊氏舍己子救沉香”“沉香尋母救母”等附屬性情節,如宋代戲文《劉錫沉香太子》、元雜劇《劈華山救母》《沉香太子劈華山》等,已初具相對完整的故事形態和敘事結構;明代以后,隨著民間世俗寶卷故事的流行,其和傳統戲曲結合,開始形成獨特的《沉香寶卷》故事,其中沉香救母情節的地位逐漸上升,成為與三娘和劉錫愛情故事地位相當、具有獨立性的回合;到了清代,因寶卷故事強調宗法人倫的倫理教化要求的進一步突出,《沉香寶卷》中沉香的敘事地位又一次拉升,劉錫和三娘的愛情抗爭部分的情節弱化,劉錫再婚楊氏等情節亦被刪去,而敘事主題也由原來的愛情故事發展為孝子故事,這一變化基本奠定了我們今日所知沉香救母故事的主要形態和結構。
可以說,所有神話故事的成功,多多少少都是因為其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它們所處時代的某種共同的人類情感。沉香救母的故事,從古說到今,每一次成功的改編,始終是因為它能迅速地捕捉與反映時代思潮與觀念的變化,并將其融入故事文本之中,使其與人們自身現實經驗和文化價值認同相符,也只有這樣的敘述才能擁有撥動人們心弦的力量。
繼承了沉香故事基本主題和框架的話劇《華山美少年》還能不能打動今日的現代人?還能不能在兩者之間找到情感的共振點?依筆者看來很難。《華山美少年》在故事結構上相比清代寶卷已有所改變,且這種改變明顯受時代較為接近的動畫改編電影《寶蓮燈》的影響,如加入“部落缺水”“沉香幫助部落打敗哮天犬而重獲水源”等現代觀眾容易辨識的情節。但其思想內核仍繼承了清代寶卷時期的特點,如以沉香的孝道為統領整個故事的立足點,而反映劉彥昌與三圣母的愛情以及劉彥昌本人經歷的故事地位則基本無足輕重。一如電影《寶蓮燈》的平庸,電影沒有克服的缺陷在此劇中也仍然沒有改變,如人物扁平單一沒有鮮明的性格特征、語言平淡、情感表現無說服力等等,正面人物的好、反面人物的壞,全都直白地寫在了臉上;而最主要的還是此劇在思想上仍固守時代久遠的觀念與認識,未能從清代寶卷所依循的傳統倫理規范中越出一絲半步,做出有價值的現代意義上的思考與拓展。總體來說,雖然《華山美少年》講述故事的形式從傳統的戲曲、寶卷轉變為現代的話劇,但其精神內質并未做出相應的改變,這仍是對傳統神話故事做出的一次毫無新意的重述。
在筆者看來,貫穿于沉香救母故事的兩個最核心的命題無非兩個:代際關系和個體的成長,如果對這兩個主題不能做出任何有價值的表現,那么這部話劇不能說是成功的。而在這個傳統神話故事的外殼之下如何表現以上兩個主題,肯定不是運用清代人的大腦與情感,而必須要運用現代人的大腦與情感。要想寫出現代人愛看的劇,必須要直面當下,找到現代人思想的焦點、情感的痛點。只有這樣,才能使這個古老的故事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在這一點上需要提到另一個較為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神話改編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這部電影取得了商業上的極大成功并非毫無理由,首當其沖的即是:同樣是對代際關系和個體成長的表現,《哪吒之魔童降世》做到了讓哪吒從一個古代人蛻變為一個現代人。在神話中,哪吒本是一位由本能驅使的反叛式英雄,雖熱血但卻魯莽而簡單,而在電影的處理中既保留了哪吒原有的性格特征,同時又顛覆性而又順理成章地從中提煉出了“做自己的英雄”這一主題,講述了哪吒這一獨特心靈自我成長的過程。這種成長的驅動力不是來自于外在的道德說教,而是對自我的一種痛苦粹煉,以及粹煉之后的重生,凸顯了是人是魔都是一種自我選擇,而不是天注定的主題。經歷了這一系列轉變之后,哪吒已不是我們印象中的“那一個”哪吒,他變成了“魔童”,是一個可以打動我們的現代人。也只有當下的現代人才能理解這一個哪吒,他所經歷的困惑與掙扎,可能也是當下這一代人所經歷的。在對代際關系的表現上,《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沒有落入傳統窠臼,時刻把一個“孝”字掛在嘴邊,哪吒與父親從誤會到理解、寬容,是一種平等、健康的現代親子關系,哪吒的母親工作忙碌而內疚于不能陪伴兒子,像極了當下社會中的普通媽媽。
再回到本文的改編多媒體舞臺劇《華山美少年》,在剝去了重重歷史外殼之后,還能給我們剩下什么。這個空洞的故事,既失去了其產生于原本所處情境中的動人力量,也無法打動當下的人們。沉香救母故事的內核是中國傳統的“孝道”思想,同時完成“孝道”的過程也是沉香個人成長的過程。儒家提出的“孝道”原本是一種積極的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觀念,“孝”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推己及人的精神品質。但是,儒家的孝道發展到后期,從一種建立于個體自覺基礎之上的自我要求,逐漸變成了一種嚴厲的外在倫理規范。當“孝”從一種道德上的自我要求變成了一種制度性的強加于人,甚至于成了打人的棍棒,此“孝”可能就會變了味。不過,盡管如此,親子之愛始終且永遠是世間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我們也不能就此走向另一個極端而徹底否定了“孝”,“孝”的本質是愛。脫去禮法的桎梏,凸顯“孝”的內在本質,將讓人無理由服從的“孝”轉化為更具現代性內涵的建構于理解與寬容基礎之上的“愛”,是今日的我們要做到的。在這一點上,《哪吒之魔童降世》顯然更為成功, 這也是為什么《華山美少年》中沉香的“孝道”不是那樣能打動我們的原因。因為沉香的“孝道”是一種純觀念性的、空洞的、抽象的東西,并不是沉香母子在撫養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具體的“愛”,這種被傳統倫理所規范的“孝道”在今日已無法引起人們的共鳴。現代社會對“代際關系”的認識深度可能早就遠遠超越沉香救母故事所產生的年代,不在劇本中將這種時代認識反映出來,則無法叩動當代人的心弦。
而談到個體的成長,劇本中美少年沉香的成長歷程是一個十分順理成章的過程。雖然劈山救母這一任務對于一個少年來說看似異常艱難而幾乎不可能完成,但是在每一個重要的時刻沉香都有貴人指點或相助,及時解決問題:餓了、病了有仙女小姑娘送來食物和藥,沒有方向有仙女小姨靈芝指點,沒有本領有霹靂大仙傾力相教,神奇的六韜三略的本領也能靠幾句俏皮話就輕松學到,頃刻間脫去凡胎,并獲贈能劈山的萱花神斧……,諸如此類劇情事件,一切來得異常輕松,可以說沉香的成長是諸多外援合力的結果。這類成長缺少內在的壓力和驅動力,也就使得角色失去了個性上的張力和說服力。反觀魔童哪吒的個人成長歷程,是一種經歷了宿命不公之后的奮力反抗,是一種對自我進行深刻懷疑、拷問之后的自由選擇。通過內在的掙扎與突破,哪吒的自我成長得以完成。而其中“做自己的英雄”“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決定”的命題可謂直接喊出了壓抑在人性深處的普遍渴望,這種渴望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雖然無力達到,但在故事中卻可以隨著主人公的熱血與激情而得到短暫的釋放。
總之,對傳統神話故事的改寫或重寫,不僅僅是簡單地重新敘述這個故事,還考驗著我們對當下這個時代與人性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