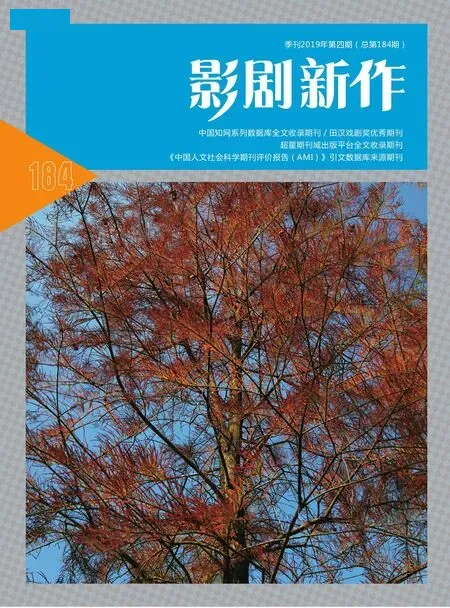愿作念郎風 長逝入君懷
——論民族舞劇《一把酸棗》舞臺呈現的戲劇性
鄒榮學
引 言
大型民族舞劇《一把酸棗》自2004年首演以來國內外演出累計已達千場以上,成為了中國舞劇乃至中國舞臺劇發展的一道奇炫風景。由眾多業內名家加盟、山西藝術職業學院華晉舞劇團演出的這部舞劇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著觀眾的注意力,在演員與觀眾之間、主創人員與評論者之間激起過一波又一波的情感碰撞與思辨波瀾,劇作藝術魅力的影響所及,無論是主創者、演員還是觀眾、欣賞者,對劇作的藝術實踐及時進行總結分析都是很有價值的。
劇作的成功經驗是多方面的,作為一部以舞蹈為主要藝術呈現形式的劇作,舞劇的戲劇性不但沒有弱化,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凸顯,這是舞劇取得巨大成功、取得感人至深藝術效果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德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理論家奧·威·史雷格爾在談及戲劇性時認為,戲劇的魅力來源于“行動”,看戲之所以是“有趣”的,是因為“在戲里可以看到人們在朋友或敵人的往來中互相較量”“以各人的見解、情操、情感互相影響,斷然決定他們的相互關系。”[1]他認為,只有劇中人在相互較量、相互影響從而導致各自心情和相互關系的變化才是有戲劇性的。分析舞劇作品也要關注劇作的戲劇性。與劇作戲劇性相關聯的有劇作情節與人物性格、戲劇矛盾沖突、戲劇懸念與戲劇發現等編劇元素,同時也與劇作體現舞劇特質的舞蹈呈現、音樂呈現、服裝化妝舞美呈現等密不可分。
一、劇作劇情的戲劇性
(一)劇情的曲折性
從上述關于戲劇性的論述可以看出,戲劇性來源于人物的行動及行動所帶來的人物自身與人物之間關系的變化。在舞劇《一把酸棗》中,為張揚劇作的戲劇性、集中刻畫人物,劇作在情節設置上做足了文章——情節新奇曲折多變,為人物的深度刻畫與戲劇性的張揚留下了充足的藝術空間。
在劇作的開端部分,小伙計走西口的走而復返給觀眾留下了巨大的懸念,也留下了隱隱的不安,小伙計與酸棗間的真摯愛情隨著酸棗因癡傻少爺而受傷、怒擲小伙計帶回來的包袱而越發變得凝重起來。在劇作的發展部分,志得意滿的小伙計從口外回來,看似順風順水的愛情卻在許多人的不知情中陡起波瀾。心生毒計的大管家在酸棗送給小伙計的信物——一包酸棗中下了毒,這個毒下得也是煞費苦心,最終通過遺失荷包、下毒、癡傻少爺送還荷包等一連串極具戲劇性的動作來完成。從酸棗得知下毒實情變成瘋癲開始,真正的戲劇高潮實際上已經開始。在西口外的荒漠路口,瘋癲的酸棗與小伙計又演出了一幕“縱使相逢應不識”的撕心裂肺的高潮戲。這一男女主人公人生最后時刻的每一幕場景都是刻骨銘心——小伙計不認識對面的酸棗、小伙計終于辨認出酸棗卻呼喚不回酸棗、酸棗見到荷包有了記憶欣喜地喂食小伙計酸棗、小伙計快樂地吃酸棗卻中毒死去、喚回記憶的酸棗也食酸棗隨小伙計死去……
“人與人的關系的相互影響,被史雷格爾看作劇作家精選戲劇情節的依據。”[2]情節的新奇曲折多變為人物性格與人物關系的表現搭建了廣闊舞臺,在情節變化的一個又一個時空情境節點上,舞蹈正好可以發揮它的藝術表現魅力。
(二)細節的逼肖性
劇作細節的逼肖為戲劇性的營造與舞蹈呈現的濃墨重彩牢牢地打下了基礎。劇中高潮處男女主人公在西口外荒漠大道上相逢的舞段格外動人心魄,其中細節的成功運用可謂功不可沒。在這一連串的戲劇場景中,男女主人公圍繞核心道具——一包酸棗的舞句與舞蹈動作都顯得那么貼切、那么真誠,充滿著生活質感。其中小伙計吃了酸棗給他的毒棗后痛苦地在酸棗膝上翻滾的舞蹈動作尤其讓觀眾能體驗到一種深入骨髓的疼痛。
西口外的大道上,小伙計與酸棗的“縱使相逢應不識”的相逢細節也格外酸楚動人。在舞段的呈現中,認出了酸棗的小伙計伸出雙臂去擁抱自己的戀人,然而,面前的戀人卻一再地從自己的臂上無力地滑到地上,有一次,就像孩子的游戲,滑落地上的酸棗居然孩子似地轉身爬行,從小伙計的胯下爬過。這不禁會使觀眾產生聯想——也許多年前,青梅竹馬的二人在孩童時代的游戲中正是重復這樣的動作(其實,在劇作的開端部分兩人有類似的背后擁抱動作),然而,今天的二人早已經物是人非。這種細節的真切逼肖讓觀眾會產生更多的聯想想象,這與觀眾間形成的共鳴效果是異常強烈的。
因為具有戲劇性的逼肖的細節,劇中相關的舞蹈動作才有了更廣大、堅實的創作空間。上述談及的舞蹈動作彰顯的雕塑感、畫面感、力度感都是很強烈的,在舞劇人物塑造上,相關舞蹈動作無疑具有點睛之效。
(三)道具的凝聚、牽引效果
劇中的道具較多且具有獨特藝術功效。
1.核心道具的牽引效果
劇中的核心道具是裝有酸棗的荷包。作為核心道具,荷包在劇情的不同發展階段多次出現且皆起到重大的劇情發展、轉折功效。因而荷包形成了一種隱形的牽引力,牽動了男女主人公的舞臺行動,關聯著相關的舞蹈動作,最終形成了具有強大主題效應的標志性物象,成為了主人公百折不撓的精神圖騰,也為觀眾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形象記憶。
在劇作的結尾高潮處,酸棗的牽引效果、舞臺功用近乎發揮到了極致。那一包酸棗凝聚了男女主人公所有的人生希冀,因而即使是處于癡傻狀態的酸棗也會見之驚醒、為之狂歡,食后中毒的小伙計滿地翻滾之際,愕痛萬狀的酸棗也會為自己心上的戀人去吃剩下的毒棗。在這里,核心道具——荷包發揮的主題功效與舞蹈呈現功效都是異常強烈的。
2.其他道具的凝聚功效
劇中其他的道具較多,比如“團扇舞”中的團扇、“算盤舞”中的算盤、“盤鼓舞”中的鼓以及小伙計走西口時帶的包袱等。這些道具參與舞段的表現,使得舞蹈的形式與內容更加規整、統一,極具民俗色彩。從戲劇性的角度來分析,這些道具的使用具有暈染戲劇情境之效——在符合舞劇藝術的舞臺呈現規律的基礎上加強群舞等舞段的戲劇情境介入感,在營造的濃重背景下凸顯主要戲劇人物的戲劇性動作與沖突。在厚重雄壯的“駝隊舞”中,正是風格鮮明的舞隊道具精妙地參與了群舞的構思與呈現,才為高潮處男女主人公最后的生命之舞設置好了濃重的背景與舞臺,才具備更加典型、更激蕩人心的爆發力。在“駝隊舞”中,伴隨著高潮處男女主人公舞蹈動作的始終,舞隊的隊形也根據情境氛圍而變,風格化、凝煉、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群舞的道具與雄壯的音樂、激揚的舞姿共同構建了一曲波瀾壯闊的生命交響。
二、劇作舞蹈表達的戲劇性效果——暢奇情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劇作的劇情新奇多變,其核心的表達訴求則離不開對人物性格、內心世界的刻畫,特別是主要人物。對于舞劇而言,最為重要的表達、呈現形式無疑是舞蹈。“人物的情感發生和變化是推動舞劇情節發展的主因和動力”[3],相對許多舞劇而言,《一把酸棗》在人物情感的表達中彰顯的戲劇性要強烈得多,因而在劇中不同類型舞蹈的藝術呈現中,戲劇性的舞蹈也是編導們想極力張揚的。
(一)雙人舞——一波三折,呼應回響
劇作運用了大量的雙人舞來表現人物與主題內涵,劇作高潮與結尾處的雙人舞尤其撼人心魄。志得意滿的小伙計從口外歸來,不期而遇了自己的心上人酸棗。本來這是人生中事業與愛情皆有所獲的無限美好時刻,富有戲劇性的是,眼前的酸棗早已不是有著正常心智、能和普通人一起享受人間情愛歡樂的酸棗,她在得知管家在自己送給小伙計的酸棗里下了毒后瘋了。在西口古道上演的這一幕戀人相逢不識、形同陌路的戲劇場景,用雙人舞蹈來表現無疑是極具震撼力的。在這個高潮與結局的舞段中,一些戲劇性的舞句與舞蹈動作也是蘊意豐富、極具戲劇性的。如小伙計認出酸棗時對酸棗的擁抱——他從背后擁抱酸棗,酸棗卻一再地從自己的懷里滑落。有一次,傻癡的酸棗滑落在地后居然孩子似地從小伙計的腿下爬過。在劇情結尾處,都已吃了毒棗的酸棗與小伙計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剪影——小伙計用盡全力單臂高高舉起酸棗在頭頂。這些舞蹈性極強的動作隱含了兩人間的戲劇性關系——縱使相逢應不識、至情相逢成路人。這樣的舞蹈表達更能引發觀眾對背后隱藏的戲劇矛盾沖突與主題的深入思考。
與舞劇高潮和結尾處的雙人舞相對應的是劇作其他不同段落處的雙人舞呈現。如劇作第一幕中酸棗與小伙計間的雙人舞。在舞段中,也是小伙計從后面抱住酸棗,也是有酸棗對小伙計屢次戲劇性地推離,酸棗對小伙計的“排斥”性舞蹈動作一再地發生,舞段高潮處的雙人舞動作也有戲劇性的托舉舞蹈動作。作為劇作的開端部分,舞段中的舞句與舞蹈動作組合似乎隱喻了劇作后面高潮結尾處的劇情。這種首尾的呼應感在全劇中形成了回響共鳴效果,對揭示主題無疑是用意明顯。再如劇作第三幕的雙人舞。小伙計學徒歸來,收獲滿滿的他與酸棗在一起情意綿綿。在這一舞段中,小伙計從背后對酸棗的擁抱、圍繞荷包的癡迷翻滾等舞蹈動作依舊與劇作后面劇情高潮處的舞蹈動作形成呼應。在第二幕中,學徒中的小伙計思念遠在家鄉的酸棗,幻象中的雙人舞有臂下穿行,背靠背倚立、下坐、滾背,托立,背后給予物品等,表達了劇情逐步深入發展的情勢,戲劇性、隱喻與相關劇情、舞蹈動作的呼應關系也是很明顯的。
戲劇性的雙人舞在劇情及動作呈現上有一波三折之效,舞蹈呈現戲劇性豐滿,不同舞段間形成了暢敘奇情、回環呼應之效。
(二)單人舞——競流逐波,烘托造勢
劇作第二幕“學徒”中小伙計們為一個有爭議的數字犯難,這時男主角小伙計自告奮勇地手持算盤很快解決了問題。在舞臺上,小伙計這個解決問題的過程是通過小伙計的單人舞來表現的。為了表現小伙計這個人物的機敏和進取精神,單人舞中大量運用了跳躍、翻滾等動作,凸顯刻畫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意志品質,單人舞的表達把人物為事業與愛情而奮斗的精神推向競流逐波的高位,這樣就為后面小伙計對酸棗的思念的舞臺幻景、第三幕小伙計學成歸來的場景表達埋下了伏筆。
在劇作第三幕“投毒”中,大管家怨恨酸棗愛上了小伙計,他決意在酸棗送給小伙計的、裝在荷包中的酸棗下毒。這個劇情在舞臺的呈現是一段單人舞。大管家的舞蹈動作在動勢的變化、空間的變化、重復的運用等方面都較好地揭示了人物的內心,對塑造主人公酸棗與小伙計起到了烘托造勢之效。
(三)群舞——民俗炫影,心靈律動
劇中的群舞為觀眾展現了精彩紛呈的晉商文化的民俗色彩。無論是“團扇舞”“傘頭秧歌舞”“算盤舞”“盤鼓舞”,還是“駝隊舞”以及饑童舞段等,無不體現了獨具特色、深厚的晉商文化的民俗色彩。在第一幕“生日”中,“團扇舞”“傘頭秧歌舞”等群舞中彰顯出了儒賈貫通的晉商倫理文化和深厚的晉商大院文化,這種民俗文化極具觀賞價值,既烘托了戲劇情境氛圍,也為人物的性格特征打上了底色——這可在酸棗持勺施粥以及給舞傘青年賞錢的舉動中得到印證。
與劇作戲劇性更加緊密相關的群舞還體現出了與情境人物心境、心靈律動密切合拍的特點。這在劇作發展與高潮部分的“盤鼓舞”“駝隊舞”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盤鼓舞”中眾多的“手勢”語言伴著緊張不安的鼓聲與漸起的民歌《繡荷包》旋律,其主題寓意訴求還是很明確的。在“駝隊舞”中,處于高潮處的戲劇人物心理狀態瞬息萬變,“駝隊舞”的音樂與節奏時而雄壯高亢、時而急促激切,很好地映襯了主角人物處于矛盾沖突巔峰之際悲苦萬端的心理狀態。
所有的舞蹈編排從戲劇性的角度上來講都是要在敘奇事的基礎上暢奇情,作為舞劇作品,本劇的舞蹈在表現情感上力度是強大的,戲劇性也是很突出的。
三、劇作音樂運用的戲劇性
(一)主題音樂的引領輝映
全劇的主題音樂起到了引領全劇情節、主題發展的效果。如在表現貫穿劇作的愛情主題時,在序曲中,作曲家在左權民歌“開花調”“楊柳青”等的基礎上,用更富有表現力的音調、樂句結構充分表現了酸棗與小伙計糾結、痛楚的內心世界。這個主題的音樂形象在全劇起到了重要的貫穿作用。在劇作第四幕酸棗被迫嫁給傻少爺時,鼓舞的表現運用了根據山西民歌《看秧歌》與《繡荷包》改造后的旋律,在舞蹈的高潮處,《繡荷包》的旋律響起,愛情主題在這個舞段中達到了高潮,而這個高潮也與序曲中的愛情主題音樂以及第五幕中根據山西民歌素材改編的二胡獨奏愛情主題音樂遙相呼應。
主題音樂的引領與輝映無疑與作品的主題密切相關,而風格渾成一體的主題音樂所要表達的也是劇作統一的主題思想,在主題思想的表達中,主題音樂的協調、輝映、統一既是主題表達的要求,也是戲劇結構統一性的要求。對舞劇而言,主題音樂需要在劇作關鍵之處畫龍點睛,這樣也就會為舞劇演員的表演留下了針對性強的舞臺表達空間與原動力,從而淋漓盡致地表現劇作人物富有戲劇性的、糾結的人物關系與人物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
(二)“情景”性舞蹈音樂對戲劇性情境的推波助瀾
“情景”性舞蹈音樂在劇中往往會起到輔助營造情節氛圍、展示民俗、敘事等功效,在舞劇《一把酸棗》中,這類舞蹈音樂對劇作戲劇性情境還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四幕中紅燈舞的舞段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在第四幕中,殷家強娶酸棗做傻兒子的妻子。為渲染這一表面喜慶實則心酸的戲劇情境的氛圍,作曲家在這個舞段中運用了山西民歌《交城山》的音樂素材進行創作,在舒緩的音樂旋律中紅燈布排的場景漸次展開,場面大且隆重,但在熱鬧的背后卻隱隱藏著一種無以名狀的悲哀與痛楚,這種戲劇性場景的敘事表達也暗合了民歌的部分歌詞內容,這對酸棗被逼與傻少爺成婚這一戲劇性情境的建構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的效果。
其他諸如“盤鼓舞”“駝隊舞”等“情景”性舞蹈音樂也是如此。“音樂能加強舞蹈的形象,加強藝術感染力,為舞蹈提供了情感和節奏的基礎。”[4]
四、劇作人物造型與舞美的
戲劇性表達——略泥存花,烘云托月
(一)人物服裝顏色設計搭配——對比襯托、凸顯基調
劇作深根于晉商文化的表達訴求決定了作品要在力求真實的基礎上表達出晉商文化的精神內涵,因而反映在服裝設計上,就是要凸顯主角人物的精神世界,同時表達出較為真切自然的民俗文化特征。舞劇劇作作為戲劇的一個門類,這些目標的完成也與劇作戲劇性的表達關系密切。
縱觀全劇,主角之一的酸棗的服裝在不同的場景、情境中有著不同的色調。在劇作序、第四幕“婚變”與第五幕“絕唱”中,酸棗的服裝顏色都是紅色的主色調,在遵從清末民初女裝款式真實的基礎上適當加工以便于舞蹈表現。但相較第四幕而言,序與第五幕中服裝用色偏紫紅,這無疑與劇作的主題思想表達訴求相一致。在第二幕“學徒”小伙計思念酸棗的幻覺場景中,酸棗的服色為淡黃與淺綠的混合色調,服色與夢幻式場景的氛圍、人物心境無疑是契合的,也為后面劇情的反轉從服裝角度做了鋪墊。
主角人物酸棗與小伙計間的服裝搭配原則是強調對比。全劇多數場景中小伙計的著裝服色都是以白色主打,配以簡潔利落的服裝造型。這樣既利于在舞蹈中表現他的聰明精干,也與酸棗柔婉深情的形象形成對比、相互映襯效果。
劇作其他人物的服裝色調多能彰顯特定情境中的主角人物心情的主基調。如老夫人多著深藍、藍紫色為主色的服裝,駝隊群舞演員著銀色服裝等,皆能凸顯人物心情基調,從而為劇作戲劇性的表達助力。
(二)頭飾、發型、化妝等的設計——凸顯風格,明凈大方
作為戲劇性較強的一部舞劇作品,劇作在角色發型、頭飾、化妝等方面的設計力求簡約、明凈大方并凸顯出鮮明的地域文化風格。縱觀全劇,男女主人公的發型、化妝幾乎沒有什么大的變化,頭飾等也結合人物的個性及戲劇情境與人物的服裝實現簡潔的統一,在這里,簡約的發型化妝等的設計隱透著人物一以貫之的性格特征,為舞劇人物行動的戲劇性表達刪繁就簡、營造便利。
(三)舞美、燈光設計——基調寫實、深層造勢
劇作舞美的基調是寫實的。無論是深宅大院,還是西口外的荒漠大道,劇作的舞美設計都是力求寫實。寫實帶來了濃濃的生活質感,這就為劇作的悲劇性主題的抒發設置好了堅實的時空舞場。
劇作舞臺燈光的運用在情境上明顯具有深層造勢之效。“在舞臺美術中,燈光與色彩也許是最有力的解釋手段”[5],劇作非常注重發揮舞臺燈光的運用效果。在自然光、追光大量運用的基礎上,劇作多處運用了藍色光和玫瑰紅色光,從燈光的角度深層挖掘戲劇情境中所蘊含的戲劇性。如在劇作第五幕——全劇的高潮與結尾處,劇作大量運用了藍色光,突顯了男女主人公憂郁不安的內心色彩。在劇作第二幕“學徒”中,小伙計思念酸棗形成的幻覺情景中大量運用了紫紅色具有夢幻色彩的光,這無疑也是劇作從燈光角度做出的對人物心理的戲劇性暗示。
總之,劇作人物造型與舞美的表現亦滿足劇作戲劇性的表達需求,具有略泥存花、烘云托月之效。
結 語
舞劇《一把酸棗》取得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相較不少舞劇作品而言,《一把酸棗》在張顯舞劇藝術本體特征的同時,其表現出的戲劇性也是比較突出的。劇作除了在劇情上做足戲劇性之外,劇作在雙人舞、單人舞、群舞等舞蹈中皆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了戲劇性,在音樂、人物造型與舞美等的運用上也是緊貼舞劇藝術本體特征的表達,助力于劇作戲劇性的營造。愿做念郎風,長逝入君懷。立足于劇作人物的情感表達需求,劇作主題思想與戲劇性、動作性的演繹令觀眾彌久難忘。劇作戲劇性精彩的舞劇藝術演繹定會給當今的舞劇乃至相關舞臺劇等的創作與研究帶來諸多新啟示。
注釋:
[1]轉引自譚霈生.論戲劇性[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3.
[2]吳戈.戲劇本質新論[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89.
[3]肖蘇華.當代編舞理論與技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2:158.
[4]李仁順.舞蹈編導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67.
[5]董健,馬俊山.戲劇藝術十五講(修訂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