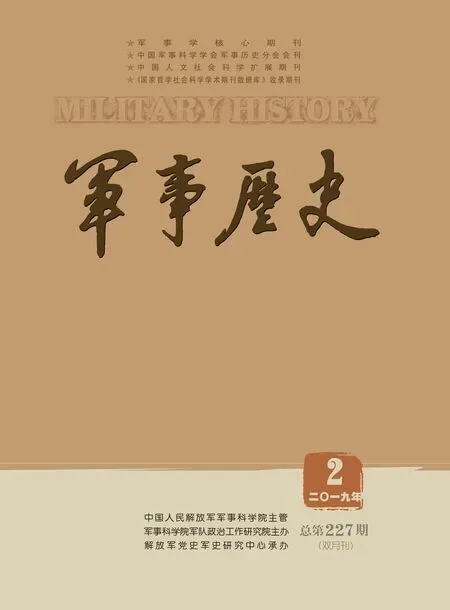從國家政體的演進看周代軍禮的興衰 *
周代是中國從分封制國家政體向郡縣制國家政體演進的歷史時期。與國家政體的演進相適應,西周、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的軍事制度和軍事文化也呈現出明顯的時代差異,分別反映了不同國家政體下的政治關系。本文擬從國家政治演進的視角考察周代軍禮的興衰歷程,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西周時軍禮的形成及其反映的血緣政治關系
據學者研究,中國最初的禮制出現于距今約4000年的龍山時代。①參見高煒:《龍山時代的禮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35~251頁。這一時期是中國原始社會的軍事民主制時代。最初的軍禮應當孕育于這一時期,它是軍事民主制時代的各部族在戰爭中逐漸形成并共同遵守的關于軍事活動的習慣與規范。夏、商時期,軍禮被進一步整合為國家的重要禮制。據學者研究,殷墟卜辭所見的商代軍禮已經包括告廟與謀伐禮、占卜擇將和冊命禮、遷廟主和立軍社禮、立中和乞師禮、蒐狩和振旅禮、獻捷獻俘禮等內容。②參見郭旭東:《殷墟甲骨文所見的商代軍禮》,《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在繼承、改造夏、商軍禮的基礎上,周代軍禮更加系統化和規范化。《周禮·大宗伯》:“大宗伯之職,……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周代軍禮內容豐富,舉凡與軍事相關的一切活動如軍隊征伐、軍賦力役、軍事演習、勘正疆界等,皆須依禮而行。
周禮是依據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而制定的。西周王朝實行分封制,形成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政治系統,又實行宗法制,形成了以“大宗、小宗”為特點的宗法系統。政治系統與宗法系統互為表里,建構起西周“尊尊”“親親”為核心的禮治秩序。作為周代“五禮”之一的軍禮,同樣發揮了維護西周禮治秩序的功能,具有鮮明的“尊尊”“親親”之義。
(一)軍禮的“尊尊”之義
西周軍禮是依據分封制下嚴格的等級制度而制定的,其首要的原則是“尊尊”,具有鮮明的等級性。
1.兵源的等級。西周實行大分封,各封國居民主要由周人和土著構成。作為征服者的周人居住在國都之中,稱為“國人”。作為被征服者的土著居住在郊野地區,稱為“野人”(或“庶人”)。國人屬于周族,他們享有充分的權利,可以參與政治、接受周代學校教育,軍事上“執干戈以衛社稷”①《禮記·檀弓下》。。野人屬于土著,他們“子孫為隸,不夷于民”②《國語·周語下》。,地位遠低于國人,不享有國人的政治權利,更不能承擔兵役。“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是“禮不下庶人”③《禮記·曲禮上》。的具體體現。
西周國人在國為民,在軍為士。列國實行“寓兵于農”,國人中的平民平時務農,農閑時由國家組織進行軍事訓練。《國語·周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西周“講武”的主要方式是田獵,即所謂“大田之禮”,又稱為“大蒐禮”。《國語·周語》:“蒐于農隙,耨獲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畢時。”《左傳》隱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
西周、春秋戰爭以車戰為主,從軍作戰的國人也是分等級的,貴族通常擔任“甲士”,稱為“君子”;平民一般為步卒,稱為“小人”。“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④《左傳》宣公十二年。
2.軍賦的等級。西周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規定列國根據其爵秩制軍作賦。《國語·魯語》:“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何休《公羊傳》隱公五年注云:“方伯二師,諸侯一師。”陳恩林先生認為:《國語·魯語》和何休注記載的是西周初期的軍事制度。在周初,天子擁有“西六師”和“殷八師”共十四師的軍隊。公爵諸侯可組建三師,元侯(方伯)可組建二師,諸侯(一般侯爵諸侯)擁有一師,伯子男不能組建獨立的軍隊,遇有征戰則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諸侯。⑤參見陳恩林:《先秦軍事制度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64~67頁。西周晚期,軍事編制的最大單位擴展至“軍”,但仍有等級的規定,“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西周將列國的軍賦納入等級制的規范,形成了以周天子為中心的一元化的軍事領導體制。
3.儀節的等級。軍禮的諸種儀節皆貫徹嚴格的等級規范。如:天子諸侯出征,舉行一系列告祭儀式。《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天子諸侯告祭的對象有不同的規定。天子可祭上帝,祭上帝是天子的特權。天子與諸侯告祭的社神有大小之別。《禮記·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天子與諸侯所告祭的山川也不同,“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⑥《禮記·王制》。。天子與諸侯告祭于“學”,但告祭的地點不同,“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⑦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32頁。。天子、諸侯告祭對象的不同,彰顯了其政治地位的尊卑之別。
周代國家檢閱或演習軍隊,參加的天子、諸侯、卿大夫及鄉遂州里官吏都各在其位豎立旗幟,旗幟上畫有不同圖形,并書有名號等。《周禮·司常》:“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旗幟、徽號是周人等級身份的重要標識。
此外,軍禮在出師、命將、獻捷等儀式中,也體現了明顯的等級性。《左傳》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⑧《左傳》隱公五年。
4.戰場上的等級身份。在分封制下,“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①《儀禮·喪服》鄭玄注。。天子為天下之君,諸侯為一國之君,卿大夫為一家之君。諸侯國的卿大夫既是本國國君之臣,也是天子乃至他國諸侯之陪臣。這種封建君臣關系即使在戰場上也要得到彰顯,作戰雙方根據對手的身份,對尊貴者加以禮敬。《左傳》桓公五年載,周、鄭繻葛之戰,鄭祝聃射王中肩。王師戰敗,鄭人不敢追擊,鄭莊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左傳》成公二年載,晉、齊鞌之戰,齊國戰敗。齊頃公進入諸侯之師,狄、衛軍隊主動對齊頃公加以保護。杜注:“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杜注不確。狄、衛的做法,主要出于遵守軍禮的要求。《左傳》成公十六年載,晉、楚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并且下令“傷國君有刑”。此類事例表明,等級觀念對周代軍事活動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
(二)軍禮的“親親”之義
周代軍禮的另一條重要原則是“親親”。西周、春秋時期,宗法制與封建制相結合,形成了周代“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和國家形態。《左傳》桓公二年:“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在這種社會結構和國家形態下,周代軍禮重視發揮血緣關系在軍事活動中的作用,具有濃厚的“親親”之義。
1.告廟禮的“尊祖敬宗”功能。在周代軍禮中的諸種告祭儀式中,告廟禮居于核心地位。天子、諸侯出征,告廟、授兵、飲至、獻捷禮等皆在宗廟舉行。行軍作戰時,天子、諸侯要將祖先的神主載以隨行。天子、諸侯告廟、載主的目的,一方面是祈求祖先神靈護佑而取得戰爭勝利,另一方面是為了利用祭祀活動強化其作為宗子的權力與地位。周代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制,當“長子繼承法成為習慣的現象時,新的家長的權力……要能制服自己的伯叔、兄弟和他們的妻兒只有靠他們的迷信觀念的幫助,正是迷信觀念使他成為死者的代表,死者從其墳墓的深處給他忠告和命令。服從他,他們只是服從死者靈魂的意志”②[法]拉法格著,王子野譯:《思想起源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第144、145頁。。《禮記·大傳》:“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人們尊崇天子、諸侯的祖先,同時就必須尊崇他們的“繼體之人”——天子和諸侯。
2.致師禮所保留的“血族復仇”孑遺。西周、春秋時期普遍存在著各種宗族組織,宗法血緣關系對整個社會有著重要影響。周代的宗族組織是從氏族社會延續下來的,因此,周代社會仍保留了血族復仇的古老傳統。這在“致師禮”中可以得到反映。《周禮·調人》:“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君之仇視父,師長之仇,視兄弟,主友之仇,視從父兄弟。”《周禮·環人》鄭玄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必使勇力之士犯敵焉。”③《周禮·環人》鄭玄注。周代致師禮能夠激發交戰雙方的“必戰之志”,與當時的戰爭保留著一定的血族復仇特征有關。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戰前的致師對于激發交戰雙方的斗志便具有了特殊的意義。致師的一方如果擒獲或殺死了對方的個別成員,意味著挑戰了對方血族復仇的道德底線,雙方間的戰爭便無可避免了。可見,致師禮是基于周代的宗族組織與宗法觀念而發揮作用的。
3.獻捷禮的“華夷之辨”原則。西周時期,列國“戰勝而有所獲,獻其所獲曰獻捷,亦曰獻功”④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977頁。。周禮規定:“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⑤《左傳》莊公三十一年。;“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⑥《左傳》文公四年。;“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昵,禁淫慝也。”①《左傳》成公二年。諸侯對四夷用兵后向天子獻捷,天子對獻捷者進行褒獎,諸侯國奉王命討伐同姓或異姓諸侯則不向天子獻捷,僅向天子告事而已。諸侯國之間不相獻捷。可見,“華夷之辨”是西周獻捷禮的一項基本原則。
“華夷之辨”是周代一種重要的政治與民族觀念。周人強調華夷之辨,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②《左傳》成公四年。,“戎狄豺狼,不可厭也”③《左傳》閔公元年。。諸夏間的血緣關系或姻親關系則備受重視,“諸夏親暱,不可棄也”④《左傳》閔公元年。。在周人的觀念中,禮制是聯結華夏的紐帶,戰爭是威服四夷的工具,所謂“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⑤《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西周獻捷禮“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的原則,既是“刑以威四夷”的體現,又是對周天子最高軍事權力的確認。“兄弟甥舅,不獻其功”“諸侯不相遺俘”的原則,是“德以柔中國”的反映,是周代以“親親”維護華夏諸侯國秩序的體現。
4.戰爭的倫理要求。周代以封建、宗法為特點社會結構,要求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符合普遍的倫理規范。正如學者所言:“西周、春秋時期,由于交戰雙方在宗法與封建結合的制度下,往往具有‘兄弟之國'、‘甥舅之國'的名分,基于禮的約束,在戰爭中產生了較為普遍的倫理要求。”⑥朱曉紅:《周代軍禮考論》,《國學學刊》2015年第2期。
周代軍禮強調諸侯國之間“依禮而戰”,提倡戰爭的公開、公平性和對敵方戰斗人員的人道保護。如要求在戰爭中“不加喪,不因兇”⑦《司馬法·仁本》。“不薄人于險”⑧《左傳》文公十二年。“不以阻礙”“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⑨《左傳》僖公二十二年。,等等。
周代軍禮主張戰勝國對戰敗國進行寬大處理。西周戰爭旨在維護王道政治秩序。對于毀壞王綱者,通過征伐使之服從而已,并不兼并滅亡其國。《左傳》隱公十一年:“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左傳》宣公十二年:“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周代的投降禮貫徹了“伐叛舍服”的原則。戰敗國向戰勝國舉行“肉袒”“面縛”“進獻宗器”“大夫衰絰士輿櫬”“委質為臣”等儀式后,戰勝國對戰敗國的處置方式通常是:赦免戰敗國君,不毀戰敗國宗廟和社稷,善待歸降者,不占戰敗國的土地。⑩參見景紅艷:《〈春秋左傳〉所見周代重大禮制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47頁。
周代將戰爭倫理概括為“武之德”“戰之器”。《左傳》宣公十二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左傳》成公十六年:“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西周時期,軍禮在軍事活動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作為周禮的重要組成部分,軍禮是周代政治、經濟制度的產物,它根據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基本原則而制定,具有鮮明的“尊尊”“親親”之義,集中反映了西周分封制政體下的血緣政治關系。
二、春秋時軍禮的式微及其反映的社會關系的變化
春秋時期,“井田、分封、宗法和禮等,在激烈的階級斗爭的影響下,都已日趨破壞”?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4頁。,春秋軍禮亦隨之漸趨式微。
(一)“尊尊”原則的破壞
1.“禮不下庶人”的打破。春秋時期,國人仍是列國軍隊的主要兵源。《左傳》閔公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國語·齊語》載,管仲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其中,三軍盡出于國中十五鄉。春秋中后期,隨著戰爭規模日益擴大,“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的舊制難以適應戰爭的要求。列國開始打破國野界限,改革兵役制度。如晉國的“作州兵”、魯國的“作丘甲”、鄭國的“作丘賦”等措施,都是把征兵的范圍擴展到野的區域,賦予野人當兵的權利。①參見陳恩林:《先秦軍事制度研究》,第128~135頁。
春秋列國的兵役制度改革,不僅打破了傳統的國、野界限,賦予了野人當兵的權利,而且標志著“禮不下庶人”原則的逐漸廢弛,必然引發階級與社會關系的進一步劇變。春秋末年,晉國的趙簡子在前線的誓師詞中宣布:“克敵者,……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皂輿免。”②《左傳》哀公二年。野人不僅可以參加戰爭,還能通過立功被舉薦為官。可見,當時部分野人的社會地位已經和國人較為接近了。春秋時期國、野差別的縮小,為戰國時期編戶齊民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2.軍賦等級制的破壞。西周軍禮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通過將列國的軍賦納入等級規范形成以天子為核心的一元化軍事領導體制。春秋時期,周天子一元化的軍事領導體制崩潰,各諸侯國紛紛突破等級制的約束,紛紛將軍隊組織擴充到了三軍、四軍乃至六軍。如:鄭國和楚國于春秋初期就組建了三軍。齊在桓公時把軍隊擴編為三軍。晉國最初僅有一軍,后來擴充到二軍、三軍、六軍。吳有三軍,后來又發展到了四軍。隨著天子的衰微和諸侯的強大,歷史進入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霸政時代。
春秋早期,列國把擴張而掠得的土地分封給卿大夫,建立卿大夫之“家”的地方政權。為了控制卿大夫,列國對其卿大夫的軍賦作了明確規定。《禮記·坊記》:“家賦不過百乘。”《左傳》哀公二年孔疏:“百乘,卿之極制也。”春秋中后期,關于卿大夫軍賦的規范失去了約束力,列國卿大夫依靠強權大肆擴張軍隊。魯國的三桓經過“三分公室”③《左傳》襄公十一年。“四分公室”④《左傳》昭公五年。,“魯之群室,眾于齊之兵車”⑤《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的三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⑥《國語·齊語》。,國氏、高氏掌握二軍的兵力。晉國卿大夫兵力之強更加驚人,僅韓氏、羊舌氏二族,“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⑦《左傳》昭公五年。,而晉國公室“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⑧《左傳》昭公三年。。春秋中后期,列國卿大夫仗恃強大的私家武裝展開掠奪、擴張和兼并,歷史進入了“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的時代。
春秋時期,禮樂征伐的權力逐級下移的歷史充分表明,軍禮的等級制規范的約束力已經十分有限,軍禮逐漸失去了維護貴族政治秩序的功能。
(二)“親親”之義的喪失
西周軍禮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利用“親親”原則維護以天子為首的華夏國家秩序。春秋時期,隨著宗法制的不斷破壞,軍禮的“親親”原則也不斷遭到破壞。據范文瀾先生統計,在長達242年的春秋時期,發生戰爭483次,平均每年兩次戰爭。⑨參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9頁。如此頻繁的戰爭,多數發生在諸侯國之間。可見,隨著王權的衰落,原本存在著兄弟、甥舅名義的諸侯國,不再顧忌“親親”之義,紛紛展開爭奪霸權和領土的斗爭。晉國是通過吞并同姓小國而擴張領土的典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左傳》僖公五年載,晉借道于虞以伐虢,虞國大夫宮之奇看清了晉國包藏禍心,曰:“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逼乎?親以寵逼,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其他幾個大國擴張的情形大抵如此。列國在爭奪霸權與擴張領土的過程中,無不將政治、經濟利益擺在首位,傳統的“親親”原則被棄若敝屣。
春秋時期獻捷禮的變化,也反映了軍禮“親親”原則的式微。據學者研究,《春秋》《左傳》《詩經》所記載的十四次春秋時期的獻捷活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違背了“中國不相遺俘”的原則。十四次獻捷禮中,只有五次是周人對夷狄用兵后發生的告慶之禮,其余九次都是周之諸侯國之間發生戰爭后而向第三者舉行的獻捷禮;(2)違背了“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的原則。見于史冊的十四次獻捷禮中,晉國向王室獻捷六次,諸侯國相互獻捷八次;(3)出現了向大國獻捷的現象。作為霸主的晉國曾兩次受到鄭國的獻捷,楚國也曾受到鄭國的獻捷一次;(4)出現了諸侯大國向小國獻捷的現象。“雖然晉國仍有向王室獻捷五次歷史記錄,但這與西周獻捷禮的性質已不可同日而語,它是大國借獻捷向王室謀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弱國向強國獻捷是向霸主稱臣納貢的新形式;強國向弱國獻捷則是借此炫耀武力以達到威脅拉攏小國的目的。”①景紅艷:《〈春秋左傳〉所見周代重大禮制問題研究》,第99頁。可見,春秋列國的獻捷活動不再遵行“尊王”“親親”等原則,而演變成了表達“霸權”的一種方式。這是軍禮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變化,也意味著傳統軍禮日漸走向了衰微。
(三)“禮戰”觀念的動搖。
春秋時期,盡管“禮戰”觀念仍有一定影響,但這一傳統觀念已經發生了動搖。《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載,宋襄公在與楚國的泓之戰中執守軍禮,“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最終因貽誤戰機而招致大敗。宋司馬子魚評論說:“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司馬子魚的評論表明,春秋時期,傳統的“禮戰”觀念已經發生了動搖,而“三軍以利用也”等觀念逐漸成為戰爭思想的主流。
春秋時期,軍禮表面上仍延續了西周軍禮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它逐漸失去了維護貴族禮治秩序的政治功能而日趨式微。春秋時期軍禮的式微,反映了春秋時基于宗法制、分封制的血緣政治關系不斷瓦解和崩潰的社會現實。
三、戰國軍事制度的變革及其反映的地緣政治關系
戰國是一個大變革的歷史時代。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周代的井田制被國家授田制所取代,分封制被郡縣制所取代,世卿世祿制被官僚制所取代,禮制思想被法制思想所取代。與劇烈的政治、經濟變革相適應,戰國軍事制度亦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周代軍禮則最終走向解體。
(一)國、野制的廢除與“大蒐禮”的廢止。
春秋時期,列國通過兵役制改革,打破了國、野界限,賦予了野人當兵的權利。然而,直到春秋末年,國、野界限并未完全消失。戰國時期,列國普遍實行了戶籍制度,將過去的國人、野人一律登記戶籍,作為國家征收賦稅和征發徭役、兵役的依據。從此,國、野界限徹底消失,國人、野人一律演變為封建國家的“編戶齊民”。隨著國、野界限的消失和編戶齊民制度的確立,列國把征兵的范圍擴大到全民范圍,普遍建立起龐大的常備軍。據《戰國策》記載,秦、楚兩國都有帶甲百萬,齊、趙、韓、燕等國都有帶甲數十萬。②參見《戰國策》的《楚策一》《齊策一》《趙策二》《韓策一》《燕策一》。列國擁有規模如此龐大的常備軍,說明列國的兵源幾乎擴大到了封建國家統治下的全體編戶齊民。編戶齊民的形成及其列國兵源的全民化,宣告“禮不下庶人”的舊制在戰國時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
隨著列國常備軍的普遍建立,過去以田獵的方式進行軍事訓練的“大蒐禮”也被廢止,取而代之的是經常化、專業化、制度化的軍事訓練。《吳子兵法·治兵》:“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尉繚子·兵教上》:“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和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國、野制度的廢除與“大蒐禮”的廢止,是周代軍禮在戰國時走向解體的重要標志之一。
(二)軍事官僚制取代貴族世襲軍職制
西周、春秋時期,列國軍事領導體制的特點是“寓將于卿”。卿大夫一身而兼文、武二職,他們既是行政長官,又是軍事將領。如晉國的六卿都是軍將,齊國的國、高分掌二軍,魯國的三桓、鄭國的七穆亦皆為軍將。戰國時期,列國廢除了“寓將于卿”制度,實行文、武分離體制。如趙國的廉頗、李牧,秦國的白起、王翦,都是善戰的名將,而不是相。列國的將由國君任命,直接對國君負責。將、相的分離,改變了過去卿大夫集行政權、軍事指揮權于一身的情形,有利于加強國君的權力。《尉繚子·原官》:“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反映了戰國時列國官僚體制的基本特點。
西周、春秋時期,列國普遍存在卿大夫世卿世祿制,軍隊將領幾乎是清一色的貴族成員。戰國時期,列國在變法運動中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同時實行軍功爵制。如吳起在楚國變法,“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斗之士”①《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商鞅在秦國變法,“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②《史記·商君列傳》。。軍功爵制與世卿世祿制有著本質的不同。世卿世祿制是西周、春秋貴族政治的產物。在世卿世祿制度下,列國軍將皆為宗法貴族,他們擔任軍職是憑借其血緣出身,職位高低取決于其宗法地位,其軍職通常又是可以世襲的。軍功爵制是戰國官僚政治的產物,它貫徹“因能授官”的原則,不論出身門第和階級階層,只要為國家立有軍功便可享受爵祿。戰國時列國通過推行軍功爵制,一方面取消了舊貴族的世襲特權,另一方面使大批出身微賤的士人登上政治舞臺并擔任國家的將、相,從而開辟了戰國時的“布衣將相格局”。
文、武分職與軍功爵制是戰國官僚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國通過實行這兩大制度,在軍事領域確立了新型的官僚制度。隨著戰國官僚制度的確立,貴族所享有的世襲軍隊職位的特權被最終取消,以維護“尊尊”“親親”為宗旨的軍禮失去了賴以存在的政治基礎。軍事官僚制取代貴族世襲軍職制,亦是周代軍禮在戰國時期走向解體的一個重要標志。
(三)“刑無等級”的軍法取代“刑有等級”的軍禮
周代的軍禮,除了具有“尊尊”“親親”之義外,還包括“確立軍事規范、懲罰軍事犯罪的‘法'的內容”③朱曉紅:《周代軍禮考論》,《國學學刊》2015年第2期。。然而,軍禮制度下的所謂“軍法”,針對的主要對象是士卒。貴族則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他們即便違反軍令,也往往能夠減免懲罰。如:晉楚城濮之戰中,魏仇、顛頡一起違背軍令,但因魏仇是世族,結果魏仇被赦免,而顛頡被誅殺。④參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雞澤之會上,晉悼公之弟揚干擾亂軍行,中軍司馬魏絳殺其車夫以為懲罰。晉悼公大怒,準備殺魏絳。經過魏絳一番解說,晉悼公才幡然悔悟,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⑤《左傳》襄公三年。可見,軍禮之“法”的特點是“刑有等級”,貴族享有一定的法外特權。
戰國時期,列國實行法治,取代了西周以來的禮治。法治的宗旨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⑥《史記·太史公自序》。,即“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⑦《商君書·賞刑》。。戰國時列國制定了系統的成文軍事法規,舉凡軍隊的訓練、編隊、城防、宿營、行軍、作戰、獎懲等,都有明確而細致的法律規定,《尉繚子》一書對此多有記載。如:《束伍令》:“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經卒令》:“鼓行交斗,則前行進為犯難,后行退為辱眾,逾五行而前者有賞,逾五行而后者有誅。”《將令》:“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兵令下》:“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已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陣中者,皆斬。”《束伍令》:“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對于違反軍令者,必須依法嚴懲,即便是軍事長官也絕不姑息。《武議》:“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
“刑無等級”是戰國軍事法規的基本原則,它取消了貴族享有的法外特權,要求所有將士必須一律遵守軍法的規定。軍將犯令,也依法嚴懲不貸。這顯然與軍禮的“刑有等級”有著根本的不同。“刑無等級”的軍法取代“刑有等級”的軍禮,是周代軍禮在戰國時期走向解體的另一個重要標志。
(四)“兵以詐立”戰爭觀念的確立
隨著軍事制度的深刻變革,戰國時期的戰爭觀念也發生了根本變化。西周以來的“禮戰”觀念徹底被摒棄,“兵以詐立”“以利動”成為指揮戰爭的主導思想。《孫子兵法·軍爭篇》:“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兵以詐立”就是要求在戰爭中運用謀略,出奇制勝。《孫子兵法·計篇》:“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這里的詭道十二法就是“兵以詐立”的具體運用。“以利動”就是要求在戰爭中因勢利導,抓住有利時機采取行動。《孫子兵法·計篇》:“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吳子·料敵》:“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涉長道后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沖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這顯然與西周、春秋時期的“禮戰”觀念有著根本的不同。“兵以詐立”“以利動”等新的戰爭觀念的確立,也是周代軍禮在戰國時期走向解體的一個重要標志。
周代軍禮在戰國時期走向解體,是指軍禮失去了過去維護“親親”“尊尊”的政治功能,并不意味著軍事禮儀退出了歷史舞臺。戰國乃至后來歷代王朝,在軍事活動中仍然舉行祭祀、誓師、凱旋、慶賞等活動。然而,這種禮儀活動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軍事儀式,其內涵及其所發揮的功能,與周代軍禮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西周、春秋時期以分封制、宗法制和禮制為核心的政治形態,實質上是基于宗法血緣關系上的血緣政治;戰國時期以郡縣制、官僚制、法治為核心的政治形態,實質上是基于地域關系上的地緣政治。戰國時期,列國通過變法運動,最終以地緣政治制度取代了西周、春秋以來的血緣政治。戰國軍事制度與軍事觀念的變革,歸根結底是戰國政治、經濟變革在軍事領域的反映。周代軍禮興衰的歷史,是周代從血緣政治向地緣政治演進的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