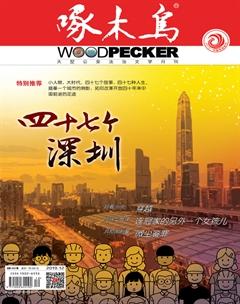十年后的情人節(短篇小說)
【日】東野圭吾

一
這家店位于高級商鋪林立的大廈一樓,入口直接面對院落,從外觀上看,極富家的情趣。推開厚重的、裝飾精致的門扉,一位戴著蝶形領結的男服務生謙恭地對他點頭致意,微笑著說道:“歡迎光臨!”
峰岸說:“我的座位是以津田的名義預訂的。”
“請跟我來!”
店堂內一長溜地排列著四人座的餐桌,約有兩成左右的客人入座。雖說今天是情人節,這個法式餐廳的經營狀況卻和平時差不多。餐廳一角的餐桌旁坐著一位女性,一見到峰岸就儀態萬方地嫣然一笑。她雖然比以前清瘦一些,但端麗的容貌風韻依舊,細長的鳳目更添魅力了。
峰岸看了一眼手表,比約會的時間早了五分鐘。“讓你久等了,真是不好意思。原本打算先來這兒等你的。”峰岸帶著歉意說道。
“是我來得太早,你不必介意。”那個女性的話語里略帶著鼻音,更顯現了高雅的氣質。
峰岸入座后,重新開始打量津田知理子的俏容,禮貌地說了一聲:“晚上好!”
“晚上好!好久沒見面了。”知理子也溫婉地回應道。
這時,一個餐廳主管模樣的人走過來,詢問客人需要什么樣的餐前酒。
知理子問:“來杯香檳怎樣?”
“好的,我贊成。”
餐廳主管走后,峰岸輕輕地說道:“真讓我意外,沒想到你約我到這兒來。”
“對不起,給你添麻煩了嗎?”
“哪兒的話。”峰岸使勁地搖搖頭,“要是麻煩的話我就不會坐在這兒,我是太高興了。老實說,我一直很想和你見面,就是沒有聯系方法,只好死心了。”
“現在好了。”知理子露出了潔白的牙齒,“你現在被稱為人氣作家,久不聯系是我失禮了。其實,我一直在關注你的作品。”
“什么人氣作家?”峰岸略顯窘態,“我已經一年多沒出新作了,這樣說不是取笑我吧?”
“你現在一定處于巧妙的構思之中,所以很高興期待你的下一部大作問世。”
“你看過我寫的書?”
“那當然,”知理子肯定地點點頭,“我看過你的所有作品。”
“哦,我太榮幸了!”
餐廳主管送來了香檳酒。峰岸激動地舉起酒杯提議道:“為我們的再次相見干杯!”
“也為十年后重逢的情人節干杯!”知理子舉起酒杯,高興地與峰岸碰杯。
峰岸一邊喝著香檳酒,一邊用眼角的余光窺望著知理子迷人的身姿。那穿著藏青色連衣裙的身材依然婀娜苗條,和十年前的體型幾乎一樣,況且現在剛三十出頭兒,正是一個成熟女性的黃金時代。
一個穿著黑色制服的男服務生拿來了菜單。
“你有什么忌口的菜嗎?”知理子翻開菜單,一邊看,一邊問。
“沒有,什么都可以。”
“那我就自己定了?”
“沒問題。”
于是,知理子很快地定了菜單,好像是情人節的特別套餐。
服務生走后,知理子笑道:“今晚就讓我請客吧。”
“不,那多不好意思。”
“沒什么,是我主動邀請你的。”
“那好吧……我知道了。”峰岸頷首同意,“你不要這樣客氣。”
“我沒有客氣。”知理子嬌笑著,晃動的右耳環在燭光下閃著迷人的光澤。
峰岸喝著香檳酒,心里想著餐后知理子會有什么打算。也許用完餐,離店時會有一種微醺的醉感,她會邀請他去另一個地方,比如酒吧之類的場所繼續消遣嗎?看來問題就在后面。
“啊,對了!”知理子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趕緊從旁邊的座位上拿起一個小小的紙袋,盈盈地笑道,“今天是情人節,我怎么把這么重要的事給忘了,你快拿著吧。”
“嗯,這是什么?”峰岸看了看紙袋里面,露出一臉的疑惑。紙袋里裝著一個四四方方的紙盒和一個粉紅色的信封,紙盒上印著一家著名西餅店的名字。
峰岸拿出那個紙盒,感慨地說道:“真是相隔太久了,情人節里得到巧克力是許多年前的事了,現在已經得不到表示愛情的巧克力了。所謂的愛情巧克力對我來說不過是句空話。”
“你沒有從那個愛你的她手里得到嗎?”
“愛我的她?你開玩笑了。如果有這個人,我還會在今晚和你見面嗎?”
“哦,那是你今年失去了她。”
“去年沒有,前年沒有,在此之前的好多年都沒有。”峰岸癡癡地看著知理子,認真地回答,“自從和你分別以后,我從沒有得到其他女人的巧克力,這樣的人到現在也沒有出現過。”
“真的嗎?別胡說了。”
“你怎么會這樣想?我說的都是真話。”峰岸繼續熱切地看著知理子。
“是嗎?”知理子緩緩地說道,“那就算是吧。”
“還在懷疑我?那好,先說說你的情況吧。我想,你一定找到合適的人結婚了吧?”
“很遺憾,我沒有這么好的運氣。”知理子聳了聳肩,“現在還是單身一人,所以才約你出來聊聊天。”
“是嗎?我剛才看到紙袋里好像還有一封信。”峰岸說著又看了看紙袋里面。
“信里寫的都是現在對你的心情,凝聚了這十年間的思念。”
“是這樣啊!”峰岸趕緊把手伸進紙袋里去拿那個信封。
“那太難為情了,現在不要打開,以后再看吧。”接著,知理子雙手合掌,“拜托!”
峰岸從那悅耳的聲音里獲得了難以言喻的甜蜜感。
“知道了!”峰岸把手從紙袋里縮回來。
真是個特別溫馨的夜晚!他從心底里發出了笑聲。
二
峰岸和津田知理子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十年前。那時候,知理子和峰岸同是大學時代某一社團的成員。該社團在夏季舉行海上運動,冬季舉行適合時令的各種運動,在學生中人氣很高,參加的人數眾多。峰岸大學畢業后,仍連續幾年參加了該社團舉辦的聯誼會。峰岸參會的目的與眾不同,主要瞄準那些女大學生,只要發現心儀的目標,就主動上去和對方交換聯系方式。
當然,這樣的狀況不太穩定,有時候順利,有時候一無所獲。不過,就在那一年,峰岸稍微有了些自信,因為他的境遇發生了變化。在此前不久,他獲得了推理小說的文學新人獎,首次作為青年作家嶄露頭角。文學新人獎是許多著名作家的搖籃,歷來受到世人的高度關注,所以他滿懷信心地認為,自己獲得文學新人獎之事定然能成為聯誼會上重要的話題。但是事與愿違。大家雖然對他獲獎有所耳聞,但反應卻很冷淡,似乎并不知道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
那次聯誼會上,主動接近他的只有知理子。知理子是個氣質優雅的標準美人,提出的看法十分入耳,峰岸對她也一見鐘情。
知理子很早就加入了那個社團,中途因去美國留學,暫時中止了社團的活動。在此前一年,知理子就參加了聯誼會,可惜峰岸當時有事沒有出席。知理子不僅知道峰岸獲獎的事,而且還盛贊他的作品。兩人越聊越熱乎,當場交換了聯系方式,并約定第二天再次見面。
從此以后,兩人開始了密切的交往。
獲獎作品在社會上引起轟動后,峰岸又接著發表了第二部作品,售書狀況十分喜人。于是,他干脆辭去了工作,成為一名專業作家,也有了充裕的時間和知理子約會。知理子每次從學校回家,都會順道去峰岸住的公寓,給他燒菜煮飯,用完餐后兩人一起躺在床上休息。
但是,誰也不會想到,這樣甜蜜的生活竟會突然中止。一天,峰岸收到知理子寫來的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我想了很久,還是決定分手。對你以往的關切深表謝意,衷心祈愿你大作不斷問世。再見!”
峰岸不清楚這到底是為什么,他不斷地給知理子打電話,無人接聽;又寫信詢問,也沒有回音。幾天以后,知理子的手機干脆停機了。峰岸原準備到她家門口等候或者去大學當面問她,但到最后還是下不了決心。因為他的自尊心很強,而且還有隱隱的擔心:一旦外界知道他老是騷擾和跟蹤一個女大學生,自己的名譽會受損,甚至連出版作品的銷路也會大受影響。
從此,知理子身在何處、在做什么,峰岸都一無所知。他只是埋頭創作,扎實地發表一篇又一篇的新作,牢牢地構筑起一個人氣作家的穩固地位。雖然曾先后和幾個年輕女性有過來往,但他始終對結婚沒有興趣,最后都一一分手了。峰岸對這些女人沒有留戀之情,唯一縈繞心際的只有知理子。因此,每當和交往的女性分手時他總會想起知理子,暗忖她過得怎么樣了。
上個星期,出版社轉來了一封粉絲寫給他的愛慕信,信封上還添了責任編輯的批注:寫信者好像是峰岸先生過去的熟人。
看到綠色信封上寫信者的名字,峰岸頓時激動得大口喘氣,寫信者正是津田知理子。
峰岸緊張地展開信箋,一行行娟秀的字跡清晰地出現在眼前:“好久沒見面了,還記得我嗎?我就是十年前承蒙你關照的津田知理子。我們曾一起參加過大學的社團活動,峰岸君是比我大八歲的前輩……那一次很失禮,所以現在還擔心您是否還在生我的氣。我深知您的才華,為您感到驕傲。這次寫信沒有別的意思,只想對當時的離開做個說明。如果您現在不想和我見面我也沒有辦法,希望您能給我解釋的機會。知道您很忙,打擾了,十分抱歉,等待您的回復……”
信的末尾還附有聯系電話和通訊地址。
峰岸反復地看著來信,每看一次,心頭更加躁動不安。看來,知理子確實希望和他見面,他也很想搞清楚當年分手的原因。
峰岸決定寫信回復。之所以不直接打電話,還是考慮到不馬上見面為好。一想起十年前她單方面匆匆分手的情景,就覺得現在不能操之過急,還是應該矜持一點兒。
峰岸給知理子寫了回信,淡淡地說:“來信收悉,若不影響日程安排,可以一見。”
信發出后不久,知理子就來了回信:“不管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務必見上一面。”
峰岸又回了信,信中寫了幾個合適的日期,表示見面的時間和地點由她決定。
知理子很快來了回信,決定見面日期是2月14日晚上,地點是位于市中心的這家著名的法式西餐廳。
知理子的選擇正中峰岸下懷。她在合適的日期中特意選了情人節,也許是為了表明自己想回到他身邊的意思吧。
三
“……那部作品讓我非常欽佩,寫得確實好!”知理子一邊手持刀叉用餐,一邊不停地發出贊嘆。
“你這樣說我很高興。那部作品確實傾注了我很大的心血,我也很有自信。沒想到你這么熟悉我的作品,真的把我的作品全看了?”
“你不是第一次聽人這樣說吧,是懷疑我撒謊嗎?”
“我原以為你可能看過我的一兩本小說,誰知你都看過。”說到此,峰岸輕輕地點點頭,“多謝了!”
知理子笑道:“不必多禮,我們只要經常快樂地聚會就行了。”
峰岸表示同意:“好的,我會努力的。”
這時,服務生陸續上了海鮮料理,有奶油焗日本沼蝦和扇貝慕斯。
峰岸喝著白葡萄酒,吃著海鮮,覺得前菜就這么精美,主打的料理一定是絕品了。
他問:“你經常來這家店嗎?”
知理子微微地搖搖頭:“談不上經常,平時極少來。”
“我早知道這家店的大名,但沒來過,是你讓我大開眼界。”
“請不要客氣!”
“這家店的料理一定很貴,不知你現在干什么工作?我整天埋頭寫作,有關你的信息一無所知。”
“我在一家普通的公司工作,主要業務就是人事調配。經常在脾氣暴躁的上司和刁鉆自負的下屬之間左右為難,每天只能小心翼翼地過日子。”
“哎呀,這可不是你應有的形象。我還以為你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比如公司的秘書,或者大飯店的高級管理人員之類的美差。”
“我現在已經無法想象自己十年前的形象了。”知理子有些遺憾地吸了吸鼻子,“不說這個了,我還有件更重要的事要說。”
“什么事?”
“小說《深海之門》你是怎么寫出來的?”
“你說的是它?”峰岸不由自主地皺起眉頭,“想起了就煩惱。”
“煩惱?可它引起了我的注意,不好意思。”
“你怎么連這樣的小說都看了?”
“但我沒有全部看完。哎,我想問一下,為什么登了一半就突然中止了?是內容不合讀者的口味嗎?我看好像不是,究竟怎么啦?”
“其實也沒什么,我只是暫時中止刊載,想重新修改后再發表。”
“為什么?我從沒見過這樣的事。”
“那部作品有點兒特殊,我一邊寫,一邊思考情節的展開,寫得不順就發生了中間間斷的情況。我也是普通人,發生這樣的事很正常。”
“你的工作真夠辛苦的。”知理子嘆了一口氣,伸手拿起了葡萄酒杯。
她說的那部連載小說是從去年開始刊載的。直到秋天,峰岸都寫得很順暢,但到后來就出現了麻煩。接下來該怎樣寫?為什么當初沒有想好完整的小說提綱?峰岸對這些問題很苦惱,最后不得不暫時中止連載。由于不愿再續寫,所以他在社交場合都盡量避免和雜志的責任編輯見面。
此時,峰岸的心中不免有些著急:知理子還要繼續這樣的話題嗎?難道大談我的作品才能滿足她的好奇心?這樣豈不白白浪費了約會時間?借這次難得的機會,我必須聽她解釋十年前突然離去的原因。
餐廳的主管走過來,對知理子輕輕地耳語了幾句,又往兩人的酒杯里倒了些紅葡萄酒。接著,服務生送上肉類料理,是非常鮮美的小羊肉。
知理子緩緩地開口道:“我非常幸運,能夠一邊和小說的作者用餐,一邊談論小說,這樣的讀者一定是前所未有的。”
“是啊,是啊。”峰岸有些不耐煩了,“你叫我來不會光談小說,想必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對她來說這就是重要的事。”知理子沒有理會峰岸的話,繼續說下去,“她想了解你的小說,因為她原本就喜歡小說,而且特別喜歡推理小說。”
“她?”
“藤村繪美。當時和我們在同一個社團,估計你也和她見過面。”知理子平靜地說道。
藤村繪美——聽到這個名字,峰岸的頭腦里立刻浮現出一個女人的面容,他感到全身發熱,心臟也在劇烈地跳動著。
“嗯……”峰岸想拿起葡萄酒杯,但是手在不停地顫抖,只好作罷,“我的印象中好像沒有這個人。”
知理子微微一笑:“她和我是同鄉,大學一年級就加入了社團,我倆的關系很好,經常在一起玩。大二那年,我決定休學一年去美國,她竟然害怕寂寞哭了起來。她留著短發,身材高挑,你真的想不起來了嗎?”
“是啊,沒有一點兒記憶,在聯誼會上也沒見過。”峰岸歪著頭,做沉思狀。其實,他心里想的是:知理子為什么要拿她當話題呢?
“她確實沒有參加我們相識的那次聯誼會,在此前一年也沒有。因為她當時已經離開了人世。”知理子像宣告似的說了這句話,并用西餐刀利索地切下一塊小羊肉,“她是在自己的房間里上吊自殺的,那是我回國前幾個月的事了。”
峰岸倒吸了一口氣。知理子說這番話絕不是偶然的,顯然帶有某種目的。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為什么不吃了?這菜很鮮美啊,不趁熱吃怎么行?”知理子若無其事地發問,并不斷地往嘴里塞入好吃的小羊肉。
峰岸拿著刀叉沒有吃菜,有些不悅地回答:“我正要吃的時候你說出這些話來,我不喜歡聽死人的事,一下子就失去了食欲。”
“我這樣說就受不了啦?峰岸君,當作家的難道就不寫更難聽的話?沒想到你這樣神經質。”
“哦,沒什么,就當你在虛構一個故事吧。”峰岸說著用西餐刀切起一塊小羊肉,吃了起來。他什么都不想地大口吃著,雖然平時很喜歡小羊肉的肥腴,但這次卻吃不出一點兒美味,只是機械地咀嚼后直接送入胃里。
“繪美在大三的時候最后一次參加了聯誼會,那時我正在美國。峰岸君也去了,社團活動簿里有這樣的記錄。”
“也許我出席了,但對她還是沒有印象,最多只是打個招呼而已。”
知理子滿足地點點頭,正色地說道:“繪美就是在那次聯誼會的八個月后自殺的。”
峰岸喝了一口紅葡萄酒,把嘴里的小羊肉送下肚去。
知理子伸了伸腰,繼續說道:“如果繪美是自殺的,想必她有著極大的煩惱,但我懷疑這個結論。”
“她不是在房間里上吊死的嗎?”
“警方確實判斷她是自殺的,不過,我想也有例外,峰岸君一定也知道幾起制造上吊假象的殺人事件吧?”
“……你認為是他殺,有什么根據嗎?”
知理子逼視著峰岸的臉,說:“因為繪美沒有自殺的動機。”
峰岸的嘴角松弛下來:“有沒有自殺動機只有她本人知道。”
“當時繪美已經有了戀人,但她沒有告訴我對方的名字。我曾經多次收到她幸福滿滿的來信,說和那位先生特別談得來。可是,她的家人卻說繪美下葬時根本沒見過那位先生,你說怪不怪?”
“換個角度想想,會不會是繪美的戀人背叛了她。如果繪美承受不了這個打擊而自殺,不就一通百通了嗎?”
“繪美不是個脆弱的女子。”
“我剛才說了,別人是無法知道這事的曲折與原委的。”由于過于煩躁,峰岸的聲音不由得尖厲起來,他趕緊干咳一聲,小聲地說,“對不起!”
知理子垂下眼簾,輕輕地點點頭:“你說的也有道理。我當時正在美國,確實對繪美自殺的事一無所知,所以回國后想方設法地搜集有關繪美的信息。”
峰岸急切地問:“結果怎樣?”
知理子搖搖頭:“結果讓我很沮喪,什么都沒搞清楚。不僅不知道繪美自殺的動機,也沒找到能證明他殺的證據,而且她的房間井然有序,不像有盜賊入室的跡象。”
“哦,什么都沒有,那太遺憾了。”峰岸開始大口地吃著菜肴,漸漸品出了其中的美味。
知理子又道:“一年后,我對這件事也漸漸淡忘了,開始熱心參加社團組織的聯誼會,并有幸和你相識,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說到此,她別有深意地看了峰岸一眼。
峰岸干笑一聲:“我總算登上了你的故事舞臺。”
知理子繼續說道:“沒過多久,我就正式開始和你交往,并且每天都很快樂。你溫文爾雅,學識淵博,甚至躺在床上也能一邊和我說話,一邊構思小說,這讓我感到特別不可思議。雖然聽你講的故事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但我立刻否定了這種想法,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自己的錯覺。所以我始終保持沉默,只聽不說話。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確實看過那篇小說,你創作的只不過是復制品。那篇小說是一個業余作家寫的,名字就叫繪美。她最大的愿望是當作家,經常利用業余時間創作小說。”
四
餐廳主管悄悄地走過來,在峰岸的酒杯里倒了一點兒紅葡萄酒后又悄悄地離開。不過,峰岸已失去了舉杯喝酒的興趣。
“我剛才忘了說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繪美一直在寫小說,據說她從高中時代就開始寫了。不管是長篇小說還是短篇小說什么都寫,甚至還有今后要寫的小說的各種構思。可惜,由于她很害羞,從沒對別人說起過,寫好的作品也不讓人看。我曾經說想看她的作品,繪美雖然面露難色,但還是讓我看了她的一篇短篇小說。拜讀后我非常驚訝,因為那是一篇非常有趣的小說,寫一個發生在滿月之夜的女高中生的故事。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處處充滿著懸疑、驚悚的氣氛,令人讀后愛不釋手。”
知理子一口氣說完之后,看著峰岸認真地說道:“那個發生在月夜的故事和你跟我說的故事完全相同。”
峰岸感到非常口渴,把口水咽了下去,但在表面上卻顯得不以為然:“不同的人也會偶然編造相同的故事,這種現象很普遍。”
知理子反駁道:“故事的場景和結尾都相同,這是偶然的嗎?”
“也不能說絕對沒有這種情況。”峰岸的聲音壓低了許多。
知理子斷然否認:“如果兩個作者完全沒有關系,我也許會同意你的說法,但是他們可能在聯誼會上相識,你剛才也承認了這一點,所以不能視作是完全偶然的現象。”
峰岸睨視著知理子:“你到底想說什么?”
“從表面上看,繪美的房間似乎沒被人盜走什么東西,實際上她最寶貴的遺產——她從高中時代開始創作的小說和寫滿未來創作構思的筆記本——都不見了。我在她的房間里到處尋找也沒有發現,不僅沒有小說的復印件,連她平時寫作的電腦里也沒留下小說的底稿。于是我的心中產生了一個可怕的設想。”知理子大口地吸氣,呼氣,胸部也在上下起伏著,“我認為這些東西一定是被罪犯偷走了,這也是繪美被害的原因。看來罪犯急需得到她創作的小說和寫滿創作構思的筆記本。”
峰岸沉不住氣了,忍不住提高嗓門發問:“難道你說的那個罪犯就是我嗎?”
知理子沒有回答,輕輕地把刀叉放在盤子上。她在剛才談論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吃完了自己的餐食。峰岸的盤子里還留著三分之一的料理,但他完全失去了繼續用餐的興趣,也放下了手中的刀叉。
“在你獲得文學新人獎的三周之前,繪美遇害了。那時候,你應該知道自己的作品入圍了獲獎候選名單。問題是,你的入圍作品到底是哪一部小說?我推斷是繪美的又一部作品。當然,你一直對她保密。如果這個推斷成立,作案動機就昭然若揭。當時你只是抱著試一試的僥幸心理讓作品參與新人獎的評選,沒想到竟然進入了最后獲獎候選名單,于是你感到十分焦慮。如果被評上文學新人獎當然很好,但也可能在繪美面前暴露了自己。你很清楚,繪美不可能對這樣的丑行保持沉默。事已至此,你更沒有勇氣向她坦白一切。所以,是你讓她走上了死亡的不歸路。”
這時候,服務生上來給兩人換上新的盤子。
“不要說了!”峰岸不快地說道,“我們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但今天好像來的不是時候,聽的都是毫無意義的廢話,所以我不得不先走一步了。”
“下面只有甜品了,你就不能再坐一會兒嗎?況且我只是閑聊,從沒對其他人說起過。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覺得還是留下來說明一下更好嗎?”
聽了知理子的話,剛起身的峰岸又坐了下來,覺得她的話不無道理。
“現在有證據嗎?就是所謂我殺害她的證據。”峰岸壓低嗓音問道。
知理子揚起雙眉:“她?什么她?那個女性不是她,她是繪美!”
峰岸歪著頭,緊咬著下唇,一時不知道說什么好。
“好了,好了!”知理子微微一笑,“那時候沒有證據,不過還存在一線希望,就是那臺供繪美寫作用的電腦。雖然罪犯刪去了電腦里的全部資料,但可以通過硬盤進行復原。”
“你已經……復原了嗎?”
“我花費了好長時間,在五年前終于完成了復原,并在它的幫助下獲得了強有力的證據。”
“強有力的證據?”
就在峰岸皺眉苦思的時候,服務生上了甜品。那是巧克力和黑櫻桃的精致搭配,巧克力被特意做成“心”的形狀。
知理子繼續說道:“通過硬盤復原,我終于看到了繪美創作的六部長篇小說和九部短篇小說,以及筆記本里的許多創作構思。其中一部短篇小說和你在床上告訴我的故事十分相似,另一部長篇小說也和你獲得文學新人獎的作品完全一致。通過深入的調查,發現你迄今為止發表的所有作品幾乎都是以繪美的小說或創作的構思為藍本寫的。還有少數幾篇是你在繪美的短篇小說中注水后擴充而成的。”
峰岸的視線落到餐桌上,但他沒有心思去享用那精美的甜品。
知理子說的一切都是真的。
和知理子一樣,峰岸和藤村繪美也是在聯誼會上相識的。由于興趣愛好相同,峰岸主動接近了繪美,繪美也很欣賞峰岸,兩人很快就開始了交往。
不久,峰岸知道繪美想當作家的志向后非常驚訝,因為他也有同樣的愿望,讀了繪美的習作之后他更是大吃一驚。
這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女大學生寫的作品嗎?小說的筆法老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且構思新奇,是一篇篇充滿魅力的優秀推理小說。它的整體結構縝密,幾乎沒有破綻,和自己的作品有著云泥之別。
一天,趁繪美洗澡的時候,峰岸把她電腦里的所有作品和相關資料全部拷入自己隨身帶來的U盤之中,準備作為自己創作時的參考。
但是,就在他躲在自己的房間里閱讀那些作品的時候,巨大的誘惑使他不由自主地產生了某種沖動,很想把其中的一部長篇小說拿去參加文學新人獎的評選。
峰岸曾經多次參加過這樣的活動,最好的成績也只是獲得一次通過。
這樣的想法越來越強烈,他終于橫下一條心,將繪美的一部長篇小說偷去冒名參加評選。當時他根本沒有想到作品會獲獎,只覺得若能二次通過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沒料到評選的結果遠超自己的預期,那部入圍的作品竟然進入了獲獎候選名單。工作人員打來電話說,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整個評委會都認為,該小說是最有希望的獲獎候選作品。
峰岸真的焦灼起來。他已無路可退,沒法兒對評委會說這部作品不是他寫的。
當給繪美服了安眠藥,在她脖頸處套上繩索的時候,峰岸幾乎沒有一點兒罪惡感。導致他作案的動機就是:只要這個女人死了,那些作品和資料就全部屬于自己了。也許,當他把電腦里的內容拷入U盤的時候,就萌生了這個邪惡的念頭。
作案后,他把繪美電腦里的所有內容都刪除了。他想,如果警方把繪美的死視作自殺的話,就不會對電腦里的內容進行復原。
峰岸盯著知理子的臉,覺得必須設法讓她閉嘴。
“很遺憾,你復原的內容不能作為我犯罪的證據!”
“為什么?”
“因為沒有客觀性。她的電腦里存入和我作品相似的習作,并不能證明是我剽竊的。反過來說,不管哪一位讀者看了我的小說,都有可能把我的作品存入他的電腦。”
知理子瞇起迷人的鳳目,臉上充滿了自信:“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我認為,你在兩年前發表的短篇小說就抄襲了繪美的習作,因為在五年前我就看到過那篇小說。”
“說五年前只是你的一面之詞。”
“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想法。”
“難道還有其他的證人嗎?是協助你復原的人吧?只要你們事先統一了口徑,隨便怎么說都可以。”
“你錯了,說明這個問題只能靠‘鑒別。”知理子一字一句地從牙縫里蹦了出來,“這是無法統一口徑的。”
“鑒別?”
知理子從旁邊的包里取出一沓文件放在餐桌上,不慌不忙地說道:“數量太多,我只復印了一部分。這是我從警視廳鑒識課拿到的鑒別報告書。請你好好看看,上面寫的是不是五年前的日期?”
峰岸取過那沓文件一看,封面上清晰地印著“警視廳鑒識課”一行字,還有鑒別責任人的印章。
“這……這是什么?”
“這是鑒別報告書,里面記錄了繪美電腦里的內容復原后的結果。”
“純粹是捏造!”
“什么?”
“這種報告書一般人是拿不到的,肯定是假的。”峰岸順手把那沓文件扔在餐桌上。
知理子舒了一口氣:“請把剛才給你的盒子打開看看。”
“什么盒子?”
“放巧克力的盒子。”
“干什么?”
“打開看看就知道了。”
峰岸疑惑地從紙袋里拿出那個包得四四方方的小盒子,撕下包裝紙,打開扁平的四方形盒蓋,就在他往里看的一瞬間,臉色頓時煞白,兩手不由得顫抖起來。那個盒子啪的一聲掉在地板上,盒子里的東西也滾了出來。
那是一副閃著銀光的手銬。峰岸的目光呆滯了,死死地看著知理子,發現她的手上不知什么時候拿了一樣東西。費了好半天工夫,終于看清那是一枚警視廳的徽章。
知理子平靜地說道:“重新介紹一下吧,我是警視廳搜查一課的津田知理子。”
五
知理子撿起掉在地板上的手銬:“對不起,這個可能讓你看著不舒服了。”
峰岸無言以對,只覺得頭腦中一片混亂。各種想法紛至沓來,一時又理不出頭緒。
知理子收起放在餐桌上的鑒別報告書,嚴肅地說道:“這本鑒別報告書是真的,是通過正規手續完成的,作為審判資料完全沒問題。”
她把報告書放進包里,峰岸呆呆地看著她一言不發。
“難道你是警察……”峰岸終于艱難地開了口,“你剛才不是說你在公司里干人事調配嗎?”
“警察們通常把自己的職場稱為‘公司。至于我說的‘人事調配也是事實,它包括安排警員查訪線索、暗中監視犯罪嫌疑人等內容。”
峰岸頓時感到呼吸困難,煩躁地松開領帶。他萬萬沒想到知理子竟然親口說自己就是一名警察。
知理子緩緩地說道:“當警察是我從小就憧憬的職業之一,但真正讓我放棄大學學習,改入警校的動機還是繪美的自殺,我覺得必須通過自己的手徹底查清這個案件。為了復原繪美電腦中的相關內容,我花了多年的時間。其中不僅包括對整個案件的再次調查,而且要和上級打好招呼,征得他們的同意。雖然我從警校畢業時成績名列前茅,但進入警視廳后不過是個涉世未深、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姑娘,做什么事都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說到這兒,知理子又對峰岸說:“請把那封信拿出來!”
峰岸默默地從紙袋里取出那封信,知理子一把奪過去,從信封里取出一張折疊好的紙片,把它鋪展開來。
峰岸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張逮捕證。
知理子淡淡地說:“現在我以殺人罪正式逮捕你!”
峰岸慌不擇言地大喊:“請等一下,我不是罪犯,我沒有殺害繪美!”
“你還是到訊問室去辯解吧!”
“你聽我說!我確實剽竊了繪美的作品,這我承認!僅僅是一念之差。當時只是抱著半開玩笑的心情參加文學新人獎的評選活動。”
“你是什么時候把繪美電腦里的內容刪除的?”
“那是……在她自殺之前。”
“在繪美自殺之前?照理說,她一旦發現電腦里的內容被刪除了一定不會無動于衷的。”
“因為她那時還沒有發現,我真的沒有殺害她。所以你不可能有我殺害她的證據,對吧?”
知理子交叉著雙臂,冷冷地注視著峰岸:“有個問題想問你,那些發表的小說都是你自己寫的嗎?”
“那當然,是我自己寫的。”峰岸急切地回答。他不明白知理子為什么要提這樣的問題,“其實,認識繪美之前我已經發表了好幾部小說。”
“這個我知道,我已經審閱了你的全部作品。不過很遺憾,除了以繪美的習作為藍本的小說之外,其他的都是失敗之作,根本無法和繪美的作品相比。你自己不清楚嗎?”
面對知理子的咄咄逼問,峰岸感到理屈詞窮,難以應答。
確實如此!盡管自己也很努力,一心想寫好小說,但寫出來的作品都不行,特別是現在,已經到了江郎才盡的地步。
知理子又問:“你想過沒有,為什么我之前沒來找你呢?五年前我就復原了繪美電腦里的內容,為什么要等到現在呢?”
峰岸渾然不知,只是默默地搖著頭。
“我是在等待,等到你把繪美的全部作品和構思用完之時。到了那一天,你必然會拿出那部作品,就是你一直不敢用的小說。”
“不敢用的小說?”
“繪美遇害的時候,正在創作一部長篇小說,就是你一直不敢用的小說,因為那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你根本不知道小說的結尾,不知道繪美將給小說安排怎樣的結局。但是,從去年春天開始,有雜志約你創作長篇連載小說,你不得不用上了它。當時你也許很自信,覺得有能力狗尾續貂,沒料到這種想法實在太天真了,隨著繪美寫的部分不斷減少,你卻想不出與之契合的后續部分,最后不得不中止連載。”說到這兒,知理子兩眼放光,“那部小說的名字就叫《深海之門》,是你為之黔驢技窮的長篇連載小說。”
峰岸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知理子的推理正中他的要害。
在此緊要關頭,他還想負隅頑抗:“你說的和那個案件有什么關系呢?”
“關系大著呢。中止連載的那一期內容就是繪美活著時寫的最后一部分。”
“如此說來……”峰岸欲言又止,感到自己的臉上已經失去了血色,一定很難看。
“你總算明白我的意思了。”知理子的嘴角漾著微笑,“我不僅復原了繪美電腦里的所有內容,也鑒別了她留下的多個文件夾,終于使真相大白。其實,在繪美的遇害之日,她正在執筆寫小說,在你來到她房間之前,一直對著電腦潛心創作。我看了她最后創作的內容,知道她是突然停筆的。這也意味著那天你去了她的房間,使她不得不臨時放下手里的工作。”
“我在她的房間里又能說明什么呢?”
“你敢說你在她的房間里沒碰過她一個手指頭?還是說只是默默地看著她上吊?或者說你去的時候她已經上吊了?你就讓她的身體吊著,自己心安理得地離開了房間?但愿法官能采信你編造的謊言。”
面對知理子連珠炮似的發問,峰岸迫不及待地起身離開餐桌。就在他即將走出門的時候,突然折回來一動不動地呆立著。因為四周有幾個男子走過來圍住了他。這些人都是剛才散坐在附近餐桌的客人,還包括那個餐廳主管。他們都目光炯炯地逼視著峰岸。
“這家餐廳是我父親開的。”背后傳來了知理子的聲音,“今天是情人節,正是他賺錢的好時機,但為了協助我破案,他慷慨地同意我包下餐廳。”
峰岸驚異地轉過身子:“為什么要弄這樣大的排場?”
“為什么?當然不僅僅是為了破案。我想十年后相見應該舉杯慶賀一下,對你來說不也是一件好事嗎?現在好了,你不必為剽竊小說而煩惱,也可以摘去作家的假面具,肩上的重擔都可以卸下了。”
峰岸無話可說。沒想到知理子已經成為一名警察,而且如此透徹地洞悉了他所有的罪行,他徹底絕望了。
“把他帶走!”知理子的聲音冷峻而又響亮。
兩個健壯的男子立刻靠近峰岸,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通過這個簡單的動作,使得峰岸在強力的壓制下無法掙扎,像一只泄了氣的皮球癱軟下來……
“主任,你也走嗎?”那個餐廳主管模樣的人謙恭地問道。
“我隨后就來!這兒還留著好些甜品,不吃完怪可惜的。”知理子一邊說著,一邊吞下了一顆巧克力。
責任編輯Euclid Frakturo@p謝昕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