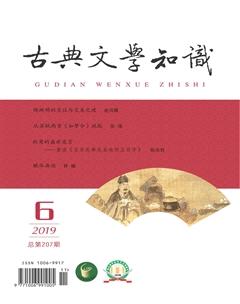一份音韻學初學筆記(中)
王小盾 閻莎莎
1988年7月24日下午4:30,我到達上海公平路碼頭,正式結束了緊張而充實的音韻學之旅。五十來天的記憶,從此和這本筆記本一起,被我存進了一個小抽屜。我不常打開它,那些寶貴的知識便逐漸蒙上灰塵,隨時光銷蝕。今天,當我重讀這份筆記的時候,不免感到陌生,因而也感到痛惜。不過,根據這份筆記,我畢竟可以總結出以下幾條音韻學教學經驗。
第一條經驗是從中古音入手。最初半個多月,我們實踐的就是這條經驗。這一做法和清儒依據《詩》韻、諧聲資料而進行的上古音研究不同,乃反映了高本漢以來的新認識。選擇中古音的理由主要有四條:其一,在隋唐之際,出現了《切韻》、《經典釋文》等語言學典籍。它們對中古漢語的聲、韻、調作了清楚的分類。依靠這些資料考察古音,才能得到比較準確的知識。其二,中古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移民運動,造成了復雜的方言現象。這些方言的文讀音與中古音緊密對應,為構擬中古音提供了切實的依據。其三,中古時期,中原文化呈現強勁的傳播態勢。漢字讀音流傳至日本、越南、朝鮮,同樣保持了與中古音的緊密對應。其四,佛經翻譯始于東漢,盛于南北朝至唐代,為考察中古音提供了豐富的梵漢對音資料。總之,漢語音韻學教學應該以中古音為綱領。這不僅因為中古音有豐富的資源遺存,而且因為中古音有特殊的歷史地位,即上承上古語音、下啟近代語音的地位。
同以上情況相聯系,《切韻》的性質問題是漢語音韻學的關鍵問題。現在,學術界基本上接受周祖謨先生《切韻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1963)一文所表達的意見,認為《切韻》的音系基礎是一個文學語言語音系統,這一系統是從公元6世紀以前金陵、洛下讀書音中折中出來的。也就是說,要理解《切韻》的功能,就要理解古代“雅言”“通語”同方言的關系,理解古代教育的意義,也理解洛陽在語音學中的地位。我們知道,早在夏商時期,洛陽一帶就是中華民族的活動中心。到周代,洛陽被周公建為東都。后來平王東遷,洛陽進一步成為各諸侯國朝聘會盟之所。洛陽王室語言遂成為周代的“雅言”。東漢定都洛陽,當時儒生鄭玄、許慎等所作的經典音注,也依據洛陽太學的標準音,于是有“洛生詠”一說。晉室南遷以后,洛陽話成為金陵政權的行政用語和教育用語。所以唐李涪《刊誤》說:“凡中原音切,莫過東都。”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說:“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
以上情況說明什么呢?首先說明,漢語音韻學研究主體上是關于漢語通用語的研究。這門學問不僅屬于語言學,而且屬于歷史學。其次說明,漢語音韻學的現代方法是歷史比較法與歷史層次分析法。歷史比較法來自語言譜系分化理論,主張通過多種方言或親屬語言之間的差別來探索語言的發展規律。歷史層次分析法來自語言接觸理論,主張把在同一個共時平面上雜糅的不同歷史層次剝離開來。從中古音入手,意味著,我們的音韻學教學是在新的方法論的照耀下進行的。
第二條經驗是勤做練習,掌握音韻學基本技術。這條經驗貫穿了學習過程之始終。除背誦守溫36字母、《廣韻》206韻和等韻圖而外,我們做了以下練習:(一) 掌握《廣韻》的結構和基本字在中古的音韻地位。首先用《漢語方言調查字表》對自己進行方言(比如贛方言)調查,通過記錄、對比來熟悉國際音標,也熟悉這份《字表》。然后拿《漢語方言調查字表》和《廣韻》對讀,了解《廣韻》的結構,同時也掌握了三千個基本字的音韻地位。(二) 通讀《廣韻》,具體了解反切。其方式是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廣韻》各個小韻的代表字注國際音標,先注反切上字,再注反切下字。(三) 對讀《廣韻聲系》和《廣韻》,一方面掌握《廣韻》的諧聲系統,了解作為形聲字聲符之“語根”的古今變化;另一方面通過逐字核對《漢語大字典》,辨析出《廣韻》所收上古字。(四) 模仿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把《說文解字》9000字逐一填進分類框架,建立對于上古六元音系統的認識。(五) 參考鄭張尚芳——潘悟云的上古音理論,利用《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來進行上古音構擬。
進行以上練習,意義很多。首先是通過反復查檢,學會使用工具書,特別是《廣韻》、《漢語方言調查字表》和《古今字音對照手冊》。其次是準確掌握漢語音韻學的種種術語,既包括國際音標,也包括攝、等、反切等等。再次是用推字的方式,生動具體地認識基本字的彼此關系,由此了解從中古漢語到上古漢語的聲調、聲部和韻部,確定各詞語的古代同源詞。關于工具書,近年出版了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即鄭張尚芳《上古音系》。此書對上古音構擬成果作了系統總結,2003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至于如何掌握音韻學術語,則可以用“反切”作為例子。
我們在開學第一天,就接觸到“反切”這個術語,知道《切韻》和《經典釋文》都保留了大量反切資料,中古音的構擬立足于《切韻》反切,也知道陸法言是根據心中所認可的讀音來定每個字的反切的。但后來的練習大大深化了我們的認識。首先,知道《廣韻》的核心就是反切。據書中反切上字可歸納出36字母,據書中反切下字可歸納出206韻。也就是說,反切提供了較韻類、小韻韻類更基本的信息;可以通過反切系聯,超越韻母層面,精確地掌握《廣韻》的聲母系統。其次,知道可利用的反切資料很多,情況頗復雜,進行反切要利用李榮《切韻音系》、邵榮芬《切韻研究》等成果。再次知道,在一般情況下,反切上字反映聲母信息,反切下字反映韻的信息(而不是韻母信息),若有例外,便可能是錯字,或者是抄自古代某個音注的僻字。除此之外,我們還知道:反切中必有介音信息,或表現于反切上字,或表現于反切下字,雖不固定,但不會缺失;反切中也有等的信息,若反切上下字都不是三等字,則被切字也不會是三等字;若反切上下字都是三等字,則被切字必是三等字。總之,進行反切,前提是弄懂中古音。要切出一個字的中古音,便要把反切上下字的字音從現代轉換為中古。
第三條經驗是立足于學術前沿。在我們進行音韻學學習之前不久,潘先生撰寫了一篇《高本漢以后漢語音韻學的進展》(《溫州師院學報》1988年第2期)。此文所討論的9個問題,正是我們學習的重點。這9個問題是:(一) 關于《切韻》性質的討論,認為高本漢所構擬的《切韻》音系代表6世紀前后最有權威的文學標準語。(二) 《切韻》的韻類音值,認為《切韻》共有6個元音音位,14個音位變體。(三) 中古的等和介音,認為要聯系中古的介音系統來解釋等,比如宋人韻圖中二等諸韻,帶r介音;宋人韻圖中的重紐三等諸韻,帶ri介音;宋人韻圖中的重紐四等諸韻,帶j介音;宋人韻圖中的一等和純四等諸韻,不帶圓唇介音以外的任何介音。(四) 《切韻》的聲母音值,認為《切韻》包含以下聲母系統:
(五) 上古韻部的劃分,(六) 上古韻母的音值,(七) 上古的韻尾,認為上古有6個主元音、10個韻尾,構成60個韻部、4個韻部類,如下:
(八) 等的上古來源,認為中古的等是上古介音發展的結果,中古的三等在上古來自于無標記類,松而短;一、二、四等來自于上古的標記類,緊而長。(九) 上古聲母,認為來母最早為r,喻四在上古是一個次濁音(l),照組來源于K′lj或P′lj,若干鼻音來自鼻音加塞音或鼻音加塞音加流音的復輔音聲母,等等。文章最后說:“每一門學科的發展,關鍵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突破性改變。從這個意義看,漢語音韻學已經經歷了兩個階段。顧炎武開始的乾嘉學派是漢語音韻學的第一個階段,或者說是漢語音韻學的前科學期。高本漢把西方的語言理論帶給漢語音韻學,從此漢語音韻學擺脫了經學的隨從身份,而以獨立的學科得到科學的、系統的研究。但是,這一階段的研究方法還只能是史學的、描寫的。近年來,漢語音韻學逐漸接受現代科學思潮和方法的影響。我們相信第三代的漢語音韻學一方面將以通過廣泛的歷史比較建立漢語歷史形態學為其特征,另一方面語音規則的研究將具有更多的定量思想、演繹思想,更大的解釋能力,一句話,將逐漸地向精密科學靠攏,變得更加規范、更加成熟。”這些話,正好概括了本次音韻學教學的基本精神。
2019年3月17日,我拜訪潘悟云先生,說起1988年的故事。我說:“當時一起學習音韻學的四個人,除我以外,都有一定的基礎。這對您的課程設置是有挑戰的,您要面對不同層次的學生。請問您是如何進行教學設計的呢?”潘先生回答了以下一段話:
那年的講課內容,首先采用了當時的最新成果,即上古音構擬體系的新框架——“鄭張—潘氏”框架。1969年鄭張提出七元音系統,囑我模仿董同龢,把《說文解字》9000字逐一填進此框架。填法類似于拼圖游戲,但發現有空檔,有重復。于是改成六元音系統,便填進去了。也就是說,六元音系統是在1969年,經過驗證后改進的系統。這個六元音系統后來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例如美國的包擬古(N.C.Bodman)、白一平(W.H.Baxter,1971年)、俄國的斯塔羅斯金(S.A.Starostin,1989年),都提出了同樣的系統。這說明音韻學成熟了。不同的人在互不接觸的情況下提出同樣的系統,原因在于他們使用了相同的方法和材料。這一系統現在成為國際學術的主流。比如沙加爾(Laurent Sagart)、白一平2015年所著Old Chinese,在美國獲得大獎,反響很大。我們在1988年講課,就用這一系統。另外,當時上古聲母也定下來了。
2005年,開上古音構擬國際會議,來了很多大學者。會是法國學者沙加爾在2003年提出來的。開會的意義是支持我們的上古音學說。這也意味著,音韻學的主要骨干,在同一主題下,取得了共識。所謂“骨干”,包括以下四個人:俄國的雅洪托夫(S.E.Yakhontov),其代表作是關于二等字復輔音和上古元部的兩篇文章(1960);法國的奧德里古爾(A.G.Haudricourt),他提出中古漢語去聲為S、上聲為喉塞音;加拿大的蒲立本(E.G.Pulleyblank),他原是中古史學家,因同西域語言發生關系,注意梵文譯音,因而采用了文獻研究加譯音研究的新方法;美國的包擬古,白一平的老師,1968年提出六元音系統。
總之,1988年的講課內容反映了當時國際音韻學的主流。這主流由六個共識組成,在巴黎會議上得到公認。1988年已經有了主體框架,后來作了少量的深入和改進。這六個共識是:(一) 上古漢語為六元音系統;(二) 來母上古音是*r;(三) 以母上古音是*l;(四) 二等的來源為*Cr;(五) 上聲在上古帶*尾;(六) 去聲在上古帶*s尾。
由于方法、材料一樣,所以得到的認識框架就一樣。這方法有三:一是歷史比較之法;二是從董同龢開始的內部擬測之法;三是蒲立本實行的對應比勘之法。材料則包括七方面:一是上古押韻資料;二是漢語方言;三是域外譯音;四是越南漢越語;五是朝日漢字音;六是梵文對音;七是周邊民族的語言。其趨勢則是音韻學同文字學相結合。
聽完潘先生這些話,我覺得慶幸,覺得1988年是我的幸運年。沒想到,在那時,我一不小心就看到了漢語音韻學的巔峰。
(作者單位:溫州大學人文學院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