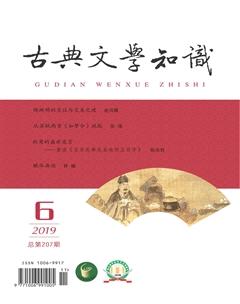物象離合
張波
《十離詩》是薛濤詩作中飽受爭議的作品。譚正璧先生《中國女性文學史》認為此詩系于薛濤名下,是其蒙受的千載不白之冤,“以后如有人重編薛濤詩,當刪去《十離詩》,以替她雪冤,才能有以對我們這位孤芳清拔的女詩人”(見劉天文《近百年薛濤研究述評》,《天府新論》2004年第3期)。可見《十離詩》中頗有些句子格調卑下,與歷來對薛濤詩風的定評不符。筆者也覺得在諸多版本中尤以《犬離主》“毛香足凈主人憐”一句難以卒讀,確實不愿意承認這是薛濤所作。然而上世紀唐詩選本《又玄集》在日本的發現,使得人們不得不承認《十離詩》確實是薛濤的作品,所幸集中所載此詩此句為“為知人意得人憐”,讀之似覺赧顏稍解。這之后愿意仔細去讀《十離詩》的人多了起來,于是有人說這是落入社會底層的女性微弱的抗爭,這是對兩性不平等的殘酷現實的吶喊,等等不一,試圖為女詩人尋找回合理的尊嚴。
薛濤詩不作雌聲,有格調,歷來有定評。晚唐《詩人主客圖》將薛濤列為“清奇雅正”之屬。宋代《宣和書譜》稱薛濤“詩思俊逸,有林下風致”。明代《唐音癸簽》有“工絕句,無雌聲”之評,《唐詩鏡》稱濤詩“氣色清老”。明人稱其“士女行中獨步”(楊慎《綠窗女史》),清人則云“非尋常裙屐所及”(《四庫全書總目》)。從《又玄集》的選詩標準“清詞麗句”來看,于薛濤詩僅選兩首,《犬離主》占其一,說明選者認為此詩可以窺見薛濤詩風之一斑。那么,這位非同一般女流、歷事十一鎮節度使皆以詩受知的薛濤,在她所創作的頗為特別的《十離詩》中,究竟呈現了怎樣的風貌?
《十離詩》的創作背景,歷來有兩種說法。據萬歷三十七年洗墨池刻本《薛濤詩》此題下記云:“元微之使蜀,嚴司空遣濤往侍,后因事獲怨,遠之。濤作《十離詩》以獻,遂復善焉。”此說最早出自《唐摭言》:“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后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獻府主。”宋洪邁《萬首唐人絕句》選此詩即題作“十離詩上浙東元相公”,署名“薛書記”。而此中之薛書記顯然不是薛濤。另一說法即《十離詩》是寫給西川節度使韋皋,最早見載于后蜀何光遠《鑒誡錄》,但按其所言,薛濤所獻為《五離詩》。而《五離詩》實則《十離詩》中的犬、魚、鸚鵡、竹、珠五題。兩說互有抵牾,因此《詩話總龜》《事文類聚》等書輯錄時皆兩存之。明代萬歷年間蔣一葵《堯山堂外紀》綜合兩說,認為薛濤“初為連帥所喜,因事獲罪,怒而遠之,作《十離詩》以獻”。
在最早選錄此詩的《又玄集》中,《犬離主》前一詩題作“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今學者一般將《十離詩》與之一起討論,認為作于同時。因《十離詩》中有兩處提到“四五年”(“出入朱門四五年”、“戲躍蓮池四五秋”),學者由此推斷薛濤在韋皋幕中四、五年時獲罪被罰。被罰時間,朱德慈先生《薛濤生年再考》認為“至多在貞元十三年(797)”,因貞元十二年(796)韋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能稱“韋相公”。劉天文先生《薛濤生年考辨》則認為被罰時間在貞元十六年(800),因貞元十二年至貞元十七年(801)韋皋加中書令應稱“韋令公”之前,恰是五年時間,符合詩中自述。不過以詩集版本而言,“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之題雖在《又玄集》《成都文類》《唐詩紀事》《唐詩鏡》《詩女史》《艷異編》皆同,而《萬首唐人絕句》題作“陳情上韋令公”,萬歷本《薛濤詩》題作“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這樣看來,由詩題所涉稱謂“韋相公”推測的時間點恐怕很難達成一致。
一個顯見的問題是,并無文獻證據指明薛濤“因事獲罪”導致“罰赴邊有懷”,因此《十離詩》作于罰邊期間只是一種推斷。薛濤被罰赴邊的原因,張篷舟先生據《鑒誡錄》所載認為薛濤因頗得韋皋寵念,使車至蜀,每先賂濤,濤亦不顧嫌疑,是以獲罪。而據《鑒誡錄》載薛濤因獻詩“情意感人,遂復寵召”。說明《十離詩》打動了韋皋,起到了實際的作用。那么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即獻詩促成了薛濤從邊地被釋回。
韋皋鎮蜀長達二十一年,因抵抗吐蕃屢有邊功。觀《舊唐書》所載韋皋對邊地歷次用兵,薛濤獻《十離詩》可能在貞元十七年(801)。此年韋皋對吐蕃全面用兵,多路兵馬深入蕃界,其中有“都將高倜、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又有“雅州經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租、松等城”,與薛濤罰邊詩所述“烽煙直北愁”、“不敢向松州”地理方向一致。無論薛濤是因與聞幕府機要獲罪,還是因某些史料所稱的“營妓”身份,本就需要隨軍酬唱,只有跟隨勝利之軍才有可能再次回到成都。而此年的戰事“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轉戰千里,蕃軍連敗”。也正是這一年,韋皋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薛濤在此時獻詩陳情,才有可能使韋相公或韋令公的稱呼皆具有流傳的合理性。
薛濤很可能是在邊地感受到戰爭的殘酷、受到真實磨難之后,經過深思熟慮創作了《十離詩》。因此這一組詩既具有種種直白、顯露的物象與結構,而細味其內在,又似乎有某種層次和邏輯。明代鐘惺《名媛詩歸》對這組作品有頗為中肯的評價:“《十離詩》有引躬自責者,有歸咎他人者,有擬議情好者,有直陳過端者,有微寄諷刺者,皆情到至處,一往而就,非才人女人不能。蓋女人善想,才人善達故也。此《長門賦》所以授情于洛陽年少也。”善想與善達確實是《十離詩》最令人稱奇的特點。善想表現在詩中采用了物象紛呈的喻體傳遞作者心緒,善達則說明詩作達成了改變命運處境的效果。而要想解讀作者如何想、如何達,我們需要將十首詩中包含的物象進行分拆重組。
《十離詩》的詩題結構是“某離某”,前者自喻,后者比喻韋皋,這似乎沒有疑問,然而,詩作中運用了多種物象去比喻薛濤與韋皋之間關系,通過對這種關系的描述,傳達作者的苦心孤詣。既往論者有認定《十離詩》“殊乏雅道,不足取也”(《歷朝名媛詩詞》),這種判斷或許是基于十首詩對人的物化和矮化,但其實卻忽視了物象之間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正是作者表述情感復雜性的重要手段。
《十離詩》的詩題中主語所包含的物象按照基本屬性可以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是動物,共有六題:犬離主、鸚鵡離籠、魚離池、馬離廄、燕離巢、鷹離鞲。其中,前三種是家中馴養之物,離開主人提供的環境無法生存;后三種雖亦從屬主人,但是與外界有聯系,離開主人提供的環境并不會有生命危險。對比這兩類動物,實際上有格調高下的區別。作者究竟是乞憐犬、籠中鳥、池中物,還是追風馬、筑巢燕、利爪鷹?這取決于不同的視角,也許以附庸關系來看,薛濤及笄不久,被節度使召入幕府侍宴,作為娛賓之妓,其身份是可悲的,但是后一組物象又體現了傾訴者內心對自己的定位和認同,她不是池中之物,而是有能力安身立命或遠走高飛的不凡之物。
第二類是物品,共有三題:筆離手、珠離掌、鏡離臺。這組物象同樣可以對照來看,在通常視角下,女性以色侍人,承歡受寵也不過“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珠離掌》),被主人捧在手心。然而薛濤不同,史載她八九歲知聲律,生平經歷十一任西川節度使,皆以詩受知,“言謔之間,立有酬對”(《鑒誡錄》),在蜀中有“女校書”的稱號。此校書之稱,或傳韋皋曾欲奏請,或傳武元衡鎮蜀時奏授。然在唐代,校書郎是唐代士人中進士后出仕的最優職位,恐難授予女性,故宋人陳振孫說“恐無是理”(《直齋書錄解題》)。但在蜀中“女校書”稱呼的流傳已經足以說明薛濤不讓須眉的文才。從這個視角看《筆離手》中“越管宣毫”、“羲之手里”,所用之筆為何等身價,筆下所寫為何等文字,便不難理解這是作者心中的自我。《鏡離臺》一首為全篇收束,這其實暗含夫妻的隱喻,由此上升到薛濤對此次被罰赴邊的深刻領悟,其結局是“無限蒙塵”,不得再出入“華堂”“玉臺”,意味著她和韋皋恩愛關系的結束。
第三類是植物,只有一題:竹離亭。如果說薛濤將自己的身世、經歷和處境進行了物化的比喻,以三個層次分別對應三類關系的認知:對主從關系的認知、對夫妻關系的認知、對自我價值的認知。那么在前兩個層面都有外界和內在兩個層面的對比,第三類則沒有對比,只有自況。“常將勁節負秋霜”的竹就是薛濤的自況。現存薛濤詩集中還有一首《酬人雨后玩竹》,也特別寫道“眾類亦云茂,虛心寧自持”、“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奇”。不刻意彰顯而是虛心涵養,直到萬物凋零的晚歲方見竹之高標勁節。薛濤以竹自喻,被釋后隱居浣花溪,得享終老歲月,其人生命運也映襯了其自喻、自況實乃真實心跡。
賓語位置的物象是韋皋的象征,這種象征性也可以通過歸類看出層次關系。第一層級的三個詩題是:犬離主、筆離手、珠離掌。這三個詩題中處于賓語位置的是主、手、掌,象征著人對物的控制。第二層級的三個詩題是:馬離廄、鸚鵡離籠、鷹離鞲。處于賓語位置的是廄、籠、鞲,分別是為馬、鸚鵡、鷹量身打造的所在,象征著三者與主人之間特殊的依附關系。稱霸一方的節度使韋皋,治下的一切人和物都依附于他,這是最本質的現實。《舊唐書·韋皋傳》載“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為屬郡刺史,又或署在府幕,多不令還朝”。正反映了中唐士人的普遍境遇,選擇到幕府就職,最現實的出路就是終身依賴幕主,仰仗幕主的提拔。另一方面,廄、籠、鞲也有束縛、羈絆的隱喻,因此這一層級的“離”也帶有主語脫離束縛的指向。
第三層級的三個詩題是:燕離巢、魚離池、鏡離臺。賓語巢、池、臺都含有家園的象征,它們作為地點的深層含義是主語的歸宿。而燕、魚、鏡在詩歌意象中經常指代夫妻關系,所以這一層級的“離”具有男女雙方分離的意味,從情感層面上說又帶有留戀不舍的意蘊。而位于最高一個層級的詩題仍是竹離亭。這首詩在最深層含義上暗示主賓分離的命運。細味《竹離亭》的主賓關系,竹生長于玉堂亭榭內自有一種風姿,然而玉堂并非竹的生長所必須依賴,二者之間本是互為映襯、相得益彰。竹子不在亭臺之中潤色風景,尚能在山林之中“虛心自持”得一隱逸名號,而因“春筍鉆墻破”而不使竹再“垂陰覆玉堂”的亭臺主人,失去了郁郁蔥蔥的茂竹,也即失去了眼前一道賞心悅目的風景。
《十離詩》的詩句結構也具有某種內在邏輯,大體來說,每首詩的前兩句都是在寫物象的本來面貌或者承寵時的景象,后兩句都是突然逆轉的悲劇或曰失寵后的落魄。然而仔細分析,每首詩都在第三句揭示了“離”的內在原因,按詩句結構的相似性又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的原因是“無端”的,“失寵”仿佛突然降臨:
無端咬著親情客(犬離主)
無端擺斷芙蓉朵(魚離池)
無端竄向青云外(鷹離鞲)
詩人借喻體在活動中無意識的錯誤來暗示命運急轉直下的不可預測性,這或許是作者對“罰赴邊”最直觀、最本質的體驗。在《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中作者稱“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這種對苦難的直接體驗觸目驚心,迫使作者開始思索緣由。其中四首詩的“緣由”最多只能算是主客觀都難以避免的微小過失:
都緣出語無方便(鸚鵡離籠)
都緣一點瑕相穢(珠離掌)
都緣用久鋒頭盡(筆離手)
為緣春筍鉆墻破(竹離亭)
這些被作者思考出的原因仍可對照來看。主觀層面,可能作者確實做錯了一些事,類似前兩題中鸚鵡說錯話、珠寶有瑕疵這樣的過失。客觀層面,幕主厭舊的心性和強勢的作風也造成了作者的“被棄”。
另外三首詩則在第三句揭示出明確的、較為顯眼的過失:
為驚玉貌郎君墜(馬離廄)
銜泥穢污珊瑚枕(燕離巢)
為遭無限塵蒙蔽(鏡離臺)
薛濤究竟為何被罰,史料語焉不詳,似乎無法達成共識。根據離薛濤時代較近的筆記《鑒誡錄》所載,薛濤“每承連帥寵念,或相唱和,出入車輿,詩達四方”。又說濤性“狂逸”,雖“遺金帛往往上納”,而韋皋“既知且怒”。于是今學者多有推測,被罰原因應該是薛濤交接四方又無所避嫌,使得韋皋心懷不滿。從“玉貌郎君墜”、“穢污珊瑚枕”的詩文來看,可能薛濤確實做了令韋皋覺得不妥的事情,不一定是金帛的收受,也可能是詩名太盛,與士子交接導致幕主不悅,使薛濤最終遭塵所蒙,鏡與臺分,與韋皋的關系終于破裂。
《十離詩》每一首詩的第四句都是以“不得”開頭。無論何種層次的比喻,最終的結果都是“不得”。這十個“不得”,既像韋皋對薛濤的嚴加申斥,令其再不得如此,又像是薛濤無奈和無聲的詠嘆,悲己再不得如何。而十個“不得”的背后又蘊含著某種“欲得”的希望,即薛濤希望以這樣的十篇詩作上達韋皋,改變自己深居邊地的處境。
《十離詩》通俗流麗的語言、詩題結構的相似和詩句構造的相通,很容易使人想到樂府民歌。已有學者指出《十離詩》與隋朝丁六娘《十索曲》具有可比性(李濤:《〈十離詩〉:男性中心社會里女性的十聲嘆息》)。后者為五言六句,皆以“從郎索某某”的語句結構結尾。索者為衣帶、花燭、紅粉、指環、錦帳、花枕之類女性意味明顯的物品。其實,《樂府詩集·雜曲歌辭》中本有“古別離”之體,解題云:“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后蘇武使匈奴,李陵與曰:‘良時不可再,離別在須臾。故后人擬之為‘古別離。文帝又為‘生別離,宋吳邁遠有‘長別離,唐李白有‘遠別離,亦皆類此。”而屬于此體之下的作品有古別離(古離別)、生別離、長別離、遠別離、久別離、新別離、今別離、暗別離、潛別離、別離曲,亦合“十離”之數。
薛濤《十離詩》作為個人創作的組詩,其藝術成就自不會囿于對民歌風調的繼承,但由此視角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十離詩》的“詩眼”:離。樂府詩的創作者們所發揮的“別離”之體,意在申發人生中各不相同的分離境遇及感受。而薛濤詩的“十離”還有遭受、背離等意義,可以說這組詩既象征著她遭受的苦難,又體現了她對造成這一現狀的反思,再以多重的組合物象層層渲染鋪墊,將“離”的不同含義表達得淋漓盡致,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此外,離亦是一個象征著火的卦象。朱熹《周易本義》曰:“離,麗也。陰麗于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由離假借麗而引申出的美麗、偶對、附著之意象征著薛濤侍宴承歡的過往經歷,而此卦所隱含的“吉”象則需要通過涵養德性來實現,是為“貴乎得正”。如果說薛濤真的以《十離詩》改變了自己的不利處境,由被罰之地釋還后“虛心自持”,獲得了“晚歲君能賞”的安穩,或許也稱得上命運的一種眷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