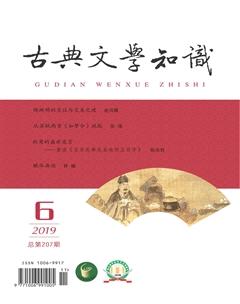見仁見智與以己度人
莫礪鋒
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題中的“九年”指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由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正是“甘露事變”發生的當日,后人皆認為詩人所“感”之事即甘露事變。當然此詩不可能作于事變當天,因為洛陽距離長安六百余里,不可能獲知當日長安突發事變的消息。況且詩人于題下注云:“其日獨游香山寺。”很像事后追記的口吻。那么此詩究竟作于何日?不妨從甘露事變的進程稍作推測:十一月二十一日,事變爆發,宰相王涯被宦官逮捕,不勝拷掠之苦,自誣謀反。二十二日,文宗在宦官的脅迫下使令狐楚草制宣告王涯反狀。賈被捕。二十三日,李訓于奔亡途中被捕,自請押送者斬其首。二十四日,神策軍用李訓的首級引領王涯、賈、舒元輿至刑場處死。白詩“當君白首同歸日”一句,乃用晉人潘岳、石崇之典故。《晉書·潘岳傳》載潘、石二人被孫秀誣以謀反之罪,“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后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白詩用此典詠王涯、賈、舒元輿、李訓等“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極為精切。這說明白詩的寫作定在“甘露四相”被戮之后,題中所云“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追記之辭也。
宦官專權是中唐政治肌體上最大的毒瘤,當時宦官們掌握著左右神策軍,連皇帝自身都受制于他們,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263中評議中唐宦官之囂張氣焰:“劫脅天子如制嬰兒”,“使天子畏之如乘虎狼而挾蛇虺”。白居易對此深惡痛絕,曾公開宣言“危言詆閹寺,直氣忤鈞軸”(《和夢游春詩一百韻》)。早在憲宗元和年間,時任學士和拾遺的白居易就曾奮不顧身地上書抨擊宦官頭子俱文珍、李輔光、吐突承璀等,甚至不惜批皇帝之逆鱗。可是當“甘露事變”發生的時候,白居易已經不是三十年前的那位無所畏懼的英年朝士了。早在元和四年(829),白居易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便開始了他的“中隱”生涯。到了元和九年九月,朝廷任命他為同州刺史,辭疾不赴,十月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那是一個“月俸百千官二品”(《從同州使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的閑職,白居易對之相當滿意。當“甘露事變”的驚人消息傳到洛陽時,白居易的心情十分復雜。一方面,他當然痛恨宦官的倒行逆施。另一方面,他又慶幸自己急流勇退,及時避開了朝廷里的政治風波,從而沒有像朝中諸臣那樣橫遭殺身之禍。那么,白居易對王涯等“甘露四相”又持什么態度呢?正是在這一點上,后人見仁見智,歧見紛紜。
北宋蘇軾《書樂天香山寺詩》云:“白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游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蘇軾文集》卷六七)蘇軾未點明“不知者”之名,今考南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六《甘露詩》條云:“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然,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事處,幾如幸災。雖私仇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詠也,如‘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沈存中即沈括,章子厚即章惇,都與蘇軾有所交往,蘇軾所謂“不知者”或即章惇。蘇、章二人乃進士同年,入仕后交往密切。章惇所言,蘇軾當有所聞,但駁議時姑隱其名。章惇稱白居易與王涯有“私仇”,當指蘇軾所云“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之事。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刺。身居卑職的白居易最早上書要求捕賊雪恥,得罪了朝中權貴,被執政者奏貶江表刺史。時任中書舍人的王涯落井下石,上疏論“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舊唐書·白居易傳》)。況且王涯其人,“貪權固寵,不遠邪佞”,為相后因行苛政而招民怨,“甘露事變”中赴刑場,“百姓怨恨,詬罵之,投瓦礫以擊之”(《舊唐書·王涯傳》)。即使白居易對其下場有幸災之意,亦不過分。但事實并非如此。白居易與王涯雖有前嫌,其后的關系也很疏遠,但白居易從未在詩文中對王涯有過微詞。王涯在“甘露事變”中慘遭宦官殺害,白居易更不可能在這個時刻產生幸災之心。況且“當君白首同歸日”所用之典乃潘岳、石崇同日罹難,這個典故的重點是同歸于盡,不能用于單數的對象。如果此句中的“君”獨指王涯,那樣怎能用“同歸”二字?所以“君”字應是泛指甘露事變中遇害的多位朝官,尤其是指“甘露四相”。白居易與賈、舒元輿一向交好,兩個月前被任命為同州刺史即因舒元輿之薦。“甘露四相”同時遇害雖出偶然,但那確是朝士與宦官長期斗爭的必然結果,身為朝士的白居易怎會對遇害朝士幸災樂禍!
蘇軾與章惇對白詩有不同解讀也許可歸因于學養或見識有異,但與他們的人品相殊不無關系。蘇軾胸襟坦率,瀟灑磊落,雖在政治風波中樹敵甚多,但從未因私怨而懷恨于心,即使對政敵王安石也是如此。章惇卻性格褊狹,睚眥必報。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章惇與蘇軾同時進士及第。因是年狀元乃章惇之侄兒章衡,章惇恥其名次居于章衡之下,竟于兩年后重新應舉高中后方肯出仕。蘇、章二人入仕后一向交好,即使在蘇軾遭受烏臺詩案時,章惇還曾上書論救。但到了哲宗紹圣年間,新黨重掌政權,章惇登上宰相寶座后,卻對蘇軾一貶再貶,直到“非人所居”的海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章惇對蘇軾的迫害,雖有黨爭的因素,但也未嘗沒有自私自利的陰暗心理在起作用。黃庭堅說“時宰欲殺之”(《跋子瞻和陶詩》),佛印說“權臣忌子瞻為宰相爾”(見《錢氏私志》),可見章惇之用心路人皆知。相反,蘇軾卻以不念舊惡的胸懷對待章惇。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突然去世,朝局又變,章惇罷相,并于次年遠貶雷州。遇赦北歸的蘇軾在途中獲知此事,立即寫信給章惇的外甥黃寔,說雷州并無瘴癘,讓他轉勸章惇之母以寬心。此后朝野相傳蘇軾即將還朝拜相,章惇幼子章援持書來見蘇軾,為其父求情。蘇軾當即親筆給章惇回信,多方勸慰,且在書信背面親筆抄錄一道“白術方”,讓章惇服用以養年。南宋劉克莊評此事曰:“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愛憐,猶欲其生。此君子小人之用心之所以不同歟!”(《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蘇軾與章惇對白詩的不同解讀,與“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不無關系。由此可見當后人對古詩意蘊產生完全相反的評判時,見仁見智固然是可能的原因,以己度人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西諺云:“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我們也可說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李白、一千個杜甫和一千個白居易。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