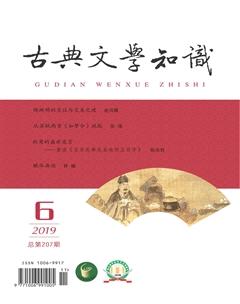賦體畫論
許結
一首抒情詩頗似一曲優美的音樂,一篇體物賦則像一幅壯麗的圖畫,而在歷史上賦體畫論的確是一種很普遍的文學批評現象。這從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說賦“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到朱光潛《詩論》第十一章《賦對于詩的影響》中所說的“一般抒情詩較近于音樂,賦則較近于圖畫,用在時間上綿延的語言表現在空間上并存的物態。詩本是時間藝術,賦則有幾分是空間的藝術”,成就了這一段賦話。了解其中的趣味,可從晚清的一篇《述畫賦》談起。
《述畫賦》的作者譚宗浚(1846—1888)是著名學者譚瑩之子,其父“長于辭賦”(《清史列傳》卷七三《文苑傳四》),受其影響,故多辭賦創作,這篇史上罕見的論述畫史的賦篇,收載于其撰《希古堂文乙集》卷一。該賦仿效唐人竇臮《述書賦》,變敘述書法史而為繪畫史,然其寫法,卻更多地仿效陸機《文賦》,以詞采與情韻兼長,這也是他在賦序中強調的仿竇賦卻不限于“纂集”,更用心于“己意”以表達賦的博麗文詞與繪畫飾象的關聯。如其描繪畫家施墨構圖時的創作情態云:“其始也,則收視反聽,經營結構,膠千慮而微茫,赴百象而馳驟。情郁而欲達,狀曈昽而似覯。總萬轡而齊條,奮千林而擷秀。宅景則神融,范跡則形就,選能則懷懌,振響則聲腠。極眾藝之標能,始咸推于領袖。”是有模擬陸賦的痕跡,但其變論“文”而為述“畫”,也有自身的遣詞造境的特點。繼此,譚賦敘述“其取局也”以描繪畫面空間之構圖,“其賦飾也”以描繪畫圖著色之方法,“感慓忽于年華,緬精能于奇藝”以描繪圖畫技藝之功用,“畫贊肇傳于顧愷,畫格實始于梁皇”以描繪畫學理論之史跡等,皆著眼于畫以鋪排其詞。又如論歷朝之畫師,評唐人李思訓謂“五色緯而云霞宣,八音會而韻鈞起。猶巨闕與明堂,神京而偉麗”,明其骨力雄健,變晉風之柔韻,開唐廷之氣象,呈“北派”畫風;又評詩畫兼擅的王維“摩詰蕭散,獨存妙悟。參氣化而標能,創經圖而獨具。矯神志之不凡,若遺蛻于塵務。如佩服趨朝,自矜風度;又如西極之化人,凌煙霞而吸風露”,則用“蕭散”“妙悟”“遺蛻”“風度”“凌煙霞”“吸風露”等詞語以闡發摩詰畫的“南宗”風貌與“詩化”妙境。在譚氏以華贍之賦筆展示畫家之繪飾的敘述中,還牽涉到一個以賦論畫的公案,即賦中所寫“浩然涉筆,氣韻特超”,指的是五代時荊浩(字浩然)的《畫山水賦》。而據學界考證,署名荊浩的《畫山水賦》始見于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畫論》,是由《山水訣》(即《筆法記》)《山水論》中內容混成,冠以“賦”名,體則多不協韻,故或謂“明代文士的誕妄”(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語)。由此來看,譚氏《述畫賦》應屬史上罕見的以賦論畫之作,其中奧秘或價值,或許還在隱于文詞之內的意蘊,即對應前引劉勰與朱光潛論賦“蔚似雕畫”、“近于圖畫”的論述,并可以由此延伸對賦與畫關系的思考。
賦與畫的關系,有著淵深的歷史積淀與彰顯的現實情懷,舉凡大要,概述如次:
從創作的層面看,則體現于兩端:其一,賦寫圖畫。早期的觀圖作賦的記述,以屈原《天問》與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為典型例證。王逸《楚辭章句》敘述《天問》創作起因說:“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佹,及古圣賢怪物行事。周流罷(疲)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引自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這就是前賢以《天問》乃因圖而作的依據。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自謂“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亦后世注家信為題圖之作的證明。尤其是王逸、王延壽父子所言“仰觀圖畫,以書其壁”、“托之丹青”、“事各繆形”內涵的賦圖關系的批評,早于劉勰“蔚似雕畫”的評賦語,值得珍重。而由此延伸到魏晉特別是唐宋以后文人畫興盛的時期,大量的題圖(畫)的出現,秉承的正是這一創作傳統。據馬積高主編的《歷代辭賦總匯》收錄,歷代題圖賦約二百題,近千篇賦,列舉同題有五篇以上的作品有:《九九消寒圖賦》、《八陣圖賦》、《太極圖賦》、《王會圖賦》、《西王母獻益地圖賦》、《河圖洛書賦》、《耕織圖賦》、《無逸圖賦》、《豳風圖賦》等,主要屬經史題,這與唐宋以后闈場考賦以附經義有關。當然,一些文人化的題畫賦作也不少,如《三友圖賦》、《山水圖賦》、《水月圖賦》、《竹林七賢圖賦》、《牡丹戲貓圖賦》、《赤壁圖賦》、《人跡板橋霜圖賦》、《晚香圖賦》、《雪中散牧圖賦》、《云山幽居圖賦》、《聽鶯圖賦》等,因圖敷文,亦多佳趣。其二,圖寫賦事。自晉人顧愷之繪《洛神賦圖》,開啟了有關“賦圖”的創作先例,繼此以后,如宋人李公麟的《九歌圖》、明人仇英的《上林賦圖》、文征明的《赤壁賦圖》、喬仲常的《后赤壁賦圖》以及歷代的同題擬作等,皆以圖畫的方式展示賦文、賦象與賦境,成為近年文圖關系研究的熱點。而圍繞“賦圖”再創造的“賦作”,如清人沈蓮的《赤壁圖賦》、方履篯的《招隱士圖賦》等,構成了賦與圖的再度書寫,有著“賦·圖”互文的審美意趣。
從批評的層面看,亦呈示于兩方面:一方面是賦論擬畫。劉勰在其賦論中,除了明確其“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外,諸多論述賦體的言說,也通于畫體。如“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詮賦》),“畫繪”之論,可見一斑;又如“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韻俱發”(《麗辭》),“宋畫”“刻形”之喻,自是明晰。于是通覽歷代的賦論,視“圖”呈“象”為其原則。如“觀象”,祝堯《古賦辯體》卷三《兩漢體上》評司馬相如《子虛賦》說:“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詞夸;取風云山水之形態,使其詞媚;取鳥獸草木之名物,使其詞贍;取金璧彩繒之容色,使其詞藻;取宮室城闕之制度,使其詞壯。”如“擬象”,劉熙載《藝概·賦概》認為:“賦取窮物之變,如山川草木,雖各具本等意態,而隨時異觀,則存乎陰陽晦明風雨也。賦家之心,其小無內,其大無垠,故能隨其所值,賦像班形。”如“構象”,俞王言《辭賦標義序》說:“藝林之技,首推辭賦。……囊括宇宙,席卷陰陽,奔走風雷,飛騰云雨,星辰惟所指顧,鬼神惟所驅役,翔鸞鳳、雕鶚于毫端,走蛟龍、麟鹿于楮末,此天地之奇觀,古今之偉業。”又劉熙載《賦概》說:“賦以象物,按實肖象易,憑虛構象難。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從“觀象”、“擬象”到“構象”,成為古人以畫論賦的主要內涵。至于賦作的具體評點,如林聯桂謂“賦之有聲有色,望之如火如荼,璀璨則萬花齊開,叱咤則千人俱廢”(《見星廬賦話》卷三)、何焯評孫綽《游天臺山賦》“履重險而逾平”一節“有秩序,頓挫歷歷如畫”(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引錄),喻畫以呈象,為其批評法則。
另一方面是賦似圖畫,即賦體(或賦格)與畫體(或畫格)在創作論上的共呈形態。德國學者萊辛《拉奧孔》把“詩”為代表的文學稱為“時間藝術”,把“畫”為代表的造型藝術稱為“空間藝術”,所以由語象完成的詩賦藝術應該都是時間藝術。這是一個層面的問題,也因此,在眾多批評家以“賦”擬“畫”的同時,也有以“詩”擬“畫”,如“詩中有畫”的說法。然區分詩與畫,誠如清人葉燮《赤霞樓詩集序》論詩及畫云“吾嘗謂凡藝之類多端,而能盡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者莫如畫。彼其山水、云霞、林木、鳥獸、城郭、宮室,以及人士男女、老少妍媸、器具服玩,甚至狀貌之憂離歡樂,凡遇之目,感于心,傳之于手而為象,惟畫則是然”,所以畫是“為有形者所不能遁”,相較而言,詩乃“為有情者所不能遁”,這與萊辛的說法有相應契處。雖然,葉燮對畫的描寫很類似賦體(尤其漢大賦),但畢竟有“語”與“圖”的區別。由此再回到朱光潛說賦“近于圖畫”與“有幾分是空間藝術”,顯然屬另一層面的問題,即“賦”較之“詩”的語象編織方法之差異,而更多地偏重于空間敘事的特征。是賦家以語象編織出“體國經野”的巨幅畫面(詩不能馭),與畫家以圖像展示出“布置山川”的宏大景觀,有著共同的創作指向與審美特征。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釋劉勰論賦體“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義,以為“本司馬相如語意”,指的是《西京雜記》卷二所載“相如曰”(答盛覽問作賦):“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也。”所謂“賦跡”與“賦心”,都內涵一定的賦家的空間感受及慣用的構圖思維,只是面對景物(象)模式而采用的空間場景,或出于宏觀鏡頭,或出于個人視角,而呈示出可視閾(賦跡的某種呈現)與超視閾(賦心的苞括宇宙)。以作品為例,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與《上林賦》,其寫楚王與天子游獵,多可視的場景描寫,如寫“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一段,具體而微,或垂直,或平面,圖繪感極強,其寫上林形勝之“水”,所謂“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場景擴大,在可視與不可視之間,具有一定的想象空間,而至于對“云夢”的全方位描述(其上、其下、其左、其右、其高、其埤等),以及所寫“上林”實質是“該四海而言”(程大昌語),多半屬于超視閾的想象。然無論是可視還是超視,賦體語象呈現的場景在于空間敘事的擬象書寫,卻是一致的。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二認為“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錦霞照灼”,其中也不乏擬畫批評的圖像意識。
圍繞歷代“賦圖”又出現了大量的題詠,也具有一定的畫論色彩。如元人貢奎題詠李公麟《九歌圖》云:“寓情托寫豈真見,龍眠落筆無遁形。凄涼展玩重懷古,尺素自足超丹青。”(《題九歌圖》)又如清人翁方綱題詠仇英《上林圖》云:“蒼然遠勢文句外,恍如相對主客言。亡是神光靜以攝,齊楚得失然不然。昔者相如二賦就,蕭然百日臥起間。孰與悟言一室客,妙瑩驪顆余三千。巨麗之中寓規諷,變態乃極于神完。”(《仇實父上林圖卷》)雖論圖,亦兼賦,表現出詩人對賦圖互文的價值取向與審美判斷。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