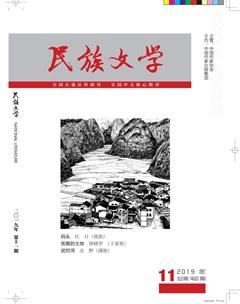十五的月亮十六圓
田興家(苗族)
弟弟的葬禮結束,遠處的親戚吃過飯都先后離開。他們離開時和他打招呼,他機械地一一回應,回應過后又木偶般地站著。此時他無端想到幾句詩。細想卻想不起完整的詩句,只記得詩中帶有“尸體”和“發芽”兩個詞。
他的大腦是一座墳墓,弟弟躺在其中,開始生根發芽。會長成一棵樹嗎?他想。像是電影快進一般,樹苗很快長大,稀疏的樹枝搖晃,他感到頭痛,愈發加重,似要炸裂。
有人推了他的肩膀一下。“喊你幾聲,你都沒有反應。”那人抱怨道。他回過神來,尷尬地笑笑,揉揉額頭。“快過去,陪你的兩個老表喝幾杯。”那人把他推過去。
兩個陌生的中年男子坐在方桌前。他們看起來風塵仆仆的,顯然剛從很遠的地方騎摩托車過來。那人按住他的肩膀,讓他在一張油膩的板凳坐下。他這才發現那人是幺叔。幺叔簡單介紹一下就走了,說是去把菜熱一下,冬天菜冷得快。面對這兩個從外縣趕來且多年沒有聯系的表哥,他一時不知道說些什么。頓了頓,他找來三個碗和一提啤酒,倒了三碗,說:“我們三老表先喝一杯。”
放下碗后,他無話找話,問兩個表哥幾點鐘出發的,騎了多長時間的車。兩個表哥也不健談,回答他的問題后便陷入沉默。一陣風吹過,他打了一個哆嗦,說:“這幾天降溫了,你們那邊咋樣?”這些年來他養成習慣,每當跟別人沒話題又覺得尷尬時,他就會談起天氣。兩個表哥對天氣似乎不感興趣,給他的答案只是一兩個簡單的詞語。
這時他又想到關于“尸體發芽”的那兩句詩。完整的詩句到底是什么?微微抬起頭,睜大眼睛,嘴唇動了動,他絞盡腦汁想事情時總是這樣的表情。還是沒有想出來,他拿出手機百度,發現兩個表哥正看著他。他有些不好意思,把手機放回包里,準備倒酒繼續喝。
恰好幺叔端兩盤菜過來放在桌上,兩個表哥拿起剛才喝酒的碗去舀飯,他們的眼睛很尖,一眼就看到飯放在屋檐下。他說:“我給你們換一下碗。”兩個表哥說:“不用換了,都一樣的。”他過去撿起碗和筷子,發現兩個表哥已經舀好飯回到桌前,他放下碗,拿筷子過去給他們。兩個表哥的吃相有些急,估計出發前沒吃東西。他讓兩個表哥自便吃飽,起身走了,感到一陣輕松。
父親佝僂著背慢慢地掃著地,母親和幾個伯娘在清洗鍋碗盆。弟弟比他小將近四歲,他模糊地記得弟弟出生的情形,像是黑白的電視畫面般。是的,當時的一切都是黑白的。母親坐在里屋,因苦痛而呻吟著,他跑到母親身邊,母親指著地上一灘模糊的東西對他說:“這是弟弟。”他聽到那攤模糊的東西響起若有若無的哭聲。接著鏡頭轉換,幾個伯娘來來回回地進屋出屋,父親在院子里掃著地。啊,他們為弟弟來到這個世界忙碌著,又為弟弟離開這個世界忙碌著。此刻,他突然感到人世間多么悲涼。
兩個表哥吃飽后,過來跟他打招呼,說要回去了,他象征性挽留幾句,然后對他們說天快黑了,騎車慢一點。接著兩個表哥又去跟父母打招呼,說一些安慰的話。幾句話過后,他們每人拿出兩百塊錢給母親,母親推辭著不收,他們把錢放進母親圍腰的包里,匆匆騎上車走了。
他沒有尿意,但還是去廁所撒了一泡尿,然后拿出手機百度。翻了兩頁,終于找到那幾句詩。“去年你在花園種下的尸體,發芽了嗎,今年會開花嗎?”出自艾略特的《荒原》。如此有名的詩人及詩作,竟然忘記了,他覺得自己好像真的不夠格當一名文學編輯。
他在作協上班,臨聘的,主要負責編發公眾號。從郵箱里選出優秀的文學作品進行簡單排版然后發出來,投稿的大多是大學生,寫得跟高中生作文一樣,難得選出一篇看得過去的。偶爾有讀者留言:別總發這種垃圾文章。他回復:鼓勵新人。經常參與作協舉辦的各種活動,他漸漸跟圈內一些小有名氣的作者熟悉起來,便直接跟他們約稿,節約了很多時間。公眾號一個星期編發三期,他感覺還挺輕松的,從沒懷疑過自己不夠格,直到有一天參加了一次活動,才突然起了懷疑。
那是一次參觀展覽品的活動,要求單位至少派一人參加。這種不重要的活動,領導都會安排他去。在會場簽到時,一位雙手提著東西的女士請他幫忙簽一下,他很樂意地笑著問:“你貴姓大名?”那位女士說:“張曦。”他寫了“張西”兩個字,他對自己的楷書還是滿意的,以為會得到女士的欣賞,得意地問:“哪個單位的?”那位女士說:“錯了,不是這個‘西,是‘晨曦的‘曦,早晨的意思。”他把“西”字涂掉,愣住了,一時寫不出“曦”字,只記得大概樣子,用筆在空氣中試了幾下還是沒寫出來。那位女士把東西放在地上,說:“我自己來。”他尷尬地把筆遞給她,感到臉上發燙。轉身走時,聽到那位女士不屑的聲音:“還是作家協會的……”
他在活動現場轉一圈就提前離開了。回住處的公交車上,用手機打出“曦”字,然后悄悄用手指在空氣中寫,確定自己記住筆畫后,鎖屏手機,又繼續用手指在空氣中寫。一路上,他不知道寫了多少個“曦”字,各種字體都有。回到住處,那位女士不屑的聲音還在耳邊響著,莫大的羞辱感在心中翻滾。頓了頓,他翻出筆和紙練字。他先寫下“晨曦”,然后想那些筆畫復雜的字,每想到一個不會寫的,就用手機打出來,然后照著寫。
寫了滿滿幾頁,肖莉回來了,打開燈,抱怨道:“天都黑了還不開燈。”他回頭看了肖莉一眼,站起來伸伸懶腰,往窗外看去,天并沒有黑,只是房間的光線差所以有些暗而已。肖莉打開電飯鍋,看著他,說:“看樣子你早就回來了,連飯都不煮。”說著肖莉把昨晚上的剩飯倒進垃圾桶,故意用瓢把鍋底刮出刺耳的聲響。他過去抱住肖莉,在她耳邊說:“你煮的飯好吃點,所以等你回來煮。”肖莉掙脫他的手,從桌下的米袋舀一碗米倒進鍋里,想想又加了一點,然后把碗丟進米袋。他說:“不要生氣啦,等一會兒我洗碗。”
應該有半年了,他們一周總會發生一兩次不愉快。他知道肖莉的同事一直對她窮追不舍,時間長了她好像開始心軟,偶爾接受同事的晚餐邀請。他自然很生氣,用冰冷沉默來面對她。她冷笑著說:“都三年了,你還是和當初一樣,一點都不會變。”當初?當初肖莉怎么說來著?“你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吧,我對生活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吃飽穿暖就行。”那時候他剛工作不久,肖莉總是含情脈脈地靠在他身邊喃喃低語。一年過后,肖莉開始委婉地提出讓他換工作,而他習慣了目前的狀態,總是說:“再等等。”一等就等了兩年,肖莉估計對他徹底失望,不再提了。
晚上躺在床上,肖莉側著身,悄悄聊微信。他也拿起手機,大學同學群里聊得正火熱,和往次一樣,他覺得自己插不上話,又放下了手機。他側過身去,抱住肖莉,看到她用小指打字,打得很快。“我準備辭職了。”他說。肖莉沒有回應。他搖了搖她,說:“聽到沒有?我準備辭職了。”肖莉淡淡地說:“隨便你。”他松開手,翻過身來,望著天花板的蜘蛛網。過了一會兒,他想傾訴自己的委屈,便把白天提筆忘字的遭遇說給肖莉聽。他覺得自己是委屈的,現在都是用電腦工作,不會寫“曦”字很正常,可那位女士為什么就不理解而且還非要嘲笑呢。肖莉聽完后也翻過身來,說:“其實,我只是覺得,你還這樣年輕,應該拼一下,多去接觸一些不同的行業。像我們行業,都只認錢,你不會寫‘曦字,也不會有人嘲笑你。”重點還是在“錢”上。肖莉已經直接表明過很多次,嫌他目前的工資低,而且沒有任何發展空間。他感到心里不是滋味。
父母的房間傳來咳嗽聲,母親的舊病又復發了,咳上好一陣才停止,接著聽到打火機的聲音,父親又點燃一支煙。他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東西收拾完畢,親戚朋友散盡,確定父母都睡下,他才關好門和衣躺在床上。盡管身體發困,卻沒有一點睡意。他翻了兩次身,又想起那幾句詩。“去年你在花園種下的尸體,發芽了嗎,今年會開花嗎?”隨之,弟弟的容貌又在腦海里清晰起來。
他去縣城上高中后,就很少跟弟弟有生活交集。時間可以改變一切,原本無話不說的兩兄弟竟變得無話可說,短暫的見面也基本上是各自玩著手機。現在他才意識到自己對弟弟一點都不了解,只是從QQ空間動態或者微信朋友圈猜測出丁點無關緊要的信息,比如弟弟高中時期談過兩次戀愛,大學期間學會喝酒,工作后又喜歡上打麻將。總之,在他印象中,弟弟的夜生活非常豐富,時常熬夜,不是吃燒烤喝酒就是打麻將,估計所有這些早就為弟弟的病埋下了伏筆。
弟弟是在單位組織的體檢中查出病的。當時弟弟和一個女同事已經發展到談婚論嫁的地步,被這突來的致命消息襲擊得睡了一天一夜,過后瞞著女朋友和家人,獨自去重慶檢查(聽說那邊有一家醫院很好),結果還是一樣的。肝癌,晚期。從檢查出病到停止呼吸,僅僅一個月的時間。他覺得弟弟的心理素質未免也太差了,不過早解脫也早好,免得把年老的父母拖垮。弟弟的女朋友請了兩個星期的長假,這以后單位不再批假,就只能周末過來陪護。那天晚上,只他和母親陪在弟弟身邊。弟弟特意讓自己看起來輕松一些,一直對母親說:“該享受的我都已經享受過了,我死了也沒有遺憾。你和我爸爸不要難過,還有我哥,他還可以照顧你們。”母親不說話,流著眼淚,強忍住哭聲。到了半夜,母親去睡了,弟弟和他說了很久的話。現在想來,那應該算是告別吧。可他已經想不起弟弟究竟說了些什么,只記得弟弟反復說到女朋友,說她人非常好。第二天早上,弟弟就沒有再醒來。
微信沒有任何預備就響了一聲,他被嚇了一跳。拿起手機,是肖莉發來的信息:睡了沒有?自從分手后就沒聯系過,他看上一條信息已經是三個月以前,這突來的問候讓他感到意外。想了想,回復道:準備睡了,你還沒睡?肖莉經常更新朋友圈,他知道她又換了一家銀行,但工作和以前一樣,還是客戶經理,有時候去另外一座城市見客戶,天黑才趕回省城,到住處已經十一二點,所以經常都睡得很晚。肖莉馬上就回復了:已經躺在床上,這幾天太忙,今晚特意進你的朋友圈,才知道你家的事情。他很少更新朋友圈,最新一條動態內容是“弟弟,一路走好”,帶弟弟的骨灰回家時發的。他不知道怎樣回復肖莉合適,細思了一會兒,說:我知道的,你工作很忙。剛發送成功,肖莉的信息就來了:能給我說說是怎么回事嗎?都分手這么長時間了,他不想打幾百字把家庭的苦難告訴她,于是回復:見面再說吧。估計肖莉忙什么去了(他猜測是去廁所),差不多兩分鐘才回:節哀,回來聯系我,早點休息,晚安。回去聯系她?要聯系嗎?聯系她干嗎?他盯著手機屏幕看了一會兒,回復:晚安。
他聽出父母已經睡著,他們這幾天忙前忙后,幾乎筋疲力盡,再傷心也有睡得著的時候。父親微弱的鼾聲有節奏地傳來,他突然覺得從鼾聲能聽出一個人的年紀,父親的鼾聲再沒有十幾年前那樣響亮有力了。那時候他總在心里抱怨父親的鼾聲影響到他的睡眠,導致他第二天上課打瞌睡被老師罰站在講臺上。想起這些,他的眼角浸出淚水。要是父親的鼾聲再跟以前一樣,我寧愿多被老師罰站幾次,他想。但是不可能了,時間雖悄無聲息,卻力大無窮,把父親原本直挺的背都壓得佝僂起來。
有了辭職的想法,他開始和肖莉商討換什么工作,但她好像已經沒有多大興趣。以前肖莉總給他灌輸跳槽的思想,在他耳邊分析每一種行業的優劣,說起來頭頭是道,現在她用不在意的口氣說:“要不你就來我們行業試試吧。”他說:“你曉得我臉皮薄,而且口才差,做不了你這一行。” 肖莉說:“哪個一開始就能做得了,哪個不是慢慢鍛煉出來的?你一直這樣不敢開口講話,口才就永遠不會進步。”他說:“我覺得我這樣也還不錯,能賺到錢也能找到女朋友,錢賺得不多,但夠生活,女朋友不夠漂亮,但我喜歡。”說完他嬉笑著去摟肖莉,她轉過臉去,冷笑一聲,說:“我看你就甘心一輩子這樣下去。”
他靜下心來想,自己并不是不敢開口講話,好像只是不想開口講話,這估計是小時候的家庭教育使然。讀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父親帶他和弟弟去縣城,他們蹲在廣場邊看耍猴,一個漂亮的小女孩從面前經過,父親招手示意小女孩過來玩,小女孩看了父親一眼,突然大哭起來,女孩的父母出現了,非要叫父親帶去市醫院看,兇巴巴的,沖上來要打人,他被嚇得緊緊拉著父親的衣擺,最終父親賠了二十塊錢才罷休。錢全部賠了,連一碗粉都沒得吃,他們走了兩個小時的路才回到家。這以后父親常常對他和弟弟說,出門在外要時刻小心,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不要摻和。這讓他慢慢養成習慣,對什么事情都少開口講話,更不會主動去接觸,生怕一不注意就會給自己惹來麻煩。
新工作沒有著落,他暫時還沒辭職,和以往一樣,工作日按時上下班,周末呆在住處看書,偶爾也寫一些看似詩歌的句子。肖莉下班回來,他就迫不及待念給她聽。“在月光下洗澡。樹頂的星群/依次墜落;人海泛起漣漪……”或者“笑一個吧,合影留念/在同歸于盡之前。她的背影……”剛開始戀愛時,肖莉安靜地聽完,故作害羞地罵道:“矯情。”現在她還沒聽完就拋下一句“能當飯吃嗎”,然后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肖莉專科畢業,比他早工作一年。起初他問她想不想升成本科,她說:“現在工作太忙,以后再看看。”以后他再問,她立即就反問:“升來干嗎?”肖莉學的是什么機械專業,跟所從事的行業毫不沾邊。他開玩笑道:“讀三年大學浪費了,學到的知識沒有用處。”肖莉則說:“當你所學的知識不能讓你賺到更多錢的時候,你就得學新的知識。”這是根據哪一句名人名言改編的呢?他從角落翻出一本落滿灰塵的《名人名言大全》。肖莉嘲笑一般地說:“快去洗碗吧,這本書教不了你生活的。”
若晚餐后天色還早,他就想出去走走,但很多時候肖莉總推辭,不是說累就是說身體不舒服。他說:“你不去我自己去了。”肖莉說:“去吧。”有時候他推門欲出時,肖莉又補充一句:“早點回來。”有了這一句補充,他就會感到舒服一些。獨自沿著河邊走,天黑盡以后,牽著手的情侶多了起來,他想,這些情侶都是剛談戀愛圖新鮮感罷了。走遠后,他買一包煙,點燃一支,沿著原路返回。他本來不抽煙的,只是想營造出傷感的氛圍。有時候回到住處,肖莉已經睡著,有時候呢,她則在跟別人視頻通話,看到他回來就匆匆掛了。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估計是哪根神經搭錯了,竟然又去買了最新版的《申論》和《行政能力測試》。他大四那年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公考,可省考結果下來連面試都沒進,那個陰雨不止的午后,他把所有考試資料丟進垃圾桶。現在看到他捧著兩本封面大紅的公考書籍回來,肖莉笑著問:“你確定還能看得進去?”他說:“你就不能選擇相信我一次?”肖莉說:“以前我每一次都相信你,后來發現自己相信錯了。”當天晚上他開始看書,肖莉白天跑了一天,估計累了,躺下一會兒就睡著了。他關掉臥室的燈,輕輕走到客廳來,看了很晚才去睡。
看了幾天書,他開始做一些模擬題目,做完后看參考答案,只做對百分之五十。肖莉對此不管不問,他的興趣慢慢淡下來,有時候看了幾頁又合上,翻開一本外國詩集。
母親起得很早,一向都是這樣。讀初中時,幾乎每天早上都是母親喊他和弟弟起床。現在,母親不再喊他早起,可他睡眠淺,聽到母親起床就跟著起了。這幾天失眠,都是下半夜后才入睡,但他不允許自己睡懶覺,因為是在家里。
吃過早餐,跟父母去地里剝甘蔗葉子。他沒怎么做過農活,但能體會到做農活的苦,特別是夏天傍晚看到忙了一天回到家的母親坐在門口喘氣的時候。從他記事起,家里每年都栽甘蔗,他和弟弟一年級到大學的學費幾乎都是賣甘蔗得來的。他工作后,勸父母別再栽,當著他的面父母答應得好好的,可過后又栽上。甘蔗長得很好,父親和母親剝著干枯的葉子,沉默著。他抬頭,從甘蔗葉的縫隙看天,像是出太陽的征兆。他似乎看到被剝過葉子的甘蔗經太陽一曬,顏色慢慢地變濃變深,糖分一天天成倍地增加。
“今年的甘蔗應該賣得貴。”稍一停,他無話找話說,想讓父母從傷痛中走出來。可母親卻往傷痛中越陷越深,說著又提到弟弟。“往年甘蔗賣出去都是你弟喊一大堆朋友來幫忙扛,今年不曉得咋辦……”母親的聲音哽咽了。“媽,你不要擔心,到時候我回家來。”他說道,可他知道他回家也幫不了多少忙,他的人緣沒有弟弟好,幾乎可以說沒有朋友。父親在石頭上坐下來休息,點燃一支煙,說:“到時候賣給小老板,一天砍五六百棵就行。”
“你以前談的那個女朋友呢?”過了一會兒,母親問。他猶豫著,但還是說了事實:“已經分開了。”母親說:“年紀越來越大,也該找個結婚了,過了年紀很難找。”他在心里細算,再過三個月就進二十八歲了,但他內心還沒感覺到自己年紀大,他戀愛時也沒談到結婚,他甚至都沒考慮過。他想,是不是因為自己有點晚熟呢?“媽,你不要擔心,這些我都曉得的。”他說道。“要是你弟不得病,今年過完年就結婚了。”母親還是忘不了弟弟,說著她哭了起來。從小弟弟就顯得比他聰明伶俐,母親要寵愛弟弟一些,他十來歲就看出了這一點,但他從沒有抱怨過。“媽,每個人都有他的命,你們不要太難過,如果你們因為難過身體出問題,麻煩就大了。”他試著安慰母親。
“你還是回來考一份正式的工作。”抽完一支煙,父親說,母親趕緊附和。弟弟在世的時候,父母沒有要求他必須考一份正式工作,確切地說,父母不關心他,不過他不在意,倒覺得自由自在。“你也可以考教師嘛,當老師也不錯,有兩個假期,還照常領工資。”母親說。他偷偷看父母,父親的背似乎比昨天更佝僂了一點,母親的頭上好像有幾根白發。“嗯,等招考我就報名。”他答道。其實,和肖莉分手后,他就想著回老家考一份正式工作,他感覺城市終究不屬于他。
晚上睡覺時看手機,弟弟的女朋友居然發信息過來,說想見見他。弟弟跟他“告別”的前一天晚上,她突然加了他的微信,是通過弟弟分享的名片加的。他在醫院見過弟弟的女朋友,個子不高,微微發胖,但顯得很靈巧。弟弟下葬那天,弟弟的同事來了十幾個,但她沒有來。他想,估計她怕在現場受到關注,所以不來。最終,他們約定明天下午三點鐘在縣城見面。明天恰好是星期天,他打算見完面就坐最晚一班高鐵去省城。
第二天下午他兩點五十到縣城,給她發信息,問在哪等她。她回信息說在orz奶茶店,讓他打車過去。弟弟的女朋友眼角略帶憂傷,坐在她面前,他一時不知道說些什么。稍一停,他問起她的工作狀況,他只是為了緩解沉默的尷尬,并不是特別想了解。她回答得也馬馬虎虎,談了幾句就提到弟弟。她說:“別人都講,同一個單位的談戀愛不好,但我和你弟莫名其妙就在一起了,我都不曉得是為哪樣。”他沉默著,她卻哭了起來。隔壁桌坐著比他們年輕的一對情侶,正好奇地看過來。他輕聲說:“這里人多,不要哭了。”
她調整好情緒,問起他的工作。他說:“在貴陽混日子,正準備辭職回來考試。”她說:“回來吧,離家近,以后方便照顧父母。”他點點頭。過了一會兒,她又問:“你學的是哪樣專業,能教書的吧?”他說:“漢語言文學,有教師資格證。”她似乎有一點開心,說:“我有個朋友開了個培訓班,要不你辭職回來,先去他那里上班,然后慢慢考。”他說:“到時候再說,如果有這個想法,得請你幫忙。”
兩杯奶茶,他的那杯喝了一半,而她的那杯一點沒喝,一盤瓜子和一盤薯條也一點沒動。他看時間,東聊西聊的,竟然已經坐了將近兩個小時。她問:“你還有事沒有?”他說坐最晚一班高鐵回省城。最后,她說請他吃飯。吃的是火鍋,他吃了半碗就放下碗筷,等她吃,她吃得很慢。吃完后他搶著把錢付了。他把她送到樓下,看著她上樓后才打車趕往高鐵站。他知道,弟弟以前和她租房子住在這棟樓里,如今只剩下她一個人住了。
他在網上查看招聘信息。有一家單位招辦公室工作人員,也是合同制,但待遇比他目前的好,便問肖莉的意見。肖莉說:“要考試就考帶編制的吧。”他想了想,說:“其實也不一定考上,只是想去鍛煉。”肖莉笑了一聲,說:“你從小到大考了那么多試,還沒鍛煉夠?”盡管肖莉不怎么支持,他還是報了名。報名通過審核后,他把喜歡讀的幾本詩集鎖進密碼箱,每天晚上都熬夜,學著寫一些材料。每當寫不下去,他就站起來扭扭身體,環顧空蕩蕩的客廳,聽著臥室里肖莉的呼吸聲。他想象自己已經考上,現在正在加班為領導寫講話稿,領導第二天要用。這樣想著,他又坐下來繼續寫,直到寫滿三千字才去睡。
有一天晚上他去睡覺時,肖莉已經睡著,手機放在桌上,綠色的指示燈不斷閃爍,他知道有新信息。看著肖莉熟睡的模樣,他突然想知道新信息是什么內容。他平時看到肖莉都是用右手大拇指指紋解鎖,他的心猛跳了一下,毫不猶豫地拿起手機,學著網上的視頻,小心翼翼地操作。解鎖成功,他的心又猛跳了一下,肖莉翻了翻身,并沒有醒。是微信信息,追她的那個同事發來的。三條信息,一條是文字:我準備買這套房子,你看看怎樣?兩條是圖片:房子的外觀圖和室內圖。肖莉有清理聊天記錄的習慣,他無法知道她和這個同事還聊了些什么。盯著這三條信息看了一會兒,他想回復點什么,但終究還是沒有回復,把這三條信息清除,關燈睡下。一直睡不著,也許是翻身吵醒了肖莉,她起床,他趕緊假裝睡著。肖莉摸到手機去了廁所,回來后放下手機躺下,不一會兒又睡著了。
考試那天早上,他起得很早,打出租車去考點。拿到試卷,掃了一遍,他就知道真的是來“鍛煉”的,但他還是靜下心來答題,堅持到最后才交卷。和他一起交卷的有兩個考生,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都一副愁眉苦臉的表情。走出考場,他想跟他們搭話,問他們考得怎樣,但話剛到嘴邊,那個女的已開好機,正打電話,那個男的朝遠處招手,一個和肖莉一樣偏瘦的女生高興地跑過來。他這才想起手機還沒開機,便開了機給肖莉打電話。肖莉問:“你考完了?”他說考完了,稍一停又說:“你都不會過來接我?”肖莉好像在忙,正跟別人談著什么,談了幾句后對他說:“我發位置給你,你打車過來,待會兒一起吃飯。”說完就掛了。他看著位置,竟然是他第一次請肖莉吃飯的地方。抬頭看熱得頭皮冒汗的太陽,要跑到那么遠的地方去吃飯,他沒有興趣,于是回復:我先回住處,晚上再說。
他越來越感覺到肖莉對他的冷漠,他也不明說什么,只是找合適的機會用同樣的方法來對她。由于晚餐吃得早,晚上肖莉說想吃點燒烤,讓他去買。要是剛戀愛時,冒著雨他都要去。可現在他覺得機會來了,說:“大晚上的不要吃東西了,對身體不好。”肖莉瞪著他,說:“你這人咋會這樣?”他說:“早的時候喊你多吃點你自己不吃,現在餓了怪哪個。”肖莉不再理他,又開始聊微信,二十來分鐘,燒烤就送到了。他預感到這外賣不是肖莉自己點的,是追她的那個同事點的,他雖生氣但又不好發作。肖莉故意一般,嬉笑著遞一串給他,問:“要吃嗎?味道還可以。”他氣鼓鼓地說:“你自己脹肚子吧。”
過不久,肖莉又要去另外一座城市見客戶。他問:“幾個人去?”肖莉說:“好幾個。”“他也去嗎?”“哪個?”“他,追你的那個。”“去的。”他瞬間有些不舒服,頓了頓,問:“晚上回來不?”肖莉說:“看情況,應該要回來。”但到了晚上,肖莉卻沒有回來,他打電話過去問,肖莉說:“沒趕上車,明天再回。”他很氣憤,沒趕上車為什么不早說,非要等我打電話問了才說。但他沒表露出來,說了聲“好吧”,掛了電話。心里還是很堵,每隔半個小時,他就用微信給肖莉發一次視頻電話,肖莉說:“放心吧,我不會背叛你的,沒和你分之前,我不會和其他男生在一起的。”他稍微放下心來,可細想,這句話好像暗含著別的意思。
第二天肖莉回來了,他下班回到住處時,她正在炒菜。菜和平常一樣,肖莉也和平常一樣,看不出有什么預兆。晚上躺在床上,他摟著肖莉,手在她身上游移著,把她的睡裙往上拉。整個過程,肖莉沒有任何反應,眼睛望向別處,甚至還拿起手機回了兩次信息。他有些不悅,匆匆完事后,問:“你哪樣意思?”肖莉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兒,肖莉說:“我覺得我們還是分開吧。”他一驚,隨即平靜下來,他知道她的這句話早晚都要說出口的。又過了一會兒,他說:“好吧。”
弟弟的女朋友幾乎每天都主動給他發信息,問他辭職沒有,他敷衍著說再想想。進她的朋友圈,動態很少,幾乎都是轉發與她工作單位相關的新聞。他看到一年前的一條動態:今夜月圓,明日離別。配著兩張圖片,一張是弟弟和她在夜色中的合影,她高齊弟弟的肩膀,幸福地依偎在弟弟的懷里,另一張是月亮,手機拍攝,不是很清晰。他再看日期,想起來了,那段時間弟弟被單位派去青島學習一個月。
周六一直下著雨,他吃過午飯,呆在住處看一本國內詩集。肖莉突然發信息來:你回來了嗎?他趕緊回復:早就回來了。陰沉的天氣以及晦澀的詩句讓他愈生孤寂,此刻想見肖莉一面。肖莉馬上發語音電話過來,說:“我恰好經過你樓下,你在住處沒有,在我就上來。”他說:“在的,你上來吧。”
他給肖莉泡了一杯茶。茶葉是以前肖莉買的,杯子也是以前肖莉用的。他注意著肖莉,她沒任何反應,似乎沒有發現他的故意為之。許久不見,他一時竟不知從哪說起,還是肖莉先開口。肖莉問他弟弟的情況,他簡單說了一下。肖莉問:“你來上班了,你爸爸媽媽在家?”他點點頭。沉默了一會兒,肖莉說:“我們都是為了生活,沒辦法。我媽一個人在家,她的腳還經常痛。”
最后他們談到辭職。他把他的想法說給肖莉聽,肖莉表示贊成,說:“那就回去吧,回去照顧父母。我們小的時候,父母為我們活著,現在父母老了,我們也要為父母活著。”他抬頭,才發現肖莉換了一個發型,看起來比以前成熟了些。他知道肖莉已經和那個同事在一起,他想問他們前段時間看中的那套房子買了沒有,開始裝修沒有,但想想還是沒開口。
又坐片刻,再無話,肖莉起身告辭。他抱住肖莉,肖莉說不行。但他還是把肖莉抱進臥室,把她推倒在床上。她不停地阻止他,堅決說不行。他沉默不語,貪婪地獵取,因動作過大還把她的衣服撕扯破了一點。肖莉突然說:“你弟弟剛剛不在,你不應該這樣。”他愣著,興趣瞬間消失,松開了手。肖莉整理了一下頭發,對他說:“我走了。”他轉過臉去,沒有回答。等再轉過臉來時,發現肖莉已經走了。
此后他依舊按時上下班,偶爾寫幾句詩。有一天他編好公眾號,請領導審核。領導看了一眼,說:“可以的,就這樣,你把關就行了。”過了一會兒領導說:“這公眾號辦下去沒有意思,明年打算不辦了。”領導說完喝了一口茶,像是無意中說的一樣。他無聲笑了笑,心想那就讓這一期成為最后一期吧。稍一停,領導又說:“到時候你可以做其他工作,你還是比較得力的,各塊工作都能做得下來。”他沒有回答,默默地把剛發布的作品分享到幾個活躍的群里。
晚上睡覺時,弟弟的女朋友又發信息過來:哥,睡了嗎?他說:睡了。她發來一個羞澀的表情,問:睡這么早,不陪你女朋友聊天?他說:目前沒有女朋友。并加上一個笑臉的表情。她問:哥,你媽催你結婚嗎?他沒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我打算明天辭職。她說:真的嗎?那太好了,我朋友的培訓班恰好急需一名語文老師。第二天他就去辭職了,領導沒挽留,還祝愿他盡快找到更好的工作,他笑著說已經找到了。
回來后一直呆在家里。弟弟的女朋友發信息問:哥,你不想來培訓班上課嗎?他回復:先休息一段時間。刷新朋友圈,又看到肖莉新發的動態,是信用卡的廣告。他給肖莉發信息:我已經辭職回家了。過了好久肖莉才回復:好的。“好的。”他在心里默念道,無聲地笑著。看到桌上凌亂的詩集,回想起與肖莉相識的過程。
“帥哥,在等公交車嗎?”一個偏瘦高挑的女生微笑著迎上來。周圍沒有其他人,他“嗯”了一聲,往旁邊走幾步,拿出手機假裝要打電話。女生又靠近,笑著說:“我叫肖莉……”肖莉跟著他走上最后一班公交車,車上空位很多,可肖莉卻在他旁邊坐下來。他本來不辦信用卡的,但肖莉一直纏著,以長期培養出來的耐心跟他套近乎。得知他沒找到工作,就說要給他推薦,得知他沒有女朋友,就說要給他介紹,還主動加他的微信。經不住她那襲人的熱情,他就辦了一張。
大學畢業沒找到工作,不好意思回家,在省城游蕩著。有時候一大早出門,隨便上一路公交車,中途下車又換另一路,不斷這樣,直到天黑才回到狹小潮濕的出租屋。他在這里沒有一個朋友,實在感到孤獨就出去買一箱啤酒回來,打開電腦,邊喝邊試著寫幾行詩歌。喝暈后又全部刪掉,然后找肖莉聊天。肖莉不再提給他推薦工作和介紹女朋友,熱情也不再那么襲人,常常以“哦”或者“嗯”結束聊天。他通過試探,得知肖莉沒有男朋友,于是鼓起勇氣說想跟肖莉跑跑,看自己能不能勝任她的工作,她很爽快就答應了。跟肖莉跑的那天下午,她一張卡都沒推銷出去,這讓他感到害怕,想不到工作竟如此艱難。但肖莉依舊開朗地笑著,提議一起吃晚飯。他說:“我請你。”肖莉說:“等你找到了工作再說,這頓我請。”他們吃得很高興(其實是肖莉很高興),當天晚上他就失眠了,一直把肖莉想象成他的女朋友。最后他去沖了一個冷水澡,心想要趕緊找到工作,以便進一步和肖莉發展。
他去年投出去的一組詩歌在一家大型詩刊發表,得到將近一千塊錢的稿費。他很興奮,但卻找不到人來分享這意外的喜悅,于是想到肖莉。他給肖莉發信息,說要請她吃飯。肖莉問:你找到工作了?他暗笑著回復:出來你就知道了。肖莉一坐下就問他找到了什么工作,他說還沒找到,她便追問他為什么突然請吃飯,他笑而不答。最后經不住肖莉的追問,他有些羞澀地說了出來。肖莉開心地說:“想不到你這么有才,我讀高中時最喜歡語文課,現在都還能背誦很多詩歌。”說著她背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只背兩節就背不出來了,尷尬地笑著,說想讀讀他的詩歌。回去后他從自己寫的所有詩歌中選出最滿意的十首發給肖莉,肖莉看完后說寫得很美,但不太懂。這以后,肖莉好像對他有了興趣,和他聊天時,“哦”和“嗯”用得少了。
已經游蕩將近一個月,他試過汽車銷售和保險兩份工作,都不如意,上幾天班就干不下去。后來無意中看到作協招人,他帶上自己寫的幾首詩和幾篇新聞直接找上門,領導一目十行地看完后就讓他第二天準時來上班。這一次他干得很順,肖莉替他高興,覺得以他的才華,早晚有一天會成功。
和肖莉見面更頻繁了,漸漸熟悉起來。肖莉的父親過世得早,母親一個人把她和兩個弟弟撫養長大,母親的腳經常痛,這兩年來有時連走路都成問題,再做不了重活。兩個弟弟,一個在讀大學,一個在讀高中,學費生活費都是她在出。“我媽真的過得很苦……”有一次肖莉說著說著在他面前流下眼淚。他才明白這個堅強的女生竟也有著柔軟的一面,忍不住摟住她的肩。
過后不久他們就在一起了。
弟弟的女朋友又約他見面,他推辭著說不想出門,但她說就最后一次,有重要的事情要說,他只得按時赴約。這次見面依舊是上次的地方,他等到天快黑了她才到。坐下后,她聊起無關緊要的話題,一直不提“重要的事情”,他也不問,喝著奶茶,等她自己說出口。她像是故意拖延時間,稍一停又談到他的弟弟。
“哥,我感覺你一點都不像你弟。”
他笑笑,說:“我和他恰好相反,我內向,他外向。”
“看得出來。”她的嘴角也微微露出一絲笑。
“你弟那段時間總是和我聊到你。”她說著在手機屏幕上點了幾下,把手機移到他面前,他瞟了一眼,是弟弟和她的聊天記錄,他點點頭,稍微移開眼睛(他不想知道他們聊了些什么),片刻后她拿回手機。
“你弟說你人很好。”弟弟的女朋友說道。
他竟覺得有些尷尬,無聲笑了笑,問道:“那你覺得呢?”
她像是被為難住了,也尷尬地笑著,想了一會兒回答說:“你和你弟都好。”稍后又補充,“你看起來比他安靜一些。”
從坐下到現在,他發現她時不時用手捂鼻子,他想是不是因為自己身上的汗味(他愛出汗),聽說女生的嗅覺比男生的靈敏,可是天氣不熱,身上根本就沒出汗。找不到話說,他又喝了一口奶茶,嗑了幾個瓜子。
她突然說:“總覺得有哪樣味道。”
他抽出一張紙巾擦手,問:“哪樣味道?”
她的鼻子嗅了嗅,然后抬起那碟番茄醬,湊上前聞。又立即放下,歪過頭去吐,幸好只是干吐,什么也沒吐出來。
“你咋了?”他有些不知所措。
她止住干吐,臉被憋紅著。他抽出紙巾遞過去,問:“你沒事吧?”
“我懷孕了。”平靜下來后,她說道。
他驚了起來,大腦瞬間空白,停了停問道:“多久了?”
“你弟住院一星期后發現的。現在差不多兩個月了。”她雙手捂著胸口,“我本來不打算給他講的,但還是講了。”
他知道這就是她所說的重要事情。“你弟說你人很好。”她剛才說的話又在耳邊響著,聯想起弟弟臨終的那個晚上和他談到女朋友,說女朋友人很好。他好像明白了些什么,一個念頭在腦海里閃現,但馬上又被他否定。他抬頭看她,她也正看著他,嘴角懸掛著復雜的微笑。
“我覺得有點突然,你給我講的這個事情。”他語無倫次,“你打算?”
“打掉。”她打斷他,說,“我想這么長時間,已經想好了。”
他咀嚼著她話里頭的兩個“想”字。想了一會兒,覺得這應該是最好的辦法了,問:“準備哪時候去?”
“明天,市里面。今天就過去檢查的,所以才回來這么晚。”
又是一陣沉默,一會兒后他問:“有人陪你去嗎?”
“沒有。你想想,如果我喊別人陪我去,我要咋給她解釋呢?”
他看向窗外,原來樓下是一個籃球場。沒人打籃球,僅有幾個大媽在跳廣場舞,估計是天氣太冷的緣故。他開始想著人流可能導致的種種結果,腦海里浮現出的每一種結果都是令人可怕的。他轉過臉來看她,她的表情很奇怪。
“要不我明天陪你去。”他說。
她沒有回答,又開始干吐,服務員趕緊過來問怎么回事。他對服務員說沒事。服務員走后,他又說:“明天我陪你去,有個人陪著要好一點。”
她點點頭,說:“回去吧,我堅持不住了,怕等一會兒真的要吐出東西來。”
送她回去的路上,他一直說讓她別擔心,就是一個小小的手術而已,不一會兒就可以搞定,而且很安全。她開玩笑道:“這么了解?你以前是不是經常帶女生去?”
他也笑起來,笑過后又設想著后果,如果她因人流出問題(比如不孕),那弟弟真的對不起她。想到這,他說:“明天你不用帶錢,我帶就行了。”
“提錢做哪樣呢?我不會花你的錢,也不能花你的錢吧?”
不一會兒就走到了樓下,他們都停下來。她抬頭,驚訝地說:“月亮好圓。”
他也抬頭,夜空異常地干凈,一輪明月鑲嵌在其中。
“今天應該是農歷十五。”
“不,應該是十六。”他說道,是無意識就脫口而出的。
她拿出手機,打開日歷,說:“還真是十六,你咋記得這么清楚?”
“沒記,看月亮太圓了就曉得的。”他說,“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圓。”
“沒聽過。哪個講的?”
“老一輩人講的。”
“老一輩人?”她顯得有些好奇,“老一輩人還講了些哪樣?”
他愣了一下,嘴唇動了動,沒有回答。一陣風吹來,他說:“快上樓去吧,免得冷著。”
剛和肖莉戀愛那段時間,他每天下班就去找她,兩人尋一家實惠的小餐館吃飯,飯后在夜色中走一會兒,然后他送肖莉回住處,再獨自到站臺等公交車(為了節約錢,不打車)。有時候他們買了菜,去肖莉的住處煮飯。肖莉跟兩個女生合租,她們約定好不準留宿男生。吃過飯他把碗洗了,又趕緊去趕公交。常常到住處已是九點多,但卻不覺得累。匆匆洗漱后躺在床上,想著和肖莉在一起的細節,心里都是偷著笑的。
這一天晚上,肖莉同意跟他去他的住處,他竟然有些緊張。他住的是一棟沒有電梯的舊樓,帶衛生間的單間,不知被多少人住過,墻上留著油漬血漬、不同風格的字跡以及因潮濕而起的濕痕。隔壁兩間住著兩家人,他們的東西屋里放不下就堆在外面,幾乎要占到他的門口,其中一家養著一條難看的狗,他的窗外有一小堆沙子,狗常常過來拉屎,而且半夜一稍有動靜就狂吠不止。睡了一晚,肖莉說:“你這地方簡直不是人住的。”他說:“習慣了。”肖莉把房間收拾干凈,買了新的床單被套來給他換上,說:“我猜,你的床單被子至少有半年沒洗了。”他笑道:“大學時用的,畢業舍不得丟,就搬過來了。”肖莉說:“要對自己好一點。”他摟住肖莉,嬉皮笑臉地說:“你對我好就行了。”
他的一組詩歌又在一家刊物發表,雖然稿費沒上次高,但他們都很開心。肖莉說:“我真想告訴我同事,你是個詩人。”他笑著說:“算了吧,現在‘詩人這個詞是罵人的。”肖莉站在床上,捧著雜志,朗誦道:“我在窗前寫詩/夜色洶涌,多么像童年的哭泣/不經意又出現在電燈下/讓人昏昏欲睡……”他笑著說:“平時覺得你普通話還可以,現在朗誦起來感覺好別扭,像是烏鴉叫一樣。”肖莉把雜志朝他扔過來,說:“是怪你寫得差,好不好?”他躲開,過去跟肖莉嘻嘻哈哈地打鬧起來。
不久后他們迎來第一次爭吵,原因是肖莉每個月都分別給兩個弟弟打八百塊錢。他很心疼似的說:“你咋給他們打這么多錢?”肖莉說:“因為他們是我弟。”他說:“你給他們這么多錢是害他們,讓他們只會享受,以后吃不了苦。”肖莉說:“我讀書的時候窮夠了,和室友去逛街,看到喜歡的衣服都買不起,我不想讓我弟重復我的生活。”他很固執地說:“你信不信,他們拿你的辛苦錢去亂花,甚至還花在女生的身上。”肖莉說:“我弟他們不是那種人。”他因肖莉不聽勸告而激動,突然說了句:“他們不是那種人?他們能好到哪去?”肖莉質問他:“你哪樣意思?”他馬上意識到自己說錯話,可不等他挽救,肖莉就丟下他走了。過后幾天肖莉都不理他,他晚上總守在她的門外。這天晚上刮大風下大雨,肖莉以為他早回去了,可天快亮時聽到因感冒發出的咳嗽聲,開門看到他蹲在走廊上。肖莉一時說不出話來,趕緊把他讓進屋,一會兒后又和好如初了。
他終于攢夠了錢,帶著肖莉去租房子。其實他早就想另租房子的,多少次想開口讓肖莉先付錢,但又覺不好意思。肖莉特意請假休息,和他轉了一天,最終選擇一處價格合適的,只是光線不太好,但也無大礙。當天晚上,他們跑了兩趟,把各自的行李都搬了過來。顧不上休息就開始布置,商量著什么東西放哪里合適。不多時,一個溫馨的二人世界就有模有樣了。
肖莉先洗的澡。等他洗出來后,看到裹著浴巾的肖莉站在窗前,用手機對著夜空拍照。他從后面抱住她,下巴放在她的肩上。她指著月亮說:“你看,月亮好圓。”
他抬頭,順著肖莉的手看去,夜空異常地干凈,一輪明月鑲嵌在其中。
“今天應該是農歷十五。”
“不,應該是十六。”他說道,是無意識就脫口而出的。
肖莉拿出手機,打開日歷,說:“還真是十六,你咋記得這么清楚?”
“沒記,看月亮太圓了就曉得的。”他說,“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圓。”
“沒聽過。哪個講的?”
“老一輩人講的。”
“老一輩人?”肖莉顯得有些好奇,“老一輩人還講了些哪樣?”
“老一輩人還講……”他笑起來,“你屬于我。”
肖莉轉過臉來,他吻在她的唇上。
責任編輯 石彥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