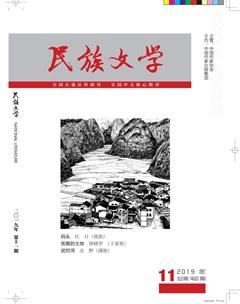山寨記
柏葉(彝族)

我的老家在一個名叫“本扎嶺”的彝族山寨。“本扎嶺”是彝語,漢語意為“群山擁擠的地方”。“本扎嶺”山寨坐落在一個群山懷抱、綠樹成蔭的山頭上,寨子四周的山野里,一年四季盛開著各種鮮艷的山花,還有成群盡情啼唱和飛翔的鳥兒。自古以來,山寨民風淳樸、熱情好客,與周圍的幾個哈尼族和漢族寨子團結友愛、和諧相處。也正因為如此,解放初期劃分階級成分時全寨子都是清一色的貧農。在我的記憶里,那棵生長在寨子東頭的巨大的核桃樹,就是寨子的象征,也是全寨子男女老幼都倍加珍惜和愛護的“寶貝”。
讓全寨子的人在別人面前引以為驕傲的是,這棵核桃樹下還有一眼一年四季長流不息,清冽甘甜而又神奇的山泉水。老輩人常說:經常喝上幾口這眼山泉水,疾病都不敢找上身來,即使是已經生病的人,只要堅持每天喝上幾次這眼山泉水,病自然就會不治而愈。事實也確實如此。久而久之,這眼山泉水的神奇名聲,很多年前就傳遍了家鄉一帶的村村寨寨。人們還說,寨子里之所以每代都出現個把百歲老人,而且大多數都能活到八九十歲,就是這眼山泉水賜給山寨的福氣。寨子里還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任何人都不得用這眼山泉水洗衣服或者澆菜地,也不允許外寨子的人隨意把山泉水挑回去日常使用,要喝可以,就在核桃樹下喝個夠。當然也有破例的時候,外寨子如果出現生病的人,不管是哈尼人或是漢人,都允許把山泉水用木桶挑回去讓其喝個夠,特別是外寨子那些上了年紀的老輩人,還可以安排在房屋相對寬敞的人家住下來,方便他們早晚都能喝上這眼山泉水。
在我童年的時候,山外世界動蕩不安,生產隊長每次從縣城開會回來,都要嚴肅地告誡寨民們說:別老想著“本扎嶺”寨子不安生,這幾年山外世界亂得很,到處都在進行武斗,聽說還死人呢。然后又說:我們要保護好核桃樹下的山泉水,有些人在打它的主意,想把它用鋼管引渡到公社里去,我們堅決不答應的。后來,因為全寨子人的一致反對,還發出狠話說:誰要想引渡核桃樹下的山泉水,首先得問問十幾桿獵槍答不答應。公社里的頭頭們最終還是放棄了把核桃樹下的山泉水引渡到公社里去的計劃。
有一天,阿媽對我說:距離我們寨子兩公里外的“黑找祝”哈尼寨子里,有個六十多歲的老人生病了,唯一的兒子又到很遠的地方修建鐵路去了,多可憐呀,要是每天都能喝上幾口我們寨子核桃樹下的山泉水,病就會好得快了。我聽懂了阿媽的意思。那幾天我也聽說過這件事,說是這個老人生病初期,還能自己走路到我們寨子里的核桃樹下喝上幾口山泉水,然后提著一小桶回去,后來病情加重,走不動路了,他們寨子里起初還有人走上來回四公里山路提山泉水給他喝,但因路途較遠,又忙于活計,后來就沒有人送水給他了。我毫不猶豫地說:阿媽,我每天提一桶山泉水送給生病的老人喝吧。阿媽微笑著點了點頭。就這樣,我每天提一桶山泉水,來回走上四公里,給“黑找祝”寨子里生病的哈尼老人喝,一直堅持了一個多月,直到老人的身體完全康復。記得最后一次送山泉水那一天,老人緊緊握住我的手,感激地說:納蘇(彝族支系)哈尼是一家,孩子,你是個懂事的好心人,長大后你一定會得到老天的保佑。幾十年過去,那個已經八十多歲的哈尼老人還對我們寨子里的人說:聽說“若福波”(我的彝語小名)如今是有名聲的作家了,我二十多年前就知道他會出名的,他心好,老天會保佑。我知道努力才是根本,但我還是愿意聽見這樣的評價。
可是,也不知什么原因,20世紀70年代初期,這棵核桃樹卻發生了變化,那些一到春天就萌芽出小孩手掌般大小綠葉的樹枝,慢慢枯死了,再也長不出每到春天就給全寨子人帶來綠蔭和快樂的綠葉了。那幾年,寨民們每當經過顯得蒼老頹廢的核桃樹下時,總會不由自主地仰起頭來看上一陣光禿禿的樹枝,然后小心地發上幾句牢騷。有人說:“是老天看不過去顛倒是非的世道,才用這種方法懲罰世人的。” 有人又說:“誰叫生產隊長盲目聽從大隊長的話,把全寨子的祖墳地開挖出來改造成耕地了呢?那些丟棄在地垅上白森森的骨頭,全都是我們寨子的老祖先呀,可能是祖靈回來報復了。”也有膽大的說得更直接:“等著瞧吧,總有一天,老天爺會懲罰那幾個一肚子壞水,整天只會動歪腦筋糊弄別人的人。” 然而,無論人們發多少牢騷和詛咒,核桃樹依然生長不出當年那一樹令人陶醉的綠蔭了。更讓人痛心疾首的是,核桃樹下那眼神奇的山泉水,也變得越來越小,到了最后,就像擠不出淚水的干癟的眼睛,一滴山泉水都流不出來了,出水口枯竭成了雞窩似的石坑。
時間一晃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山外突然吹來了一陣陣暖融融的春風。首先是一年苦到頭也吃不飽半年肚子的生產隊體制,宣布結束了,田地實行了包產到戶;接著,生產隊的大小牲畜分到了戶,集體山林也分別實行自留山和責任山,由家庭戶為單位來負責管理。僅僅過去年把時間,寨子里多年來一直無法解決的嚴重缺糧現象改變了,每家每戶的土掌房里,裝滿了金黃的稻谷和玉米,不準家庭種植而被放荒的自留地里,也長出了各種各樣的蔬菜,一直干精瘦骨的牛羊,放養得膘肥體壯。人們臉上的笑容再也不用硬生生擠出來,爽朗的笑聲隨處飄蕩著,人們說話的嗓門大而洪亮,充滿了自信。更讓全寨子人興奮不已的是,那棵枝條枯竭多年的核桃樹,仿佛一夜之間又發出了綠綠的嫩枝與葉子,更讓人驚喜的是,核桃樹下那眼神奇的山泉水,也慢慢擠出了清冽冽的泉水,而且越來越大,穩定下來后,涌出來的泉水居然比當年還要大一倍。小小的寨子又熱鬧起來了,沉寂多年的山歌,白天回蕩在田間地頭,夜晚飄揚在山寨上空。古老的彝族傳統跳大娛樂活動也時興起來了,每當夜幕降臨,或是兩個相鄰彝族、哈尼族和漢族寨子的男女青年們,按照預約好的時間和地點,跑到山頭上或深箐里,一夜歌舞到天亮;或是本寨子的姑娘小伙們,自覺自愿相聚在核桃樹下的那塊草地上,跳起大娛樂,讓整個寨子沉浸在歡樂的夜色中。
前年,在紀念峨山彝族自治縣成立60周年而舉辦的大型慶祝活動期間,二弟一家帶著年過七旬的父母雙親來到了城里。峨山,是中國第一個彝族自治縣,這也是我時常在別人面前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緣故,也因為如此,在紀念60周年縣慶節日來臨之前,我就向二弟發出了邀請。吃晚飯的時候,我和二弟自然而然談起了老家的變化。我離開老家來到城里工作許多年了,回去時間很少,寨子里發生的變化,了解不多,和二弟談談,心里較舒坦。二弟連干幾杯玉林泉酒后,臉上出現了桃花色,說話聲音也亮堂了許多。二弟告訴我,老家近幾年變化更大,山村公路建成了水泥路面,寨子里那些坑坑洼洼的巷道,已經修建成筆直的水泥路面,還實行了人畜分居。二妹是村里的計生委主任,在說完作為民族地區的老家,現在家家戶戶都能自覺遵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后,轉了話題說:大哥,現在山區農村也熱鬧啦,每每有了閑暇時間,周圍幾個彝族、哈尼族和漢族寨子就會跳起大娛樂,跳起花鼓舞,僅我們寨子就有兩支花鼓舞表演隊。我知道我們峨山是彝族花鼓舞之鄉,也知道峨山彝族花鼓舞曾經多年銷聲匿跡,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才逐漸恢復起來,但我還不知道老家這樣一個由彝族、哈尼族和漢族組合起來的地方,如今已成為歌舞之鄉。
這時,一直笑瞇瞇聽著我們談話的老父親,突然插話道:過去呀,彝族、哈尼族和漢族都不團結,經常因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打架斗毆,現在好了,黨的政策合人心,各民族的生活都變好了,心在一起了,真是人心齊,解萬難。接著又說:有了美好的小家,就會有美好的大家,農村富裕起來,國家就會安定,就會變得強大,國家繁榮強大了,別人就不敢隨便來欺負。接著,老父親還高興地說:也多虧了核桃樹下那眼山泉水,全寨子的老人現在很少生病,身體好得七八十歲了還挑得動百多斤的擔子。
哦,老父親雖然只讀過兩年書,居然也能說出這般道理,我心里的激動真是無法用語言表達了。老父親說得對,有了美好幸福的小家,有了團結和諧的村寨,我們就會擁有繁榮富強的國家,我們就會盡情享受到新時代美好的生活。
從峨山縣城前往西北方向的富良棚鄉政府,路程53公里,途經岔河鄉和塔甸鎮。我要去采訪的塔沖村,就坐落在富良棚鄉政府往東三公里處一個四周長滿茂密松柏的小平壩里。作為中國第一個彝族自治縣的峨山,境內彝族居住最集中的就是富良棚、塔甸、岔河、甸中這四個鄉鎮,塔沖村是這四個鄉鎮當中居民清一色彝族,新時期以來社會經濟發展變化最大的一個彝族村。
“塔沖”是彝語,漢語意為松柏蒼翠的地方。在前往塔沖村的路上,公路兩邊的田地里,油菜花已經開謝,飽滿的油菜籽在微風中紛紛向我點頭致意,那些散布在山野里的桃樹、梨樹和桑樹,盛開著紅的、白的和淡紫的花朵,它們有的是種植的,有的是野生的,但在開花時節,人的眼睛很難辨別開來,只感覺到繁花似錦,分外妖嬈。走進村口,眼前陡然出現一片整齊劃一、白墻綠瓦、十分醒目的民居,還有一條條筆直寬敞的街道。村口有一個碧波蕩漾的人工湖,幾十只鴨子悠然自得地在湖面上游玩著,十幾棵種植在湖邊的香椿樹已經吐出了粉紅的嫩芽。看著眼前耳目一新的景象,回想起37年前我在校址富良棚的縣民中讀高中時對塔沖村的印象,變化之大使我一時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
正當我滿懷激情地觀賞著這令人感慨不已的村容村貌時,一位年紀70多歲,身板硬朗的老人,健步向我走來,顯現在臉上的笑容明確地告訴我,他已經知道我今天前來塔沖村的目的是什么。一走近我,老人就爽快地伸出手來,一邊熱情握手,一邊聲音洪亮地說:“歡迎,歡迎,村主任李成濤一個多小時前就告訴我今天中午你要來我們塔沖村采訪。”然后,他自我介紹說,他是塔沖村關工委副主任,名叫李良仕,今年已經73歲了。我們邊走邊談,十幾分鐘后來到了一個四方形的大約1000多平方米的廣場,廣場左上方直立著一個巨大的青石,上面鏤刻著五個紅色的大字:“合家歡廣場”。老人告訴我,每當夜幕降臨,“合家歡廣場”就成了歡樂的海洋,男女老幼齊聚在廣場上,圍起一個大圓圈,跳起彝族傳統舞蹈大娛樂,實在熱鬧非凡。
來到關工委辦公室,老人首先給我倒了一杯熱茶,然后滔滔不絕地講起了塔沖村的變化。老人說,如今的塔沖村,有252戶,943人,是峨山縣境內彝族居住比較集中的村寨。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彝族大村,20世紀50年代初期,全村只有瓦房20所,其他全是土掌房,而且無論瓦房或土掌房,都破舊不堪,用現在的標準來說,都是危房。后來,在“大躍進”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些祖先遺留下來的文物古跡又遭受到了嚴重破壞,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塔沖村簡直不成樣子了,別說民房七零八落,破舊不堪,就連一處茶余飯后休閑娛樂的場所都沒有。更突出的是,人心不齊,思想觀念落后,經濟一無所有。因為貧窮落后,連年饑餓,村子里經常出現小偷小摸,鄰里糾紛也鬧得一塌糊涂,小姑娘紛紛嫁出村子去,小伙子久久娶不到媳婦。那年頭啊,每個人做夢都盼著何時能吃上一頓飽飯,哪年種的糧食夠吃一年,什么時候能把塵土飛揚的馬路修建成寬敞的水泥路面。老人還跟我回憶了一個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故事:有一天,縣文化館搞攝影的柏映泉老師到塔沖村拍攝照片,需要找幾個村子里年齡80歲以上的老人拍幾張人物肖像,可是,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一個80歲以上的老人,直到這時候,人們才突然發現整個塔沖村里,年齡最大的老年男人只有71歲,女人只有69歲。而如今,全村80歲以上老年人已經有四五十人,最高年齡已到91歲,而且都充分享受到了政府的關愛、家庭的溫暖、社會的和諧和生活的幸福。現在,村子里早已建立衛生所,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人管,長壽老人越來越多。
這時,有個一直坐在我旁邊的老人,滿面紅光地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好政策,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日子。”接著又說:“過去,我們村的小伙子總是因為娶不到媳婦而整天愁眉苦臉,有些甚至好吃懶做,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現在是倒回來了,到處都有人在說‘嫁女要嫁塔沖人,上門要上塔沖村。這是了不起的變化呀,我們當年做夢都做不到的這一天,現在終于看見了。”說完,老人喝了口水,又向我談起了他們家的生產生活情況:現在,他們家有五口人,兒子兒媳在家生產勞動,孫子高中畢業后出外打工,兩位老人已經70多歲,不再做什么體力勞動,只是力所能及的幫忙做點輕松的家務,即使如此,每年的烤煙收入也有四五萬元,前幾年種植的核桃現在也掛果了,這幾年每年又增種了一畝多菜豌豆,加上一些雜七雜八的收入,一年忙碌下來,至少也有六七萬元的收入,除去生產生活方面的開支,結余下來的也有三四萬元。
當我問到新農村建設方面的情況時,辦完事剛來到關工委辦公室的村委會主任李成濤說:現在全村已有53戶在2017年春節前搬進了寬敞明亮的鋼混結構新民居;第二批120戶新民居建設工程目前已經開始動工,預計年底可以搬遷新居;第三批新民居建設項目也已規劃好。根據現在的進度情況來看,塔沖村在不超過兩年的時間內就可以完成全村新民居建設任務。
李主任剛說完,縣委工作組派駐富良棚鄉協助配合鄉黨委和鄉政府開展扶貧開發與基層黨建雙推進工作的邱永洪告訴我,在新農村建設方面,目前,除了完成第一批53戶新民居的建設任務外,同時還完成了黨員活動室、科技文化活動室、居家養老中心、衛生室,合家歡廣場、兩座公廁、三個停車場、兩處水景觀等公共設施項目的建設任務,總計項目投資達2500多萬元。當我詢問到塔沖村群眾的經濟收入情況時,邱永洪說:塔沖自然村分為四個村民小組,2016年全村經濟收入1300多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7500元,這次新民居建設,平均占地面積120㎡,建蓋二層,建筑面積228㎡,每套房子工程造價約22.5萬元左右,其中,國家及省、市、縣補助3萬元,需要貸款的農戶,政府出面給予貼息貸款15萬元,三年期限內的利息5.7當中,政府負責貼息3.7,農戶負責2,三年期滿后,如果還沒有還清貸款,利息由農戶負擔,但這種情況應該很少。
這時,村委會李主任補充道:多年來,烤煙一直是塔沖村的經濟收入支柱,全村每年種植烤煙在1800畝左右,總收入650多萬元;其他還種植核桃3500多畝,2016年收入20多萬元;種植櫻桃50畝,冬桃500畝,一兩年內即可收益;還有養殖大戶6戶,其中黃牛40頭,生豬400頭,本地山雞1.5萬只,本地山羊120只,全年養殖方面的收入也在100多萬元。現在,養殖大戶雖然只有6戶,種植業方面也有更大的拓展空間,養殖業和種植業兩個方面的發展基礎和勢頭都比較好,因為現在的塔沖村,群眾對保護自然生態的意識已經有了很大提高,近十年來,經過宣傳教育,群眾本身也總結吸取經驗教訓,到處亂砍濫伐,隨意亂挖亂采的現象已經不再出現。
聽到這里,我緩緩走出辦公室,來到樓頂,舉目望去,發現這個群山環繞的小平壩,四周森林密布,松濤滾滾,藍天白云,陽光燦爛,群鳥紛飛,山花爛漫,生存環境確實有了根本上的保證。
對此,塔沖村三組組長龍家榮有著更深層的體會: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光靠政府出面宣傳教育是不夠的,一定要讓群眾自己切身體會到破壞自然環境帶來的后果是如何嚴重,群眾本身才會自覺自愿行動起來,也才能最終達到切實保護好自然生態和生存環境的真正目的。他還深有感觸地說:我們這一帶地處高寒山區,地下水資源少之又少,生產生活用水主要還得靠雨水來積蓄,而森林就是天然的蓄水池,森林遭到了破壞,雨水又靠什么積蓄得起來呢?所以,首先要讓群眾從思想上認識到這個根本性的問題,自覺自愿去履行好作為村民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只有這樣,我們基層領導的各項工作才能得到順利開展,我們塔沖村的塔沖夢,才能變得人心聚齊,清晰明了。
在文化教育方面,村主任李成濤深有感觸地說:20世紀70年代,全村只有群眾推薦出去的一兩個工農兵大學生,很多年輕人僅僅是附設初中畢業。現在,塔沖村在外讀大學的年輕人已有30多個,每年都有好幾個大學畢業生,甚至有了博士生。有些年輕人高中畢業后沒考上大學,就外出打工,一方面自謀生路,一方面見世面、學技術,他們是現在和將來我們塔沖村各方面建設事業的中堅力量,同時也是塔沖村走向更加美好明天的致富帶頭人。
說到這里,李主任笑了笑說:這也是我們塔沖村一個不可或缺的塔沖夢,這個夢就是我們塔沖村所有夢想的基礎之夢。一切建設都離不開科學文化,掌握好了科學文化這個基礎,各項建設才搞得好,精神文明建設才能搞上去,搞好了精神文明建設,全村團結和睦的優良傳統就會自然而然的發展和傳承下去。邱永洪接著說:“說到文化教育,我也認為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一定要抓緊抓實,決不能放松。有文化的人和沒有文化的人,質的區別就在于人的素質的高低,素質低下的人,是不會有什么理想的。要實現我們塔沖村的塔沖夢,教育是基礎之中的基礎。有個老人跟我談起過,說是一輩子吃虧就吃虧在沒有文化,無論搞點種植業或者養殖業,都離不開文化知識。這是大實話。”
我說,上午從富良棚鄉政府前來塔沖村的路上,我看見幾十臺農用拖拉機在田地里忙碌著,發現那些農用拖拉機駕駛員都很年輕,寬敞的鄉村公路兩邊,還停放著很多摩托車。說到這個情況,李主任告訴我,現在塔沖村又忙碌起來了,再過個把月,就到了烤煙移栽的時節,家家戶戶都在忙著整理移栽烤煙的田地,烤煙是塔沖村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這是黃金季節,不忙不行。接著又說:那些年輕人本來還在城里打工,因為是農忙季節,特意趕回家里幫忙的,他們都是有文化、懂科技的人,現在的農業生產,缺少不得科技文化知識,每家每戶都很重視這方面,所以,真正意義上的普及農業科技還得依靠他們來實現。
在離開塔沖村返回縣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塔沖村的塔沖夢,應該是個什么樣的夢呢?用他們自己的話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年到頭苦死累活只要能夠吃飽肚子就行,其他沒有任何企望;到了八九十年代,他們最大的心愿也就修建一條水泥路面的鄉村公路,多出來幾個讀書人,其他沒有什么更多的期盼;而現在的塔沖人,已經非常明顯地看得出來,他們的要求不僅僅是吃飽肚子和修建一條鄉村公路這樣簡單了,他們已經從思想上、觀念上改變了以前的夢想。如今的塔沖人,不但要一個整齊劃一、寬敞明亮的新農村,而且還要一個團結和睦、環境優美的新生活,還要一個文化濃郁、文明富裕和素質高尚的人文新天地。這就是塔沖人的追求,這就是塔沖人的塔沖夢。
責任編輯 陳 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