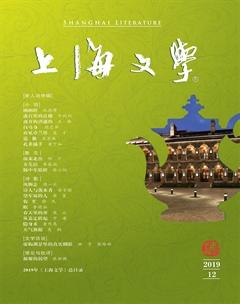凝聚的渴望
張怡微
問題的提出
我發(fā)現(xiàn)青年寫作者們似乎總說不好友情故事,尤其是對于女性的青年寫作者而言,女性友誼的呈現(xiàn)更成為了一個創(chuàng)作難點。總結(jié)下來,有幾方面的原因可能形成了講好友誼故事的阻礙:一、家族有姐妹,一般而言血緣關(guān)系比非血緣關(guān)系牢固,打發(fā)時間的需求可以滿足;二、利益平衡/爭奪是任何關(guān)系的試金石,年輕創(chuàng)作者缺乏參與社會資源分配的實際經(jīng)驗;三、消費主義對身份認同焦慮的影響。不少青年寫作者們認為,友誼故事很難寫。盡管“結(jié)交最好的朋友”是青春前期兒童同輩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童年自覺“爭取”友誼的努力在寫作中卻很少發(fā)揮出良好的情節(jié)功能和敘事潛力。在大部分故事里,友誼的言說方式既沒有發(fā)揮以兒童之眼看世界的優(yōu)勢,也沒有展示性別差異的敘事功能。
要在中國故事中尋找一些友誼書寫的范例,最容易聯(lián)想到的依然是經(jīng)典名著《紅樓夢》,因為《紅樓夢》里人多、女性多。然而,仔細研判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富貴場”、“溫柔鄉(xiāng)”幾乎是一個封閉的環(huán)境,家族身份的認同更體現(xiàn)為“人在體系中所占據(jù)的結(jié)構(gòu)位置”,大觀園不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體系,少男少女在成長過程中所經(jīng)歷、參與到的,是借由身份進入的阻力最小的路。歐麗娟教授提醒我們,在《紅樓夢》的神女譜系中,警幻給男性的幫助是“啟悟與解脫”,在點化過程中她還會積極介入給予幫助,試圖改變他們的命運,但小說不斷暗示著讀者,“女性”,即使是優(yōu)秀女性,所面對的都是悲劇的命運,其中沒有人為努力的空間,也就沒有扭轉(zhuǎn)命運的機會(歐麗娟:《大觀紅樓2》)。在當(dāng)代文學(xué)中,作家蘇童也寫了不少女性(友誼)故事。王宏圖教授曾經(jīng)和蘇童做過一個訪談,問蘇童“怎么看待女性命運?一些女權(quán)主義者認為女人的困境是男人和男人的文化造成的;但也有人出來反駁這種觀點,他們認為男人也是某種社會體制和結(jié)構(gòu)的受害者,他們拚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博取女人的歡心,女人也沾了男人的光,間接的得益匪淺。你對女人的基本看法是什么?”這當(dāng)然是非常學(xué)院派的問法,蘇童回應(yīng)說,“我從小便覺得女人命苦,這主要是外婆留給我的印象……我的作品中女性是處于弱勢的一方,她們受到了傷害。如果問到底是什么傷害了她們,可以說是男權(quán)社會,國家機器,或者傳統(tǒng)的文化。然而,大家在談?wù)撨@個問題的時候,常常忽略了女性對自身的損害,在很多時候她們會有作繭自縛的選擇。我認為關(guān)照女性在小說中的功能時,我要凸顯她作為女人本身的這個問題,這是文學(xué)應(yīng)該關(guān)注的問題。”(王宏圖:《蘇童王宏圖對話錄》)作為映照可以看到男性視角在女性關(guān)系書寫中的潛在意圖,即女性命運的悲劇性在小說里是如何呈現(xiàn)的——呈現(xiàn)為,“幫不了”。作家看到了她們的聰明、美麗,也看到了她們掙扎、損害,可惜的是,“沒有扭轉(zhuǎn)命運的機會”。這可看作是一類女性故事書寫的潛意識。本文無意討論文學(xué)研究中的性別議題,相反性別在此將會是一個較為棘手的分別方式,因為它并不會解決青年寫作者為什么寫不好友誼故事的問題。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寫作的困難本質(zhì)上反映了創(chuàng)作者對于“友誼”命名的困難。說起來很稀奇,因為我們想當(dāng)然認為每個人都有朋友,女性日常社交的朋友數(shù)量會比男性更多,但要說清楚友誼形成的過程卻比較麻煩。“有朋友”卻不一定有完整的友誼故事,日常友誼的延續(xù)不是以故事的完整性作為支撐的。生活中的友情可以是沒有情節(jié)可言的,但小說里的友情卻少不了要有情節(jié)的需求。這是寫作的難點,也是創(chuàng)造的樂趣。
它對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對于友誼故事來說,什么是“關(guān)鍵情節(jié)”。在這一點上,男性友誼的論述非常值得參考。如河合隼雄在《大人的友情》一書中給我們提供了頗為小說化的指標:“所謂朋友,就是半夜十二點開車來,后備廂里裝著一具尸體,問你該怎么辦時,都會二話不說地幫忙想辦法的人。”河合隼雄認為,這一具體例子可以化為平常說的,“不管任何時候,發(fā)生任何事情”、“不管你做了多么惡劣的事情”、“二話不說”、“幫忙想辦法”……這意味著彼此擁有深厚的信賴關(guān)系。又如小說《圍城》,方鴻漸與趙辛楣的友誼起源于他們同時喜歡上了蘇文紈但都追求失敗,這也會結(jié)成深厚的男性友誼。其他事件如借錢、托孤、為別人坐牢等……指標化的情節(jié)雖然通俗,卻十分具有說服力,會讓讀者相信忠誠、團結(jié)、信任是有價值、有力量的。然而在女性友誼故事書寫中,這樣的例子就很稀缺。因為“耐心傾聽陪伴”這樣日常生活中女性友誼的建構(gòu)方式,很難在具體的文學(xué)實踐中有效推動故事的展開。本文關(guān)切的問題在于,能否通過理性爬梳“友誼”故事建構(gòu)的過程,發(fā)現(xiàn)更多的復(fù)雜欲望,并照亮一些新的寫作契機,和女性寫作的優(yōu)勢。
“友誼”的命名
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第八卷中曾定義“友愛”,他認為“(友愛)是一種德性或包含一種德性。而且,它是生活最必需的東西之一。因為,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沒有人愿意過沒有朋友的生活……關(guān)于友愛本身的性質(zhì),人們有許多不同意見。有的人認為,友愛在于相似。另一方面,有的人則說,相似的人就如陶工和陶工是冤家”。他將友愛提升至公正、共同道德、共同體同樣的高度,讓“共同”這一關(guān)鍵詞在友愛關(guān)系中成為核心。我們的四大名著中,有兩部男性故事表現(xiàn)了類似的友誼觀念,《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對于“共同利益”的描繪就很精彩,讓我們確認了關(guān)于中國式“友誼”的大眾常識,即“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劉關(guān)張?zhí)覉@三結(jié)義,一諾千金。以至關(guān)羽在曹操手下時,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關(guān)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情義至深,曹操只能表示敬佩。作為映照,我們卻很難用一句話說明《紅樓夢》或《紅粉》中的女孩們的共同利益到底是什么,她們互相教育的訴求又是什么,想要發(fā)現(xiàn)新的“友誼”故事的敘事空間,當(dāng)務(wù)之急是找到新的“共同”使命,或持續(xù)的“共同利益”。“結(jié)盟”是需要社會動機和符合社會條件的。在中國的語言環(huán)境中討論“友愛”,我們不太說“善”,而更喜歡說“義”。“義氣指同道中人之互相撐腰,是朋黨之間的忠誠而已……講義氣的目的是求取相互保護以增加生存的機會;再進一步言之,所有自覺在危險中斗爭的人群,也罕有不講究分辨敵友的小圈子道德的。”①孫述宇認為,“義”字背后有迫害感和邊緣性,“聚義”代表了同做危險的勾當(dāng),“義膽”表示在法外行徑上與同道合作的勇氣。這種文化心理甚至超越了國界,被一再搬演。
如最明確表達要對“友誼”這個詞語的內(nèi)涵進行重新命名的作品,是馬里奧·普佐的暢銷小說《教父》。老教父唐·柯里昂經(jīng)常談起“友誼”。小說開篇就說,“人人向唐·柯里昂求助,希望也從不落空。他不許空頭支票,不找借口掩飾懦弱,說什么世上還有更強大的力量束縛他的雙手。他不必是你的朋友,連你有沒有能力報答也無關(guān)緊要。不可或缺的條件只有一個:你,你本人,要承認你對他的友誼。”他暗黑的權(quán)力大廈似乎非常需要一個柔軟的包裝,而他選擇了命名“友誼”。故事的起點出現(xiàn)了六個需要唐·柯里昂幫助的人,西西里人在女兒結(jié)婚的那天有不能拒絕別人要求的風(fēng)俗。老柯里昂將這些人曾經(jīng)、或未來寄存的所謂“人情”以預(yù)支的方式加以兌現(xiàn)。他執(zhí)意為這種明確的“交易”命名為“友誼”,小說之外的我們,卻很容易就能感覺到這種“友誼”不過是一種優(yōu)雅的說辭。好像老教父總是彬彬有禮地表示“我會提出一個他不會拒絕的要求”,最后卻用槍頂著別人的腦袋一樣。《教父》中“友誼”的建構(gòu)不斷加固著老柯里昂的權(quán)力體系。他并沒有依靠威脅,甚至不透過購買,而是依靠權(quán)力本身的“吸引力”(庇護作用)獲得人間“友誼”,獲得的方式是“交換”。讀者都知道,這是法外交易,而且懲罰規(guī)則完全由教父本人制定。他拒絕幫助殯儀館老板的時候說,“你踐踏我們的友情,唯恐欠我的債……你生意興隆,過得不錯,以為這世界是個無憂無慮的地方,你可以隨心所欲享受快樂。你不用真正的朋友武裝自己,因為有警察保護你……我的感情受到了傷害,但我不會把友誼硬塞給并不需要的人,尤其是那些看不起我的人。”而且他認為“男人比女人更理解友誼”。我們很難揣測作者本人為什么選擇“友誼”這個名詞來形塑老教父的人格,在教訓(xùn)別人的時候,老教父問了和亞里士多德一樣的問題,“幸福的人需要朋友嗎?”讓“友誼”的問題回歸到了倫理學(xué)的拷問中。實際上,對于這部通俗小說而言,“友誼”只是一個虛擬的象征。從“麥克”的角度來看,《教父》有很強的成長小說的味道,說的是一個在父權(quán)陰影下曾經(jīng)善良、叛逆的翩翩少年,如何一步一步成為了“真正的西西里人”的故事。家族親情的不死不棄,基因力量的頑強,要遠遠勝過所謂呈現(xiàn)“友誼”價值的企圖。
不僅男性友誼書寫受限于這種邊緣性的牽絆,好讀的女性友誼故事也多是風(fēng)塵中的結(jié)義(如小說《紅粉》),亦或是因故被社會邊緣而結(jié)伴共同生活的情誼(如電影《自梳》)。“好人好朋友”這樣的敘事因缺乏沖突,是青年創(chuàng)作者面臨的困窘。“江湖義氣是亡命漢的商標”,但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亡命的經(jīng)驗。友誼除了“義”之外,還有些什么搬演的路徑呢?友誼的舞臺很可能轉(zhuǎn)移到了虛擬世界。技術(shù)時代對我們每個人的社交生活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中間當(dāng)然包括了年輕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當(dāng)機器(手機、電腦、互聯(lián)網(wǎng))越來越成為我們生活史和情感史的重要載體,“友誼”將如何重新命名。它會不會受到古典時代對于“友誼”書寫的規(guī)范,又會不會打破那些規(guī)范,這都是非常有趣的話題,有待未來的寫作者來開拓。簡而言之,小說的責(zé)任是發(fā)現(xiàn)“友誼”在虛構(gòu)的世界里應(yīng)該是什么樣的,或者將問題的焦點更集中一些,女性的友誼在小說里應(yīng)該是什么樣的。
“當(dāng)兩人結(jié)伴時”
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是,男性友誼的呈現(xiàn)更多表現(xiàn)為兩人以上的團體(如《美國往事》、史蒂芬·金《尸體》),而女性友誼的呈現(xiàn)則表現(xiàn)為“當(dāng)兩人結(jié)伴時”,這幾乎已經(jīng)成為窠臼。這種故事類型被演繹得非常多,近期比較暢銷的小說如《我的天才女友》(埃萊娜·費蘭特)、《搖擺時光》(扎迪·史密斯)、《螢火蟲小巷》(克莉絲汀·漢娜)、《對岸的她》(角田光代)等都表現(xiàn)了兩個女孩共同學(xué)習(xí)、共同成長的歷程,在游戲或?qū)W藝的過程中,她們會討論到身體的變化、外在相貌的差異、自我表現(xiàn)和異性關(guān)系等內(nèi)容,對外部世界的關(guān)注程度或許會決定故事的深度。如扎迪·史密斯本人對公共議題(“種族、階級、女性”)的參與度就很高,《搖擺時光》將“友誼”當(dāng)作觀摩外部世界豐富面向的媒介;埃萊娜·費蘭特則揭露了那不勒斯女性生存和女性教育的殘酷境況,莉拉和埃萊娜可以看作是同一類女性的不同命運,實現(xiàn)了“what if”虛擬敘述的意圖,這也是文藝作品描繪女性友誼的常見套路(如電影《七月與安生》)。兩個女孩的敘事模式或成為了兩種命運的可能性,或互為鏡像(“世界上的另一個我”),在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期內(nèi)表現(xiàn)為內(nèi)部競爭,甚至是相互嫉妒。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我的天才女友》和《我是紗有美》(角田光代)都提到了美國作家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小說《小婦人》,雖然《小婦人》描寫的是親姐妹的故事,但對女性自我教育而言是一部一再被創(chuàng)作者致敬的經(jīng)典(“如果你覺得你的價值只在當(dāng)裝飾品,恐怕有一天你會相信,你真的只是這樣。時間會腐蝕所有表面的美,時間無法消滅的是,你心靈美好的運作,你的幽默,你的仁慈,以及你的道德勇氣”)。《小婦人》中男性的缺席并不是她們主觀造成的,而是南北戰(zhàn)爭的外部原因。女性結(jié)盟的方式也受制于時代的局限性。
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中曾提到“女人間的友誼其實是用芥蒂結(jié)成的,越是有芥蒂,友情越是深。她們兩人有時是不歡而散,可下一日又聚在了一處,比上一日更知心”。既是描述、也是評議小說主人公王琦瑤和她人生不同階段女性好友的關(guān)系。此外,王安憶有兩篇紀念散文同樣型塑了女性友誼在文學(xué)呈現(xiàn)上的特征,追憶陸星兒的《今夜星光燦爛》與追憶程乃珊的《她多么愛生活,愛得太多太多》。在《她多么愛生活,愛得太多太多》一文中,王安憶借用越劇《紅樓夢》黛玉焚稿的唱詞:“這詩稿不想玉堂金馬登高第,只望它高山流水遇知音”,揭示了長久以來女性寫作的初衷并不是為了功名,也沒有途徑求取功名,而是為了求知音。在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期內(nèi),中國女性能寫的事情不多,女性沒有資格寫作所有的事。在有限中尋找意在言外的心靈價值,成為了女性書寫精神性的指標。在《今夜星光燦爛》一文中,王安憶提到了“隨著交往漸深、漸久,我們的話題也輻射開去,覆蓋彼此之后二十多年的生活,然而,寫作,卻始終貫穿其中,是一個基本的線索……我們在許多事情上會發(fā)生嚴重的分歧,可我依然十分驚訝她的感受是如此不同。”文章反復(fù)提到“談不攏”的氣餒,但談不攏并非是因為不想談攏,恰恰是“止不住地還要談”。“交到最好的朋友之后,對他的和最好朋友的行為抱有更高的期望,這些期望往往導(dǎo)致異議或爭論”②是《今夜星光燦爛》一文真正的動人之處。一樣是少年時期開始熱愛寫作的文字生涯中人,三位女作家(另一個是王周生)通過寫作生活凝聚到了一起,擁有了共同的理想和使命。
在西方小說里,女性友誼呈現(xiàn)的類型不少,主要表現(xiàn)為女性對“友誼”的看法,這種看法是和女性主義的意見緊密相聯(lián)的,如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和《謝莉》,是有意識書寫女性結(jié)盟的作品。我們在中學(xué)里閱讀《簡·愛》,經(jīng)常把它當(dāng)作一部女性如何成就自身的范本來閱讀。即使知道簡·愛具有許多珍貴的品格,她的形象依然像一個永遠在憤怒的人一般難以親近。如果我們用現(xiàn)代心理學(xué)的觀點來看,簡·愛這種天然的個性特質(zhì),與其說是反抗特征,不如說是她拒絕向世界提供某種獎賞價值。勞渥德學(xué)校的橋段巨細靡遺地描述了一個十歲時失去雙親的女孩子所經(jīng)歷的家變、瘟疫、飲食及所能獲得的有限的教育等等。這似乎是一所黑幕重重的學(xué)校,有非常多的暴力、霸凌、凌辱和饑餓,“揭露”的勇氣是需要一個強動力支撐的,作者胸中有怒。這種怒火不是針對疾病本身,而是針對道貌岸然的管理者,針對少女命運的不服從。在這一團怒火中,簡·愛在學(xué)校也完成一段非常正常的、陪伴型、精神性的女性友誼的確立。簡·愛的童年好友海倫·彭斯是一個天使般的女孩子,受的苦也比簡·愛多,但她卻對簡·愛說,“你把她(里德太太)對你所說所做的一切記得多么詳細啊……”記錄詳細的,還有勞渥德學(xué)校的體罰、惡劣的伙食和不被及時治療的兒童傷寒。這個因傷寒早逝的女孩還對簡·愛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她說“你把人的愛看得太重了……”與簡·愛相比,海倫·彭斯要平和很多。這令人相信,作者能夠辨析公正與偏見。作者之所以保留偏見,一定是有所意圖。此外,《簡·愛》對“友誼”是有一些獨特的描述的。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小說,會發(fā)現(xiàn)與《教父》類似的關(guān)系建構(gòu),她執(zhí)著于命名關(guān)系。繼承遺產(chǎn)后的簡·愛以一萬五千英鎊確立了與圣·約翰一家的親情。簡·愛對圣·約翰說,“我已經(jīng)下定決心,要有一個家和幾個親戚……部分地報答深厚恩情,給自己贏得終身朋友的樂趣……而你卻根本想像不到我多么渴望兄弟姐妹的愛。”稍微理性一點的圣·約翰表示質(zhì)疑,“簡,你所渴望的家庭聯(lián)系和天倫之樂,除了用你考慮的方式之外,你還可以用其他方式獲得啊;你可以結(jié)婚。”但簡·愛固執(zhí)己見,不耐煩地拒絕了。所以簡·愛也在試圖命名關(guān)系,她要以自己的方式定義“親情”和“友誼”,而不是服從社會約定俗成的慣例。這與創(chuàng)作者想要在小說中重新命名“關(guān)系”的企圖是相似的。
在寫作《簡·愛》之后,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部作品《謝莉》同樣描寫了女性之間、母女之間的友誼、同盟,她用大量筆墨描寫了女性之間的對話,反復(fù)肯定了女性友誼的價值,這反映了19世紀女性面對的種種社會偏見,并非針對性別,而是針對“關(guān)系”。如“男人眼中易變善妒的女性之間能否產(chǎn)生真正的友誼”、“女人之間的關(guān)系可否健康”、因為男女的社會地位不同“你也許同一個男人有友誼,而在他看來,卻沒有什么重大的看法和興趣是同你有關(guān)聯(lián)的”等等。卡羅琳與謝利之間的友誼具有精神性的排他功能,且作者認為,婚姻會有破壞女性友誼的排他性,而且女性能夠互相給予的東西,父兄及丈夫都無法給予,她們卻渴望那種東西。《謝莉》的寫作意圖有其更為獨特的時代背景,19世紀英國女性人口的極大過剩導(dǎo)致了多于百分之三十的女人終生不嫁,這些獨身女性如何自主自立成為 一個全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謝莉》應(yīng)被看作是一個要自謀生路的女作家對當(dāng)時的社會焦點的自覺回應(yīng)③。
“婚戀”與女性友誼的關(guān)系有別于男性友誼書寫傳統(tǒng),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數(shù)。《水滸傳》中梁山好漢訂盟,訂的那么勤又那么急,可見背后迫切的生存愿望。女子結(jié)婚卻不可能集體草率。回到亞里士多德所言,雖然尋求利己是個考慮,友誼會帶來互惠,但互惠是最脆弱、最經(jīng)不起考驗的。我們說的情誼,不管是兄弟的、親人的、夫婦的,都在描述一種關(guān)系,一種使人與人凝聚起來的力量。友誼,當(dāng)然屬于那樣一種力量。人愿意與自身以外的人在一起,產(chǎn)生凝聚的意愿非常重要。而如果意愿接近到渴望的程度,就必定會產(chǎn)生交往,遭遇磨合的風(fēng)險。好的友誼,一定會使人共同成長、共擔(dān)風(fēng)雨,也能共享福樂。
“男人比女人更理解友誼”?
“男人比女人更理解友誼”這話來自于《教父》,作為文本之間的交際,夏洛蒂·勃朗特的回應(yīng),能使女性產(chǎn)生“凝聚的渴望”的力量顯然是要戰(zhàn)勝這種偏見。因為無論是厭女的硬漢故事類型,還是擅長世情書寫的男性作家,很少有看好女性友誼的范例。
蒙田在《論友誼》一文中就認為,“以女人尋常的能力來說,她們難以勝任維系這個神圣紐帶所需要的交流和溝通;她們的靈魂不夠堅強,不能承受如此沉重而持久的關(guān)系。④”愛爾蘭小說家威廉·特雷弗也寫過友情。短篇小說《友誼》表面上圍繞著女性婚姻與友誼不相容的主題,實際上還是在表達對女性友誼不可靠的嘲諷。不可否認的是,女性婚姻與友誼的矛盾是存在的,男性婚姻與友誼的矛盾則顯得微乎其微。這是在小說中作為變量的“婚姻”對于男女成長的不同影響所造成的。
夏洛蒂·勃朗特寫作《謝莉》的故事也非個案,金雯教授曾細讀英國小說家理查遜的書信體小說《克拉麗莎》,提到小說里“克拉麗莎唯一感受到的純粹友誼來自安娜小姐,在她受勒夫萊斯誘騙離家出逃陷入困境時,安娜不僅提供金錢支援,還提出和她一起去倫敦。正因為如此,她與安娜小姐的關(guān)系在小說里成了克拉麗莎唯一認可的親密關(guān)系,被賦予了崇高的類似婚姻的含義。她多次稱安娜小姐為愛人,并把自己的戒指作為遺產(chǎn)贈送給這位唯一的朋友”。她指出,克拉麗莎的選擇并非空穴來風(fēng),而是與18世紀早期的女性思潮相吻合,且在小說里就受到了男性父兄的蔑視。但“婚姻是友誼的最高形式”,仍然不失為一個好的話題。《克拉麗莎》中單身女性及女性之間友誼的刻畫方式,有和男性友誼書寫相似之處,如救援之力的呈現(xiàn);也有差別,如信物或遺物的托付。金雯最后提出,“女性間的友誼是《克拉麗莎》開拓出來的一個新的文學(xué)母題,體現(xiàn)了這種情感對于異性婚姻的重要補充作用,也顯示出其脆弱和艱難”。
古今中外,在相當(dāng)長的時期之內(nèi),女性的生存處境決定了女性在文學(xué)中的處境,這暗示著女性命運與悲劇創(chuàng)作的親密聯(lián)結(jié)。女性通過觀察母親、模仿母親獲得女性經(jīng)驗,通過友誼、創(chuàng)傷等經(jīng)歷完成自我啟蒙,女性友誼又會受到異性婚姻的考驗。歸根結(jié)底,一個女性在社會上闖蕩總是有風(fēng)險的,這種風(fēng)險性會彰顯規(guī)訓(xùn)的作用,例如在遇到利益沖突的時候,女性終究會選擇丈夫和后代,而不是女性盟友和真相。韓劇《我親愛的朋友們》中有一句臺詞,一位女主人公對她的好友哭訴道:“你為什么每天都活得那么苦,讓我沒辦法完全依靠你”,暗示女性不是不想講義氣,而是女人因為自己受苦,才看得見朋友的苦。她們都是沒有辦法從苦海中脫身的人。回應(yīng)到本文開篇所引蘇童所言,“我從小便覺得女人命苦”,可見女性友誼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再向閨蜜發(fā)出共同受難的邀約。
另一方,面對于小說寫作而言,風(fēng)險未必是一件壞事,還可能是一種敘事契機。許多女性精英在小說里完成自我蛻變,結(jié)果不一定是悲劇。如德萊塞筆下的“嘉莉妹妹”,從一個面粉廠工人的女兒逐步攀登,終于成為了芝加哥尤物。可惜我們很難對“嘉莉妹妹”發(fā)問,她是不是需要一個幫助她的女性朋友,因為幫助她的男性已經(jīng)很多了。又如愛麗絲·門羅,同樣寫作了大量的女性,她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社會身份,生活于不同的時代,她們可能是女兒、妻子、情人、繼母、祖母……她們各自經(jīng)歷的內(nèi)心生活與命運波瀾。作為個體的她們甚至?xí)慌酝怂餐p蔑(如《恨,友誼,追求,愛情,婚姻》)。所以,共同討厭一個人似乎也能結(jié)成女性的同盟,這種同性的迫害之力,從另一層面上居然也能幫助小說主人公完成命運的突圍。
本文開篇曾經(jīng)提到有幾方面的原因可能形成了講好友誼故事的阻礙,第三點是“消費主義對身份認同焦慮的影響”,只能在此略作補充。在近期青年寫作的題材方面,出現(xiàn)了“追星”與“微商”的內(nèi)容,那顯然也是符合“凝聚的渴望”特征的,且與消費、與機器的聯(lián)結(jié)非常緊密。它不再拘泥于同性、異性友誼關(guān)系的習(xí)套,且涉及金錢、時間、沖突等多重通俗性的要素,還相當(dāng)具有女性特征。可惜的是,這雖是年輕人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卻并沒有出現(xiàn)特別有心靈價值的作品,有待于未來的研究者和創(chuàng)作者繼續(xù)觀察實踐。
余論
至此可見,想要理順一些習(xí)以為常、卻不知其所以然的關(guān)系并非易事。西方有其得天獨厚的文化路徑,例如從打破基督教父權(quán)的庇護,或要求直接與上帝對話等方式⑤,重塑“凝聚的渴望”,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有瑪麗蓮·羅賓遜的《管家》,小說的訴求非常明確,通過露西爾和姨媽希爾薇的結(jié)盟,重塑女性與自然的關(guān)系(而不僅僅是與男性的關(guān)系)。如果能去性別化地看待“友誼”的寫作母題,“友誼”故事并不一定非要獨立成為創(chuàng)作題目,而是靈活隱藏于童年書寫或成長小說中的。圍繞這個主題,大部分優(yōu)秀作品,都會寫到青春的逝去與友情的落幕。這并非是女性寫作獨創(chuàng)。如宮本輝的《泥水河》,表面上寫的是童年友誼,實際上寫的是戰(zhàn)后心靈創(chuàng)傷對孩童命運的影響。史蒂芬·金的小說《尸體》很好詮釋了友誼、死亡與失去。《尸體》在1986年被改編成電影《伴我同行》,故事的主題被凝練為“后來我再也沒有交過像我十二歲時那樣好的朋友了”。而這段深刻的友情故事,緣起于尋找一具尸體的游戲。小說里寫到“最重要的事情往往也最難以啟齒”,“這種事隨處可見,有沒有注意到,朋友在你生命中進進出出,好像餐廳中的侍者來來去去一樣。可是每當(dāng)我想起那場夢、想到那兩具尸體正用力拖我下水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樣也好。有的人會沉淪,如此而已,并不公平,但世事就是這樣,有的人會沉淪下去”。回應(yīng)到歐麗娟認為《紅樓夢》傳遞出的悲劇主題,表現(xiàn)為女性的命運沒有人為努力的空間,也就沒有扭轉(zhuǎn)命運的機會……其實在新的時代,年輕男性也未必有扭轉(zhuǎn)命運的好運。“友誼”問題不是區(qū)分男性和女性的邊界,但友誼書寫是一個非常好的媒介,為創(chuàng)作者所利用觀看外部世界的變遷。這是可以被一再書寫、一再挖掘的母題。
本文討論了為女性寫作“友誼”重新命名的文學(xué)可能性,期待一種打破“兩人結(jié)伴”的俗套模式,照亮生活史和情感史的縫隙,創(chuàng)作前景廣闊。從世情角度而言,重組家庭的倫理關(guān)系中就存在有類似親戚的“友愛”關(guān)系。從機器與傳播角度而言,如今的游戲、閱讀APP大多帶有社交功能,虛擬交往和情感依戀未必存在于現(xiàn)實世界,其中一定有發(fā)現(xiàn)新故事的可能性。從女性角度而言,有非常多的前沿研究發(fā)現(xiàn),“女性之間的友誼,可以提供學(xué)習(xí)成為自我的最佳條件。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女人的交談無足輕重或是自我放縱。女性的亞文化以交談為中心:我們應(yīng)該把它視為我們的力量之一,而非弱點之一”⑥。文學(xué)化的“交談”與交際,可能成為青年寫作者探索世界的協(xié)作工具。女性的友誼,雖然從未成為人類關(guān)系的典范,卻正因沒有答案、沒有結(jié)論的現(xiàn)狀,為青年寫作創(chuàng)造了寫作條件。問題的關(guān)鍵,是要找到能使女性產(chǎn)生“凝聚的渴望”的關(guān)鍵力量。無論是在文學(xué)內(nèi)部,還是在文學(xué)以外。
① 孫述宇:《水滸傳:怎樣的強盜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頁。
② 【美】威廉·科薩羅《童年社會學(xué)(第二版)》,上海: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2014年,第213頁。
③ 史汝波:《淺析〈謝莉〉中的女性同盟與友誼》,參《山東社會科學(xué)》2004年第5期,第78頁。
④ 轉(zhuǎn)引自金雯:《理查遜的〈克拉麗莎〉與18世紀英國的性別與婚姻》,參《外國文學(xué)評論》2016年第1期,第35頁。
⑤ 到2015年,英格蘭圣公會才有首位女主教。
⑥ 【英】詹尼弗·柯茨:《女士交談:建構(gòu)女性的話語》,吳松江等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第3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