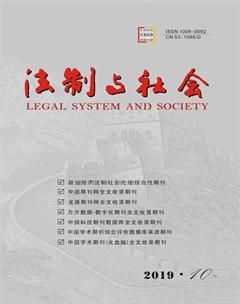試論我國前科消滅制度構建的必要性
于光明
關鍵詞前科 前科消滅 犯罪標簽 社會要求
我國現行刑法沒有明確規定前科的具體涵義,但學界存在兩種主流觀點:一為前科就是以前的犯罪認定或記錄;二為前科須以刑罰處罰為必要前提。首先,本文認同第一種觀點。前科的成立沒有必要以處刑作為條件。其次,設立前科,是為了向社會表明該犯罪者存在潛在的人身危險性,預防其再次犯罪。為什么說只有被進行過有罪宣判的人即成立前科,這是因為相對于未犯罪者,其實實在在存在一定的社會危險性。最后,本文認為,前科的設立,是為了最大程度上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但我國刑法中還存在著有罪宣告但免于刑罰處罰的特例,比如赦免,超過追訴時效等。然而,這些因素都不會降低其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
盡管我國未明確規定前科的具體涵義,但在1997年刑法修訂時增加了前科報告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典》第100條規定:“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求有關單位加強對犯罪者以往犯罪記錄的有效監管,防止其再犯可能性。
一、我國前科報告制度的缺陷
首先,并未明確犯罪者的社會危害程度。在前文中提到,前科應以有罪宣告為前提,無須進行刑事處罰。從犯罪的主觀方面來看,其社會危害性必須差別對待。此外,一個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與犯罪情節輕微的犯罪分子,這二者的社會危害性是大有區別的,但他們卻毫無差別地終身報告自己曾經犯罪的事實,其實質上忽視了犯罪者社會危害的差異性。其次,前科報告制度并未規定履行報告義務的期限。從這一制度的內容可以發現,前科報告義務與刑滿釋放之后需要履行義務的時間長短并無關系,也就是說向有關部門報告其曾經犯罪這一事實在時間上沒有固定的限制,即無期限地報告。那么,假設罪行廢止,就沒有報告的必要了。但在我國,無論是以何種形態的犯罪都存在犯罪記錄,而且終身不能消除。因此,本文認為,無期限地進行前科報告,有悖于“浪子回頭”的目的,不利于犯罪者完全重新回歸社會。最后,前科報告制度的義務僅僅是單純地向有關部門報告。而這樣的“自我式暴露”使得犯罪者遭受現實社會的拋棄。出于本能的自我保護,犯罪者勢必會以各種隱瞞的方式逃避這種報告義務,因此,前科報告義務履行的效果并不會達到理想的效果。出于以上幾點原因考慮,前科消滅作為前科制度的重要內容,在我國司法改革領域中仍然應當被立法者重視。
二、我國建立前科消滅制度的社會要求
(一)建立前科消滅制度的現實要求
在建設新時代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司法改革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而前科消滅制度作為刑事立法的重要環節,有必要對其大膽嘗試,進而填補我國在前科制度方面的立法漏洞。基于此,前科消滅制度的構建具有現實的社會意義。
1.構建和諧社會與法治文明的需要。當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時代發展的主題,而和諧社會的構建離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將如空中樓閣一般。所以,在社會主義發展的今天,確立前科消滅制度,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就目前的社會中,仍存在著許多威脅和諧與穩定的因素,其中,前科人員高頻度的再次犯罪率占據著重要地位。和諧社會追求以人為本,而“以人為本”應該是一個內涵廣泛的概念,當然,它應當包含前科人員。我國社會主義的刑法本著“懲罰與改造相結合”的理念,更應該盡力消除社會對前科者的身份歧視,使其盡早融入到正常的社會生活中去。通過建立前科消滅制度,預防犯罪者二次犯罪,真正意義上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穩定發展。
2.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要求。人權,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法治中國所追求的,而且也是世界為之奮斗而永恒不變的主題。但是,在現實中,那些曾經犯過罪的人或誤入歧途的人卻因“前科”這一“犯罪標簽”并未真正受到社會的尊重。從表象上看,是社會輿論給前科者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壓力,比如用人單位和同事。首先,犯罪者刑滿釋放,回歸社會后,由于法律規定,禁止他們進入某些行業;其次,有些前科者雖已就業,但他們無時無刻不受到同事道德上的歧視。但從內在方面看,立法與司法制度層面關于前科問題的空白應該是其根源所在。而前科消滅制度以關注人性、尊重人權、肯定人的價值為理性目標,為犯罪者與社會構筑了一座橋梁。
3.刑法走向現代化的追求。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當然離不開刑法的現代化。我國刑法的現代化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實現與政治、經濟、思想密不可分。我國刑法走向現代化,既需要人們在思想領域樹立全新的犯罪認識,也需要制度領域和司法實踐的改革。在此,本文認為如何正確對待幾千年中國傳統刑法文明是解決我國刑法走向現代化必須重視的一個問題。
中國歷代的刑法都給犯罪者貼上了刑罰的“標簽”。除死刑之外,以殘害犯罪者的肢體最為殘酷,比如,為了方便官方和普通人能夠鑒別、遠離犯罪者,在犯罪者臉上刺字,同時也以此來羞辱犯罪者。
前科消滅這一刑事政策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廣泛采用,在刑事領域具有蓬勃的生命氣息和深遠的實踐意義,進一步推動了人類法律文明的進步,是一個國家法治走向成熟的標志。從法的移植與繼承看,我國立法,都是在繼承我國原有立法精華并正確認識國情的基礎上吸收、借鑒外國優秀立法成果,當然,實現我國刑法的現代化,在司法改革過程中,有必要在犯罪前科領域進行制度創新,與世界刑事立法接軌。
(二)建立前科消滅制度的理論來源
1.前科消滅制度的法理學依據。本文認為,前科制度,永久性地存在違法的正義性,即與法律公平、平等背道而馳,應當予以消滅。此處有必要談及到前科消滅與功利主義的關系問題。
功利主義學說最早由17世紀的邊沁提出,其主張“絕大多數人的幸福”。即只要法律實現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令其幸福,就認為該制度是公平的、平等的。此說法與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強調國家利益至上,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要求是一致的。
按照功利主義理論,只有在社會產生最大限度的幸福和利益的基礎上,才能保證個別或少許的幸福。但這樣,將與最初法律的公平和平等的理念自相矛盾。比如,當有前科者在刑滿釋放后積極向上,遵紀守法,但現實中他們卻不能和普通人一樣正常就業,正常尋求法律的保護等等。在現實社會中,前科制度是以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對犯罪者的利益有所侵害而存在的。古人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社會資源的利益分配面前,前科者因其過往的罪過而喪失其對社會資源的占有與分配,勢必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2.前科消滅制度的刑法目的性要求。前科消滅制度,作為一項刑事范疇的法律制度,應當與刑法的目的性在實質上具有共同的趨向性。
刑法所要追求的,一方面是打擊犯罪,另一方面是對犯罪者的權利進行保障。但二者實質上卻是沖突的:如果過分強調對社會的保護,那么勢必降低對犯罪者人權保障的標準;反過來,如果過分強調保障人權,那將是變相地縱容犯罪。我國刑法理論界通說認為,我國刑罰的目的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本文認為,在偏重兩種預防的基礎上,應注重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要求犯罪人有必要因其犯罪行為與罪過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和刑罰。
犯罪者的改造效果真正體現在釋放出獄后較長一段時間內是否遵紀守法、不再犯罪。然而,這樣的改造需要社會給予犯罪人一個改過自新的平臺。因此,本文認為,我國司法領域應該將前科消滅作為一種激勵機制貫徹執行,使犯罪者在二次犯罪面前真正“懸崖勒馬”,從根本上減少社會對抗,緩解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