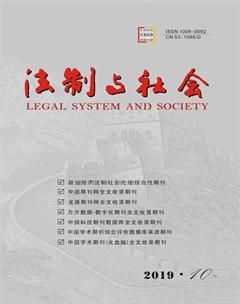論單位犯罪代罰制的缺陷及完善
張應林
關鍵詞單位犯罪 處罰模式 代罰制 缺陷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刑法對單位犯罪采用的是“以雙罰制為主,以單罰制為輔”的混合制處罰模式。具體而言,“單罰制”在我國特指“代罰制”,即“指刑法只規定對單位中實施單位犯罪的自然人處以刑罰,而不處罰犯罪單位的模式”。雙罰制與單罰制(代罰制)并存的混合制說是我國通說。
據筆者統計,《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刑法》規定為單位犯罪的罪名共128個,其中既處罰單位又處罰責任人員的罪名115個,占89.8%;處罰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罪名8個,處罰直接責任人員的罪名5個。從刑法修正案對單位犯罪的調整情況來看,九個修正案共增加了25個單位犯罪罪名,其中規定對單位和責任人員均予以處罰的罪名21個,占84%;處罰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罪名3個,處罰直接責任人員的罪名1個。從刑法修正案的發展來看,代罰制出現了逐步調整的跡象,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11個單位犯罪罪名,采用的都是雙罰制。我國單位犯罪處罰模式為何沒能統一?代罰制有何利弊?取消代罰制統一處罰模式是否可行?本文將試圖解答這些問題。
二、單位犯罪代罰制的主要情況及其存廢之爭
我國《刑法》規定單位可以構成犯罪但只處罰責任人員的法條共10條,涉及13個罪名。從罪過形態上看,這13個罪名可分為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從犯罪是否牟取經濟利益的角度看,又可以分為貪利型單位犯罪和非貪利型單位犯罪。
立法部門對某些單位犯罪實行代罰制,是基于對很多特殊情況作出的特別規定,具體如下:
1.對單位進行處罰在特定場合下有違立法本意。如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該條立法本意是為了保護中小股東和其他人的知情權,如對單位進行處罰將損害無辜者的合法利益,故只規定處罰責任人員。
2.單位過失犯罪是單位成員的過失犯罪,責任人員應罪責自負。分析單位犯罪的實質,根本淵源還是自然人的意識。尤其在單位過失犯罪中,單位也是直接受害者,因此只宜處罰瀆職責任人員,不宜株連單位。
3.追訴犯罪時單位已不存在。如妨害清算罪,雖在清算階段單位仍然存續,但實踐中,案發之時往往已清算完畢,單位已辦理注銷手續而不復存在,此時對單位處以罰金刑已無可能,只能追訴具體實施妨害清算行為的責任人員。
4.不應對非貪利型單位犯罪科處罰金刑。如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作為規定在危害國家安全罪一章中的罪名,該罪不以牟取經濟利益為目的,若處罰金刑將使犯罪與刑罰不相適應,綜觀該章的所有罪名,均沒有罰金刑的適用余地。
5.刑罰手段的單一使得有些罪名只能適用代罰制。如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考慮到發生安全事故的單位應立即整改,還要對傷亡人員進行治療、賠償,需要大量資金,所以沒有規定對單位判處罰金。既然不宜判處罰金,刑法對單位犯罪的刑罰種類又只規定了罰金刑(不得緩期執行),故只能對單位不予處罰。
上述分析不無道理。但代罰制破壞了刑法的基本原則,與單位犯罪的理論依據和刑罰目的不符,應當對代罰制進行嚴格地檢視,以厘清代罰制存廢之利弊。
三、單位犯罪代罰制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分析
單位犯罪代罰制的缺陷表現如下:
1.代罰制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與傳統的罪刑相適應原則相比,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更強調體現刑罰個別化,將單位犯罪置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中考量,單位實施犯罪行為與被科處刑罰之間必須考察其有無刑事責任及責任之大小,有則處罰,無則免處,大則重處,小則輕處,這是刑罰個別化的體現。單位既然可以成為犯罪主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卻在個別罪名中不對其規定刑罰,無異于承認刑事違法性、有責性與應受刑罰處罰性可以割裂開來,實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縱然代罰制單位犯罪有故意與過失之分、貪利與瀆職之別,但其充其量只是刑罰個別化的考量因素,而不足以對單位免予處罰。
2.代罰制有損刑罰的公平性。資助恐怖活動罪與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同為單位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與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同為《刑法修正案(八)》認定為特殊累犯的適用類罪名,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大抵相同,但前者實行雙罰制,后者卻實行代罰制,令人費解。又如,強迫勞動罪已被《刑法修正案(八)》調整為雙罰制,但該條之一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仍然實行代罰制。該罪的主觀惡性與社會危害性與強迫勞動罪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對這些單位進行處罰同樣令人費解。
3.非單位犯罪罪名與代罰制單位犯罪罪名表述相同,易產生誤解。我國刑法判斷一罪名是不是單位犯罪,一是看條文中有沒有“單位、公司、企業、機構”等用詞,二是看表述上對處罰對象的規定。代罰制單位犯罪一種常見的表述方式是不說明犯罪主體,在處罰對象上表述為“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或“對直接責任人員”。筆者統計發現,刑法中另有5條罪名的表述方式與此相同,根據司法部門的解釋,這些罪名不屬于單位犯罪。從表述來看,二者很容易引起誤解,代罰制單位犯罪的范圍變得莫衷一是。
四、單位犯罪處罰模式的完善
1.正確界定單位犯罪的范圍。單位犯罪的概念是一個從立法、司法和理論上都沒有得到明確界定的問題,且一直存在爭論。盡管單位犯罪概念眾說紛紜,但“為單位謀取利益”這一要件已為學界、實務界所公認。筆者認為,在立法部門對“單位犯罪”概念作出界定前,不妨以“為單位謀取利益”要件為標準,將一些非貪利型單位犯罪罪名排除出單位犯罪的范圍。這些罪名有的屬于過失犯罪,單位本身蒙受重大損失,還有后續重建、賠償等事宜需要大量資金,對其處以罰金刑并不現實;有些罪名雖是故意犯罪,但單位本身是受害人,雖以單位名義為之,但所得利益歸自然人所有,單位并非適格的犯罪主體,不構成單位犯罪。因此,對這些罪名以自然人犯罪論處,就能解決適用代罰制帶來的弊端。
2.完善刑罰手段。如果單位的設立是為了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或者單位設立時雖然不是為了實施該犯罪,但后來主要轉為實施該犯罪的,不構成單位犯罪。如果單位有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又有資助行為的,如何處罰?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國外立法例,對資助單位處以資格刑,如禁止從事職業性或社會性的活動(相當于對自然人科處“自由刑”);對自然人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解散法人(相當于對自然人科處“生命刑”);還可以向社會公布單位罪行。對于虛假破產罪,可以設置罰金刑緩刑制度。
一方面,對單位實施“假破產、真逃債”行為的,仍然規定罰金刑,以保持刑罰的統一;另一方面,對罰金刑設置緩刑,有利于保障債權人能夠充分追償,對單位的經濟活動能力也不會形成扼制,還可以通過緩刑監督程序來促進犯罪單位的改造。
3.對部分貪利型單位犯罪嚴格實行雙罰制。對于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正如上文所述,可以比照強迫勞動罪實行雙罰制。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對于依法負有信息披露義務的單位而言,具有明顯的牟利性,侵害的客體是公司、企業的信息披露制度,對社會公眾的利益以及國家經濟決策的制定危害很大。盡管有論者認為對單位科處罰金會株連無辜股東,但在公司法上,公司與股東是分離的,“投資者履行出資義務、成為公司股東后,不再對其出資享有所有權,……只有公司自身而非股東才能成為公司財產的所有者。……若將股東權理解為物權或所有權,就將走向否定公司法人所有權(或公司財產權)甚至公司法律人格的理論誤區,或陷入違反‘一物不得二主原則的‘雙重所有權的泥坑。”可見,公司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對違反信息披露制度的單位處以罰金刑,嚴格地說處罰的是公司擁有所有權的財產,而并非直接針對股東。“這種對法人刑事責任的追究,實際上就是對法人人格的一種否認,因而必然使處罰效果及于法人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等。”因此,對單位和單位中責任人員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對于違法運用資金罪,由于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受托管理機構有可能利用公眾資金進行投資營利,且這類犯罪主體一般都有獨立于公眾資金外的自有資產,對單位處以罰金刑既符合可罰性,又具有可行性。對于妨害清算罪,雖然追訴犯罪時單位往往已不存在,對其處以罰金有落空之虞。但是,“處于清算狀態的公司仍是公司,清算中的公司與解散事由出現前的公司共享同一法律人格。”既然妨害清算行為由單位實施,單位即使已辦理法定手續注銷,仍應對其財產的承繼單位追究刑事責任,沒有承繼單位的,仍應在處罰自然人外,以處罰單位的名義對違法獲取單位財產的自然人處以罰金。否則,不足以有效打擊和預防公司、企業在清算階段的犯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