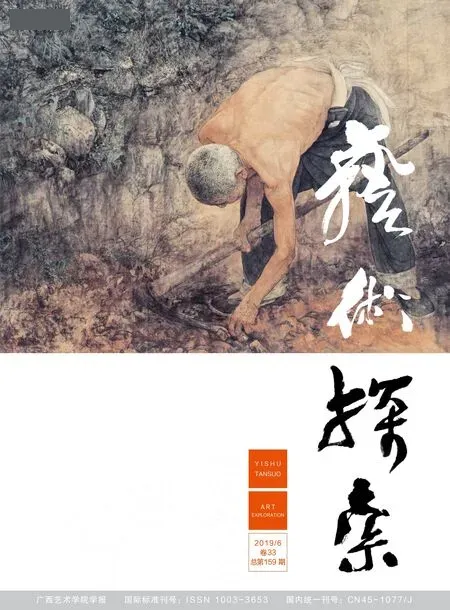也談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關系
——以兩個音樂實地調查案例為例
林立策
(泉州師范學院 音樂與舞蹈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
局內人和局外人是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老生常談的一組概念。“局內人與局外人產生于語言學,后在人類學中被廣泛應用,兩個概念強調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兩種身份。”[1]45沈洽、張伯瑜、楊民康等學界前輩,對這組概念及相關理論都有過很詳細的論述,似乎已再無討論的必要。然而,以往人類學家或民族音樂學家作異文化(他者)的研究時,局內人(被研究者)和局外人(研究者)的身份界線十分清晰。但是,近年來隨著“雙重音樂能力型學者”的成長,以及“本土文化研究者”的出現,兩者的身份變得不易區分。在此情形下,探究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關系又有些許必要,也有現實和理論意義,這關乎研究者能否在實地調查中收集有用可靠的信息,以及能否作深層的文化闡釋和相對客觀的論述。
本文所論源于筆者在音樂實地調查中的感悟,不當之處,望方家指正。
一、兩個“音樂實地調查”案例
(一)案例一
2008—2014年間,筆者因撰寫碩士和博士論文①筆者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是有關道教齋醮科儀音樂方面的研究。之需,經常去溫州地區的一些道教宮觀和民間道班做調查。期間,溫州大學音樂學院正在開展“浙南音樂文化數據庫”建設,其中本地道教音樂是該數據庫所要收集的對象之一,于是,業師陳克秀讓筆者協助參與相關工作。
2012年1月4日,溫州市甌海區白云觀舉行“大羅寶殿落成典禮道場”。筆者與溫州大學音樂學院的陳克秀和劉青松兩位老師,以及舞蹈和音樂理論專業的兩名學生,全程記錄了當天的活動。在調查過程中,當我們面對同一場“齋醮科儀”時,不同學科專業的人所關注的對象或者說切入點是不一樣的。筆者更關注音樂本體,及它與科儀行為之間的關系;劉青松老師是攝影專業,更關注儀式過程中各種畫面的不同呈現,及畫面在空間上的意義;舞蹈專業的學生更關注舞蹈(如道教禹步和手印)的肢體語言及其象征內涵。由此可見,不同學科專業的研究者面對同一文化現象時,其切入點及所選的局內人對象可能會存在差異。
筆者有做道士的經歷,又長期調查研究科儀音樂,對科儀相關內容相對比較熟悉。因此,在調查過程中,老師和同學們遇到一些不懂的科儀行為及其內涵都會來詢問我,在他們眼里,我似乎已具有了道教“局內人”的性質。
對于永嘉正一道的法事,筆者如其他道友一樣直接參與做道場沒有太大問題。有時參與做道場會有信眾詢問:“這位‘先生(即筆者)’是哪里來的?平時并不多見。”此時,道友們介紹說:“他可不是真正的道士先生,他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生,專門來作道教音樂研究的。”可見,即使我的參與在信眾眼里與其他道士無異,但在道友眼里,我與他們又有所區別,畢竟我不是以做道士為正業。
(二)案例二
2014年9初,筆者到泉州師范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工作,學院領導將我分配在南音系,希望我能參與南音的調查與研究。
2014年11月7日晚,本院碩士三年級研究生陳振梅帶筆者去泉州文廟聽南音。文廟古色古香,原為祭祀孔子的場所,現被私人承包來做茶館,每天晚上都有南音表演,供當地百姓或外來游客欣賞。當晚,觀眾中有一位德國游客,我問她:“對南音的感覺如何?”她說:“非常好聽!我喜歡這種優美舒緩的旋律,但是聽不懂。如果像你們一樣能聽懂那就更好了。”一對從湖北來此旅游的年輕夫妻對同樣問題的回答也是“聽不懂”。另外,我還特意詢問了一些當地人,讓我意外的是,來此聽南音的一些當地人也“聽不懂”南音。
若以地域文化來區分,相對于泉州當地人,湖北與德國的游客都是泉州文化的局外人,泉州當地人為局內人;但若以南音技藝所屬而論, 南音藝人才是南音文化的局內人。可見,對于局外人與局內人的劃分,又存在著對象選擇和劃分標準的差異。
陳振梅從小是在南音圈子里長大的,對南音文化了如指掌,技藝很嫻熟,對當天茶館表演的曲目也是如數家珍。當晚李建瑜先生邀請她上臺“玩南音”,可她婉言謝絕,并說明自己是來做調查的。在我眼里,陳振梅儼然已是南音文化的局內人,但當晚她因陪同我做調查,把自己當作了局外人。
二、研究者的“中間人”角色
對上文兩則案例,筆者有兩點思考:首先,筆者和陳振梅都是從小成長于本土文化之中,而后走上學術道路并研究該文化的人,在做田野調查時,我們扮演著什么角色;其次,不同學科選擇局內人的依據或標準是什么。
欲弄清這些問題,先來看看學界關于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定義。
局內人指的是與研究對象同屬于一個文化群體的人,他們享有共同的(或比較類似的)價值觀念、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局內人之間通常有類似的生活經歷,對事物也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局外人指的是處在某一文化之外的人,與這個群體沒有從屬關系。局外人通常與局內人有不同的生活體驗,只能通過外部觀察和傾聽來了解局內人的行為和想法。[2]81
前文已述,局內人與局外人的劃分是為了區分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差異。因此,只要明確了研究者(局外人)的身份,自然也就明確被研究者(局內人)的身份。然而在實際情況中,研究者是否能完全融入成為局內人,或將自身完全置于研究對象之外?
在實地調查中,當研究者帶著一定的理論與方法對研究對象進行調查研究時,他們已不可能完全跳出該文化群體而成為純粹的局外人。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強調研究者(局外人)參與觀察以獲得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有“參與”就不再是純粹的“外部觀察和傾聽”,研究者就要與局內人以及他們所屬的文化打交道,了解他們的文化,并盡可能地站在他們的文化立場(如“雙重音樂能力”)來參與、思考、理解,在此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推理、判斷和解讀,否則就是研究者的主觀臆測。雖說絕對客觀的研究不存在,但所有的研究還是要以一定的事實為根據。因此,研究者實際上也就具有了部分局內人的特征,而不是純粹的局外人。
研究者雖然知曉研究對象,但還是不能真正如局內人一樣完全理解其所屬的文化。因為思維是獨立的個體活動,也是長期習得的結果,個體與個體之間無法進行思維轉移,所以,研究者只能在一定限度內對該文化有所理解。“極少數人類學家試圖‘變成當地人’,但仍然被當地人當作外人。”[3]278“無論彼此如何熟悉,在當地人眼中,調查者難以成為真正的‘局內人’。”[4]24
對于那些成長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者”,他們又是否還是純粹的局內人?
“作為一名局內人,當他轉變自己的身份,開始對自身文化進行研究時,他為了研究所進行的學術訓練必將完成了或部分完成了他作為局外人的塑造過程,當他自認為帶著局內人的眼光來看到自己的音樂文化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站到了局外人的位置。”[1]47“當一個人作為一名研究者對自己的文化進行研究時,他就已經與自己的文化拉開了一定的距離。他已經(而且必須)站到一個與自己同胞不同的觀察視角上,才有可能看清楚自己的文化和人民(包括他自己)。……所有的科學研究者實際上都是一定意義上的‘局外人’,他們在從事研究的時候必然地帶有自己的理論框架,代表的是某個特定的科學家群體的研究范式。”[2]86
一旦以學術研究為目的,那么,即使是本土文化成長起來的研究者,也不再是純粹的局內人了。上文兩則案例中,筆者和陳振梅雖然都成長于自己所屬的文化,我們與樂人們“同屬于一個文化群體”,還“享有共同的(或者比較類似的)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但我們的行為方式或生活經歷,以及看法已經不完全一致了,該文化群體也不會把我們視為其成員,因此,我們再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局內人了。
研究者所扮演的這種既不是局外人(Outsider)又不是局內人(Insider)的中間人(Inter-sider)角色,無論與主位研究(Emic)還是與客位研究(Etic)相比較,都有很大的區別。它既不是從研究者的立場出發,也不是從調查對象的立場出發,而是從保持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自然的矛盾張力狀態出發。在調查中,研究者若發現與調查對象之間的關系太近,就主動疏遠;若發現太遠,就主動靠近。總之,研究者要始終與調查對象之間保持一種自然的矛盾張力狀態。[5]51
綜上所述,局內人—局外人顯然已經無法作為對應被研究者—研究者身份劃分的依據。研究者的身份其實非常特殊,他們既不是真正的局內人,也不是純粹的局外人,而是游離在局內人—局外人的關系之間,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而自然兼備“雙視角觀照”[6]20的研究方法。因此,局內人—局外人的關系已不是用來說明研究者的身份問題,而是強調研究者所持研究視角的問題。
三、局內人與局外人的“動態關系”
研究者作為中間人的角色明確后,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關系,仍需作進一步討論。研究者做研究以獲得有用的資料和信息為首要,對研究者而言,能否找到真正的局內人,是有效開展研究的關鍵。局內人是文化持有者,也是該文化最有力的解釋者。研究者找到了真正的局內人,也就等于找到了解讀該文化內涵的一把鑰匙;反之,研究者沒有找對人,其研究成果也將會大打折扣,不能使人信服。那么,以身份差異來劃分局內人與局外人的關系也仍有意義,只是局內人不再簡單對應于研究者(局外人),而是取決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他所持的研究視角。那么,誰是真正的局內人,誰又是局外人?
第一個案例給我們的啟示是,當不同學科的人來研究同一個文化事項時,因不同學科究對象、研究方法和觀察視角的不同,他們對局內人的選擇會存在差異。不僅如此,同一學科的研究者也會因不同的研究側重點,對于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劃分有所不同。
第二個案例給我們的啟示是,研究者若以地域文化來劃分局內人和局外人,那么,會建立起千萬種局內人—局外人關系。比如,對于德國人而言,我們都是所屬中國大文化的局內人;對于湖北來的游客來說,泉州當地人都是南音文化(小文化)的局內人;對于南音館閣而言,館閣樂人才是其文化的局內人。這如同幾何圖形,一個“大圈”包含幾個“中圈”,一個“中圈”又包含許多“小圈”。地域范圍從大到小,被研究者群體對象不斷減少,研究者對文化的認識則是從宏觀到具體、從共性到差異性的不斷深入。還有很多其他的劃分標準,比如若以掌握南音技藝而言,所有南音樂人都是南音文化的局內人,它又包含了不同館閣的群體。
局內人和局外人所對應的群體,仍是研究者人為劃定的結果,一旦局內人的身份被劃定,局外人也隨之而定。只是“局內人與局外人之確定條件是研究者與(音樂)文化的‘距離’”[1]47。局內人—局外人的關系既取決于研究者具體的研究意圖,又由研究者所處學科的特性而定。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再選定具體的文化事項及其所涵蓋的群體對象。因此,局內人—局外人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種動態關系。這由研究者游離于局內人—局外人關系之間的中間人角色使然,體現了不同學科研究對象和研究視角的多樣性,必然也帶來不同局內人對文化解釋的不同。這也說明,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者在一定范圍內劃定對象的有限認識,而不是某些文化的全部。
研究者的中間人角色,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動態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局內人域局外人的動態關系
小結
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以往用局內人和局外人這組概念來劃分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身份,顯然有其局限性。研究者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既不是局內人,也不是局外人,而是在局內人—局外人的關系中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其研究自然兼具“雙視角”的觀照。因此,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劃分,不是用來說明研究者的身份問題,而是來強調研究者所持研究視角的問題。在實地調查中,研究者能否找到真正的局內人是有效展開調查和研究的前提,因為一定的文化內涵只有特定的局內人能解釋。因此,對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身份劃分仍有意義,只是研究者游離于局內人—局外人之間,其研究意圖和研究視角,決定了局內人—局外人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呈現出動態關系的特征。局內人所選對象有所差異,對文化的解釋就會有多個面向,那么,研究者在此基礎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自然也會呈現出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