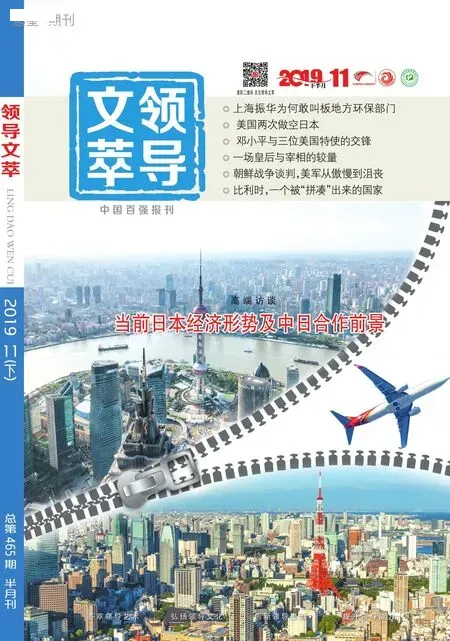明朝大內總管違反政治規矩的下場
廖保平
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二十五日,天空明凈湛藍,京城格外熱鬧,人們圍觀大內總管劉瑾被凌遲處死。
劉瑾乃非同尋常之人,他6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后凈身入宮當了太監,遂冒姓劉,侍候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朱厚照。由于他頗能掌握太子的玩性,投其所好,用打獵、斗雞、遛鷹等把戲拴住朱厚照的心,博得太子的喜歡。朱厚照繼位,是為明武宗,劉瑾順理成章得到重用。
1508年,他掌握了司禮監掌印大權,這是明朝管理宦官與宮內事務的眾多部門中權力最大的部門,成為實實在在的大內總管,無論臣工奏疏、官吏任免、邊關來往文件以及皇帝詔諭的傳發,都經由此部門過劉瑾之手。
處在這樣的一個地位,貪腐受賄,撈取錢財,開口即有,點頭可得,最終達到了無處不伸手的地步。
只是對于皇帝來說,貪腐是皇帝對官僚忠誠的一種收買,只要官僚對皇帝忠誠,不因貪腐導致“民憤極大”,危及政權,這點錢財對于富有天下的皇帝來說算得了什么?反貪腐常常不過是清理政敵、平息民憤的手段。
就是在與劉瑾有矛盾的官員楊一清和太監張永趁平叛安化王朱寘鐇叛亂,密告劉瑾十七條罪行,并且連夜逮捕和查封劉瑾的宮內外宅第的情況下,明武宗仍只是把他降職為奉御,將其派往鳳陽守祖陵了事。絕不死心的張永就請皇帝親自去抄劉瑾的家,明武宗在劉瑾家里一看就傻眼了,他親眼看見私刻的皇帝印璽一顆,以及皇帝御用的龍袍、袞服、玉帶等物品,還發現劉瑾經常拿在手里的扇子中,藏有兩把鋒利的匕首。家中還發現穿宮牌五百多個,許多盔甲、刀槍、弓箭等武器、用具,明武宗這才勃然大怒,認為劉瑾是要造反,下旨將其處以極刑。
其實,劉瑾雖然權傾一時,畢竟是一個太監,快60歲的人了,他可能確有權錢貪念,但說他要謀反,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都難以令人信服。
明武宗也未必真相信劉瑾能反了天,最后將劉處死,而且用的是非常殘酷的肉刑,罪名用的是“謀逆”,但實際原因是劉瑾嚴重違反了政治規矩,這是皇帝絕不能容忍的。這個政治規矩就是皇家禁臠乃皇帝獨占,不容他人染指,一旦有人染指分享,哪怕只使用了仿冒品,也構成嚴重的征象性侵犯。更深一層來說,使用占有皇家禁臠,即為越權用事,是圖謀不軌,是對皇權一統的蔑視和破壞。
什么是政治規矩?政治規矩其實就是未明文載入法律、規章制度,但又是約定俗成的政治紀律,它可能只是傳統和慣例,卻對政治人有紀律要求,但哪些屬于規矩,哪些不屬于規矩,邊界并不好把握,常常需要依時依事依勢而定。核心只有一條,就是不得觸犯和動搖皇權,必須維護皇權的絕對領導。
大內總管的工作職責決定了是應該服從服務、絕對地效忠于“大內”,維護皇權的“集中統一領導”,而不是反其向而行之,暗中對抗,有什么政治野心。作為大內總管,劉瑾染指皇家禁臠,就是冒犯皇權,是不守政治規矩,這比貪腐更令明武宗難以接受。
事實上,同樣是作為大內總管,同樣是明朝,劉瑾之后的宦官魏忠賢,某種程度上也是死于嚴重違反政治規矩之上——形成以魏忠賢為首的一個擅權亂政的幫派,即所謂“閹黨”,同樣是冒犯皇權,危及皇帝的統治。
魏忠賢的上位之路與劉瑾如出一轍,本是“市井一無賴爾”,后“入宮養家”,有幸得以服侍東宮太子朱常洛的王才人,一手帶大朱常洛長子朱由校。魏忠賢還與皇長孫朱由校的奶媽客氏搞起“對食”——字面上是說男女合伙吃飯,其實就是“夫妻”,而朱由校對他這個奶媽又特別依戀,說她是“亙古今擁祜之勛,有誰足與比者?”把奶媽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位,封為“奉圣夫人”,“儼如嬪妃之禮”。
1620年,朱由校登基,是為明熹宗,由于有了上面兩層關系,魏忠賢深受明熹宗的寵愛,咸魚翻身、雞犬升天,做到司禮秉筆太監,東廠提督,參與國事,是名副其實的大內總管。
魏忠賢沒有宦官王振的學識、宦官汪直的心機、宦官劉瑾的貪婪,他最初入宮無非想混口飯吃,但是權力就這么陰差陽錯地落到了自己的手上,他來者不拒地收受下來。一旦大權在手,他已經不是當年的小混混,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其權力運行就是資源的分配,必然會有益于人,有損于人,必然成為投靠和反對的對象。為了不被反對者打倒,保住自己的權力和地位,魏忠賢難免要拉幫結派。
而且當時,朝廷中的許多士大夫都是東林黨人,并以江南士大夫為主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他們在朝中占據了一些重要位置,比如內閣首輔葉向高、禮部尚書孫慎行、吏部左侍郎鄒元標和吏部尚書趙南星,以及左都御史高攀龍、左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等人都是東林黨人。
開始時魏忠賢與東林黨人并無矛盾,但東林黨人既是政治集團,必有其對立或是反對者,對立或反對者為了反擊東林黨人必然要找更大的靠山,而魏忠賢權勢炙手可熱,東林黨人的對頭就紛紛投靠魏忠賢,這就觸犯了東林黨人的利益,引起東林黨人的不滿,就要想方設法削弱魏忠賢的權勢,不斷地向皇帝揭發魏忠賢,魏忠賢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勢,勢必要反擊,要“集團作戰”,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勢力,拉幫結派、搞山頭主義、越權用事等等在所難免。
在內廷,魏忠賢網羅太監,擴大自己的勢力,司禮監太監王體乾、涂文輔、石元雅、李永貞等人都成了他的黨羽,被安插在內廷的要害部門。他甚至在大內培植自己的武裝,他在宮中挑選體格健壯的太監組成一支禁軍,將自己的心腹安插到軍中擔任要職,將從兵部要來的大量火器配發給太監,還經常在紫禁城內操練這支部隊。
在外廷,魏忠賢結交朝廷文武大臣,一些趨炎附勢者投其所好,不但投靠他,還認其為親。于是認親者絡繹不絕,踩破門檻。《明史》說“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形成了一個以魏忠賢為核心的政治勢力集團。
由于明熹宗過于信任魏忠賢,對其拉幫結派、培植私人勢力、擅作主張越權辦事、非組織活動不以為意,可是轉到1627年明熹宗駕崩,其弟朱由檢繼位,是為崇禎帝,魏忠賢深知自己拉幫結派,黨羽眾多,已經嚴重違反了政治規矩,肯定不能容于崇禎皇帝,等待他的只能是被崇禎皇帝一步步收拾的命運。
崇禎皇帝先是罷免了魏忠賢的心腹兵部尚書崔承秀,等于斬其手腳臂膀,接著將最早提出給魏忠賢建立生祠的浙江巡撫潘汝楨貶為平民,又將魏忠賢的對食客氏遣出皇宮。一些官員看出了皇帝的意圖,紛紛上疏彈劾魏忠賢,給魏忠賢列了十大罪狀。有了這股反魏之風,崇禎皇帝乘勢解散宮內太監武裝,免去魏忠賢司禮監和東廠總督的職務,然后命魏忠賢赴鳳陽皇陵擔任燒香太監,看守祖陵。在南下途中,魏忠賢聽說崇禎下旨要處死自己,驚恐之中上吊自殺。崇禎皇帝緊接著剿滅魏忠賢政治團伙,當即被處死者6人,秋后處決19人,充軍11人,革職44人,徒刑三年后準許贖身為民者129人。
明朝的兩位大內總管的落馬一再揭示了一個道理,在帝制時代,最大的政治規矩就是維護皇權統治的規矩,這些政治規矩可能包括了國法,也可能不明文載于法紀,但威力往往極大,是不容碰觸的政治底線,當不得兒戲。誰違反了政治規矩,誰就沒有好果子吃,這是屢試不爽的。
(摘自騰訊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