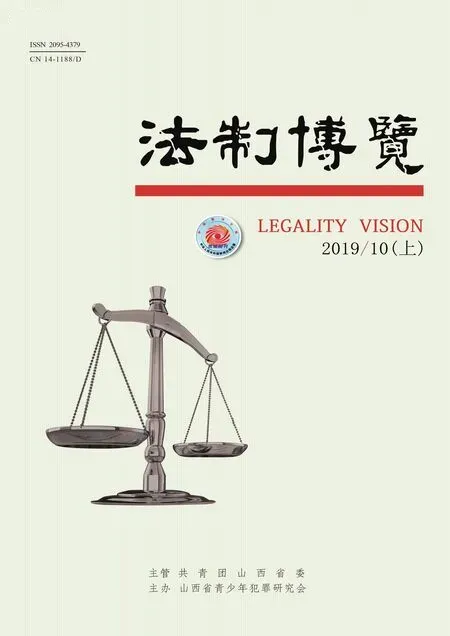尋釁滋事罪理論分析及實踐認定
喻以詩
江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尋釁滋事罪的淵源
我國現行《刑法》第293條規定的尋釁滋事罪,是從“七九刑法”第160條規定的流氓罪中分離出來的。因此,今天我們要研究尋釁滋事罪,就不得不考察其母罪流氓罪。“七九刑法”第160條規定了流氓罪的相關內容,但是,“七九刑法”實施不到四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3年9月2日通過的《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修改了“七九刑法”關于流氓罪的規定。最終,原有刑法規定的流氓罪被分裂成若干個罪名,其中一個罪名即為現行刑法第193條規定的尋釁滋事罪。
二、尋釁滋事罪的理論分析
尋釁滋事罪,顧名思義,“尋釁”通俗的是指故意找事挑釁;“滋事”是指惹事,制造糾紛。由于本罪所保護的法益為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則尋釁滋事行為侵害的即為良好的社會秩序,且由于本案衍生于流氓罪,行為人犯罪的客觀方面需表現為行為人在公共場所破壞公共秩序、無理取鬧、無事生非、起哄搗亂、肆意挑釁、毆打傷害無辜、橫行霸道,法條采取的是全部列舉的方式,也就是說,只有符合以上的客觀要件,才能構成尋釁滋事罪。但對于尋釁滋事罪這樣的在理論及實踐中爭議較大的罪名,僅僅以傳統犯罪四要件的分析方法對其進行分析是完全不夠的,因此,在實踐中,我們實務部門還需具體結合行為人的犯罪客觀表現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對行為人的犯罪行為進行客觀綜合評價。
三、尋釁滋事罪的實踐認定
在長期的刑事理論探討及司法實務中,對于實踐中我們認定尋釁滋事罪無疑是極其有利的,本文基于現有司法解釋及有效司法文件的規定,對尋釁滋事罪展開細致的分析。
(一)對本罪名的詳細闡釋
1.對“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中“隨意”的理解。因行為人主觀上的流氓動機,本罪中“隨意”應表現為行為人為逞強耍橫、發泄情緒、尋求刺激等,無事生非,體現為行為人肆意妄為,在態度上對良好社會秩序的輕蔑。
2.對“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中“情節惡劣”的理解。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出臺的《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尋釁滋事司法解釋》)第二條對“情節惡劣”的情形做了詳細的規定,該解釋第二條規定情節惡劣的情形共有七項,其中第七款為兜底條款。但是,立法者希望通過如上例舉的方式將紛繁復雜的社會現狀涵括進本罪認定的“情節惡劣”之中的想法顯然是不能夠實現的,因此筆者認為,作為第七款的兜底條款應在社會現實發生之時而現有規范不能夠對其行為進行認定的時候發揮作用,但同時也應在此過程中防止刑法適用的擴大化現象的發生,即我們在認定第七款規定的“其他情節惡劣的情形”的時候,在能夠做出此行為的主觀惡性及社會危害性與前幾款規定行為具有相當程度的前提下將其認定為“情節惡劣”行為。
3.對“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中“情節惡劣”的理解。依據《尋釁滋事司法解釋》第三條對“情節惡劣”的情形的詳細規定,我們在認定該條第六款中“其他情節惡劣的情形”時,也應通過以上的方式對行為人行為進行甄別,防止刑法適用的擴大化。同時,依據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出臺的《關于辦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極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二、準確認定案件性質(八)”中的規定,以“宗教叛徒”、“異教徒”等為由,隨意辱罵、追逐、攔截、毆打他人,“擾亂社會秩序,情節惡劣的,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
4.對“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中“強拿硬要”財物價值認定的理解。根據《尋釁滋事司法解釋》第四條對“情節嚴重”的情形的規定,任意占用、損毀公私財物或者強拿硬要,破壞社會秩序,具有本條規定情形之一的,認定為情節嚴重,但是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本條第一款中關于強拿硬要財物價值的認定與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以下簡稱《刑事案件立案規定》)第三十七條第三款關于強拿硬要財物價值的認定金額是不同的。對此,筆者作如下理解:雖然《尋釁滋事司法解釋》出臺時間要比《刑事案件立案規定》的時間晚,根據法理規則,在兩部同層級的法律規范產生沖突之時,后法優于前法適用,但是,尋釁滋事罪作為普通刑事案件,只有在公安機關對行為人行為進行了立案之后,刑事訴訟的第一道門才算開啟,待偵查完畢移送審查起訴后,才有可能進入法院審理程序,進而適用《尋釁滋事司法解釋》的此條規定。所以,在《尋釁滋事司法解釋》與《刑事案件立案規定》對“強拿硬要”財物價值的認定金額上產生沖突之時(如“強拿硬要財物價值1500元”),應首先適用《刑事案件立案規定》的要求,對行為人進行立案處理。
5.對“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中“公共場所”的理解。一般包括運動場所、醫院、影劇院、機場、商場、展覽會、公園、碼頭、車站等其他同性質場所。但是,隨著社會變化的日新月異,供人們進行社會生活的公共場所也已經遠非以上列舉項可以涵蓋了,比如,網絡作為虛擬社會活動空間,如在網絡空間起哄鬧事,造成輿論嘩然,影響公共秩序的,能否認定為在公共場所鬧事,且根據尋釁滋事相關法律進行處罰?筆者認為,在紛繁復雜的當今社會現實,對于“公共空間”法律含義的理解,應根據立法本意及行為后果進行全面闡釋,如果行為人起哄鬧事的空間同樣可以造成嚴重的秩序混亂,對尋釁滋事所保護的良好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的侵害,即應將此空間認定為公共空間。因此,在網絡空間起哄鬧事完全符合這一要求。
6.對“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中“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理解。依據《尋釁滋事司法解釋》的規定,要求辦案機關在綜合考慮以上各要素的前提下,結合案件對社會現實秩序的沖擊程度,依法作出相應處理決定。這是對辦案機關自主裁量權的授予,同時也是對辦案機關自身素質的一種挑戰。
(二)對利用網絡實施誹謗行為的處理
近年來,由于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我國網民數量已接近我國人口總人數的一半,且信息傳遞的終端化以及通訊技術的發展,更是加快了網絡信息的傳遞。由于網絡空間以上的特點及信息傳遞速度的成倍增長,現實社會中利用信息網絡進行違法犯罪的現象也日漸增多,因此,為有效遏制相關違法犯罪的發生,引導社會公眾合法開展生產生活,同時為解決刑事實務部門在相關案件的認定中遇到的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出臺的《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部司法解釋第五條規定了行為人”利用信息網絡進行辱罵、恐嚇他人的行為,如達到“情節惡劣,破壞社會秩序”時的處理;以及行為人編造虛假信息或在網絡上散布不實信息,起哄鬧事,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時的處理,即是對社會現實的積極回應。
(三)涉醫違法犯罪行為的處理
隨著我國社會轉型,人民日益增長的醫療衛生需求與現階段的相應供給不能滿足之間的矛盾隨之加劇,由此導致醫療糾紛不斷、醫患關系緊張,且前些年的非法醫鬧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使醫療糾紛矛盾升級、更使醫患關系雪上加霜,這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正常的醫療秩序,且造成了社會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亂,為此,為依法嚴肅追究、堅決打擊涉醫違法犯罪行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等五部委于2014年出臺了《關于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該《意見》對“在醫療機構內毆打,故意傷害、殺害,非法拘禁,公然侮辱、恐嚇醫務人員”、“故意損毀公私財物,在醫療機構私設靈堂、擺放花圈等形式擾亂醫療秩序,在病房、搶救室等公共開放區域違規停放尸體”的行為人行為進行了規定,實踐證明該《意見》為解決刑事實務部門在相關案件的認定中遇到的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同時在遏制相關違法犯罪發生方面也起到了明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