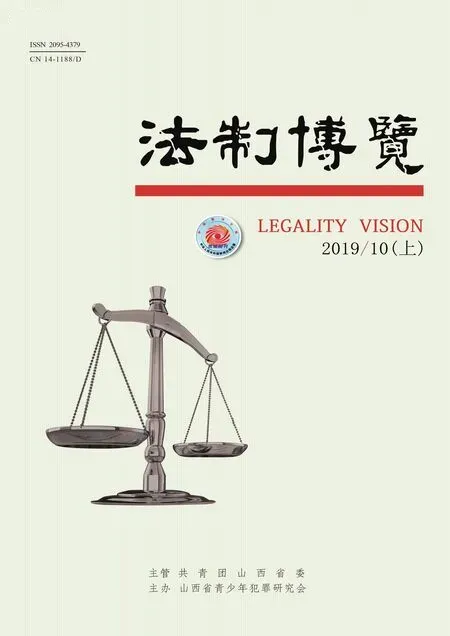律師參與調解群體性糾紛的思考
——以民商事件糾紛化解為例
王晨潔
南京市高淳區司法局,江蘇 南京 211300
在我國整體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進程中,商品經濟越來越繁榮。與此同時,群體性糾紛事件也越來越多,而民商事件糾紛在其中占據著十分大的比例。傳統的律師執業模式已經很難滿足當前社會的實際需要,因此,有關部門應當結合實際情況對律師參與群體性糾紛現象展開深入思考,確保相關制度得以優化。
一、群體性糾紛與民商事件糾紛概述
(一)群體性糾紛
群體性糾紛即當事人方人數較多(超過十人),且就同類或者同一法律、實事問題和另一方有利益上的糾紛[1]。此類糾紛多發生于保障農民工權益、拆遷房屋、庫區移民、征用征收土地、污染環境、企業改制以及集資詐騙等事件上。此類糾紛通常擁有較復雜的政治、社會以及經濟原因,會直接影響社會秩序乃至國家穩定。在一般狀況下,此類糾紛具有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法律關系較復雜以及矛盾容易被激化等特征。在群體性糾紛當中,當事方很容易會出現集體上訪、過激行為等沖擊社會穩定的行為,以便使政府部門對其重視。
(二)民商事案件
此類案件即由民商事法律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的糾紛或者案件。從廣義層面看,此類糾紛主要包含了財產以及人身案件、糾紛,具體上能夠被劃分成商事糾紛以及民事糾紛。有關民商事件糾紛的法律、法規,包含了《合伙企業法》、《合同法》、《繼承法》、《婚姻法》以及《民法通則》等。
二、律師參與調解群體性糾紛的可行性
(一)專業律師的執業技巧以及法律知識
在律師對糾紛進行調解時,通常會用自己專業的法律知識對糾紛中當事方所提到的各類問題加以專業解答,從而及時消除當事方由于對法律不明所出現的錯誤理念,使其對律師更加信任。與此同時,律師還會對其加以引導,以便使其經由法律途徑對糾紛、矛盾加以解決,進而確保矛盾不會被激化而導致社會問題的發生,最終使糾紛、矛盾被合理化解。
(二)律師的執業活動擁有廣泛性
相比于政府部門,律師的日常執業活動通常不會受到地域影響,除了在法律法規所規定的一部分較特殊的領域中,律師需要相應的資質,大部分時間律師的日常執業活動都擁有很大程度的廣泛性。因此,律師在開展日常的執業活動時,往往能夠接觸各地區、各行各業的差異人群,接觸的群眾面極為廣泛[2]。而這種廣泛性,正是確保社會糾紛、矛盾得以有效調解的重要基礎。
(三)律師在執業活動中保持中立
從本質上來看,律師在調解民間各種糾紛時,其和民眾的地位是平等的,這能夠幫助民眾拋開一些對法律、仲裁等的誤解,從而拉近律師與民眾間的距離,獲得其信任,進而使自身法律見解、意見等更容易被廣大民眾所接納,這可以幫助律師更順利地調解群體性糾紛。
三、律師在化解民商事件糾紛時存在的風險
我國屬于法治國家,長期以來,我國都在不斷落實、貫徹“依法治國”的政策方針,而這也是我國依法治國的基本政策。所以,在新時代的法治大環境中,民眾已經明確通過法律形式對自己進行保護,而訴訟已經成為廣大民眾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主要舉措。然而在法律歷史長河中,虛假訴訟、偽證案件等不斷挑戰著法律的權威,使民眾的期待值、信任度有所下降,負面影響極為嚴重,不僅不利于維護當事方以及律師的合法權益,更對司法的公正發展產生了阻礙,為社會穩定埋下了安全隱患。
四、律師參與調解群體性糾紛的合理化建議
對于人民調解委員會而言,其主要的任務便是對民間糾紛及其調解的狀況進行反映,對民間糾紛進行及時調解以及對國家政策、法律法規展開宣傳。因此,律師若想有效參與到化解包含民商事件在內的群體性糾紛,應當從上述三點著手,主要體現在:
(一)代理群體方調解群體性糾紛
在我國有關法律法規中有所規定,律師能夠接受當事方的委托,進而參與到糾紛調解以及仲裁等活動當中。這屬于律師參與調解群體性糾紛的法律憑證。雖然在實際的糾紛調解過程中,律師參與調解工作的案件數量并不多,然而伴隨我國依法治國方針的不斷落實,越來越多的律師開始參與到包含民商事件糾紛在內的群體性糾紛當中。
在非訴訟解決程序較為完善的國家當中,調解屬于一項該國律師的重要義務,如果某律師沒有積極履行此義務,則會導致其自身需要承擔較大的法律責任。我國有關機構在完善律師參與調解群體性糾紛的相關制度、體系時,應當充分借鑒國外成功的案件經驗。因此,對于民眾日常生活具有較高發生頻率的、具有清楚事實,且法律關系極為明確的糾紛,亦或當事方想要盡快解決、也不愿和另一方的關系出現裂痕的糾紛,律師需要充分結合當事方權益,及時建議其采用調解的方法來結案。
然而需要律師注意的一點在于,在當前的法律法規中,并沒有明確地規定當事方如何授權律師展開糾紛調解。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要求,當事方在委托其他人員展開訴訟時,相關授權委托書當中應當明確記錄委托的權限和相關事宜。然而,從本質上來看,糾紛調解卻要求當事方舍棄一部分權利來收獲利益(包含了防止不能及時執行判決、維護雙方以往關系或者加快調解時間等)。所以,律師在接受當事方委托的時候,應當在書面中明確地約定好處分實體權利的各類事項[3]。
除此之外,律師在受到當事方委托參與調解群體性糾紛的時候,還應當明確授權委托書的簽訂方式,即與當事方代表簽訂還是與當事方一一對應地簽訂;明確調解的最終結果能否被全體當事人員接受;明確如果當事方對調解的結果不承認時,應當怎樣進行處理等。
(二)以中立身份對群體性糾紛展開調解
律師在調解群體性糾紛時,應當按照有關法律展開評估、預判,并且對當事方合理的訴求以及違法表達間的實際利弊,隨后把評價的意見反饋給當事方所有人員,而這也是律師參與調解的關鍵環節。在以往,律師一般會根據自身辦案經驗以及專業知識取得當事方信任,其調解計劃通常也會具備一定程度的權威性,容易被當事方接受,所以律師參與調解群體性糾紛具有較高的公信力。
律師若想確保調解的方式合法、正當,可以競聘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以此身份展開調解時,一方面律師需要確保糾紛調解公平、公正、公開,并非忠于當事人單獨一方;另一方面,律師還需要嚴格遵循道德、事實、政策以及法律。這些都屬于法律當中有明確要求的,其可以確保律師參與群體性糾紛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公正性。
(三)積極展開相關糾紛的涉法信訪活動
在有關規定中,對律師參與信訪工作的相關要求以及其重要意義進行了明確,進一步為律師參加涉及群體性糾紛的信訪工作提供法律憑證。這就需要律師在參與相關工作的時候,應當充分展現出自身的專業性,同時不斷提升自身的工作積極性,進而將自身的職能作用全方位發揮出來。與此同時,民眾、政府等社會各個領域呼吁律師參與此類工作的呼聲與日俱增。在此過程中,信訪工作屬于律師參與化解群體性糾紛最為關鍵的一個環節。近些年,政府領導在接待群眾的上訪時,有律師隨同的體制逐漸在我國多地開始實施,經過多年的實踐,社會效果、反響良好,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各地政府部門對“依法行政”的重要作用越來越重視。
2.廣大專業律師不僅對法律知識、技巧精通,在持續的經驗累積以及反思過程中,逐漸意識到融合律師工作的社會性價值以及服務性價值的重要意義,同時明確了服務于社會、政府的必要作用。
3.正如前文所述,相比于政府的信訪機構,律師人員規模龐大,且擁有極為靈活的工作時間,不受地域的影響和限制,因此在信訪層面優勢巨大。
各地應當逐漸實施將律師事務所與社區工作站相掛鉤,使律師可以直接將法律咨詢義務服務提供給廣大的人民群眾,以便從更加專業的角度為民眾解答涉法信訪的各類問題,進而使民眾、政府以及律師實現共贏,為社會的穩定發展提供可靠的法律基礎。
五、結論
總體而言,在社會中群體性糾紛日益增多的新時期,律師參與調解意義深遠,除了具備極其重要的意義外,其可行性也很高。律師參與其中,除了能夠有效對糾紛加以調節,維護社會的安定和諧,更能夠有效宣傳、普及法律知識,使得社會法治水準得到質的飛躍。在此過程中,律師的社會價值也得以充分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