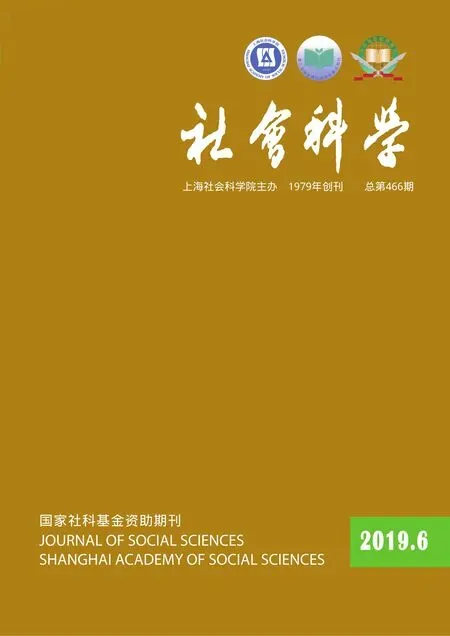亞東圖書館及“亞東精神”的思想傳播史意義*
王海剛
中國近代出版業發祥于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局等是當時非常有影響的出版機構,安徽人汪孟鄒創辦和經營的亞東圖書館亦為其中翹楚,它為近代中國思想啟蒙與文化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亞東圖書館由汪孟鄒于1913年在上海創辦,其前身為蕪湖科學圖書社。最初的亞東圖書館只是銷售一些自己出版的地圖類圖書,1919年由陳獨秀牽線,開始經售北京大學出版部的圖書,成為該部在上海的總經售處。五四運動之后,亞東圖書館首先采用標點分段的方式出版中國古典小說。其后,又出版了不少文化書籍,營業興旺,工作人員達20多人。從1929年開始,有不少不良商販開始偷印、翻版和盜印,使亞東營業大受影響,加上后來國民政府的文化高壓以及抗日戰爭的爆發,亞東圖書館開始走下坡路。新中國成立后,主張公私合營,亞東圖書館被并入通聯書店。1953年初,因其30年代出過一些托派書籍,被上海軍管會勒令停業,至此亞東圖書館走過了它風雨飄搖的四十年,老板汪孟鄒也于同年逝世。在40年的發展中,亞東圖書館逐漸形成了為社會所稱道的“亞東精神”。研究和總結“亞東精神”,對我們從事編輯出版工作,提高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亞東圖書館與“亞東精神”的內涵
亞東圖書館是我國近代出版業中有相當貢獻的一家出版社,在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做了積極有益的嘗試和探索。特別是從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期間,亞東出版了《獨秀文存》、《胡適文存》、《孟和文存》等文集,《嘗試集》、《草兒》、《蕙的風》等新詩集,并首創用新式標點和分段方式,整理《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等中國古典小說。許多出版物風行一時,影響甚大。
亞東圖書館40年的發展史,凝聚著中華民族在近現代史發展進程中的文化智慧,體現出中國知識分子的高貴品質與文化自信,充滿歷史啟迪,也淬煉出了“亞東精神”。“亞東精神”是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又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還包括多管齊下的經營精神。
二、“亞東精神”的凝練
(一)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
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和亞東圖書館創始人汪孟鄒早期接受的新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汪孟鄒在《大公報》的《出版界》第46期說:
先說我為什么從事新書業的。我少年時候,科舉還未廢除,我也跟著當時的知識青年學做八股文。那時甲午戰爭剛過去,中國戰敗了,大家都認為非改革內政,國家就要亡了。康有為、梁啟超幾位先生發起了維新運動,各地方志士都贊成他們,我的業師同邑胡子承先生就是最熱心的一個,他教我們八股文之外,還教我們歷史和地理,而且勸我們節衣縮食,購閱當時出版的新書和新報。這就是我接受新思想的原因,也就是我對新書業發生興趣的原因[注]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頁。。
在維新思想影響下,汪孟鄒25歲時(1903年),在蕪湖創立科學圖書社(亞東圖書館前身)。據汪原放回憶,科學圖書社是安徽蕪湖第一家洋書店,店堂明亮干凈,照明使用電燈,店門朝外(按習俗一般朝里,有俗語“店門朝里開,元寶滾進來”),玻璃櫥窗陳列錯落有致,既沒有供奉財神菩薩的龕座,也沒有“老太”(即狐仙,過去蕪湖人有迷信狐貍的風氣,認為狐貍不能得罪,否則會遭報應)的龕座,店里也不燒金銀紙,這與老書店有著天壤之別。關于蕪湖科學圖書社的創辦宗旨和經營范圍,《安徽俗話報》1904年3月15日有廣告云:
本社創設宗旨為輸入內地文明起見,去秋開辦情形已登日報,近復增集股本,力圖擴張,特約日本東京同鄉諸君,并委派妥友駐滬專司采辦所有東京、上海新出書籍、圖畫、標本、儀器、報章等件,務求完備,以副同人創辦之初心。所售各書籍因鑒于欲開民智、教育為先,故于蒙學、小學所用教育書籍及用品尤所注意[注]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9-11頁。。
從廣告可知,蕪湖科學圖書社創立伊始,就經銷反映新思想的圖書和雜志。除了銷售書刊,科學圖書社也踏足出版領域,曾出版胡子承編著的《高等小學修身教科書》,發行陳獨秀主編的《安徽俗話報》,從此在新書業小有名氣。《安徽俗話報》刊登的文章既有倡導改良教育的,也有譴責封建倫理道德的,既有激勵愛國熱情的,也有呼吁挽救民族之危亡的,被當時老一輩視作“洪水猛獸”。1922年,科學圖書社廿周年慶,社會上有評價云:
我們自前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開設于蕪湖,到現在(1922年)已有二十年了。有的說我們是安徽的第一家新書店;有的說我們的書籍、雜志和儀器、文具也是安徽最完備的第一家;更有的說是安徽風氣之開通,文化之進步,我們都有關系。
這樣的盛譽,我們萬不敢當;但我們因此不敢不更加努力——順時代的思潮,搜集最新的書籍、雜志;應各界的需要采辦最精良的儀器文具。——已答諸君的盛意[注]科學圖書社編:《廿周年紀念冊》,科學圖書社1922年版。。
蕪湖科學圖書社吸引了大批進步人士在店內聚集,他們關注國事、交流思想、議論時局,科學圖書社成為了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場所。
1913年,汪孟鄒在上海創辦了亞東圖書館。《生活日報》1913年12月5日登載了《上海亞東圖書館宣言》,全文如下:
中國書籍之興,肇于《墳》、《典》,隆于晚周。暴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書缺簡脫,而向、歆所錄尚有三萬數千卷,百家咸備,翳古藝文,炳焉可觀矣。西方希臘、羅馬,文教覃敷,亦當中國周、秦之際,東西相較,無多讓也。
顧自意大利國文藝復興,五百年來,歐洲列國,百家競起,繼軌增飾,制作之富,溢市闐城。官書庋蓄,且軼天祿、石渠之盛。東鄰文藝,雖不能比隆歐美,亦足以逴躒諸夏。識者將于此校民族之文野、卜國勢之隆替焉。
諸夏之不振,因緣萬端,宋、明以來,尊向制藝,廢置《詩》、《書》,人知以晦,國力以墮,此其大原也。近歲情勢稍稍變矣,然猶攘臂論政之士多,冥心著述之士少。人不知古今,予以印綬,則為土偶;予以矛戈,則為盜賊。群一國不學無文之人民,雖有圣君、哲相,求幾及小康且不易,況期以共和大同也耶!
同人夙凜斯義,相與醵金立社,最海內耆宿、歐學巨子,綜輯群藝百家之言,迻譯歐美命世之作,接翼并軌,以趣修途,邦人諸友,倘亦樂觀其成也[注]《上海亞東圖書館宣言》,《生活日報》1913年12月5日。。
宣言從中國書史談到意大利文藝復興,論述書籍對于傳播文明、振興國家的重要性。感慨當下國勢衰微,指出興辦出版機構之宗旨,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亞東圖書館在其經營的40年間,總共出版了300多種書籍,其中名家作品占了1/3,包括陳獨秀、胡適、章士釗、高語罕、蔣光赤、朱自清、陶孟和、劉半農、錢玄同、吳虞、康白情、劉文典、俞平伯、徐志摩等人。亞東率先出版的新詩集、白話文存以及標點舊小說等,可視為新文化運動成果的直接反映,也是一個出版者對時代潮流積極響應和出版支持的表現[注]吳永貴:《汪孟鄒:行走于文化風云人物之間》,《光明日報》2007年1月27日。。《中華民國地理新圖》是我國第一本地理分類圖集,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研究價值。這本地圖集曾得到當時社會名流的一致好評,梁啟超先生評,“瀏覽一過,欽佩無量。治地理學最苦乾燥,此書注重人文,導以趣味,而歸諸實用,其津逮學子之效遠矣”[注]《時報》1916年9月15日廣告。。章士釗先生評:“胡子承先生,且學且晦,不厭不倦,素所心折。是書注重人生地理,令讀者多所觸發,興味濃郁,于中等教育最為相宜。蓋其學地也,而學之者人,烏可拋荒本位而從事;況其為本國地理,固當以闡發國家思想為要義。”[注]《時報》1916年9月15日廣告。《嘗試集》是我國第一本以白話寫成的詩集,由亞東圖書館于1920年3月出版。此書收錄胡適創作的詩歌若干首,其宗旨在于倡導文學革命:
現在且說我為什么趕緊印行這本白話詩集。我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這一年以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得很快很遠,但是大多數的人對于白話詩仍舊很懷疑;還有許多人不但懷疑,簡直持反對的態度。因此,我覺得這個時候有一兩種白話韻文的集子出來,也許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許可以供贊成和反對的人作一種參考的材料[注]胡適:《嘗試集》,亞東圖書館1920年版,第5頁。。
《嘗試集》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詩壇的轟動。有人做了這樣一個統計,從1920年4月起到1921年1月,對于《嘗試集》的通信討論,先后有十多個人參與其中,每個人在三到四種日報和雜志上發表文章[注]胡寄塵:《<嘗試集>批評與討論》,泰東書局1921年版,第45頁。。被熱議的另一面,是《嘗試集》的熱銷。此書在兩年之內印了四版,銷售了一萬部。到1953年亞東歇業為止,《嘗試集》共印了二十多個版次,總數達四萬七千冊。在新詩出版發展史當中,留下了輝煌一頁。
亞東圖書館還首創了古典小說標點本,先后標點的古典小說有《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等。1920年2月,教育部向各校頒布采用《新式標點》的法令,差不多同一時期,年僅23歲的汪原放說出了自己的計劃,“我有一個計劃,要出四部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大小說:《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西游記》。先出一部《水滸》,要校得沒有錯字。如果不成功,算了;如果成功,再做第二部”[注]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頁。。這個計劃得到了陳獨秀和胡適的贊賞與支持。陳獨秀指出,“亞東圖書館將新式標點加在水滸傳上翻印出來,我以為這種辦法很好”[注]陳獨秀所作之序,亞東圖書館1920年標點本《水滸傳》。。胡適在考證中指出,“亞東出版的《水滸傳》首次采用了新式標點符號將小說進行句讀分段,它在教育上的效果,會比教育部頒發的標點符號使用方案要大得多,將來一定能成為標點符號推行的教用范本。汪原放在校對這本書時所花費的精力也是自己深深欽佩和贊賞的”[注]胡適所作之序,亞東圖書館1920年標點本《水滸傳》。。到1922年,《水滸傳》印了四版,共一萬四千部。《儒林外史》是亞東標點分段的第二部小說,錢玄同在《儒林外史》新敘中指出,“就青年學生的良好讀物方面著想,則《水滸》、《紅樓夢》還有小小地方不盡適宜,惟獨《儒林外史》則有那兩書之長而無其短。所以我認為這是青年學生的良好讀物,大可以拿他來列入現在中等學校的模范國語讀本之中”[注]錢玄同所作新敘,亞東圖書館1920年標點本《儒林外史》。。亞東版的古典小說不僅充當著“白話教本”,還承載著錢玄同、陳獨秀等人的新思想和新的文化觀念。在目前查到的資料中,該書在1933年已經印到了第15版。《紅樓夢》標點本于1921年5月出版,首次選用程乙本,并載有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考證后記”、顧頡剛的“答胡適書”以及陳獨秀的“紅樓夢新敘”。在出版預告中聲稱,“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亞東本的《紅樓夢》借鑒西方書籍的方式,采用新的版式和標點,改變了人們長期形成的閱讀習慣。文獻中有吳組緗購買亞東本《紅樓夢》的記載:
自己小學時代曾到別處借閱石印本的《金玉緣》(即紅樓夢),上面字跡密密麻麻,看得人頭昏眼花,雖然字跡似懂非懂但心里卻很感興趣。從那個時候開始,《紅樓夢》在吳組緗心中占據了重要地位。……現在他新買的《紅樓夢》,跟之前他看過的所有《紅樓夢》的版本都不一樣,白色的報紙用紙、整個大小恰到好處,每一個章節都進行了分段,還加了標點符號,行距看著也很舒服,字跡也很清晰,拿在手里賞心悅目。這樣的《紅樓夢》,吸引吳組緗的不再是小說的內容,還有它的用詞遣句,標點、分段、行距、空格,等等。
亞東的《紅樓夢》在1953年以前總共發行過16版,在出版發行中,形成了自身特色,精裝三冊,平裝六冊,裝幀考究。亞東版《紅樓夢》憑借對新紅學的影響,成為解放前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紅樓夢》本子。在亞東的標點本打開市場銷路后,群學社、大中、掃葉等書店開始競相效仿,廣益甚至拿出十萬元做資本,專做標點本。據汪原放回憶,“他們門口,天天有大箱大箱的標點本運出,很大很大的書包也很多,不單出標點本《水滸》、《紅樓夢》、《三國演義》等,也出其他筆記小說等,文言、白話的都做”[注]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頁。。
(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非為良賈,且為良士”是徽商的商業行為準則,這一準則也處處體現在汪孟鄒身上,他們以盈利為目的,卻不唯利是圖。汪孟鄒有句名言,“與其出版一些爛污書,寧可集資開妓院好些”。不僅嚴格要求自身,同時堅決打擊盜版。20世紀30年代,亞東曾舉行“標點舊小說,暑期大廉價”活動,登在《申報》上的廣告,標題是“劣本雖廉,不堪卒讀;稍增代價,便得佳本”[注]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頁。短短十六字,針砭偽劣,宣傳優質書籍,實事求是,讓人深思。遍觀亞東的出版物,我們找不到帶有淫穢色情或散發銅臭的低級趣味書。這既是對自身名譽的愛護,更是一種對讀者負責任的態度。魯迅先生曾言,“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我,皆非其選也”[注]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頁。。由此,亞東圖書館在出版界的聲望與名譽,可見一斑。
著名出版家汪家熔曾說:“創新和質量是出版社成功的最根本問題。不論你的班子多強,發行網多健全,碰到的機遇多好,如果沒有好的貨色,仍然不能幫你站住腳。”[注]汪家熔:《舊時出版社成功諸要素——史料雜錄(之四)》,《出版發行研究》1994年第6期。所謂好的貨色,既有對圖書內容的期許,還有對圖書形式的要求,包括校對、裝幀、印刷、紙張等方面。校對是保證圖書質量的重要環節,校對時發現可疑的地方會立刻記下,然后再查找資料或者與同人商量討論,若三校、四校后仍舊沒有結論,則與作者聯系,如果是古書,則存疑,請求讀者指教[注]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74-75頁。。正是這樣嚴格的工序保證了亞東出版物的質量。胡適曾多次在出版的作品中感謝亞東人的精細作風。任白濤也說:“我看他們對社會的信用很好,印校一切,更是常常謹慎,絕不茍且,所以把發行權讓給它。”[注]任白濤:《應用新聞學》,亞東圖書館1926年版,第8頁。張靜廬在文章《一本書的誕生》中對亞東本的校對工作倍加贊譽:“不過這里要特別提一提,就是亞東版的舊小說,錯字的確不曾有,據我所知道,汪原放先生每一部書的校對,總在十二次以上,其工力與耐性是值得我欽佩的。”
1920年春,汪原放與胡鑒初校對《水滸》,為盡快出版,兩人每每通宵達旦,每天早上都把最新的校樣送去附近的印刷局印刷。1921年12月,亞東出版了《胡適文存》初集,汪原放、章希呂與余昌之三人共同校對完成,排校過程甚為認真,“我們校書時,往往在初校時就提出的問題,到二校還不能解決,一直要到三校,甚至末校,才能改定。總要査考下來,肯定是錯了的,才改定;同時立刻發快信到北京和適之兄商定妥當與否。這些信現在也無從去找了,是很可惜的”[注]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6頁。。胡適身為大學者,但引用文字時難免也會出現紕漏。在校對此書之前,可供汪原放三人使用的參考用書還很少;在校對工作開始后,三人隨時添置參考書,只要是存疑之處,三人共同商量,多處查找資料。亞東同人對收錄的每一篇文章、每一處錯誤都進行了認真的核定。亞東校稿的用心程度,胡適到了晚年還回憶,“我現在在臺灣出書就不那么容易了,我過去在亞東圖書館出了許多書,都是靠原放、希呂、洛聲等一班朋友,隨意及時把我的文章收集起來,進行分類編目,我自己非常省事,只需稍加校對,增刪或少作修改,就可成書”[注]謝慧:《胡適與上海亞東圖書館》,《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5年第4期。。作為一名管理者,汪孟鄒治事嚴謹,一絲不茍,“連一張廣告稿子,他也必定規劃妥善,算準字數,并且請人謄正,然后付排”[注]蕭聰:《汪孟舟——出版界人物印象之一》,《大公報》1947年8月10日。。作為一名出版人,汪孟鄒始終將信譽、質量和品位放在首位,對每一本圖書都精益求精。
亞東出版物的裝幀也很精美。1924年,亞東出版雜志《我們的七月》,該雜志用上等的瑞典紙印刷,封面是豐子愷先生所畫的一幅漫畫,題為《夏》。雜志內頁有鋅版的漫畫,題曰:“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這樣的裝幀別開生面,無怪朱自清收到亞東寄去的《我們的七月》時,“閱之不忍釋手”。《我們的七月》的廣告云:“OM同人為發抒他們的興趣起見,經營這小小的園地。在這園地里,有怒放的奇葩;有扶疏的嘉樹;有纖柔的芳草。他們這番躍試原以供自己賞心的。游客們如不嫌棄它的荒蕪,他們將引以為甚深的光寵。本月是第一次園游會,敬請大家光臨。來年花草栽培好的時候,還要奉邀呢。”在這則廣告中,將作品比作風景秀麗的園地,把讀者想象成游客,比喻奇特,語言精美,意味無窮。
(三)多管齊下的經營精神
“好酒也需巧吆喝”,有了好的圖書依然需要廣告宣傳來達到廣而告之的目的。它一方面需要好的廣告設計,另一方面需要多樣化的傳播渠道。亞東圖書館在圖書、報紙、雜志上對其出版物進行多介質互動宣傳,可謂精彩紛呈。
圖書本身既是出版社所宣傳的對象,同時也是天然的廣告媒介。圖書包含的各類信息要素均可成為宣傳陣地,例如書名、序文、凡例以及圖書的封面甚至是圖書的正文,等等。民國時期諸多出版機構通常會在圖書正文開始的前幾頁或正文結束的后幾頁刊登出版物廣告,即所謂“書載廣告”。亞東圖書館在其出版的許多出版物中,都有在圖書的最后幾頁推介自家圖書的習慣,例如,“亞東版”古典小說《鏡花緣》(1923年再版)的書末,廣告長達11頁之多,主要推介了亞東的重版書和新出版的書籍。其中,對重版書的推介大多以組合的方式出現,而對新出圖書則用整版介紹,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差別,是因為新書對于讀者而言是陌生的,需要更多的篇幅介紹,吸引讀者注意。如果每一頁只介紹一本或者兩三本圖書會顯得不夠劃算,因此,出版社在圖書中往往還會刊登叢書廣告或者圖書組合廣告。例如,1931年的《胡適文存》(十五版)的書后就有3頁這樣的廣告,標題為“胡適之先生的譯著”、“愛好文藝者的讀物”以及“整理過的舊小說十三種”,廣告內容大致包含書名、作者和標價,“舊小說”廣告還有一段介紹序跋的小字,“各書全有胡適之先生的考證傳敘或引論,有的有錢玄同先生的序,有的有陳獨秀先生的序,有的有劉半農先生的序”。這類廣告可以使讀者對亞東圖書館同系列圖書出版狀況有一個整體的了解。
當然,除了書載廣告這樣的硬廣告之外,好的圖書本身也是一個行走的軟廣告,例如書名、封面甚至是作者,都可以成為吸引讀者的因素。書名是對圖書內容的概括和提煉。在一般情況下,讀者可以根據書名判斷出圖書的內容主題、學科性質。從營銷的角度看,出版發行企業不僅要求書名能起到揭示圖書內容性質的作用,而且還要求書名能吸引讀者,激發需求,刺激銷售。例如,“三葉集”這一書名就帶有一定的懸念,為何取名叫“三葉”?這個名字和其中的內容又有何聯系?基于好奇的心理,讀者會很自然地想要翻閱這本書。對于這一問題,田漢在《三葉集》的序中給出了答案,“Kleeblatt,拉丁文作Trifolium,系一種三葉矗生的植物,普通用為三人友情的結合之象征。我們三人的友情,便由這部Kleeblatt結合了”。鑒于此,《三葉集》的封面是用一株三葉矗生的植物作裝飾,簡單而又清新。當然亞東還有許多其他的圖書,封面同樣非常吸睛,富于創意。例如,1924年出版的俞平伯《西還》一書,采用橫式開本,封面是畫家洪野所繪,一幅月下泛舟,清雅脫俗。再如,同樣橫向開本的《冬夜》,封面由許敦谷所畫,一位女子在撥弄手中樂器,身旁還蹲著一只黑貓,既畫出了人物風韻又富有生活情趣。又如,朱自清的《蹤跡》,封面為豐子愷所畫,色彩、筆墨都很簡潔,海上冒起的一個個氣泡,海面飛翔著的一只只海鳥,都能引發人無限的遐想。這些封面都是20世紀20年代初的作品,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歲月,卻依舊保存著生命力。
為了更好地傳達出版訊息,擴大圖書銷售,各大出版發行機構通常都會選擇發行量大、影響力深遠的報紙進行廣告宣傳。1915年,亞東承接發行《甲寅》雜志,亞東深知《甲寅》雜志的影響力,即使此時身處創業起步階段,仍舊多次在《申報》刊登關于《甲寅》雜志的廣告。從1919年以后至國民大革命期間,亞東的身影便頻繁地出現在《申報》上,基本上每天都會有廣告刊登。《申報》上首次使用白話文以及新式標點撰寫廣告文案的出版機構便是亞東圖書館,時間為1919年11月18日,廣告語為“北京大學《新潮》第一卷第三版預約”。除了《申報》以外,亞東在其他報紙上刊登的廣告也不在少數,如《時報》、《新聞報》、《民國日報》、《生活日報》和《大公報》等。
傳播面廣泛的報紙固然是宣傳圖書的不錯選擇,但報紙存在“讀者或未幾寓目,且不便保存”的缺陷,因此,具有周期性、連續性的雜志成了出版機構的重要宣傳途徑,尤其是出版社自辦的雜志則更是其宣傳出版物的天然媒介。亞東圖書館雖然沒有自辦雜志,但負責發行和代派的雜志不在少數,其中不乏發行量大、影響廣泛的雜志,例如《建設》、《少年中國》、《少年世界》等。相比報紙中眾多廣告摻雜在一起,雜志中基本一個廣告占據一頁,這樣可以使讀者不受其他廣告影響,對當前所看的廣告更為專注,在對廣告的版面設計上也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亞東的廣告更多刊載于自身發行的雜志上,《少年中國》1919年7月15日第一卷第一期,就有6則亞東的廣告。此外,當時雜志之間還交換登廣告,相互登同樣大小的版面,一概不算錢[注]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頁。。因此,在雜志上刊登廣告不僅可以節省宣傳費用,還能達到宣傳目的,既經濟又實用。
三、“亞東精神”的文化價值
(一)文化傳播價值
出版不僅是一種商業行為,更是一種文化行為。魯迅先生指出,“出版的社會意義,在于以物質的形式,以閱讀的方式,給予社會成員以文化的引導和制約,使其獲得在特定社會秩序下自我辨識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出版就是一種社會行為和社會文化的導向和選擇。一個時代的出版為了對社會負責,總得對文化作出選擇并加以組織,這是出版的一個基本任務,這也是出版之所以必要的一個基本理由”[注]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頁。。1918年,朱執信找到張元濟,商量《孫文學說》的出版事宜,張元濟考慮到政治風險,婉拒了其請求。此后多處輾轉,經介紹,朱執信找到了亞東圖書館,汪孟鄒思量再三,同意出版《孫文學說》。后來孫中山領導創辦的《建設》雜志,多方尋找合作書店,均被拒絕,最終再次交給了亞東圖書館。《建設》雜志的主導思想為三民主義,內容也有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學說和唯物史觀的介紹。《孫文學說》和《建設》出版后,受到了海內外讀者的廣泛關注,一時影響很大。在新思想尚未普及的背景下,汪孟鄒明知可能面臨牢獄之災,卻敢孤注一擲出版《孫文學說》,承接《建設》雜志,可以看出其藝高人膽大,有相當的政治覺悟和遠見卓識。正如汪孟鄒所說:“規模越大、資本越多的出版機構,經營者難免瞻前怕后,而如亞東這樣小規模的出版機構,經營者膽子就大一些,顧忌的東西沒有那么多。”[注]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頁。
亞東出版的標點本小說,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過充當“白話教本”,傳播陳獨秀、胡適等人的新思想。胡適在《鏡花緣》一書的序中說,這本書關于女子貞操、教育、選舉等問題的看法獨到,肯定了它在中國女權主義認識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這些序不僅僅是教讀者如何閱讀小說,更重要的是傳播新的思想與治學方法。除了傳播國內先進的知識文化,亞東圖書館同樣注重對西方知識文化的引進和傳播,亞東的出版物中譯著多達70多種,占其出版物總數的1/4,大多在二三十年代出版。五四運動時期,隨著知識青年沖破禮教束縛,追求戀愛自由,亞東先后出版了《戀愛心理學研究》和《近代戀愛名論》。1923年,國內爆發了一場科學與玄學的大論戰,汪孟鄒嗅到其中的文化與出版價值,迅速搜集論戰雙方的文章,并請陳獨秀、胡適作序,做成了論文集《科學與人生觀》向民眾普及。1929年,社會科學出版物尚未形成氣候時,亞東已經出版了社會科學類讀物,并預測社會科學出版物將成為閱讀新趨勢,這一點在1929年12月16日亞東在《申報》刊登的廣告中可以得到證明:
我們已經感受到現代青年的要求,已由一般的學術涵養進而為社會科學之具體的探討,這是全國的文化階段上一個必要地進步的現象。但是社會科學亦應有程序:(1)歷史的,(2)方法的,(3)基本原理的,(4)系統的專門著作。本館已出之法國革命史,社會經濟發展史即所以應第一部門的需要,現出之康德的辨正法、產業革命、社會農業即所以應(2)、(3)、(4)部門的需要。現已約定海內外專家從事編譯,組織刊行,以副讀者急切之望。
在1930年前后的幾年中,亞東出版了《辨正法的唯物論》、《斐斯特的辨正法》、《法國革命史》等16種社會科學類讀物。面對已然開始的世界范圍的政治、經濟、軍事的爭奪,亞東在1937年前后出版了《日本企業與太平洋戰爭》、《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日本能否獨霸遠東》等書,雖然此時的亞東已經步入式微,但其傳遞新思想的理念沒變,鮮明的時代意識依舊如故。
1947年8月10日《大公報》的《出版界》中寫到:“在二十五年前,當號稱文化街的上海四馬路上鱗次櫛比的書店櫥窗里正滿擺著艷情小說和黑幕大觀的時候,能夠不為時風所左右,嚴肅地出版著性質純正的書籍的,除了故趙南公先生所經營的泰東圖書局之外,還有一家亞東圖書館。”可見亞東對出版事業的認真,對讀者的負責。究其原因,是汪孟鄒認識到新書業與中國文化的傳播、傳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亞東版《孫文學說》、《嘗試集》、《胡適文存》、《獨秀文存》、《普希金小說集》、《俄羅斯名著(短篇小說集)》、《少年漂泊者》等無一不在中國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熠熠生輝。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這些作品提高了國人的思想境界,提升了國人對于文化審美和思想解放的追求。
(二)文本價值
亞東圖書館首創了古典小說標點本,使小說文本呈現出全新的面貌。據汪原放所注的“句讀符號說明”,運用的標點符號主要有“。”、“,”、“;”、“:”、“?”、“!”、“……”、“——”等十一種。用新式標點斷句,能夠提高讀者的閱讀效率。例如,《鏡花緣》第五十一回,“不但有緣,而且都有宿緣;因有宿緣,所以來結良緣;因結良緣,不免又續舊緣;因續舊緣,以致普結眾緣;結了眾緣,然后才了塵緣”。這個長句加了逗號和分號后,層次關系一目了然。魯迅對汪原放的標點給予了肯定的評價,“雖不免小謬誤,但大體是有功于作者和讀者的”[注]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頁。。受亞東本的影響,北新書局、新文化書社、文明書局、北京樸社等也出版了多種明清小說的標點本,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批標點本的出現,提供了學習國語的“模范國語讀本”,促進了白話文的推廣和普及。亞東本還推動了現代漢語書面體的形成。吳祖緗在《胡適文萃·序》一文中提到了他讀亞東本小說與讀石印本小說的不同感受:
我開始嘗到讀小說的樂趣,心里明白了小說這東西以及讀小說的人所受的待遇在新舊時代對比下是如此迥然不同。我們不止為小說的內容所吸引,而且從它學做白話文、學它的詞句語氣,學它如何分段、空行、提格、如何打標點符號。這樣,我們自然而然拜亞東版的白話小說為師,閱讀中不知不覺用心鉆研,仔細琢磨。新版的《紅樓夢》、《儒林外史》、《水滸》等不止教會我們把白話文和口語掛上鉤,而且進一步開導我們慢慢懂得在日常生活中體察人們說話的神態、語氣和意味。如此,我們的表達能力就有了明顯的進步[注]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頁。。
由此可見,亞東本培養出了一大批小說閱讀的愛好者和新式標點本的擁護者。
亞東版圖書在當代還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922年9月,《獨秀文存》開始編排,11月第一次印三千部很快銷售一空,12月再次印了三千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便停止印行。在這六年中,一共印行了兩萬九千部。1933年,亞東重印了一千部試賣,有廣告云:
此集所收為著者在民國十年(1921)以前發表于《新青年》雜志之作品,分論文、隨感錄、通信三卷。內容乃提倡文學革命,改進倫理觀念,討論宗教問題。讀此可見著者十余年前之思想與主張。九版后有蔡孑民先生的序,說“本書各文大抵取推翻舊習慣、創造新生命的態度;而文筆廉悍,足藥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沒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資格。”洋裝兩冊,兩元七角。平裝四冊,兩元一角[注]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頁。。
廣告刊登后,圖書銷路不錯,次年又續印了兩千部,這便是《獨秀文存》的第九版與第十版。1979年,為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據亞東圖書館的第三版《獨秀文存》進行重印修訂再版。
1922年,亞東圖書館出版了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這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第六部新詩集。該書收錄了《蕙的風》、《一對戀人》、《天亮之前》等一百多首詩,分為四輯,按寫作的先后順序編排,書中還有朱自清、胡適以及作者自己所作的序。寫作《蕙的風》時,汪靜之還是一名在校的學生,青春年少、天真爛漫,詩歌中少了一些深刻的反思,更多地是直抒胸臆,自然坦率。例如,這首《月夜》,“我時時注意著伊/伊婉淑的姿態/伊嬌嫩的言笑/伊輕妙的步聲……我那次關不住了/就寫封愛的結晶的信給伊/但我不敢寄去/怕被外人看見了/不過由我底左眼寄給右眼看/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唉/假使或真使/爹媽們允許了/那么我只藉此而樂生啊”[注]汪靜之:《蕙的風》,亞東圖書館1923年版,第64-66頁。。胡適在書的序中說,汪靜之的詩也許充滿稚氣,但稚氣比暮氣好得多;有些詩也許太過直白露骨,但這樣的直白比晦澀難懂又好得多;而且這樣的稚氣中總是帶著一種新鮮風味,“往往有我們自命‘老氣’的人萬想不到的新鮮風味”。魯迅先生很欣賞汪靜之的詩作,對其作品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多次通信給予作品修改意見,鼓勵其創作。“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籟,不是硬做出來的。然而頗幼稚,宜讀拜倫、海涅、雪萊之詩,以助其長。”[注]王訓昭:《湖畔詩社評論資料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頁。與其內容相呼應,《蕙的風》的封面設計也是別具匠心。書的封面是一個抱著愛心的少年,背上插著兩只翅膀,仿佛愛神丘比特,解開了羈絆,下面是解開的繩結,封面的畫下,是周作人題寫的書名,再下是“汪靜之作”的字樣。1922年《蕙的風》初版后,于1923年9月再版,1931年7月第6版時對詩作進行了刪選,只剩下了100首。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亞東初版《蕙的風》為藍本,重新對其篩選編輯出版,1992年漓江出版社以此二者為基礎又出版了《蕙的風》增訂本。2013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將亞東版古典小說四大名著全部重印出版。
結 語
魯迅先生說:“出版對于國民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方面是幫助讀者求取知識,這是對國民智能的影響。近代出版業的消費主體是日益擴大的青年學生群體,他們是社會的新生力量,這是出版業對于青年學生的影響。……另一方面是輔助讀者獲得休閑,這是對于市民生活的影響。……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是由消費的轉軌而達于思想內心的變遷,而達于更深的思想層面,是出版業對于國民生活最大的影響,也就是思想的影響。”[注]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頁。亞東圖書館是一家給中國出版界帶來新鮮血液的出版社,也是一個給中國思想界帶來驚濤駭浪的陣地。亞東圖書館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策源地,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陣地。
亞東圖書館雖已消逝在歷史中,“亞東精神”卻代代相傳。亞東創始人汪孟鄒秉承徽商所強調的“士商異術而同志”的主張,多出高尚的書,堅決杜絕出版“爛污書”,即使是在自身光景慘淡的時候,也不出版糊弄讀者、欺騙讀者的書籍,這也為亞東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亞東圖書館創造過諸多“第一”:中國第一本分類地理圖集《中華民國地理新圖》、中國第一本新詩集《嘗試集》、中國第一本新詩選集《新詩年選》、中國第一本現代作家書信集《三葉集》,等等,帶來了中國出版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一系列革命性的轉型與進步。亞東人對每一字、每一句都反復斟酌,一絲不茍,力求還文本以原貌,創造出優質的亞東本。這種灌注于字里行間、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是亞東的文化良心。亞東廣泛利用多種媒介,多管齊下,招徠讀者,促進銷售,在出版的“義”和“利”之間取得相對理想的平衡。“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亞東精神”值得編輯出版工作的從事者們歷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