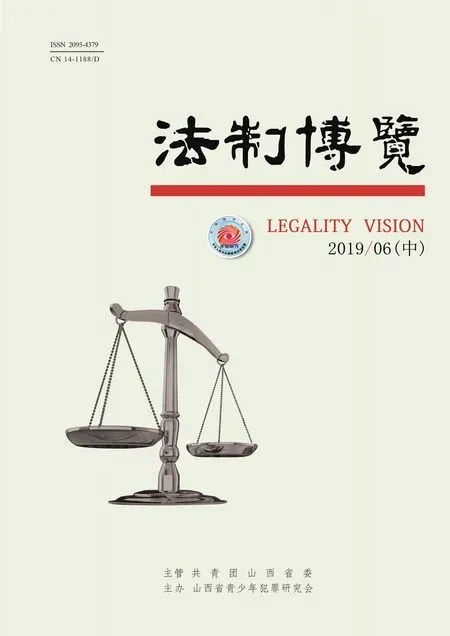論我國電信詐騙犯罪案件的特點與偵查方法
郭旭英
甘肅政法學院,甘肅 蘭州 730700
電信詐騙作為一種新興的犯罪手段,依托網絡媒介于近年來頻繁出現。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經濟的上升趨勢,互聯網逐步普及,作為網絡信息系統傳輸的載體,電腦、手機等移動終端設備普及化程度很高,尤其是智能手機已經基本上達到了人手一臺。老百姓遭受電信詐騙是家常便飯,連有些一線明星也未能幸免。根據公安部數據統計:全國的電信詐騙案件的發案率呈現直線上升的趨勢,2011至2014三年時間案件數量從十萬余起直接上升至四十余萬,詐騙犯罪所牽涉的財產數額也從四十多億增長至一百多億。偵查部門曾經開展多次專門性整治,力爭從源頭上打擊電信詐騙犯罪,曾有力地阻止了電信詐騙犯罪的蔓延與猖獗,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電信詐騙犯罪還是不同程度上存在于社會的各個角落,屢禁不止。
一、電信詐騙的涵義
電信詐騙不是憑空產生的,是社會政治經濟法治等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出現的必然產物,具有其特殊性,是傳統意義上詐騙的衍生,依托當代的先進電信技術。在理解電信詐騙的時候,首先界定“電信”一詞含義。“電信”在現代漢語詞典釋義為:在某通信系統范圍內傳輸或接收信息或信號的方式。將這種現代化技術與犯罪相結合,可以得出電信詐騙的目的是非法占有,采取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手段,運用當代通信技術手段發送欺詐信息,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的犯罪手段[1]。
(一)電信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
電信詐騙犯罪的主體和大多數刑事案件犯罪的主體是一致的,只要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的人均可以構成電信詐騙犯罪。犯罪人在主觀方面存在著違法占有數額較大公私財物,其表現是直接故意。本罪侵犯的客體是一種權利,即單位或者個人的財物所有權,同時也可以是國家財物。犯罪人在客觀上采取手段行騙,目標是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客觀要件首先是欺詐行為,即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其次,使被害人產生了錯誤認識,在其出現判斷偏差的情況下,并不影響其行為的成立。再次,財產處分也是被騙人在基于一定條件下的錯誤認識所做出的一系列決定,并且行為人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獲得被害人的財物,如果遇到金融機構緊急凍結的情況下并不妨礙其罪名的成立。
(二)電信詐騙犯罪的起源發展
電信詐騙犯罪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具有一定時間的發展歷程。電信詐騙類型的犯罪產生于20世紀末期,當時科技水平還不高,一些詐騙手段諸如刮刮卡、六合彩等開始流行,引起了許多人的好奇心,促使人們產生了一種不勞而獲、一夜暴富的心理,進而許多人被花言巧語所蒙蔽,深陷其中無法自拔。隨著科技水平的進步,互聯網時代的快速發展讓人們逐漸了解并掌握信息技術,手機和電腦等移動設備迅速普及。我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速度快,移動終端設備逐漸走進千家萬戶,基本上實現了智能手機的普及。到2010年左右電信詐騙犯罪已經呈現一種極速蔓延的態勢,手段花樣百出,數額巨大,嚴重危害社會安定。在生活中我們都或多或少地接到過騷擾電話、垃圾短信、不明郵件,在有些湊巧的情況下就會使我們的判斷力驟然下降,甚至不經過大腦的思考就落入了犯罪分子所布下的陷阱,最終導致財物損失。
二、電信詐騙犯罪的特點
(一)犯罪程度高智能化
犯罪行為人依托當代高科技設備來實施犯罪,如手機、電腦、ATM機等。隨后一些高科技手段逐步被犯罪行為人所掌握,如變號器、偽基站、群發工具,這些技術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一般是接觸不到的,所以給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機。作案人掌握了熟練運用這些工具的能力,為的就是讓被騙人對于其虛構和制造的圈套信以為真,深信不疑,從而在犯罪人的掌控下一步步地完成詐騙行為。
(二)犯罪具有很強的隱蔽性
電信詐騙與傳統詐騙最為明顯的區別之一就是行為人與被害人無正面接觸,即通過網絡通信介質實施高科技遠距離詐騙[2]。犯罪行為人的體貌特征通常無從得知。許多人對于電信技術都是一知半解,所以錢財安全是一個及其嚴重的隱患。另外,電信詐騙犯罪涉及的地域跨度非常廣,有時候甚至是國外的犯罪團伙對國內的人民群眾所實施的犯罪。一些傳統意義犯罪現場上的所能夠提取到的物證和痕跡就會使電信詐騙犯罪案件的偵查陷入困境,民警的思維尚未完全適應,因而這種情況下也會導致案件高發。
(三)作案手段花樣百出
電信詐騙由于主要是以語言或者文字為媒介進行傳輸的,那么其種類繁多,形式多樣,一般作案人主要采用冒充的方法進行詐騙。首先,這種冒充主要表現在與我們日常生活緊密聯系的一些單位或部門如公檢法司、電話運營商、國稅與地稅以及相關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其次,主要是冒充熟人進行詐騙,這種情況下犯罪行為人一般掌握了一些被害人的相關信息,包括社會關系與社交情況。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的情況后就編造一些如“發生意外”、“資金困難”、“代理繳費”等托詞理由來促使被害人給其提供的賬戶中匯款。另外,重金求子、引誘裸聊、投資返利以及校園貸等詐騙手段也在不斷翻新,據公安部披露出的新型常見詐騙手段多達48種[3]。
(四)犯罪組織呈現專業化
電信詐騙犯罪在當前已經成為一條具備產業鏈條的犯罪組織。國內最近摧毀了多個電信詐騙組織來看其特點是顯而易見的。“公司”型結構產生讓一些人聚集在一起,通過投資者資金的注入,進行一些具體職能分工。在團伙中具體表現為技術、通信、洗錢和后期等幾個組別,分工不同,職能不同。首當其沖的馬仔就是這個犯罪團伙中處于最底層的存在,可獲得一定比例的勞務費,他們通過“地下錢莊”將涉案資金轉移到海外。公安機關在單打獨斗的過程中往往耗費不計其數的人力物力財力,導致偵查效率低下,破案率上不去,人民群眾的滿意度降低[4]。
三、電信詐騙犯罪案件的偵查方法
(一)加強陣地控制,善用刑事特情
一般而言犯罪是一個因果關系的完整體現,那么犯罪就會依托于具體的媒介而存在。犯罪工具和贓款是電信犯罪詐騙案件最重要的作案途徑[5]。金融系統和電信部門作為與電信詐騙犯罪緊密聯系的兩支機構,偵查部門可以考慮在這兩支機構中安插、物建刑事特情,加強陣地控制。在具體案件偵辦的過程中,刑事特情可以向偵查部門提供第一手的最新的重要情報,通過對犯罪脈絡的掌握,銷贓渠道的把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擊犯罪行為人并且控制贓款贓物,從而達到案件偵破。
(二)利用技術手段進行偵查
偵查機關可以運用大數據云端服務器的手段,對涉案電話號碼或者手機數據流量的相關基站痕跡進行大數據庫碰撞分析。在經過一些基站的碰撞后就會篩選和挖掘出相對穩定的數量的涉案號碼。當前手機監控定位的功能逐步也出現在各大主流APP軟件上,利用相關時間和空間的作案手機反跟蹤技術,可以順利地鎖定信息傳播源頭,通過網絡瀏覽記錄、資金出入賬記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情況對有共同犯罪情況的團伙成員進行分析,跟蹤并逮捕在逃嫌疑人。
(三)依托電信詐騙偵查破案協作平臺
電信詐騙犯罪的隱蔽性是顯而易見的。在不確定的對象中偵查機關很難對于一些特征區域和違法行為做出準確的反應和界定,所以偵查意識、信息意識、情報意識是當前偵查人員所應該樹立的意識方向。電信詐騙犯罪的區域信息和平時工作情況的具體收集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要積極運用全國電信詐騙偵查合作平臺,開展聯合偵查、協同作戰,發揮偵查機關的整體力量。基層公安部門應當及時輸入本地平臺的電信詐騙犯罪,通過陣地控制與并案偵查,根據信息采集的刑偵協作平臺,對電信詐騙犯罪趨勢進行深入剖析,梳理出犯罪高發地區,結合網絡信息及時響應。公安機關可以在偵查辦案過程中通過網絡中提取到的犯罪證據和電信詐騙犯罪的材料,及時總結,快速實現跨區同步取證,提高偵查效率,促使案件順利破獲。
綜上所述,電信詐騙犯罪案件近年來的逐步高發使得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遭受極大地損失,其社會負面影響不斷加大。公安機關在不斷加大打擊力度的同時要結合當前法治社會“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要求,與電信和金融行業加深合作,盡力取得符合電信詐騙犯罪案件證明標準的證據,強化電信詐騙的宣傳工作,定期通報最新出現的詐騙形式與手段,從根源上遏制電信詐騙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