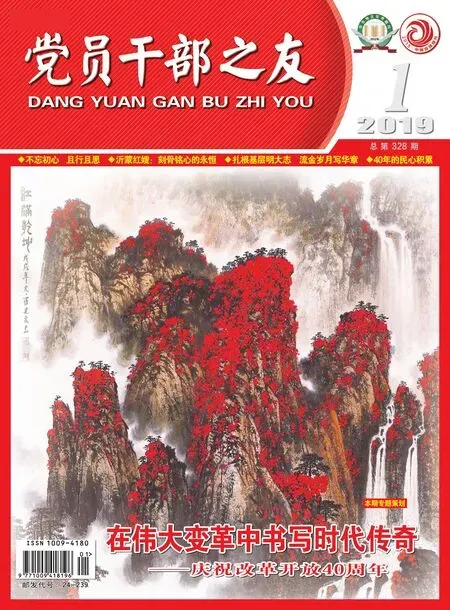從敘利亞危機看海灣地區重建困境
□
2018年敘利亞危機發生重大轉折,戰事已見分曉,巴沙爾政府占據上風,雖然大局已定,但戰火并未停息,各派依然處于交火狀態。
海灣地區秩序總體評估
眼下,國土面積只有185180平方公里的敘利亞境內,駐有眾多外國軍事力量:美軍已增為5000多人,在幫助敘政府的反對派作戰;俄羅斯、伊朗的軍隊,黎巴嫩真主黨,在幫助敘利亞政府作戰;土耳其軍隊越境進入敘利亞,驅趕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圍剿“在敘境內活動的土耳其庫爾德武裝”;以色列軍隊時常出動戰機偷襲敘境內軍事目標以及幫助敘政府作戰的伊朗軍事目標。近日,沙特、阿聯酋、約旦、科威特和巴林5國組成聯軍進入敘境內的美軍基地,美國揚言要用聯軍來對付土耳其。
駐敘的外來軍隊分為兩類,一類是幫敘政府不被顛覆的,另一類是幫敘反對派的,兩類敵對力量在敘混戰了近8年,原本只是內戰的敘利亞因此變成了多國博弈的戰場。目前,海灣地區呈現為戰亂秩序,這種戰亂秩序并非是從“阿拉伯之春”開始,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海灣戰爭。海灣戰爭(取得了聯合國授權)是美國為首的國際聯軍發動打垮薩達姆的戰爭。如果從那時算起,海灣戰亂秩序已持續了28年之久,海灣地區秩序已今非昔比。
海灣地區秩序的變化
變化一,美俄博弈比冷戰時更加激烈。1990年,2003年,美國先后發動了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兩場戰爭之后,美國在海灣地區處于一國獨大的地位。從2011年“阿拉伯之春”開始,尤其是2015年以來,俄羅斯對敘利亞的支持力度加大,公開出動軍事力量驅趕“伊斯蘭國”,穩住敘利亞政權,俄用武力成功重返中東政治舞臺,打開了新局面。此后,美俄博弈進一步深化,表現在以下兩點:
1.“阿拉伯之春”之后,美國主導著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集團”國家,俄羅斯主導著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集團”國家,展開激烈爭奪,在敘利亞和談進程中,甚至出現了兩個運作中心。俄羅斯在海灣地區屢屢以軍事行動走強,令世界刮目相看。當然,在美俄博弈中,盡管出現了“俄進美退”的局面,美國地位有所下降,但總體上美國依然掌控全局走向,占據主導地位。
2.海灣地區秩序目前凸顯兩組格局:一組是美俄兩極博弈格局,另一組是地區大國伊朗—沙特陣營博弈格局。這兩組格局之間緊密相關,相互配合。
冷戰時,美俄通過軍事、經濟、政治、外交等支援手段干預海灣事務,現在,已經變為投入軍事力量直接參戰,這種變化比冷戰時的博弈更為嚴重,更有損于地區國家。據悉,俄在敘已部署了“伊斯坎德爾-M”短程彈道導彈,其射程覆蓋整個中東地區,均攜帶核彈頭。換言之,俄將不惜任何代價,誓死捍衛其在敘和海灣地區的地位和利益,同時已做好與美國魚死網破的準備。
可以說,美俄誰也不能甩開誰,沒有誰可以單獨決定海灣地區局勢的發展走向,兩者在博弈的同時尚需對話、協商、溝通以及利益分享。
變化二,教派間的殊死博弈已難以控制。遜尼派陣營與什葉派陣營之間的殊死博弈,已占據地區沖突的前沿位置,兩者水火不容。海灣戰爭之前,遜尼派與什葉派的沖突處于可控狀態,薩達姆政權垮臺后,強人強國都沒了,敘利亞又處于自顧不暇之中,該地區被釋放的教派沖突發展到不可控狀態。
當今海灣地區秩序中,凸顯勢不兩立的兩大陣營,即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結為什葉派陣營;沙特與該地區遜尼派阿拉伯國家結為堅實的遜尼派陣營,兩大陣營呈殊死對抗局面,看不到盡頭。地緣政治爭端通過教派因素使問題更加復雜,教派爭端被賦予了政治內容,已成為本地區秩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今后,海灣地區新秩序的重建必然會有教派力量的參與。
變化三,地區大國對敘利亞事務的干涉越來越公開,力度越來越大、越深。伊朗軍隊、土耳其軍隊、以色列軍隊,都根據自身需要選擇進入敘利亞境內作戰,甚至軍事力量遠不是土耳其對手的沙特及海灣君主國,在美國的作用下,也敢紛紛進駐美軍駐敘基地,擺出一副攪局的態勢。
變化四,敵友關系發生顛覆性變化。阿拉伯國家作為一個整體,長期對以色列奉行一個共同的政策,即不承認以色列的存在。然而,這個曾經鐵一般的政策現在明顯變化了。以色列作為阿拉伯共同敵人的定位被瓦解,擁有了不少“阿拉伯盟友”。這個觀念的改變,直接導致敵友邏輯改變了,敵友陣營亂了。敵友陣營發生顛覆性變化和錯位,必然造成整個海灣地區安全秩序發生重大改變。
“阿拉伯之春”以來,沙特一直參與顛覆敘利亞政權的活動,阿拉伯兄弟轉眼成了敵人,相反,沙特與固有的敵人以色列交往凸顯。為了對抗共同的敵人伊朗,沙以走在一起,沙以敵友關系的轉變是互有所需的結果。現今,海灣地區出現了一個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聯盟,即對抗伊朗的聯盟——沙以聯盟。“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正在海灣地區被驗證。說到底,國家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國家利益。
海灣地區秩序重建的困境及前景
敘利亞危機走到今天政權尚在實屬不易,現正逐步轉入戰后重建進程,但這并不意味著戰亂結束,戰爭后遺癥繁多,敘戰后重建將受到以下制約:
第一,受世界大國的制約。當前海灣地區戰亂秩序是美國發動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直接后果,是動用武力打下的美國主導地位。俄羅斯緊步其后,在敘利亞靠動用武力打出天下,占據了與美共同主導該地區事務的地位。目前局面對美俄雙方都有利,敘利亞作為海灣地區大國,其局勢發展對海灣地區新秩序的構建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美俄將會繼續參與包括敘戰后事務在內的海灣地區新秩序的重建。
第二,必將受地區大國的深度參與。敘利亞政府目前需要應對的局面依然嚴峻,必將繼續應對來自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陣營發起的挑戰。教派爭端作為戰略博弈,勢必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第三,受國內反對派制造麻煩的挑戰。敘利亞伊德利普省仍有5至6萬被包圍的反政府武裝,還有美軍支持的庫爾德武裝,以及土耳其支持的敘利亞自由軍,他們不斷向政府發起挑戰,戰場形勢可謂嚴峻。
第四,確立新的政治體制的嚴峻挑戰。敘利亞戰后重建首先要轉入“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伊拉克戰后重建很有可能是敘利亞參照的模板。在美國的干預下,伊拉克由“共和制”轉為了“聯邦制”,敘利亞將如何轉變呢?是否會參照伊拉克的模式呢?告別舊體制,建立新體制,各派在權力分配過程中的博弈,必將伴隨著若干不確定的新沖突。
第五,庫爾德人鬧獨立問題。目前,在美國的支持和扶植下,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實力大增,已形成相當的氣候,不斷壯大的勢力范圍幾乎囊括了敘利亞的整個東北部,以及伊拉克北部地區。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坦克、裝甲車等重型裝備,開到敘利亞邊境地區嚴陣以待,并時常發起空襲行動。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和土耳其四國的庫爾德人都在鬧獨立,他們之間密切互動、互相影響,問題錯綜復雜,各國都不得不認真應對。
第六,應對“伊斯蘭國”殘余勢力的反撲。目前,“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殘余勢力還有生存空間,其主要力量已經被國際聯軍包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邊境區域,但他們伺機而動。遏制“伊斯蘭國”突發崛起,中東反恐使命是長期的。
第七,外國撤軍問題。2018年12月19日特朗普宣布,美軍將在60到100天內撤出敘利亞。特朗普突然撤軍的原因復雜,其一,可自圓其說,美稱已經贏得了對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戰爭。其二,撤軍是特朗普“戰略收縮”的組成部分,即減少在中東的投入,以避免重蹈陷入伊拉克戰后泥潭的覆轍。況且,俄支持的敘政府已控制了大部分國土,大勢已定,美軍在敘駐扎4年多,已不能改變當今敘利亞的局勢。其三,特朗普以退為進,欲借沙特為首的地區盟友之力掌控海灣事務,戰略撤退對美更加有利。美軍一旦撤出,美俄力量對比將發生有利于俄的改變,但撤軍并不意味著美國對海灣的掌控力變弱,一旦局勢需要,美軍依然可以重返敘利亞。
美軍撤出后,俄軍、伊軍、土軍、沙特聯軍、英軍、法軍、德軍等多國特種兵還駐扎在敘境內,敘行使主權依然受到制約。敘由強國到弱國的格局短期內難以改變,若要恢復到戰前的地區秩序,可能性幾乎為零,重建阿拉伯國家主導的海灣地區新秩序的條件處于不利態勢,同時也存在著不確定的巨大風險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