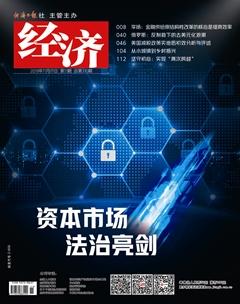從小城鎮到鄉村振興
魏永剛

費孝通當年調研寫作《江村經濟》的吳江區七都鎮開弦弓村新貌
吳江是江蘇省蘇州市一個區。歷史上,這是蘇州郊區的農業主產區;現在,地鐵把蘇州和吳江緊緊聯系起來,吳江向東和上海交界,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區域。
之所以選擇這里進行調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上世紀80年代初,費孝通先生曾經在這里調研,提出“小城鎮大問題”。他30多年前的記錄形成一個坐標,能讓我們看到這些年走過的距離;第二個是,吳江區這幾年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很有成效。
從小城鎮到鄉村振興,是不同歷史時期黨在農村的政策。這兩者之間有多長,我們經過了哪些階段,走到了什么地步,還面臨哪些困難,探尋這些問題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一定現實意義。因此,記者利用四天時間,重訪費孝通先生當年調研過的七都、震澤、盛澤、平望、同里等鄉鎮。
收入:老話題有新內涵
農民收入多少關乎生活富裕,關乎產業發展。增加收入,是鄉村振興的一個基礎性目標。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對這個目標有著不同理解。
記者隨機走訪吳江四個鎮的11戶農民家庭,年人均收入最少的也在3萬元以上。費孝通先生當年從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角度來看待發展鄉鎮企業的緊迫性。今天,這些地方的農村居民,主要收入來源是工廠上班。有兩個概括性認識:一個是政府統計數據。吳江區2018年統計公報顯示,全區居民2018年可支配收入是52969.3元,其中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2193.7元。再一個是我們在盛澤鎮一個農村聽到的說法。村黨支部書記介紹,一個3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屬于低收入戶,是幫扶對象。
記者在震澤鎮眾安橋村跟一戶徐姓人家算收入賬。這個家庭6口人。老徐的母親83歲,每年有近6000元養老金;58歲的老徐在附近打零工做泥瓦匠,年收入10萬元左右;老伴原來在紡織廠上班,現在“專職”看孫女,每月領1000元社保;兒子在鎮里一個服裝廠上班,妻子是廣西人,也在鎮上工廠上班,小兩口每年工資收入12萬元左右,還有一個女兒,剛剛上幼兒園。6口之家,年收入將近24萬元,家里有汽車,住的是樓房。
人均年收入3萬元以上,人們生活表現為一個什么狀態?通過對8個村莊的入戶調研,大致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印象:有新房,有汽車,不愁吃住。

農名過著新生活,鄉村更加美起來,在家門口養花種草,已經成為吳江農村新的習俗,這是眾安橋村一戶農名正帶著孫女給花澆水。
費孝通先生當年在《小城鎮再探索》中敘述了“草房改瓦房”“瓦房改樓房”的變化,通過看住房來衡量一個地區農村發展水平高低。如今,吳江農民住上樓房之后,又把磚混式住房改造為上下三層的別墅式樓房。隨著小城鎮發展,不少富裕起來的農民還在鎮上買了房子。最近10多年,經過集中整治和新農村建設,農民紛紛在原有宅基地或村莊規劃地段重新翻建了住房。這一輪建房熱潮正在過去。現在,吳江農村農戶一般住房都是三層別墅式,每層140平方米左右,大部分農戶在集鎮還有一處住房。從某種意義上說,“住房剛需”在這里正慢慢減弱。
私家汽車保有量也許可以成為衡量人們生活水平的一個“新指標”。記者在吳江4個鄉鎮8個村莊入戶走訪,得到的結論是,戶均汽車2輛,有的6口之家有4輛小汽車。當地干部介紹,戶均1.5輛汽車。一位村干部說,在房屋建設中,村里就是按照戶均1.5輛汽車來分配停車位面積的。2018年統計數據顯示,吳江區264296戶,私人汽車保有量達到346362輛。按照這個數據,戶均汽車1.3輛。同樣的指標,記者在甘肅東部、湖南南部山區農村得到的數據是,村民中40%農戶擁有小汽車。
與農戶收入相對應的是農村集體收入。記者調研8個村莊,集體收入最多的超過千萬元,其中有4個村莊在800萬元以上,最少的年收入320萬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吳江區和蘇州市都有一個幫扶薄弱村舉措,他們對薄弱村的“定義”是集體經濟收入在250萬元以下。



寫在吳江農村墻上的“農耕文明”。人們祖祖輩輩賴一生活的農耕生活,正在凝結成一種文化符號,吳江農村的農名已經很少,但農耕文化卻作為一種文化資源,被人們記憶和描畫。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吳江鄉村已實現了生活富裕。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產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增收有著新內涵。
在吳江農村,不同年齡段居民,收入來源和收入水平有很大不同。60歲以上老人是一個群體,收入的重要來源是養老金。養老金分為城鎮養老和農村養老兩種。享受城鎮社保制度的老人每月生活費在1000元以上;領取農村社保的老人每月生活費是300元到500元。這里鄉鎮企業發展充分,60歲以上的老人大都在企業工作過,享受城鎮社保制度的老人占大多數。
30歲到60歲的主力人群是另一個收入群體。他們大部分已經成家,統計項目中沒有專門計算他們的收入。根據記者隨機調研,這個群體每戶年收入在20萬元以上,最少的10萬元左右,而最高收入則超百萬元。當地人介紹,收入最高的是中小企業主。他們與普通農戶的收入差距在數倍以上。因為就業穩定性強,人們的收入預期也相對穩定。
吳江這幾年正在進行“退二進三”,直接表現在要求村里拆除一定面積的廠房。這是環太湖流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也是地區產業轉型的必然選擇。這項工作力度很大,但對當地就業和增收的直接影響并不大。記者調研中感到,最直接影響到的是50歲以上的老人。
五六十歲的老人過去受益于“亦工亦農”“離土不離鄉”的生產方式,習慣于在周邊工廠打零工增加收入。工廠退出村莊進工業園區,會影響他們就業,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收入。影響程度有多大?有些老人一年打零工的收入在10萬元左右。如果工廠距離村莊較遠,他們的這部分收入可能減少一半以上。我們在村莊調研中看到,有不少農村老人70歲以上,還在附近打零工。產業“退二進三”,對他們的收入影響最大。因為有養老保障制度,加上家庭負擔不重,老人的打工收入可以稱為“補充性收入”。受影響的是這部分收入,但不會直接傷及生活水平。
產業轉型影響最大的是中小企業主。我們在同里鎮遇到一位藺草加工的企業主。他的廠子最多時有20多個工人,今年在“退二進三”中廠子被關閉了。他兩個女兒已經成家,都在城里工作。他自己、愛人和岳父、岳母兩位老人住在村里。岳父是退休職工,月工資2990元;岳母領農保,每月460元;家里已經有每層140平方米的一棟兩層樓房,還有兩輛私家汽車。雖然關閉企業給他家帶來暫時困難,但并沒有對生活帶來太大影響。他表示,準備看情況去找地方打工。
因為有過鄉鎮企業的充分發展和小城鎮建設的基礎,得益于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吳江這樣的地區產業轉型不會直接威脅到群眾生活。對部分群眾,比如老年人的獲得感,是會有一定影響。增收是“剛性目標”,但并不是緊迫要求。
融合:產業發展求新解
吳江多年前就提出打造“江南水鄉標桿”,實現生態美、文化美。費孝通先生在《小城鎮大問題》中曾經說過,“小城鎮建設是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人口出路的一個大問題”。正是從這個現實需求出發,過去幾十年,這里有了鄉鎮企業的充分發展,有了小城鎮建設的城鄉融合、統籌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富到美的過程。如今,產業基礎和產業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
人多地少、農工相輔是費孝通先生幾十年前敘述的蘇南農村實際和歷史傳統。這個傳統已經有了很大改變,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農工相輔”變成了“以農補工”,農業正在成為工業和服務業的“補充”。在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占絕對大頭,農業占比已經很低。2018年的統計公報顯示,全區三次產業結構比為2.2∶51.3∶46.5。一位在開弦弓村的社會學者說:蠶桑之鄉,蠶沒有了,現在只有30張左右;魚米之鄉,米沒有了,稻谷種植已經很少。
從就業人口和農業經營方式來看,有關部門的同志介紹,吳江全區人口83萬多,流動人口97萬多,但從事農業生產的只有1萬多人。2009年,吳江曾經以政策補貼形式推動土地流轉,在鄉村實現了集約化規模經營。我們在多個農村調查顯示,一個村從事田間勞作的人不過百人,而且大都是50歲以上的勞動力。這些年,有不少外地人到吳江的一些鄉村承包土地,從事農業生產。
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讓我們重新認識農業。從經濟角度看,農業不發揮吸納就業作用,增加農民收入不靠農業,當地糧食供應也不靠本地的幾畝田。那農業還有沒有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吳江農村發展的一個選擇是文旅結合,一產和三產融合發展。他們努力使農業發揮生態作用、休閑功能,成為文化載體。
到吳江,就要訪江村。七都鎮開弦弓村因為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而出名,“江村”成為流傳甚廣的一個文化品牌。該村黨支部書記感到,現在面臨產業發展“陣痛”,“痛”在二產提升不易,一產、三產融合困難。
開弦弓村發展旅游某種程度上占“先天優勢”。費孝通紀念館建在村里,最多時每天有2000多名參觀者。開弦弓村人口幾經合并,現在才2800多人。村里幾年前就建設了文化弄堂,美化了街道。走在這個太湖邊的村落里,小清河曲折環繞,座座小橋連通兩岸,充滿江南文化氣息,時不時能碰到慕名而來的游人。

震澤鎮眾安橋村新“落戶”的農村菜館,村里的旅游開發剛剛開始,在村里的農家菜館吃農家菜,是新的鄉村體驗。
但是,村里的民宿今年才開始建設。6家農家樂飯店,服務、標識都不統一,難以產生品牌效應。最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充滿文化意味的村莊,至今還沒有開發出像樣的文創產品,游客來“帶什么走”依然是個大問題。2017年起,這里打造特色田園鄉村,建設文化禮堂,認真謀劃“江村文化”這個特色品牌。他們今年請上海一些大學教授專門研發游學課程,針對性地開發適應大中學生學習的旅游項目。村干部感到,實現產業融合發展,最缺人才。
眾安橋是震澤鎮的一個村莊,這個1750多口人的村莊,近幾年騰退出35畝的廠房面積。村里原有16家企業,去年關停了7家,今年準備關停余下的9家。2018年,鎮里成立公司運營村莊的文旅項目,開啟鄉村轉型發展之路。眾安橋也被確定為江蘇省第一批特色鄉村。記者到村里時,當年那些寬闊的廠房正在加固改造,發展民宿和文化禮堂。街道和民居外觀整修一新,引進的一處咖啡館已經開始營業。行走在這稻田簇擁的村落里,濃郁的鄉土之風撲面而來。
村黨總支書記是一位1980年出生的年輕人,這位從江蘇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對于鄉村振興很有信心。他們引進了浙江大學合作團隊,注冊了商標,自覺地打造農產品和鄉村旅游的文化品牌。這個村莊生態優勢明顯,自然環境好,而且交通發達,有發展文化旅游的條件。
實現一產和三產融合,不是簡單相加。其中隱含著一個如何認識農業,如何發展農村的大問題。鄉村干部說,“農業持續性吸引力”和旅游發展與鄉村承載力的矛盾是現實困難。我們在眾安村聽到一個油菜花的故事。每年春天,油菜花盛開,游客蜂擁而至,這里便會出現停車難、行路難、吃喝難等。但是,油菜花開過之后,就是幾個月“空當”。如何讓一產“接續”營造出美麗風景,怎樣提高村莊旅游的接待能力,這是鄉村產業融合發展面臨的具體問題。
鄉村振興不是單個鄉村的自我發展,而是一個區域性的選擇。村落邊界本身是規模和品牌的界限,在規模和品牌內涵、文化輻射上都難以適應產業融合的需要。吳江區提出打造“中國江村”鄉村振興示范區。他們按照區域內的產業特色和文化基礎,以文化為紐帶,以特色產業為重點,規劃將環長漾片區打造成江南水鄉生態文化特色帶的先行示范區;以國家級品牌為引領,充分發揮國家級農業示范區核心區(北聯)、同里國家濕地公園及同里古鎮等優質資源優勢,著力推進農業和旅游、教育、文化、康養等產業深度融合。以特色田園鄉村為樣板,打造美麗鄉村建設的升級版,統籌推進12個特色田園鄉村示范點。
這是一種以地域特點來規劃,打破村莊邊界的努力。他們正在書寫另一篇富有時代新意的“江村故事”。
治理:社會建設新課題
我們在開弦弓村遇到了吳江區藍天環保志愿者協會的志愿者。他們正在幫助農民改造庭院,把農戶隨意栽種在院子里的花草,修葺改造,形成庭院風景。他們把這叫做“美麗庭院”活動。
這些志愿者幾次來到村里深入農戶做工作,已經改造了20多個農家院。到今年9月底,他們將開弦弓村45個農家小院改造為景觀。把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修葺成好看的風景,得到了農民歡迎,開弦弓村黨支部書記也積極支持。他說,也許通過這個活動能解決心頭的一個困惑:辦農民想辦的事情,動員農民主動參與鄉村建設。
如何在鄉村振興中更好發揮農民積極性主動性,是不少村干部的“共同煩惱”。這些年,在鄉村建設中通過政策補貼來動員群眾參與,是一種有效形式。但在社會建設方面,這種努力有時候卻收到相反的效果。一位吳江藍天環保志愿者說,帶著農民一起干,為農民做示范,要比簡單的政策補貼好。“靠補貼發動老百姓不可行。補貼會讓群眾產生過高的心理預期,而達不到預期就會引起不滿。”
有時候,吸引農民參與需要轉變觀念。我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吳江鄉村前些年建設了不少鄉風文明館和村史館。但這些館大都建在一個個院落里,平時去的人不多,發揮作用不夠大。他們這兩年改變思路,把“館”改為“廊”,在村里建設鄉風文明長廊。長廊下面常常會聚集很多人,潛移默化地發揮了育人作用。
農村社會建設面臨的一個更具體的困難是協調利益糾紛。農村糾紛的內涵在發生著變化。同里鎮一位從1992年起就擔任村干部的老支書感慨,過去是耕地占多占少會吵架,現在是建房子占多占少,蓋高蓋低,是不是擋住了陽光,都要起紛爭。村外的糾紛少了,但村子里的糾紛多起來了。
更難處理的是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記者調研的8個村莊,集體支出最大的項目都是村莊基礎設施改造。當基礎設施建設觸及農戶個體利益時,協調起來非常困難。七都鎮隱讀村就遇到了水管難題。村里改造自來水管道,涉及具體農戶,他們不同意從自家房屋前通過。排污管道要通達到戶,也遇到很多困難。
北聯村一位村干部說,現在農村發展已經不是一家一戶模式了,需要統一起來,整體規劃。但是,村干部協調矛盾存在“本領恐慌”。他的體會是,和過去相比,現在對村干部要求越來越高,但村干部的辦法越來越少。
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農村基層社會建設是許多地方都存在的共性問題,也是實施鄉村振興需要著力解決的。吳江經濟相對發達,有其他地方不具備的社會建設資源。記者印象最深的就是村莊的凝聚力和家庭的和諧。
因為經濟發達,吳江的農村人口是“輸入型”的。農村居民有外出的,但沒有形成“空心村”,反倒是每個村莊都有外來人口。吳江全區83萬多人口,外來人口97萬,超過了本地居民。記者走訪的8個村莊,外來人口最少的400多人,最多的3000多人,超過了本村居民。因為人氣旺,村莊建設動力就更足,人才資源也更多。這與中西部地區許多“空心村”社會治理遇到的困難大不相同。人,是農村社會治理的對象,更是社會建設的力量。
吳江鄉村的別墅式住房改變了家庭結構。記者在四個鄉鎮看到的家庭結構大致是奶奶在家里照看孫輩,爺爺在附近打零工,青壯年夫妻在附近集鎮或者吳江上班。三層別墅按照“編年史”結構安排著一家人的起居。一層通常住著爺爺奶奶,他們房間不大,但省了上下樓梯;二層是青壯年夫婦,按照結婚時的樣式安排獨立起居空間;三層則是孫子輩,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這種家庭結構保留了鄉村生活的溫情,也守住了鄰里關系的信任。
這些獨立的三層別墅式住房,第一層通常都把最大的房間當作客廳,而且房門非常開闊。只要家里有人,房門就是打開的。鄰里之間的信任和鄉村熟人社會的特點從這打開的房門透出來。
行走在這樣的鄉村,與中西部空心村莊、留守老人獨居的情景相比,我們總感到,這種保留著農業社會特點,卻已經不是種田農民占主體的鄉間,有著豐富的社會資源。基層農村社會建設應該充分認識和發揮這筆資源的作用。
“鄉腳”:舊瓶新酒意味長
吳江農村集體收入中,有一項重要項目是村里“宴會廳”出租收入。記者在4個鄉鎮8個村莊看到,有的村竟然有3個宴會廳。最多的村子,一年宴會廳出租收入達300多萬元。
記者參觀了不同村莊、不同規模的4個農村宴會廳。給村集體帶來豐厚收入的農村宴會廳,其實就是一個面積較大的飯堂,前后都有舞臺,可以方便地隔開,形成不同區域。宴會廳附設有廚房和廚具,舉辦宴會時,允許租用者自帶廚師,自帶食材,自行做飯。小宴會廳能放上百張桌子,大的則可容納300多張桌子。
來“設宴”的都是什么人?大都是本村和附近農民。從上世紀90年代之后,別墅式住房代替了過去的庭院,農民辦喜事沒有辦法在一家一戶的院落里完成。盡管集鎮有各式各樣的飯店,但農民并不喜歡到那里辦喜事。宴會廳每桌可坐8到10個人,“伙食標準”280元左右,比飯店便宜,更重要的是滿足了農民聚集起來熱鬧的情感需求。這種設宴形式受到農民廣泛歡迎,每個周末,這些宴會廳都是客滿。
盡管如此,宴會廳卻并不是每個村莊的“標配”,往往是一個宴會廳服務一個區域的農民。根據農民和村干部的介紹,我們給宴會廳劃出了“服務半徑”:最遠可以輻射到50多里,一般情況下一個宴會廳服務周邊20多里路的地方,老百姓說,開車20多分鐘能到達最好。
一定半徑距離的農民圍繞一個“宴會廳”辦喜事,讓記者想起了費孝通先生多次提到的“鄉腳”。費孝通先生在《小城鎮大問題》中是這樣表述的:鄉腳并不是以鎮為中心的一個清晰的圓周,每一種商品都有各自的鄉腳,所以一個小城鎮的鄉腳由許多半徑不等的同心圓組成。他還以震澤鎮為例說,“鄉腳”就是“一片滋養著震澤鎮同時又受到震澤鎮反哺的農村”。費老當年以商品銷售半徑來認識“鄉腳”,以此做出了城鎮層次劃分。今天,農村宴會廳則以服務半徑來劃出自己的“鄉腳”。這已經不是商品銷售服務的范圍,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農村公共服務的“半徑”。
城鄉一體化發展使吳江這樣的地方,已經模糊了城鄉界限。村里人說,現在到鎮上、到吳江城,甚至到蘇州和南京,他們都不叫“進城”。現在人們講“進城”至少是到上海。
家家都有一輛以上小汽車,公交通達每個鄉村,再加上快遞等新型消費形式的發展,可以說,城鎮和農村已連成一片,商品交流“無縫”進行。在同里鎮北聯村,我們訪問了一個農村小賣鋪,70歲的店主介紹,他1992年開始經營農村小店。原來是一個門面,后來擴展到一個屋子,現在則又縮回到一個門面。20多年前,小店一年收入過萬元,現在每月不足百元。他說,村里人更愿意去城鎮超市買東西,已經不需要到小賣鋪來。
商品的“鄉腳”正在模糊,而公共服務的“鄉腳”則凸顯出來。宴會廳之所以在農村有那么大市場,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滿足了農民的心理需求和經濟發展水平。公共服務既需要一定交通條件,更需要在習俗和生活習慣上貼近農民。
有些公共服務是需要以點帶面輻射周邊的。如何布局這類公共服務?“鄉腳”具有啟示意義。這類服務項目不能簡單按照行政區劃來布局,也不能隨意劃定中心。不同項目在不同村落之間的層次劃分,基層政府可以“鄉腳”為參照,認真研究服務項目的輻射半徑,讓農村公共服務更加貼近農民情感需求和生活習俗。
公共服務對于吳江這樣的人口“輸入型”地區,還有另一層經濟意義。過去幾年,建標準廠房是幫扶農村集體收入薄弱村的有效舉措,不少村莊集體收入中,廠房租金占大頭。這兩年,隨著地區經濟轉型高質量發展,拆廠房成為“退二進三”在農村的重要工作。沒有了廠房,集體經濟怎么辦?建集體公寓,服務外來人員成為許多村莊的一個選項。我們走訪的8個村莊,至少有4個都把公寓收入作為集體收入來源。從辦工廠到辦服務,這是吳江區農村經濟發展的又一個有意思的轉變。隨著農業集中程度的提高,工廠入園區,哪些村子需要有外來人員公寓,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外來公寓和服務外來人員可能也存在一個“半徑”,也需要以“鄉腳”的思路來謀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