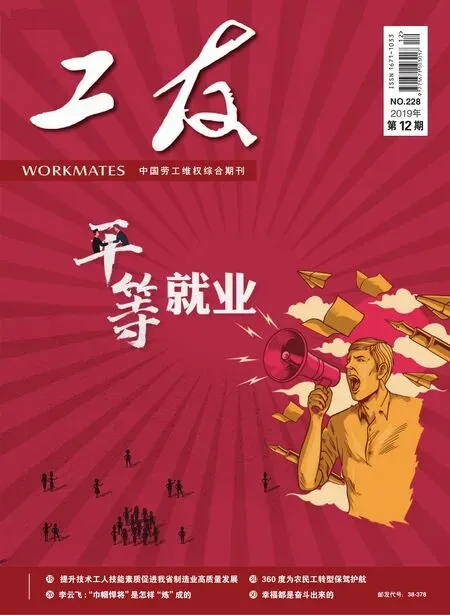就業歧視的認定與責任承擔
文_肖雪
關于就業歧視,國內現行法律法規對其僅作原則性規定,未明確具體的認定標準。
《1958年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第一條規定,“歧視”是指“基于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見解、民族血統或社會出身等原因,具有取消或損害就業或職業機會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區別、排斥或優惠”,以及“有關會員國經與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如存在此種組織)以及其他適當機構協商后可能確定的、具有取消或損害就業或職業機會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其他此種區別、排斥或優惠”。但“對一項特定職業基于其內在需要的任何區別、排斥或優惠不應視為歧視”。
歧視事由一般由法律明確規定。根據《勞動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以及《就業促進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等規定,歧視事由限于勞動者的性別、民族、種族、殘疾、戶籍、年齡、宗教信仰、既往刑罰經歷、傳染病病原攜帶。
(一)歧視事由
從以下幾則案例可以看出,法院通常基于法定的歧視事由,直接援引禁止歧視乙肝患者等法律條款,判決用人單位構成就業歧視:
① 年齡歧視——陳國祥與廣州市運輸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一般人格權糾紛案
萊蕪市萊城區人民法院認為,用人單位的用人自主權應當依法行使,不得侵犯勞動者的平等就業權。公安部已從駕駛人的年齡條件、身體條件、駕駛技能等各方面對各類準駕車型駕駛證的申領以及各類車型駕駛證的審驗管理,進行了綜合考量并作出了規定,而被告運輸公司自行設定的高于部門規章規定的且與個人能力無關的年齡標準顯然超出了依法行使用人自主權的界限,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業權。
法院判決:一、被告廣州市運輸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應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向原告陳國祥口頭賠禮道歉;二、被告廣州市運輸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應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向原告陳國祥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3000元。
②疾病歧視——衣守峰與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一般人格權糾紛案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中,被告沒有在招聘時告知患有“肺纖維化病灶”不符合入職條件,在報到入職時被告以原告患有“肺纖維化病灶”拒絕錄用原告屬于就業歧視,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業權,被告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對原告為應聘被告支付的交通費、學歷學位認證費、住宿費以及放棄其它工作的務工損失,被告應當予以賠償。
法院判決:一、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衣守峰誤工費、學歷認證費等共計7880元;二、駁回衣守峰的其它訴訟請求。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以維持。
③ 性別歧視——梁海媚與廣東惠食佳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廣州市越秀區名豪軒魚翅海鮮大酒樓人格權糾紛案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規定,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權利。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第三條之規定,勞動者依法享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視。惠食佳公司、名豪軒酒樓僅因招聘者性別而產生的區別、限制以及排斥的行為不具有合法以及合理性,損害了女性應聘者的就業平等權,應構成就業歧視中的性別歧視。
法院判決:一、惠食佳公司、名豪軒酒樓在判決生效之日起7日內連帶向梁海媚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二、惠食佳公司、名豪軒酒樓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梁海媚作出書面賠禮道歉(致歉內容須由法院審定,如未在指定的期間內履行,法院將在廣州地區公開發行的報紙刊登判決書主要內容)。
(二)免責事由
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因用人單位正當經營需要等理由,選擇性地錄用職工,而不構成就業歧視:
① 用人單位正當經營需要——沈如龍與廣東綠由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勞動爭議糾紛案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法律并不禁止用人單位根據自身經營的特點,對某些特定崗位設置相應的用工條件。被上訴人綠由公司并未因為上訴人廣州方言不通暢、不熟悉而不錄用上訴人。實際上,被上訴人亦為上訴人提供了相應的工作崗位。被上訴人之所以解除與上訴人的勞動關系,是基于上訴人廣州方言不熟悉,而導致溝通不通暢,影響了正常的工作。因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存在就業歧視,要求上訴人賠償的理由,依據不充分,本院亦不予支持。
② 特殊崗位資格需求——楊旭達不服新鄉市紅旗區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民事裁定案
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就業歧視是指沒有法律上的合法目的、原因和工作上的關聯性而是基于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原因,采取區別排斥或者給予優惠等任何違反平等權的措施侵害勞動者勞動權的行為。《人民警察政審考核程序及內容》規定,“無尚未查清的違法犯罪嫌疑”為政審考核的內容之一。本案中,公安機關根據其單位的特殊性質按照《人民警察政審考核程序及內容》規定,將“無尚未查清的違法犯罪嫌疑”作為招錄條件不屬于就業歧視。
③ 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免責事由——
如根據《就業促進法》第三十條、《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禁止經醫學鑒定為傳染病病原攜帶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傳染嫌疑前,從事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禁止從事的易使傳染病擴散的工作,以及禁止婦女從事不適合其從事的工作和勞動的,不屬于就業歧視。
(三)就業歧視的責任承擔
《就業促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實施就業歧視的,勞動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就業歧視糾紛,勞動者可不經仲裁,直接向法院起訴,并可要求用人單位承擔賠禮道歉、賠償損失、賠償精神撫慰金等民事責任。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系副教授沈建峰說,由于《就業促進法》沒有明確如何具體認定就業歧視行為,且沒有規定勞動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后在實體法上的救濟方式,以致于發生歧視后,司法機關往往需要參引《侵權責任法》以及《民法通則》的規定來處理。而這兩部法律本身并沒有明確就業歧視的責任構成規則,再加上就業歧視本身舉證的困難,這些因素共同導致就業歧視禁止規則落實得非常有限。
沈建峰說,就業歧視的損害包括精神損害、求職成本和失去就業機會的損失,但這些在法律上怎樣進行填補,需要進一步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