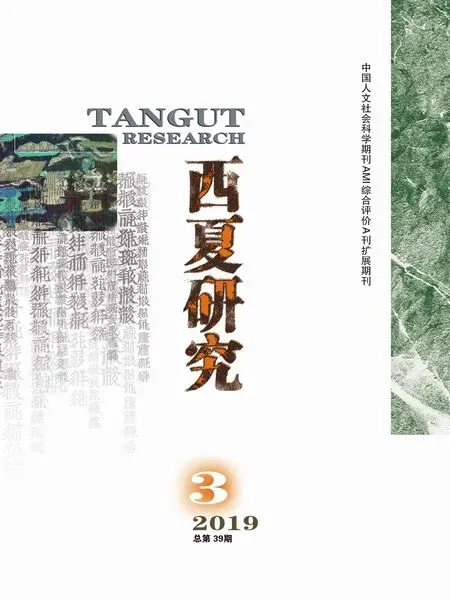民國時期的兩部西夏史著:《西夏紀》與《〈宋史·夏國傳〉集注》
□王軍輝 楊 浣
在可資參考的西夏漢文文獻中,傳統史志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00年以來這一研究領域取得了重要進展,胡玉冰的《漢文西夏文獻叢考》(2002)和《傳統典籍中漢文西夏文獻研究》(2007)可視為其代表性成果,兩書全面系統地梳理和研究了民國以前涉及西夏的各種漢文著作。在此基礎上,本文擬對學界關注較少的民國時期兩部漢文西夏史著作——《西夏紀》與《〈宋史·夏國傳〉集注》進行考察。不當之處,尚乞方家指正。
一、《西夏紀》
《西夏紀》是民國時期一部西夏專史,作者為戴錫章。戴錫章(1868—1933),字海珊,四川夔州府開縣漢豐鎮人,近代著名史學家。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科鄉試舉人,次年赴京會試期間積極參與“公車上書”,支持“維新變法”,曾任法部主事外員郎、地方初級檢察官等職。1917年,戴錫章受聘為《清史稿》纂修,1928年完稿后返回故鄉開縣。1932年春,戴錫章領銜編修《開縣縣志》,不久病故,享壽六十五。戴錫章湛深史學,文章爾雅,留下《〈西夏紀〉凡例》(抄本)、《西夏紀》二十八卷、《西夏叢刊》十余卷(未刊)、《〈清史稿〉邦交志》十余卷等著作。戴錫章性清簡無他嗜,唯好收藏古書,刊有《虞文靖公〈道園全集〉》、《道園詩遺稿》、《道園學古錄》等書籍。
《西夏紀》卷首前有六篇書序,作者分別是趙爾巽、柯劭忞、王樹楠、胡玉縉、王秉恩和戴錫章本人,內容或為書籍評點與議論,或為撰寫經歷與緣起。緊隨其后的是征引書目,列舉三百一十一種。全書共分二十九卷,正文采用編年綱目體撰寫,“每條仿宋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例,各注書目,雖乖史法,為便省閱,亦征信之意也。至所引書,有經三家綴緝、聯貫而仍注以原書者,以三家雖異流而同出一源”[1]17。《西夏紀》卷首略言西夏先世史事,卷一至卷二十八起于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李繼遷反宋,迄于南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西夏滅亡,記載了西夏興衰首尾246年的歷史。其中,卷一至卷三記載夏太祖繼遷朝史事,卷四至卷五記載夏太宗德明朝史事,卷六至卷十一記載夏景宗元昊朝史事,卷十二至卷十三記載夏毅宗諒祚朝史事,卷十四至卷十八記載夏惠宗秉常朝史事,卷十九至卷二十三記載夏崇宗乾順朝史事,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五記載夏仁宗仁孝朝史事,卷二十六記載夏桓宗純祐、夏襄宗安全朝史事,卷二十七記載夏神宗遵頊朝史事,卷二十八記載夏獻宗德旺與末主朝史事。書尾有跋一篇,記錄夏史今鑒之題旨。
據戴錫章自言,《西夏紀》始撰于宣統三年(1911),“中經國變旋里,訖于再亂復出,往來京津,參考各書,多得之各圖書館及各藏書家,或廠肆書賈及海外之所得,又兩經寒暑,未嘗或間”[2],“手自輯錄,稿數四易”。1917年“凡六易稿矣”,在已頗具規模的基礎上手訂《西夏紀》與《西夏叢刊》的共同《凡例》[2]。“是書初以陳書(陳昆《西夏事略》)為主,輔以張(張鑒《西夏紀事本末》)、吳(吳廣成《西夏書事》)二氏,用低一格雙行,以示區別。質之膠西柯鳳蓀先生,先生頗稱善。既而,先生以張、吳書中亦有大事,當頂格單行大書者,因屈于陳氏,列置低格,不無稍欠。謂不如獨自成書,而以陳書另行,既靡喧賓奪主之嫌,并免削足適履之病,因特謹從用志教益。”[1]1“7因連復仿前、后《漢紀》之例,更名曰《西夏紀》。”[2]直到1924年,《西夏紀》一書才最終完成,前后歷時13 載,“然欲以為紀傳,仍未能也”[1]17。
戴錫章編撰《西夏紀》的緣起有三:一是補斷代史闕。作者有感于“西夏聲明文物,誠不能與宋匹,然觀其制國書、厘官制、定新律、興漢學、立養賢務、置博士弟子員、尊孔子為文宣帝,彬彬乎質有其文,固未嘗不可與遼、金比烈!乃遼、金有史,而西夏無史,何也?”[1]17為西夏著史,戴錫章之意在還其歷史公道。王秉恩曾評價道:“吾鄉戴海珊比部,奮然撰《西夏紀》二十八卷,《叢刊》十余卷,征集書三百余種,殫十余年精力而成。西夏一國事實,粲然具備,纂敘述大旨,詳載序例。”[1]13二是以史為鏡鑒。戴錫章認為“西夏以河內、外數州之地,而能抗三大國,搘捂至二百年之久”的內在原因,對于“地大于西夏數倍,人民眾于西夏數十倍;而一經變亂,內憂外患,隨以俱來,如火之燎原,不能撲滅;又從而煬之,以至于不可救;內不能保境息民,外不能折沖御侮;徒為內哄私斗,以自逞其恣睢;傲睨之雄,而不知螳螂、黃雀之喻之行將自及”[1]678的近代中國振衰起蔽具有警示和鏡鑒作用。三是糾前賢之疏。《西夏事略》、《西夏紀事本末》、《西夏書事》等史著雖有成績,但所采史料終究有限,“中秘之藏,仍未窺也”。戴錫章“因亂辟地京師,承乏史館,適值圖書館啟,而宋、元善本及《四庫全書》本均燦然在目,因得次第縱觀,左右采獲,津逮綆汲,時有獲于數子之外,則時與地之幸也。……余從數百年后,遠溯數百年前,而成此書。以三家為先河,合百氏為一冶,不復區為誰某,而各溯所自出。上自朝章、國典,下至小說、短書,茍匪不經,皆在所錄。更于《西夏紀》外,成《叢刊》十余卷,西夏一代事實略具矣”[1]16-17。
與陳昆《西夏事略》、張鑒《西夏紀事本末》、吳廣成《西夏書事》等舊史相比,《西夏紀》因為“書最晚成”,所以“博采旁搜,頗為宏富”,“差為詳備”[3]。具體表現在:一是紀年界定“頗費參考”,以宋紀年為標準,確定和校正遼、夏、金紀年和改元。二是每條“各注書目,雖乖史法,為便省閱,亦征信之意也”。“原書(陳昆《西夏事略》)先以張氏鑒《西夏紀事本末》、吳氏廣成《西夏書事》對校,故征引獨夥,然張氏、吳氏書不注所出,此則一一標明,惟二氏所引何書,有經二氏刪節聯貫,較原書便易者,即以二氏書標目,不復測原所出,用省繁縟。”[2]“凡正史之舜訛,四家之疏漏,皆一一參稽補正,燦然成一代信史,其用力可謂勤矣。”[1]7三是史料引述“寧從博,不從約”。“原書(陳昆《西夏事略》)征引各書,多就正史要刪,而旁及別史、野史及各家文集,義取謹嚴。此則專于別史、野史及諸文集雜錄,凡有一字一句關涉西夏者,皆綴輯焉。蓋以西夏向無專書,夏文散佚,零縑斷簡,彌足多珍,故寧從博,不從約。駁雜之譏,知所不免。”四是引用一絲不茍。“宋、遼、金三史抵牾處甚多,今用《資治通鑒考異》之例,以按語疏證之,于原書(陳昆《西夏事略》)不更易一字,不敢僭也。”五是排版嚴謹。“原書(陳昆《西夏事略》)用單行大字,增輯用雙行小字,或接寫,或另行低格,曾用按字,以示區別,其原書有小注者,冠以原注二字。”[2]
然而瑜中有瑕,該書也有若干美中不足之處。一是遷就正統,有乖史法。“《西夏紀》,既名從主人而稱之為紀,無論紀字于史載者若何,而以宋紀年未免不充其類。”[4]二是書為編年,“實不能表現西夏文化之全體,今日而欲為西夏史,必當改變體例,以分析綜核其文化為歸”[3]。三是“是書初擬全注原書,繼因見聞有限,未能悉考所出,即以三家書標目,亦譚鐘麟《通鑒長編拾補》稱《西夏書事》之例”[1]17。“引用史料過窄,表現在大量引用《西夏書事》的材料,因《書事》未注明出處,戴氏所注明部分的可靠程度也受到影響;大量引用《長編》是其優點,但因《長編》只記北宋事,且存本有散佚,致使戴氏書在仁孝朝后史事極為簡略。”[1]2四是“戴氏囿于自身的條件,未諳西夏文字,不能采用西夏的原始數據,致使本書述及西夏內部情況語焉不詳”[1]2。
《西夏紀》成書后廣受政、學兩界贊譽,1924年教育部的評語是:“西夏建國二百余年,文獻無征。近世有張氏鑒之《西夏紀事本末》、吳氏廣成之《西夏書事》、周氏春之《西夏書》,皆不免于疏漏。作者因其鄉人陳氏昆之《西夏事略》,重加改訂,成此巨制,引書至三百余種之多,考核精詳,尤為前人所不及,真名山之盛業也。”[1]17《清史稿》總撰趙爾巽評曰:“同館戴君海珊,以《西夏紀》廿八卷(附叢刊若干卷)乞序于余。受而讀之,《紀》蓋本張氏鑒《西夏紀事本末》、吳氏廣成《西夏書事》、陳氏昆《西夏事略》而增輯之者,益以叢刊搜獵之廣,使一代得失之林昭然可睹,匪特有功于夏臺,抑亦有國者之殷鑒也。”[1]17《新元史》作者柯劭忞評曰:“開縣戴海珊比部湛深史學,文章爾雅,薈萃諸家,重加訂補為《西夏紀》廿八卷(附以《西夏叢刊》十余卷)。用力十年,而后成書。義例之嚴,援據之博,考核之精,皆為前人所不及。”[1]1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作者胡玉縉評曰:“友人戴君海珊,乃重為排比,各注其所出,復搜討群籍,益以百數十種,恐其喧賓奪主,因以直敘夏事者入《西夏紀》,以還體例之嚴;以旁及夏事者入見聞之助。考訂異同,補查漏,倍極勤奮,此書出而周、張、吳、陳諸書,雖以為皆可廢焉可也。”[1]17盡管不乏同館與至友的唱和溢美之偏向,但是戴錫章的《西夏紀》及其《西夏叢刊》在西夏史學史、西夏文獻史上無疑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西夏紀》問世后,由于它的編輯內容和編纂體例遠勝出《西夏事略》,所以《西夏紀》漸行于世,而《西夏事略》漸漸失傳”[1]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
二、《〈宋史·夏國傳〉集注》
《〈宋史·夏國傳〉集注》(簡稱《集注》)共計十四卷,另有系表一卷。羅福萇撰寫未成而逝,遺稿一卷,刊于1932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 卷第3 號《西夏文專號》。羅福萇之弟羅福頤續補,析為十四卷,石印本一函八冊,收入1937年自編叢書《待時軒叢刊六種》。
羅福萇(1895—1921),字君楚,羅振玉第三子,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蘇淮安,古文字學家、西夏學專家。“君幼而通敏,年十歲,能讀父書。其于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強記縣解,蓋天授也。年未冠,既博通遠西諸國文學,于法朗西、日耳曼語,所造尤深。繼乃治東方諸國古文字學。”[6]“光緒末,俄人某于甘州古塔中,得西夏譯經數篋,中有漢夏對譯字書,名《掌中珠》者。君楚得其影本數葉,以讀西夏石刻《感通塔記》,及法屬河內所藏西夏文《法華經》殘卷,旁通四達,遂通其讀,成《西夏國書略說》一卷。又嘗從日本槲教授亮受梵文學,二年而升其堂,凡日本所傳中土古梵學書,若梁代真諦《翻梵語》、唐代義凈《梵唐千字文》以下若干種,一一為之敘錄,奧博精審,簿錄家所未有也。君楚體素弱,重以力學,年二十二而病。瘍生于胸,仍歲不療,二十六而夭,時辛酉(1921)九月也。”[6]“其學于經史古義無不通,絕代方言若西夏書、突厥書、回鶻書、梵天今古文,一能究其本末流變,將大有所著述,發明中國古書,補歐洲學者之闕失,觀其通,規其全者。”[7]220“所著書多未就,以歐文記者,尤叢雜不可理。今可寫定者,《夢軒瑣錄》三卷,即古梵學書序錄,及攻梵語之作也;《西夏國書略說》一卷;《宋史·西夏傳》注一卷;譯沙畹、伯希和二氏所注《摩尼教經》一卷;《古外國傳記輯存》一卷;《大唐西域記》所載《伽藍名目表》一卷;《〈敦煌古寫經〉原跋錄存》一卷;《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一卷;《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一卷。”[6]
羅福頤(1905—1981),字子期,羅振玉第五子,祖籍浙江上虞,生于上海,古文字學家、金石學家、西夏學專家,別號梓溪、紫溪,因晚年背微曲,自戲號僂翁,室名待時軒、溫故居。羅福頤自幼秉承家學,諳習古器物、文字之學。1939年在沈陽博物館工作,抗戰勝利后遷居北京,任職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1949年以來,羅福頤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研究所、革大政治研究院、文化部文物處、故宮博物館任研究員,兼任國家文物局咨詢委員會委員,為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考古學會、西泠印社等學術團體理事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研究會會員。羅福頤畢生勤奮治學,于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古璽印之形制與文字,戰國、兩漢竹簡,古代石刻墓志、敦煌經卷、古代醫書、夏遼金元少數民族、明清檔案等皆有深入研究,留下著述263 種,其中專著126 種,文章137 篇。《漢印文字征》、《古璽文編》、《古璽匯編》、《古璽印概論》、《印章節概述》(合著)等論著和文章考證嚴謹,對篆刻藝術影響極大。在西夏研究方面,羅福頤有《〈宋史·夏國傳〉集注附系表》、《西夏文存》、《西夏官印匯存》等研究論著[8]。
《〈宋史·夏國傳〉集注》共十四卷,另有系表一卷。正文前有《序》一篇,《〈集注〉引用書目》一篇。正文采用紀傳體敘事,卷一至卷十四分別為《彝興、克睿、繼筠、繼捧》、《太祖繼遷》、《太宗德明》、《景宗元昊(上)》、《景宗元昊(中)》、《景宗元昊(下)》、《毅宗諒祚》、《惠宗秉常(上)》、《惠宗秉常(中)》、《惠宗秉常(下)》、《崇宗乾順(上)》、《崇宗乾順(下)》、《仁宗仁孝》、《桓宗純佑、襄宗安全、神宗遵頊、獻宗德旺、末帝》,正文后附有《西夏世系表》,篇末為《跋》。根據有年可稽、有事可附、隨注正文之下以便省覽的原則,搜討群籍,重為排比,各注其所出。
由羅福頤書序可知,1911年其兄福萇隨父旅居日本時因“治西夏文字之學”始做《〈宋史·夏國傳〉集注》。書稿“以《宋史傳》為經,旁搜別史及他載籍之記西夏事者,采以為注。略仿裴氏之注《三國志》例,不厭其詳,并記其所從出,俾讀者不迷所自”。然而,“成書未及五卷以病中輟”,1921年“屬稿未半,仲兄不祿”。十年后,因“友人索兄遺著,擬為刊行。君美伯兄(羅福成)乃取此注錄副貽之。頤惜其未為完書也,不揆簡陋,欲續兄之志。乃以壬申(1932)仲春,一遵舊例,從事賡續,竭四月,力成書十四卷,前五卷有遺佚者并為補之”[9]2。
夏臺史跡賴宋、遼、金三史而傳之,自《〈宋史·夏國傳〉集注》而信之。何也?首先,明史文之來源。《集注》之前,西夏專書“凡五六家,然多不得傳者。清浦吳氏廣成《西夏書事》,烏程張氏《西夏紀事本末》,近開縣戴氏錫章《西夏紀》三書,雜采前籍,吳、張二家均不注所出,戴書注所出矣,而一事兼諸書復增損其文,甲乙混糅,讀者莫能辨別”。《集注》伊始,開列書目四十八種,上自宋元傳世文獻,下至出土西夏文書,咸不齊備;正文諸行,凡可舉證者,無不旁征博引,并記其所從出,俾讀者不迷所自。其次,補史事之細闕。如元昊之死,舉《任顓墓志》發宋夏外交折沖之覆;如西夏“設官之制,多與宋同”,則舉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人事下》所載“中書、樞密、經略司、正統司、統軍司、殿前司、御史、皇城司、宣徽、三司、內宿司、巡檢司、工院、馬院、陳告司、磨勘司、審刑司、大恒歷院、農田司、群牧司、受納司、閤門司、監軍司、州主、通判、正聽、承旨、都案案頭、司吏都監”為證,確鑿無疑。第三,究盛衰之事理。《集注》雖為注釋之作,然與《胡注通鑒表微》一樣,其筆墨盡處乃民族復興之寄托,正如尾跋所嘆“然其之亡也,不亡于中原大定之日,而亡于天水南渡之后;不亡于數世構兵之宋,而亡于初造未成之元。所謂禍敗之來,蓋亦多故,有國有家者,其謁鑒諸”[9]435。
當然,囿于時代和傳統史學,《〈宋史·夏國傳〉集注》也有缺點,如內容上重政治、軍事,輕經濟、文化,征引不得不借重《西夏書事》和《西夏紀事本末》等二手史源。于此,作者也很坦然,自言:“聞見有限,掛漏茲多,董正之事,期之異日!”[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