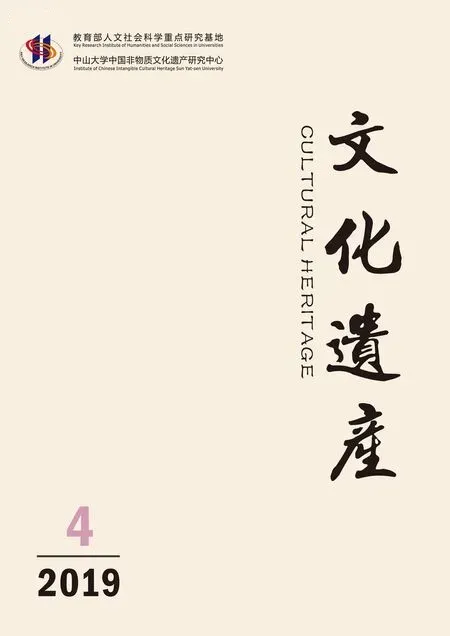李漁《閑情偶寄》美學的當代啟示
肖伊谷
李漁(1611-1680)是明末清初的戲劇家、生活美學家,他的《閑情偶寄》是一部關于戲曲藝術以及生活美學的作品,作品一改中國傳統的題材與文筆,將生活“閑情”的瑣碎搬進書本,雖然李漁在他所處的時代曾一度被評價為“趣味低俗”,但仍然無法撼動這部作品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到二十世紀初,周作人、林語堂等人開始推崇晚明之后的文學作品,對李漁的生活美學態(tài)度非常贊賞,認為他是一個極具現代意識的古代文人。如今,在經濟高速運轉的社會,人們對提高“生活美學”素養(yǎng)的需求也越來越大。
《閑情偶寄》這部作品,不僅體現了李漁對戲曲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揚光大,更在早期為人們提供了日常生活和世俗風儀的圖像:從亭臺樓閣、庭院門窗的布局,到花卉種植、家具陳設;從女子的修容體態(tài)、服飾,到飲食頤養(yǎng),都可以深刻認識到李漁廣泛的藝術領悟和無限的生活樂趣,而僅是李漁對生存環(huán)境的詩意塑造就已經精彩萬千。《閑情偶寄》一方面著眼于高雅的藝術蘊涵、人生情趣,即所謂的“才人韻士”的審美情趣;另一方面,李漁又執(zhí)著于世俗生活實踐,將審美精神注入日常生活,塑造了一種既實用,又充滿逸趣的生存環(huán)境——即“生活藝術化”。在李漁的作品中,文學、戲曲不再僅僅是文人抒情言志的工具,也不再是文人們勸俗化民的意識表達,而是充滿樂趣、娛樂受眾的消費產品。李漁生活美學思想的起點是對死亡問題的思考,他認為人終有一死,因此要及時行樂。行樂之關鍵在于有行樂之心,這是進行生活審美應持有的主觀態(tài)度,是其必要前提。[注]馬草:《李漁生活美學思想研究》,《美育學刊》2015年第6期。李漁的創(chuàng)作與其成長背景息息相關,他“及時行樂”的哲學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來自于他所身處的明末清初時代,在變幻多端的社會與起伏的人生經歷中,他學會了與困境和解。他的美學思想理念經過實踐的反復驗證、提煉,在眾多古代文學作品中彰顯獨特。
李漁著作《閑情偶寄》的美學啟示,在某種程度上,對我們當代文化藝術的普及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通過李漁的美學理念,我們能了解不同時代背景下,生活美學以何種方式觀照大眾以及市場,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審美以及當今的文化產業(yè)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 日常生活審美化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生活和藝術逐漸向“審美泛化”演進,有關生活美學的學術探討和實踐便呈現日益繁榮的態(tài)勢。
生活美學離不開文化的影響,現今大致可以將文化分為兩種情況:首先是“高雅文化”,是以知識分子以及文化人為主要受眾、包含社會批判或美學探索的文化形態(tài)。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創(chuàng)作高雅文化作品時,多以強烈的責任感關注社會問題,體現精英群體對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懷和憂思。高雅文化的特點具有豐富內涵、高雅審美趣味以及小眾性。與之相對的,便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工業(yè)化與都市化以來運用大眾傳播媒介傳輸的、注重滿足普通民眾日常通俗趣味的文化形態(tài)。大眾文化的特點是信息龐雜、流行化、模式化,且具娛樂性。
李漁在文化上屬于士大夫精英階層,但在經濟方面屬于市民階層。李漁身份的特殊性,在他的藝術實踐和著作中都有所體現,他擅長將士大夫精英藝術轉變?yōu)槭忻裎幕袌鲋械母哐潘囆g,并從生活、文學和藝術各方面提升市民的品位。李漁在創(chuàng)作理念方面,對高雅文化和民眾文化的交融與突破非常有經驗,所以娛樂性是它最基本的屬性。李漁作品和他的成長背景、人生閱歷、生活方式息息相關,他的創(chuàng)作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學里是一個非常另類的存在。首先,他的文學藝術作品始終以“娛樂趣味”作為重要的參考標準之一,在《閑情偶寄》中,李漁談到“填詞之設,專為登場。”[注](清)李漁:《閑情偶寄》,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3年,第55頁。這句話就足以看出,他將戲劇的“上演”視為創(chuàng)作的首要目標。相比之下,與李漁同時代的許多文學藝術作品都過多地用文人的標準來創(chuàng)作,而并非將受眾的感受融入創(chuàng)作。其次,李漁的受眾范圍非常廣,有達官貴人也有市井平民,男女老少、婦孺皆知,不管任何層次的受眾,他希望能將他們統統吸引到自己“閑情世界”中。因此,他的作品生活性與藝術性兼?zhèn)洌Z言直白并富有生趣。再次,李漁的審美與創(chuàng)作代表了當時的士大夫精英階層,所以他的作品不僅受普通市民的歡迎,同時他也非常注意用自己的才智將精英文化與市民文化相融合,產生出富有新意的創(chuàng)作,也吸引了文人雅士的眼球。他指出,新穎是文學作品非常重要的一個創(chuàng)作目標,“新也,天下事物之美稱也。而文章一道,較之他物,尤加倍焉。……至于填詞一道,較之詩賦古文,又加倍焉。”[注](清)李漁:《閑情偶寄》,第8頁。同時,李漁主張雅致之旨是生活審美的價值標準,其源自于日常生活形式的精致化。雅致具體表現為新異,但自然是李漁生活美學思想的最高追求。[注]馬草:《李漁生活美學思想研究》,《美育學刊》2015年第6期。新奇趣味,一直是李漁所尊崇的創(chuàng)作之道,作品的結構、選材、語言都非常具有娛樂性,這也是李漁區(qū)別于同時代文人的一個最大特征。
李漁出生于地主家庭,年少時優(yōu)渥的家庭環(huán)境使其受到良好教育和擁有開闊的視野,本可以考科舉功成名就,但家道中落、考科舉失敗,命運驅使他走向了另一個方向,成為了一個文化商人。所以李漁作品中的娛樂性,與一般的通俗作品相比更具有“雅俗共賞”的意味。他的創(chuàng)作技巧極富藝術性,同時,迫于生計,他又時刻能照顧觀眾與市場的品味,兼具了文人、商人、藝術家等多重身份,并且他也將這幾種身份很好地融匯在一起,找到之間的平衡點以及融合狀態(tài)。從傳統的文學觀念來看,李漁并不算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與他同時代的眾多作者比較,他屬于一個另類。他放棄了功名仕途的道路,在自己搭建的閑情“園林”中悉心經營,將士大夫精英階層的文化藝術用通俗方式傳達給大眾,也讓大眾通過趣味化的形式接收到了高品位的生活方式。在物質和精神領域都為后人留下了不少的財富。李漁的創(chuàng)作既代表了精英階層的文化審美,也貼近了市民階層的精神需求。他演繹了文化人的使命:引領大眾更加貼近真理和善于思考,以及提升普通市民的生活品位。
在如今的文化產業(yè)領域,打造IP已經是一種常見現象,它的出現與其背后的產業(yè)發(fā)展與運作機制有關,也離不開文化的資本化和產業(yè)化。[注]IP全稱是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指“知識產權”。例如創(chuàng)造發(fā)明、文學和藝術作品,以及在商業(yè)中使用的標志、名稱、圖像以及外觀設計,都可被認為是某一個人或組織所擁有的知識產權。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中國需要建立文化自信,要從文化大國走向文化強國。在其號召下,如今越來越多傳統文化的瑰寶嘗試融入影視、娛樂等文化多邊產業(yè)中,如北京故宮的網絡營銷案例,近年來老樹發(fā)新枝,“故宮IP”取得極大的市場成功,是傳統文化IP產業(yè)化的成功案例。不過在清代,早有一位“文化商人”具備超前的現代IP意識,便是李漁。在研究李漁的創(chuàng)作以及他的文化產業(yè)經營萌芽意識時,應思考在當下IP思維對文化產業(yè)的重要性,如何創(chuàng)作好的作品獲得市場認同,激活文化藝術市場的創(chuàng)意性氛圍,同時也對消費社會中的藝術功利化、產業(yè)化現象提出深層的思考。
縱觀近幾年,我國傳統文化創(chuàng)新發(fā)展日益增強,人們的文化意識也越來越強,人們對產品的功能消費開始轉向符號消費。北京故宮IP已經成為當下文化產業(yè)營銷的經典優(yōu)秀案例。[注]北京故宮IP近年來主要區(qū)別于故宮長久以來的莊嚴肅穆形象的趣味皇家文化創(chuàng)意產品和創(chuàng)意形象符號活躍于大眾視野范圍內,并圍繞故宮文化內核及文化符號通過產業(yè)鏈的橫向延伸向多個領域擴張。
二、 生活美學的商業(yè)化展現
明末清初,商品經濟發(fā)展、思想解放,從社會面貌、價值觀念以及當時的文藝創(chuàng)作,都能夠看到那個時代的變化。文人士大夫逐漸擺脫了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束縛,他們開始追求個人價值和個性解放。在此領域,李漁表現得更加突出,“新穎、靈活、獨創(chuàng)”可謂李漁作品以及審美風格的主要特點。
三百多年前的李漁就已經具備了生活美學的前瞻性與現代意識。在中國文化史上,明末清初的李漁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文人。他在大俗大雅之間來去自如,在文學與商業(yè)之間游走,在藝術生活與市井民生中尋找平衡。作為生活美學家的鼻祖,李漁不僅在其作品《閑情偶寄》中記敘了令人心馳神往的生活方式,以閑適文人的筆觸記載生活的格調,將人生過成藝術的旅程。
李漁不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也堪稱“寫作產業(yè)化”先驅以及具有IP思維的文化商人,其創(chuàng)作無一不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他在《閑情偶記》中曾經寫到,即使如《牡丹亭》、《邯鄲記》這樣膾炙人口的佳作,也是“得以偶登于場者,皆才人僥幸之事,非文至必傳之常理也。”[注](清)李漁:《閑情偶寄》,第55頁。即便如湯顯祖、吳炳這樣的大戲劇家,如果他們的作品沒有在市場上流傳,也終歸會被歷史的風塵所埋沒。甚至可以說,沒有票房,就沒有影響力。[注]李向民:《李漁:炒作IP的鼻祖》,《董事會》2017年第5期。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應。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所決定。許多文人走上了經商道路,在十六、十七世紀表現得最為活躍,出現了偏離傳統價值取向的“儒商”邊緣群體和“市民文人”的準職業(yè)群體。李漁的創(chuàng)作理念中,既有自身的文藝訴求,也體現了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李漁所在的時代,商品經濟異常活躍,具體表現為商品的豐盛、流通的便利以及消費的繁榮。
即便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文化始終與政治、經濟保持緊密的聯系。在當今社會,藝術家的生存也同樣受到考驗。文人、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具有商業(yè)色彩相當普遍。比如當下文化市場,培訓機構蓬勃發(fā)展。如古代文人也有開設書肆、刻坊,經營戲班等以生計為目的的活動。文人身處社會,日常生活離不開世俗,其文藝創(chuàng)作絕大多數都具有濃郁的市井色彩。
從文學到戲劇,從居室到庭園,從室內裝飾到界壁分隔,從婦女梳妝、美容、施粉黛到烹調藝術,還有富人和窮人尋求樂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悶的途徑,性生活的節(jié)制,疾病的防治等等。《閑情偶寄》看似龐雜,實則以“生活”為主題一以貫之。李漁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戲曲以及對生活美學的見解,盡管在清代無法同當今互聯網時代一樣,但已具備如今IP意識的雛形,其個人風格和對藝術風格的獨特理解,可謂是那個時代一個鮮明的IP。
在不同時空下,對文化產業(yè)的IP創(chuàng)造來說,百老匯戲劇是不可忽略的經典模式,在全球巡回上演幾十年后,每次演出還像首演時那樣火爆。每一部經典戲劇都有自己的獨立劇院,一條百老匯大街坐落著各種不同的戲劇劇院,每個劇院每天不同時段都會重復上演,整個劇院的裝修風格以及購物商店都是專屬于這部戲劇的風格。更有近幾年大熱的“浸沒式戲劇”,將餐飲、體驗式觀劇、購物商店結合在一起,不僅讓觀眾深刻感觸戲劇的文化內涵,更讓觀眾享受在其打造的娛樂氛圍中。細看美國每部經典劇目,多有深刻的文化核心內涵,以及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優(yōu)質作品內容。打造一種“沉浸式”的文化消費體驗,無論是企業(yè)品牌還是文學藝術作品,在商業(yè)化氛圍濃厚的今天,對于吸引大眾都十分重要,與此同時,也要保證傳播內容的精良。例如美國商業(yè)社會的成功案例:迪士尼樂園、環(huán)球影城,借助一部又一部經典電影向世人呈現主題公園、酒店、度假村等一系列商業(yè)模式,每年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前往消費。主題公園的游樂設施、商店的背景環(huán)境多勾人心魂,引人入勝。
如今,IP由傳統走向開放,包括游戲、著作、影視、動漫、舞臺劇、表情包、音樂等諸多內容。IP主題展讓消費者與購物中心形成紐帶關系,是商業(yè)營銷的重要方向之一。例如,我們在全球各大著名博物館的商品店經常見到知名藝術品的周邊產品。在1871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就設立了博物館商店,通過觀眾的消費,博物館藝術品所承載的思想、價值觀、傳遞的精神融入觀眾的生活。
究其根本,IP向受眾傳遞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體驗,當中是令人沉浸的完整世界觀,抑或是創(chuàng)作者獨特與個性的文藝表達。于李漁而言,其生活情趣為后世帶來與眾不同的審美視角,其作品蘊含與眾不同的情緒與情感表達。這離不開他具備一定啟蒙性的IP意識。當下已是一個“內容為王”的時代。品牌與IP最大的不同在于:品牌提供的是功能屬性,IP提供的是情感寄托。例如百老匯十年如一日上演的音樂劇《獅子王》已經俘獲了全球無數家庭和兒童的心,可謂是好幾代人童年的回憶,這樣經典的內容生產出的影視、戲劇藝術形式,同時也帶動了《獅子王》內容的產業(yè)鏈。
當今在中國,有關部門也開始注重文化輸出的重要性。影視劇在IP文化盛行中促使了傳統文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例如,熱播電視劇《延禧攻略》制作精良細致,不僅參考了各種史料古畫,極盡所能做到經得住推敲考證,更融入了刺繡、緙絲、絨花等多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元素。電視劇也還原了2000多年來的歷史,從學術研究和工藝實踐上都可觀見非遺傳承人的心血,不僅使影視藝術作品更加優(yōu)質,同時也將中國傳統藝術通過大眾媒體普及,在帶動文化產業(yè)發(fā)展的同時也完成了將民族精神文化精髓向大眾傳播的使命。
還有許多將高雅文化、民族傳統文化向民眾普及的經典案例。例如《朗讀者》《曉說》《一本好書》。不論是公眾號還是影視節(jié)目,這些IP都有一個特點,創(chuàng)始人或者博主都是積累深厚的知識分子,憑借個人品牌及人格魅力,打造觀賞性高的內容,將高雅文化更好傳播給大眾,達到寓教于樂、雅俗共賞的效果。
總而言之,在當今的文化藝術領域,文人走上經商道路、文化產業(yè)等成功案例,與李漁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秉承的“雅俗共賞”的原則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那個商品經濟萌芽的特殊時期,一位特立獨行的文人憑借自己獨特的審美品味和生活情趣,就已經實現了高雅文化藝術與市民階層文化娛樂之間的平衡點,例如他的戲曲特點表現為文采性與通俗性的并重,并且統一貫穿于語言的曲詞、賓白、科諢這個三要素當中。在當今,做內容的“儒商”都在將知識、文化、藝術用一種娛樂化或者更接地氣的方式展現,以獲得更多的人支持,實現“流量變現”。[注]流量變現是指網站流量通過某些手段實現現金收益。在互聯網行業(yè),有這樣一個公式:用戶=流量=金錢。要實現流量變現最重要的就是有足夠的流量,網站流量指網站的訪問量,是用來描述訪問一個網站的用戶數量以及用戶所瀏覽的頁面數量等指標,流量變現的關鍵在于流量的變現方法、推廣方式和用戶粘性。
三、 消費社會中對藝術功利化的思考
美學思想在早期的儒家經典以及道家經典著作中就已經產生了,例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注]吳根友譯注:《老子》,湖南:岳麓書社2019年,第29頁。,“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注]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63頁。,這些都涉及到日常審美的境界。
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趨勢下,生活美學也廣泛運用到商業(yè)模式中。那么,我們是否應思考在消費社會中,生活美學的真正意義?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文化市場迎來了生活美學以及精神世界更新迭代的契機。其實,生活美學無論在哪個年代都已經有相關的發(fā)展,探尋中國歷史,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有著源遠流長的發(fā)展史。
顯而易見,藝術精神至上的觀念是學術界認識藝術的一種普遍常態(tài),而現代商業(yè)社會中以商業(yè)利益為訴求的藝術作品與其背道而馳。現代消費社會,似乎使藝術的精神性和創(chuàng)造性減弱,以大量的工業(yè)化復制生產取而代之。所以,藝術“無功利”與“產業(yè)化”兩個矛盾對立點,成為當代藝術發(fā)展爭論的重要焦點。
表層看,藝術的“無功利”與“有功利”是相悖的,但從藝術發(fā)展的歷史來看,“無功利”也并不是藝術與生俱來的特征。如李漁的美學主張,看似無所不容,實則有著相對統一的命題,那便是作者作為古代文人對于文藝與商業(yè)的摸索與整合。由此可見,李漁的審美主張對于當下IP作品和藝術作品如何在功利化氛圍下保持自我等重大命題上頗有借鑒價值。
高度文明的社會讓藝術更加貼近了人們的生活:從博物館的美術展到商場舉辦的文化活動;從公園里的公共藝術到各大奢侈品牌的設計開始融入藝術元素;從網絡上點擊率超過十萬的公眾號軟文到流行文化與高雅藝術的融合……人們早已經習慣了生活中以商業(yè)或非商業(yè)形式出現的大眾藝術。也許,智能手機的普及和互聯網的發(fā)達讓大量零散的信息從四面八方涌向每一個手機屏幕前的受眾,雖然社交網絡上的信息以及知識付費時代所生產的內容很多時候對都市人并沒有什么幫助,但在接受信息的同時,受眾從大眾藝術或者說有審美化引導的生活方式信息中有所感知,這也在潛移默化中讓大眾得到美的享受。由此可見,在生產優(yōu)質內容和創(chuàng)新性思維的前提下,藝術的“產業(yè)化”能加速整個社會對藝術和審美的接受與感知,使藝術變得更加常態(tài)化,從而促進日常生活審美化。
筆者從2014年5月起參與文化藝術普及系列的公益講座,藝術家們用深入淺出的演講將大眾帶進藝術的殿堂,同時也用精彩的現場表演與觀眾交流,讓觀眾懂得如何真正欣賞藝術。在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的同時,人們需要一塊屬于自己的精神田園。[注]楊成同:《走進雅村——廣東省文化學會打造“雅村文化空間”普及高雅文化藝術》,《大社會》2018年第4期。
當藝術越來越走近大眾,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方式也模糊了精英藝術與大眾藝術的界限,也將藝術的“無功利”與“有功利”的爭論深化到對于藝術本質的探討。我們是否也要反思一個問題,在世界變得審美化之后,藝術與生活美學的界限不再清晰,會不會導致嚴肅藝術在大眾視野中的漸漸淡化?在眾多關于“生活美學”的學術研究中,“生活美學”試圖在一種對生活的本質直觀中超越主客二分的主體性美學。然而,超越主體性美學是可能的,但否定主體性或將主體性與客體性等量齊觀于一種混沌狀態(tài)中,卻無異于返回到前現代美學,乃至返回到一種前人類的自然狀態(tài)。歷史上那些號稱取消了主客二分的哲學和美學,無不暗中承認主體性的這一地位。但無疑,“生活”的確可以被解釋成為一個比實踐、生活更廣的因而可以把實踐、生活揚棄于自身之內的范疇,從而“生活美學”不僅可以成立而且是極具發(fā)展?jié)摿Α注]王江松:《“生活美學”是這樣可能的——評劉悅笛的〈生活美學〉》,《貴州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藝術作為主體性美學,是生活美學得以出現的本源,其審美功能性無法被替代。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是藝術介入生活的一種方式,但不等同于生活美學會與藝術處于原始的混沌狀態(tài),相反,在當代社會,生活審美的提高,更有助于大眾在審美消費中加強藝術修養(yǎng),從而更加關心藝術的本質,以美學賦能生活。因此,生活美學在當下的迅速發(fā)展,為藝術的普及、審美教育的延展實現了更多可能,這并不代表無功利的純藝術會消失,而應是轉換了存在的形式。藝術類型與審美趣味永遠千差萬別,因為人類的多樣性決定了這一點,藝術創(chuàng)作的個性也永遠是千種百樣的,這也是藝術的走向。我們作為藝術工作者以及傳播者,不能回避藝術性與審美性對藝術產業(yè)化的重要性,因為其中的平衡點在于,“有功利”的藝術不但沒有放棄藝術性,并且能夠借助于市場規(guī)律不斷豐富和開發(fā)藝術價值,不斷傳播藝術真正的核心思想讓人們受益,這樣才能使藝術多維度的發(fā)展。[注]于漪:《從藝術無功利到藝術產業(yè)化》,《貴州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
四、 總結
當代社會中,不同的藝術形式精彩紛呈,從傳統理論上的藝術無功利走向現代消費社會的藝術產業(yè)化顯然是人類命運發(fā)展中不可回避的一個重要命題。由于人類生活的社會狀況、經濟條件、文化背景等種種不同,無論是對高雅藝術的追求,還是跟隨大眾藝術產業(yè)化的潮流,藝術對于人類的作用,最關鍵的還是在于啟發(fā)人類的審美以及對于世界和自身的思考。任何藝術形式在任何時代都需要尋求平衡,回歸現實,藝術的商業(yè)化也加速藝術的傳播和流動。在文化產業(yè)的洪流中,作為創(chuàng)作者,應對受眾與市場有足夠敏銳的感知和至深的體恤,對創(chuàng)作、創(chuàng)新有極高要求,樂于實踐并富有生活審美的李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優(yōu)秀的研究案例。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不同群體對藝術的差異化需求,也需要在實現不同發(fā)展之際,讓藝術的美與商業(yè)化利益協同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