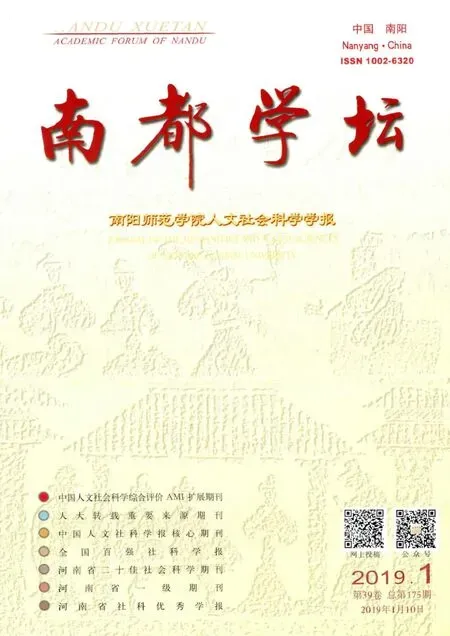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意識向自我意識的辯證過渡
王 傘 傘
(遼寧大學 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自古希臘以來,哲學家們便開始探索自我的發展過程,但是自我的真正確立卻是在近代哲學發生了認識論轉向之后。以“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哲學原理著稱的近代哲學的創始人笛卡爾首先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凸顯了理性精神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的基礎性地位。此后,無論是康德還是費希特、謝林,都繼承了笛卡爾哲學所奠定的哲學基礎——自我。黑格爾更是吸收了整個近代哲學的發展精髓,使自我意識的哲學發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非常重要且具獨創性的一部理論著作,馬克思曾經這么評價黑格爾的這部著作:“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起源和秘密。”[1]整個《精神現象學》就是一部意識的經驗發展史,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意識向自我意識的過渡則是精神發展的關鍵性和基礎性的一環,意識經由感性確定性、知覺和知性,通過否定自身、超越自身,最終在這個充滿矛盾的辯證發展過程中一步步走向了自我意識。因此,對于意識如何走向自我意識的研究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整個精神的發展將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更是我們理解黑格爾哲學的開端。
一、意識的開端——感性確定性
雖謂之為“開端”,但也正如我們所了解到的,“對于科學說來,重要的東西倒并不很在乎有一個純粹的直接物作開端,而在乎科學的整體本身是一個圓圈,在這個圓圈中,最初的也將是最后的東西,最終的也將是最初的東西”[2]。因此,在黑格爾這里,也無所謂開端與終點。但實際上,黑格爾還是強調了二者的區別。
在感性確定性的兩個方面中,對象理所當然的就是本質,認知者則是非本質的東西。因為對象的存在是不以認知者為轉移的,不管對象是否被意識到,它都存在著。對象的存在就是感性確定性的真理,但是它的真理性究竟在何意義上、在多大程度上被稱為真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去考察對象的本質,事實上它所具有的本質地位經過反思卻可以走向相反的結論。經驗世界中的任何對象都處于時空之中,任何“這一個”都有一個時間和空間的問題,因此黑格爾認為我們應該從“這時”和“這里”的雙重形態來把握對象。黑格爾首先為我們論證了“這時”的辯證關系。感性確定性所要把握的是“這時”,可是當它以為自己把握到真理的時候,卻發現“這時”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復存在,它已經是曾經存在了。但這絕不是感性確定性所要追求的真理,于是“這時”的真理成了非存在,“這時”成了一個保持下來的否定的東西,“一個這樣的,通過否定作用而存在的單純的東西,既不是這一個,也不是那一個,而是一個非這一個,同樣又毫無差別地既是這一個又是那一個——像這樣的單純的東西我們就叫作普遍的東西;因此普遍的東西事實上就是感性確定性的真理性”[3]74。同理,對于“這里”依然如此。“這里”不會因為我們的轉身而消失,它是長存于事物的消失之中的。無論是“這時”還是“這里”,都使感性確定性走向了它的反面,它所堅守的真理也隨之遭到瓦解。
此外,“當我們說出感性的東西時,我們也是把它當作一個普遍的東西來說的”[3]74。語言是一種共相,只要是我們說出來的,它就一定是普遍的東西。因此,感性確定性本身所意味的東西就無法得以言明,任何感性存在想要訴諸語言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感性確定性必須將自己的真理確定下來,這就必須使用語言,而只要運用語言,它的真理性就成了共相。感性確定性最初認對象為自己的本質,認知則是非本質的,認知必須要符合對象才能獲得真理;但現在共相成了感性確定性的真理,感性確定性的意謂則取決于我們的認知,由此出現了一個完全的顛倒。
感性確定性的辯證發展使它的本質經歷了從存在到非存在、直接性到間接性的辯證發展過程。但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自我意識產生的基礎。因為“自我意識要把意識所區別開來的對象看作是與意識沒有區別的,首先就必須把對象的客觀存在性加以揚棄,或據為己有。最初被看作固定不移的客觀事實的感性對象,在感性的經驗中一個個被取消而變成非存在,被視為虛無。如果沒有這一步,意識的對象將永遠自在地存在著,永遠和意識有著固定的、不可取消的區別,那么自我意識將無法實現突破”[4]。感性確定性要把握真理,實際上只要是“確定性”就一定不會是真理,因為真理是一個過程,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所以,正是由于感性確定性階段感性對象的不可確定性才使意識有了走向自我意識的可能。
二、意識的進一步發展——知覺階段
感性確定性作為直接性的存在,是終將逝去的,這使它追求確定性的愿望幻滅。但是它雖然沒有達到目的,卻已顯示出了真理,只是它自己沒有覺察到而已。一旦它開始反思自己曾經走過的歷程,并想要把握這種真理的時候,它便進入到了知覺階段,因為只有知覺才把共相、普遍性作為自己的原則。相應地,知覺階段的各環節也必是以普遍性為原則。如此,在普遍性原則出現的同時就出現了兩個環節,一個是指出的環節,即知覺;另外一個也同樣是這一過程,不過被認作簡單的東西,即對象。而在這兩個環節中,二者是處于對立關系的,這就決定了二者之中只能是一個處于主要地位,一個處于次要地位,而這處于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對象。在知覺階段,意識仍然是延續了感性確定性階段視對象為真理的進路,這就使得必須對于對象做進一步的考察。對象是知覺的本質,所以它的原則就是知覺的共相原則,但是這個共相在它的單純性里只是一個被中介的原則,它是包含著無數殊相在內的共相,只有通過否定無數殊相的運動普遍性才能得以保存下來。當然,對象必須在它身上把這一特性呈現,“這樣一來,于是對象就被表明為它自身是具有許多特質的事物”[3]84。
(一)事物的簡單概念
對象在知覺階段顯現為事物,而事物是由很多漠不相關的屬性構成的,這些眾多的屬性通過一個“又”聯系起來。當然,這只是一種外在的結合,“又”只是作為一種媒介以及這些屬性的更高一級的普遍性而存在,屬性通過它共存于事物之中。但同時,事物又是“單純的否定性,是單一,是對于相反的特質之排斥”[3]85。事物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特殊性是對事物與他物之區別的界定,只有把特殊性、排他性納入進來事物才能得以成其為一個事物。由此,事物便既是肯定的普遍性又是否定的單一性,通過肯定和否定這兩個環節,事物的個別性才得以真正展現。事物的形成也正好體現了黑格爾正反合式的辯證法則。
(二)事物的矛盾概念
由于知覺以普遍性為原則,所以對于普遍性之外的他在也必須是歸于普遍性的原則下看待,他在是被知覺者揚棄在普遍性之外的。知覺必須以自身等同性的標準來對待不同的東西,如果在知覺者把握外部世界時出現了某種不等同性,這也只能是因為知覺本身產生了錯覺,而非對象本身的不等同性。
知覺的對象事物是建立在“一”之上的,但同時事物本身又是由許多屬性構成的,事物的“一”要通過屬性的“多”來表現,而這些屬性作為共相又是對個別性的超越,這就造成了“一”的個別性和屬性的普遍性之間的矛盾。對于屬性,一方面它是共相,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同于他者的屬性,具有排他性和否定性。如果從屬性的規定性即排他性來看,則把對象性本質規定為一個廣泛的共同體或連續體又是不可取的,因為這跟屬性的規定性是不相容的。只有界分開連續體,事物才成其為事物。既然對象的本質既不是“一”,又不是“連續體”,那么它到底是什么?黑格爾認為,我們應該把這個“一”分開來考察。此時,直覺的真正對象就是單個屬性,但是這樣我們依然沒有真正把握到對象,因為在現實中知覺不可能建立在單純的一個屬性上。因此,對象現在也只能是被看作一個普遍的媒介,一個把眾多屬性聯系在一起的媒介。但是把對象規定為媒介,同樣也偏離了真實的知覺,因為我們不可能知覺到媒介,而只能知覺到這些孤立的特質。由于這些屬性沒有一個“一”作為載體,而且不再具有否定性,因此它只能是一般的感性存在。知覺此刻發現事物的真理也只是一個意謂。事物規定性自身的矛盾使意識完全退回到了感性確定性階段,然而卻再次進入同樣的循環之路,但它卻是站在知覺立場上的再次啟程。
知覺最初的目的是要把握事物的真理,可現在卻發現其最終的結果卻是事物性的解體,自己否定了自己。知覺的解體使知覺走向了對自我的反思,并認識到這種非真理性是屬于自身的。意識承擔起了犯錯誤的責任,當然也力求揚棄這種非真理性,并走向對象的真理性。其實在知覺的經驗過程中同時存在著意識和事物的矛盾發展,二者最終都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為滿足人們的對居住環境高需求,需要建筑工程行業不斷提高與完善現有的建筑水平,并引進先進技術,打造更符合人們審美視覺的建筑物。但在土木工程建筑結構設計上出現整體性比較差、細節不完善、設計方案呈現問題等眾多問題,影響著土木工程建筑行業的發展,不能有效滿足人們的需求,這需要相關建筑部門與設計師加以完善與改進,優化建筑結構設計方案。土木建筑結構在土木工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關系到施工工作是否可以得到順利的開展。所以,建筑企業與設計部門應加大對建筑結構設計的完善以及對出現的問題進行合理解決,提高人們的居住質量,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由知覺到知性的進展
意識現在繼續向前發展,它揚棄了之前的主客二分,從而把對象本身看作就是這整個運動,把運動中對立的雙方全部歸為了對象。這樣,事物在它自身中包含著對立面,一方面它“是一”,是自為的;另一方面又是為他的,因為它要承載各種各樣的屬性,事物既作為自身而存在,又作為那些有差異的屬性而存在。但既然它“是一”,就不能是多,如此這樣雙重的、有差異性的存在怎樣才能達到統一,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如果意識把這個“是一”歸為自己,是自己使事物成為“一”,那么事物就成了“多”,事物便隨之解體了。所以只能是事物自身中就蘊含著使自己成為“一”的那種能力。但“是一”與事物本身是不同的,事物是各種各樣差異性的存在,“是一”不能歸于同一事物,而是歸于不同的事物。事物自身“是一”,但它同時又是多,只不過這個“多”是與別的事物相關的。對于一個事物來說它自己“是一”,其他事物就是多。但實際上這個外在的區別還是由于事物自身的本質使然,事物既然“是一”,就是說它與別的東西都不同,而這個“一”是通過他物得以規定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事物“一”的本質同時也就是多、區別。不過顯然事物的單一性才是它的真正本質,雖然多樣性對事物來說也是必要的,但也只能是非本質的。但事物作為自為存在的“一”也只是就它與別的事物不發生關系而言的,可也正是這種絕對特性和與他物的對立才使它與他物發生關系,事物的這種特性以一種否定的方式規定著他物,在這個意義上,事物自身就是他物,事物由此通過自己否定自己走向了毀滅,這就是事物本身的辯證法。
知覺的辯證發展表明了在知覺階段,意識的普遍性和共相仍然是感性的,受感性東西的制約,意識的真理性發展必然不能滿足于此,它必然要對知覺的這種有條件的共相進行揚棄,從而走向無條件的共相。此外,事物由于自身的規定性而走向他物,這種對自身的突破在黑格爾看來是一種“壞的或否定的無限”[3]199,這就暗示著無限性的發展還有更高的層次。
知覺對于事物矛盾隨意地玩弄詭辯,矛盾雙方被它任意分配到不同的方面,雖然這已經進入到了知性的領域,但這種知性顯然是一種樸素的健全知性,這種共相也只是一種有條件的共相。因為它時而把一切錯誤歸咎于自身,時而又認為假象和錯誤是由事物的不可靠造成的。健全知性想要通過此種方式維持住真理性,卻表明了自己的非真理性,因此,在黑格爾看來,它必須進入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即知性的階段。
三、走向自我意識——力和知性
健全知性雖然已經達到了知性階段,但它依然不能正確處理共相之間所蘊含的矛盾。它只是以一種詭辯的方式,時而這樣認為時而那樣認為,并以此來回避矛盾。但是知覺的知性何以能夠通過這種方式使這些觀念不自相矛盾,實則是因為有一個無條件的共相的視域能夠讓它把那些有條件的共相放在一起。知覺的知性其實已經達到了無條件共相的高度,只是它自己沒有意識到而已,它還沒有對這個無條件的共相進行反思。只有把那些有條件的共相放在一個無條件的純粹的共相中,才能統攝所有的矛盾,而這也便進入到了真正的知性階段,因為只有知性是建立在無條件的共相基礎上的。
(一)力和力的交互作用
力的概念,也即無條件的共相,作為意識的對象,它不是靜止的,而是一種運動。因為一旦它被視為靜止的,它就會再次淪為有條件的共相。力的概念本身就是包含著自為存在與為他存在的差別的,因此真正的力必然要表現出來,這就形成了力和力的表現,然而二者又是不可分割的、辯證統一的關系,而能夠將兩個不同的環節統攝起來進行把握的就是知性,力的概念是屬于知性的。力的概念表現為兩個環節,其一是“力之分散為各自具有獨立存在的質料,就是力的表現”[3]102;其二是這些獨立存在的質料消失的時候被迫返回到自身,回到本來意義上的力。力和力的表現實際上就是實體和實體的存在之間的關系,但是力和力的表現只能在思想和概念上做出區別,在現實生活中這兩個環節是同時存在的,因為力本身是不可見的,它只有通過它的現實顯現才能為我們認識。力將自己一分為二,“但是事實上力既然必然地外在化它自己,則它在自身中已具有那被設定為他物的東西了”[3]103。力內在地就是自身的他物,而他物也不過是它自身的外化,因此他物又要揚棄自己返回到它自身。力就是那眾多質料之持存的媒介,但同時它又具有將這些質料揚棄的形式;力之為力也就在于它是一種外化與內斂的雙向運動過程,通過這一雙向運動力實現了對自身的不斷超越。
力的概念雖然一分為二,但雙方卻是相互過渡和轉化的,而這也就表明二者在根本上是同一的,兩者的差異實則是沒有差異,差別只是暫時的,因為雙方很快就會轉化為對方。因此,力就是通過把自己分裂為兩個環節,在兩個環節的生滅辯證關系中體現出來的,力的概念也只有在現實的實體身上才能證明自己的本質。
(二)力的內在本質
力和力的表現交互作用,二者最后提升為力的概念和力的作為概念的概念。第一個共相力的概念是知性的對象,這是從對象的角度來講的,也即作為實體的力;而第二個共相作為概念的概念則為力的真正本質,這是從人的認識活動角度來講的力,也即主體;這也體現了由實體到主體,進而把二者視為統一的邏輯進程。力的概念使我們認識到事物內外部之間的聯系,也因此讓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有了現象與本質的區分。
在力的階段,事物是作為力的現實的東西出場的,通過力的相互之間的轉換知性得以認識到事物的內在本質。而力的轉換作為知性的中介則是力之發展了的存在,它是一個不斷消逝著的過程。在事物的現象中我們看到了事物的內在東西,而這個超越于感性之上的自在之物就是知性的對象,通過這一過程知性便進入到了超感官世界。超感官世界來自現象,現象是超感官世界的本質。在現象和超感官世界的關系中還蘊含著一個中介,這就是規律。規律是力的轉換本身的結果,是現象的真理,是“作為不穩定的現象界之持久的圖像”[3]113,由此我們便進入到一個靜止的規律王國。
規律雖然是知性的真理,但也只是知性的初步真理,在把握規律的時候必須要揚棄掉那些偶然性。抽象地講規律,它是確定的;但是在具體的場合下,它又是不確定的;這就說明特定場合下的規律不是一般的規律,如此就會有多個規律,這就違反了知性的普遍原則。那么,在這些規律的背后有沒有一個普遍的規律來統攝這所有的規律?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在黑格爾看來,知性是能夠將眾多規律合并為一個規律的,但因此這個規律的規律就成了完全抽象的概念,即規律的概念,失去了規定性。
一切規律內在地都有一種必然的東西起作用,這就是萬事萬物的生命力之所在。規律與力之間還是有區別的,規律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力本身則是事物的內在本質,我們可以通過規律來把握力,但并不能說把握了規律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質,因為力與力的實存是漠不相關的,力本身相對于規律是一個更高層次的概念。規律是知性對客觀世界的各種各樣的現象所做出的解釋,它與力沒有必然的聯系。規律所做出的區別只是一個空洞的區別,它并非事物本身的區別。但實際上,通過這種解釋我們可以認識到在規律中所缺乏的“絕對轉化”,在黑格爾看來,知性建立規律的運動也應該被看作事情本身的運動。知性的運動與對象的運動二者是絕對轉化的,而非知性所認為的對象是靜止的,“因為它建立一種差別,這個差別不僅對我們沒有區別,它自身反而取消了這個區別”[3]118。通過這個建立區別、又揚棄區別的過程,現象界的轉變和轉化進入到了超感官世界。但我們的意識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它意識不到這個轉化本身就是客觀自在本身的規律,這也就是第二種規律。
第一種規律是知性為把握各種現象而建立的區別,是非純粹的區別;而第二種規律則是建立在純粹區別之上的,是通過知性建立區別又揚棄區別的這一運動而對第一種規律的提升。規律雖然是靜止的,但在第二種規律中,這種靜止卻是充滿了轉化的辯證的靜止。它是對第一種規律的否定和揚棄,因而也就形成了第二個超感官世界,即顛倒的世界,我們也便從存在論進入到了本質論。只有進入到第二個超感官世界,才能用這第二個規律來解釋一切現象。
(三)無限性
顛倒成了第二個超感官世界的本質,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揚棄第一個超感官世界對事物做出的外在區別,從而上升到事物的內在區別,也就是事物是自己同自己相區別的。第二個超感官世界把第一個超感官世界作為自己的一個環節涵蓋在了自身之內,實際上二者根本就不是兩個世界,而是一個世界;這個顛倒的世界自為地就是它自己的對立面,它們是一個統一體。只有把兩個世界看做是一個統一體,事物的區別才是內在區別,也才能是無限性的區別。通過這種無限性,規律達到了必然性,“現象界的一切環節都被吸收到內在世界里面去了”[3]124,而這個通達無限性的過程正體現了正反合的辯證關系。
客觀世界紛繁復雜的“多”最終化約為“一”,一切運動都是源于事物自身的運動。“這個單純的無限性或絕對概念可以叫作生命的單純本質、世界的靈魂、普遍的血脈”[3]124,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區別,一切區別亦即無區別,它打破了一切界限的無限性。真正的無限性就是純粹自身運動的絕對不安息,它不斷地把自己區分開來,又揚棄區別回到自身,在自身內不斷地循環著。一旦認識到事物是自己把自己區別開來的,也就達到了自我意識;對象意識也必然就是自我意識,自我意識才是對象意識的真理。
從感性確定性經由知覺再到知性,意識從一個較低級的階段逐漸發展為相對高級的階段,并走向自我意識,這是一個不斷否定自己、不斷前進的過程,它體現了黑格爾存在論、本質論、概念論的邏輯體系。但無論是在感性確定性還是在知覺,抑或是知性階段,意識的每一次發展或者是過渡都充滿了辯證的色彩,它是不斷發現矛盾并解決矛盾的過程,也正是因為這一艱難曲折的過程,意識才得以從對象意識走向自我意識的高度,才能最終進入真理的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