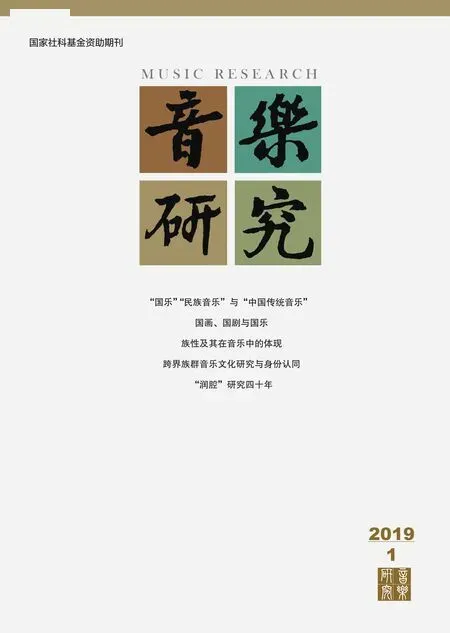音樂研究怎樣“把目光投向人”?
主持人◎楊民康
“音樂與文化認同”專欄導語
二十多年前,著名音樂學者郭乃安先生針對音樂界時局,倡導大家:“人是音樂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我說: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①郭乃安《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中國音樂學》1991年第1期。閱讀這篇文章時,我發現郭先生并非像一般人那樣,僅是針對人所持有的音樂觀念和音樂行為泛泛而談,而是兼涉了人們面對音樂時所具備的主體性地位,亦即以人的主體性及文化本位為中心的意識。應該說,無論在當時或在當下,這都是十分超前,卻非常在理的觀點和主張。然而,鑒于郭先生的文章篇幅不長,對于通過什么樣的研究路徑?怎樣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尚未來得及給予明確的答案,以致它一直成為擺在中國音樂學者面前,且一直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去努力攻克的一個學術難題。比如,中國傳統音樂研究領域諸多同人多年來以“音樂與文化認同”為話題和主旨,經歷了多個不同的階段和曲折的過程,如今取得了一系列的相關研究成果。其目的和意義正在于此。
近幾年來,中國音樂學界圍繞“音樂與文化認同”問題,召開了多次學術研討會議,陸續出版和發表了多本專著及數十篇學術論文,在研究話題上,由以往以“族性音樂與身份認同”為中心,轉而集中于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沿著宏觀把握和抽象論述的路子,去討論諸如“如何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框架下理解中國民族音樂文化話語體系?”“中國音樂話語體系與文化認同”等問題;一是更多集中于“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族性認同與文化建構”問題,并且以音樂民族志個案或多點音樂民族志比較的方法,對之進行腳踏實地的分析和論證。②參見楊民康《“音樂與認同”學術現況及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實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魏琳琳主編《音樂與認同:民族音樂學與人類學的跨文化對話》,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年版。
本期《音樂研究》刊載的五篇相關論文里,有兩篇結合了宏觀、抽象層面與微觀、具體層面,以人的主體性為中心視角,討論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發展及認同現況及其應對策略。其中,楊民康的《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與身份認同——以中國西南與周邊跨界族群的比較研究為例》(以下簡稱“楊文”),從身份認同的角度思考中國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的分層和屬性,提出作為國家、民族社會文化體系的子項之一,中國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文化在表征文化認同時,呈現為一張多面、多層的文化與身份認同之網,并且攜帶著自己的編碼程序和表述方式。該認同之網上存在著按文化圈、文化層的歷史性規律而發展、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認同階段和層次序列,其中的不同認同類型,是自族群和地域內部傳承向跨地域、族群、文化傳播的方向,前后依序,順著時針,由小漸大,由點到面,滾雪球般地自然增長,最后形成一張由族群認同、區域認同、信仰認同到國族認同等構成的認同階序之網。然后從定點、多點音樂民族志研究與族群、地域文化認同,跨界族群音樂比較研究與國族音樂文化認同,跨界族群音樂文化圈研究與信仰認同,區域音樂文化比較研究與區域文化認同和離散族群音樂與族裔散居身份認同等五個方面,討論了跨界族群音樂研究采用的不同方法論及研究分析思維與音樂文化認同之間的關系。
張應華的《宏觀與微觀:西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認同研究的雙重視角》(以下簡稱“張文”)認為,音樂文化認同研究的宏觀視角,即在動態、多點、線索等研究策略中討論音樂文化的共性特征,側重不同文化主體、文化空間之間相互認同的文化敘事和理論探究。其微觀視角則側重于具體的民族志田野實踐,強調以相對靜態、定點、結構分析的方法,去描述不同音樂事項內部的差異性特征,突出其結構內部相互“認異”的文化敘事。在此概念基礎上,“張文”聚焦于西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認同研究的宏觀視角,提出了相關的五對學術關系:歷史民族音樂學與西南少數民族音樂的內地文化認同研究、區域音樂研究與西南少數民族音樂的區域文化認同研究、族群音樂民族志研究與西南少數民族音樂的族群文化認同研究、西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跨境認同研究和西南文化通道的音樂認同研究。可以說,該五對關系分別從宏觀的關系思維與中觀的方法論思維兩個層面上,與前述“楊文”的觀點形成了呼應和互補的關系。繼而,“張文”又借用美國闡釋人類學學者格爾茨“歷史構成、社會維護及個體適應”③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pp.363-364.的分析模式,從微觀研究的層面,討論了“音樂文化歷時性的‘差異性認同’:口傳歷史的規約”“音樂文化空間性的‘差異性認同’:社會維護的規約”以及“民間藝人角色性的‘差異性認同’:個人創造的規約”三個方面問題。最后還結合相關文化人類學理論,對宏觀視角與微觀視角的理論取向進行了比較討論。
趙書峰的《傳統的發明與本土音樂文化的重建——基于中國少數民族音樂身份認同變遷問題的思考》,聚焦于當下少數民族音樂存在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身份認同與文化變遷關系問題。該文提出,傳統音樂的形成與建構是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文化間“濡化”“涵化”的當代歷史結局。因為任何原生性傳統的形成過程決不是一源的,而是多元文化融合、互動而成的產物,其中包含對傳統文化的發明、改造與借用,尤其是前者在傳統文化的延續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對傳統音樂文化的發明與改造,不但為了適應其所處時代社會、歷史、民俗、審美語境的需求,而且是為了更好地延續音樂的傳統。作者借助于人類學有關文化濡化、涵化的理論及許多相關的音樂發展現況實例,試圖論證以下基本觀點:族群間彼此的文化認同是本土音樂身份重建的重要前提;傳統的“發明”是多維度權利與知識互動語境下的主觀話語建構。然后進一步討論了傳統的“發明”與本土音樂文化的重建在當下音樂文化發展過程中具有的社會意義。
楊曦帆的《傳統的建構與理解——岷江上游地區的音樂民俗與文化認同研究》側重從中觀至微觀視角,立足于音樂表征文化認同的網絡及階序中的一個重要層面——區域文化認同展開討論和分析。該文認為,文化認同研究在國內已有較為穩健的起步,但對于中國博大的文化當量而言,理論與個案相結合的區域文化認同研究還應當引起更多關注。岷江上游地區存在著包括族群、信仰、習俗在內的較為豐富的多元文化結構,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流動與變遷,音樂常常成為信仰儀式和民俗活動的情感表達手段,因此,以音樂為接入點,能夠較好管窺這一地區人們的真實生活與文化屬性。作者還在討論文化認同理論、歷史語境中的文化認同、認同的音樂體驗、認同與不認同、特殊自然環境與區域音樂文化認同等問題的基礎上得出以下結論:岷江上游地區多族群文化元素在社會文化層面上表現為“復雜結構”,融合、邊界、分離和變遷等文化現象同時共生,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流變與建構。認同不僅是簡單的“聚攏”,而是具有著文化上的互動與多種表現形式。相關樂舞的文化背景也可能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對于“背景”的解讀需要結合于當下的需要,需要理解“當下”人們情感/情緒的表達。
魏琳琳的《樂器、身體與文化認同——以安達組合演奏的冒頓潮爾為例》,通過具體的音樂民族志個案,去討論音樂表征文化認同的一個特殊面相——樂器及其身體表演行為與文化認同的關系。該文指出,樂器是一種預期目的的物質實現,是人類活動中音樂普遍存在的證明。在樂器研究中,有一種未引起注意的潛力,即以象征的方式與身體接觸,在不同文化中樂器的使用與感知方式表征文化認同。安達組合作為近年來中國蒙古族音樂走向世界的民族音樂組合,其音樂及表演形式,在保持自身傳承與文化身份的同時,將全球化理念融入自身表演當中,并以此得到海內外受眾群體的廣泛認同。安達組合中所使用的樂器(包括馬頭琴、拖布秀爾、冒頓潮爾等)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其中冒頓潮爾(Modonchoor)因其特有的音色在蒙古族音樂文化中占據重要位置。該文通過樂器與身體的互動及民族志個案的描述,關注冒頓潮爾作為一件世界性樂器、廣義跨界族群的產物,通過不同表演語境中表演者的個性化表達體現了現代民族的文化訴求,從而彰顯不同程度的認同階序關系。
筆者亦曾在另文中提出,以音樂分類法為代表的傳統音樂分析方法,正在經歷著由較單純的以音樂為主旨的對象性研究,到文本間性,繼而主體間性,亦即以物——音樂為對象和中心到以人——音樂文化持有者為主旨和中心的文化轉型過程。④楊民康《中國傳統音樂分類法的方法論轉型及文化認同特征》,《民族藝術》2018年第6期。若結合近年來的相關成果去檢閱,可見學者們進行的上述討論,并非是建立在空中樓閣之上,而是以特定語境中的人和文化為研究目的,以音樂分析為入門之徑和對象性過程,并且以眾多的音樂民族志個案成果為學術支撐。據此可以說,當代中國音樂學者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和路徑,去努力實現郭乃安先生“把目光投向人”的生前夙愿,把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事業推向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