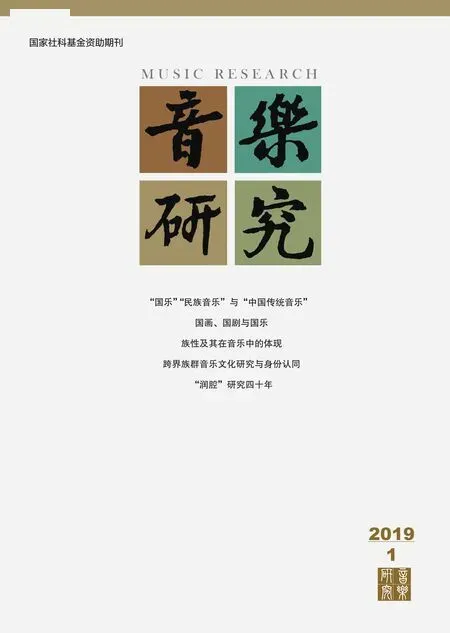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國樂”“民族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
——并非作“歷史變遷”理解的現象觀察與思考
文◎劉 紅
引 言
自《民族音樂概論》于1964年出版以來,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并未引起學界的廣泛注意和思考。《民族音樂概論》成就、成熟之前的“民族音樂”情形如何?民族(或說傳統)音樂理論體系和學術范式是怎樣的?具體而言,曾經以“國樂”作稱而形成的“國樂觀念”“國樂行為”及“國樂教育”,與之后的“民族音樂”這一概念、現象和行為有否承接、關聯?再后來于當下,“民族音樂”到“中國傳統音樂”之名稱與概念轉換,從完整的“思想體系”和“理論體系”有了怎樣的轉變?對此轉變應當做如何解釋?
顯然,從“國樂”到“民族音樂”再到“中國傳統音樂”,不應簡單當作名稱上的更替、變化和演進理解,而應關注其于當時和當下社會、政治及文化環境下,自身內在基本元素和本質特性被不同看待和理解而成就的事實。基于此,文章并非只是從史學的角度把歷史上和曾經發生過的涉及名稱、概念及其相關行為之改變的現象作羅列和梳理,而是欲求帶著實際問題進行觀察和思考。①文章生成于筆者為研究生開設“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學科認知”專題研討課的教學過程。撰稿時,除摘錄筆者部分授課筆記之外,參與課程學習的王悅、張若塵和高川惠三位同學亦協助進行了資料搜集及整理工作,特此致謝!
1964年,《民族音樂概論》出版。至此,以民歌、民族器樂、民間歌舞音樂、說唱音樂和戲曲音樂為主體內容的“民族音樂理論”這一學科(專業)隨之形成。近年來,“民族音樂”作稱的這一學科,主體內容由原本“五大類”(亦或不包括歌舞音樂的“四大類”)增加了“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等類項而更多地被“中國傳統音樂”所替代。針對改變了的這一事實,本文關注、思考并討論的問題包括以下方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建立起來的“民族音樂”理論體系,由于“民族”本身具有明確的“國家”含義,因此,學科淵源、理論基礎,部分與該體系建立之前的“國樂”有關聯。于是,需要深究的是,在國體、政體發生重大改變的新時代,“國”為主體的“民族音樂”,在學統、傳統層面,無論是理論、理念還是現實、現象,與舊“國樂”的深度關聯到底體現在哪里?“民族音樂”悄然冠之以“中國傳統音樂”,不僅僅只是學科使用了新的稱謂,更重要的是其實體也產生很大變化。名稱上,原先的“民族”,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概念上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定的“國家”之含義,實際包含著廣大“勞動人民”為主體的基本屬性,因此,“民族音樂”可以理解為“人民大眾的音樂”,重視和強調的是人民共和國之“人民”這一根本。改稱“中國傳統音樂”之后,立于“文化中國”的視野和角度,更為強調的是概念最大化產生、形成并傳承于“中國本土的”“中國人的”音樂。實體上,之前不被“民間”所包容的文人音樂、宗教音樂和宮廷音樂被納入了這一“傳統”范疇。如果說,這一名稱、概念的改變是因為原先“民族音樂”未能完整和全面地涵蓋“中國音樂”現象,而使用“傳統音樂”之名的“大家庭”有了本身就存在的“新成員”擴充,令實際內容、理論體系更為完善的話,那么問題是,傳統大家庭里的新舊成員,是否可以在傳統的“傳統觀念”下做出一致的解釋?由表及里作探究,名與實,今與昔,“傳統”二字如何辨析、認知?
是為問題的提出與緣起。
一、“國”之名義,“國樂”如何?
國樂,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盡相同的概念和定義。1943年,陳洪在《國樂的定義》一文中說:“‘國樂’這個名稱還是很新的,以前大都稱為‘中樂’。‘中樂’也不是一個頂舊的名稱,在閉關自守的年代,樂便是樂,無所謂中西;海禁開,‘西樂’來,才有人給它起這個稱號,叫做‘中樂’,借以區別于‘西樂’;和用‘中文’、‘中畫’、‘中醫’等名詞用以區別于‘西文’、‘西畫’、‘西醫’等一樣。……愛國之士們,便又把‘中’字改成‘國’字,于是‘國畫’、‘國醫’、‘國術’等名稱乃相繼出現,‘中樂’也便改成了‘國樂’。”②陳洪《國樂的定義》,《音樂教育》1943年第2卷第12期。
眾所周知,國樂是于20世紀上半葉在“新音樂”發展變化的背景下,隨著西樂進入本土而出現的新稱謂。正是因為伴隨著西樂的進入而產生出國樂之名稱和概念,因此,“國樂”觀念很大程度上是相對于、區別于或說比較于“西樂”而形成。
魏廷格對國樂形成的歷史背景做了三種情形的概括③參見魏廷格《反思中國現代音樂文化問題的重要歷史文獻——關于楊蔭瀏先生〈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國音樂學》1989年第4期,第18頁。:
“全盤西化”主張。持此論者認為:中國需要的,“不是所謂‘國樂’,而是世界普遍優美的音樂”,“中國新音樂的建立,要‘全盤西化’,……使基礎先立定了然后再創作新的中國音樂”。④歐漫郎《中國青年需要什么音樂》,《廣州音樂》1935年第3卷第617期。轉引同注③。
“全盤中化”論。此論,直接見諸史料的不多。從間接材料可知,持此論者是兩種背景截然相反的人士。一種是所謂“舊派樂師”,總以為“聲音之純正與精微,舉世界當推吾國第一,他日西方樂師,必來吾國研究”。另一種是西方音樂家。例如當時活躍于上海的意大利指揮家帕奇,⑤Mario Paci(1878——1946),該觀點見青主《論中國的音樂(給上海交響樂隊指揮Mario Paci一封公開信)》,《樂藝》1931年第1卷第5號。轉引同注④。就主張將來的中國音樂要由中國人指揮,用中國樂器演奏。
與前述二者取不同的角度,20世紀30年代還有一種觀點,即“內容決定國樂”。只要“內容”是中國的,形式方面西式中式均無不可。既然西方的工具比我們的先進,工具就應當“全盤世界化和現代化(也可以說是西化)”,但是“內容”則要“徹底中國化”。⑥陳洪《新國樂的誕生》,《林鐘》1939年。轉引同注⑤。
總體而言,彼時國樂觀念大體不離乎此。那么,國樂的實質內容及其特征如何呢?
李巖對冠有國字的音樂的特征進行過這樣的總結:⑦參見李巖《論國樂改進觀念的衍變(1899—1949)》,載洛秦編《朔風起時弄樂潮》,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5頁。
第一,歷史最為久遠。如葉伯和在《中國音樂史》中提出“古時的國樂”:“古來一朝一代,都要制一個曲子,拿來紀念,并且一切儀式都要用它,恰像現在的國樂。”⑧葉伯和《中國音樂史》(上卷),成都冒福公司1922年版,第19頁。
第二,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音樂。如陳洪在《國樂的定義》中闡釋的“‘國樂’是和‘西樂’不同的,用的是我國的樂器(其中雖有多種來自夷狄,然而經過了歷史的磨練,文化熏陶,已經被同化了),唱的是‘合四乙上……’,寫的并沒有五線譜那么難懂……這便是‘國樂’”。
第三,能夠代表民眾意愿、情趣的音樂。如匪石曾指出古樂與國樂的區別:“古樂者,其性質為朝樂的而非國樂(的)者也,其取精不弘,其致用不廣,凡民與之無感情”;王光祈也就國樂做出論述,他認為:“國樂是足以發揚光大該民族的向上精神,而其價值又同時為國際之間所公認。因此之故,凡是‘國樂’須備具下列三個條件:一、代表民族特性;二、發揮民族美德;三、暢抒民族感情;這樣的音樂才配稱‘國樂’”。⑨王光祈《歐洲音樂進化論》,中華書局1924年版。
第四,是一種意義寬泛的,并受到西方音樂技法深刻影響的,并不囿于以往“國樂”范圍、界限的音樂。如廖輔叔提出:“國樂,顧名思義,自然是指本國的音樂,中國人管中國事,那末,國樂就是中國的音樂。但是積習相沿,有些人竟把國樂解作中國的樂器”⑩廖輔叔《湊熱鬧談國樂》,《新夜報·音樂周刊》第16期,1935年3月7日。。青主甚至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盡真、盡善、盡美的音樂藝術,并沒有國樂和西樂的區別。中國人如果會做出很好的所謂西樂,那么,這就是國樂。”?青主《我亦來談談所謂國樂問題》,載張靜蔚編《搜索歷史——中國近現代音樂文論選編》,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頁。
再看看直接或間接影響、促成“民族音樂理論”形成的一些國樂事實。
從現有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以國樂之稱進行的具體行為包括:組建國樂社團、國樂演出、國樂創作、國樂刊物出版和國樂教育,等等。
“五四”運動前后,南北各大城市里有許多民族器樂的愛好者組成各種社團,定期進行練習,不時也舉行一些公演。其中比較重要的社團有:“天韻社”“國樂研究社”(1919),“大同樂會”(1920),“霄雿國樂會”(1925),“云和樂會”(1929),“今虞琴社”(1934),“上海國樂研究會”(1941),等等。這些社團的成員大多數是城市中的舊文人、職員、店員以及中小學教師等,研習的范圍包括絲竹、吹打、古琴、琵琶以及戲曲(如昆曲和京劇)的清唱等。他們對傳統樂曲的整理、研究、改編和民樂曲譜的刊行以及在對民族樂器的改革和制作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并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演出和灌制唱片等活動。如“大同樂會”柳堯章等人曾將琵琶曲《夕陽簫鼓》改編為民樂合奏曲《春江花月夜》等。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大同樂會創辦者鄭覲文曾邀蔡元培、梅蘭芳和周信芳等為贊助人,聘汪昱庭教琵琶,蘇少卿、陳道安教京戲,楊子永教昆曲,鄭覲文本人任樂務主任并教琴瑟,早期還曾請歐陽予倩教歌舞。樂會成立之時即設有研究部、編譯部和制造部,負責出版音樂理論書籍、樂譜,教授樂器演奏,研制樂器,創作改編器樂曲。編譯部先后出版了鄭覲文的《中國音樂史》和《笛簫新譜》,另作有《中西樂器全圖考》《雅樂新編》,惜已佚。1930年1月,《國民大樂》在游藝會上首演,并將演奏實況攝制成影片,同年6月開排《中和韶樂》。1931年制成全套仿古樂器,共計163種。?陳正生《鄭覲文與大同樂會》,《樂器》1994年第2期,第39—41頁。1935年由于主任鄭覲文的逝世,其活動亦不復往昔。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個民間職業化音樂社團,在國樂的實踐中做出了許多新的嘗試。不難看出,此時的國樂社團發展的興衰,與創辦人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系,“國樂”這一概念更多地被理解為中國器樂(也就是后來我們所稱的“民族器樂”)這一面向,其創作的樂曲大多通過改編的方式而完成。
1922年,劉天華至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任國樂導師,接任王露先生的琵琶課,并于1927年成立國樂改進社,該社團主要針對國樂的調查、整理、提倡而進行。具體工作包括:刊印《音樂雜志》作為提倡音樂的至要工具;設立研究部,解決國樂各項問題;保存古音樂(合樂);音樂演奏會;舉行國樂義務教育;開設樂器制造廠;名奏蓄音(保存現有國樂最緊要問題);創辦《國樂改進雜志》。?劉天華《我對于本社的計劃》,《國樂改進社成立刊》1927年2月。面對所做的這一些,劉天華曾說:“這種整理國樂的工作,哪里該人民組織團體去做,該是政府的責任。它早應立出正式機關去辦理。”但“后來一想,現在國內政府如許之多,可是哪一個能注意到這件事的,還是省說廢話罷!”?同注?。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此時對于國樂的整理和研究,主要還是以民間的社團自發性的活動為主,而國家對于“國樂”的關注度顯然是不夠的,也并未設立相應的研究機構進行調查和整理。在這一時期,“國樂”之“國”,更大程度上是民眾出于一種新的國體的認同而對音樂進行的搜集與整理。
類似上述國樂藝術活動進行的同時,國樂教育也隨之出現。
1918年6月,由成立于1916年的北京大學音樂團改組而成的北大樂理研究會,由蔡元培校長親自草擬章程,宗旨是“敦促樂教,提倡美育”,下設“國樂部”和“西樂部”,并設置一些課程。如音樂學、音樂史、樂器和戲曲等。但因初創,先暫以教師之便設琴、瑟、琵琶、笛和昆曲五項。其中最早來北大任教的王露(王心葵)先生,受邀演奏古樂之后,被蔡元培聘為國樂導師,教授琴、瑟等古樂,開創了我國歷史上古琴教學進入高等學府之先河。?李靜《北大的美育傳統與音樂教育》,《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第141—145頁。1927年,蕭友梅與蔡元培創建國立音樂院之初,即樹立“一方輸入世界音樂,一方從事整理國樂,期趨向于大同,培植國民美與和的神志及其藝術”的辦學宗旨,在選修或副科開設國樂課,朱英即受聘于該院,教授琵琶、笛子,吳伯超教授二胡,開高等專業音樂學府培養國樂人才之先河。朱英作為首批在中國專業音樂學府任教的國樂教師,是全程見證國樂成為中國高等專業音樂教育的親歷者,也是將琵琶引入高等專業音樂學府的重要奠基人。他對國立音樂院——“國立音專”在初創十年間逐步確立的中國高等專業國樂人才培養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肖陽《朱英其人其事及其貢獻——朱英在國立音樂院——國立音專十年間對國樂表演和教學經驗的總結與思考》,《音樂藝術》2016年第4期,第74—81頁。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在楊仲子擔任院長期間,大力推行國樂教育,增設國樂系,并聘請楊蔭瀏、儲師竹、陳振鐸和曹安和等擔任國樂導師。對于國樂教育的目的,楊仲子在《“國立音樂院”三十年度增設國樂系計劃大綱》中寫道:“1.造成兼長獨奏伴奏及合樂之技術人才;2.造成國樂材料收集整理及研究之干部人才;3.造成國樂曲調修改及作曲人才。”?參見湯斯惟、張小梅《楊仲子音樂教育思想的演變探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第128—137頁。國樂系常設組別為研究組、合樂組、古琴組、琵琶組、二胡組、昆曲組以及一個其他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時任國樂導師兼任國樂教研室主任的楊蔭瀏,于1942——1944年間在《樂風》雜志連載專論《國樂前途及其研究》。為滿足教學需要,還先后編寫《國樂概論》《笛譜》《簫譜》《三弦譜》《音樂物理學》等教材。其中《國樂概論》被視為20世紀中國高校最早編寫的“國樂”教材和專修課程。?喬建中《20世紀中國傳統音樂教材的歷史回顧與評述》,《人民音樂》2016年第12期,第32—35頁。
基于上述事實,聯系本文關心的問題,這里要討論的是,“國樂”與其后的“民族音樂”在概念、現象和行為上有否承接或關聯?
作為一個音樂概念,“國樂”的提出與主張與當時的“國家”意識和狀態有著密切關系。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之后,當時的“國”是由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國樂”因此具有彼時“國家”之屬性和特性。民國承接晚清,中國社會處在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階段,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都經歷著一系列巨大的變化。國家政治發生重大變革,成為共和制度。由于當時各種不同性質政權的并立,使得在文化上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在地域、社會階層分布上均呈現出不平衡的特點。整個民國時期,社會結構呈現出十分復雜的狀態,作為各個社會階級和階層意識形態表現的文化也同樣呈現出更為錯綜混雜的狀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當時的文化狀態有這樣的概括:“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參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688頁,第693頁。這些代表不同階級、不同利益的文化,在民國時期進行了大規模的分化組合與激烈交鋒,形成了復雜的文化場景。
“國樂”與“民族音樂”這兩個稱謂都包含有國家的概念和屬性。我們雖然從上述國樂現象和行為中,很容易地看到其中涉及國樂社團、國樂演出、國樂創作、國樂刊物出版、國樂教育等相關內容在之后“民族音樂”中的部分延續或保留,但是,國體、政體、國家關系及國家實體的改變,先后出現于新舊兩個不同的“中國”的“國樂”與“民族音樂”因此而有了某些(或某種)本質上的區別。其中顯明之處在于,如果說國樂的名稱是相對于、區別于或比較于西樂而出現,實體內容即是唯中國所有、唯中國人所為的話,那么,這一國樂之“國”,還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具體于國樂為誰所為、為誰所用、為誰所有的主體、主人意識尚處于并不十分明確的狀態。“民族音樂”則不同,它呈現于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中國,擁護社會主義和祖國統一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人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的主人。因此,具有國家概念和屬性的“民族音樂”,“人民”是其主體和主人,此前中國的“國樂”中有違背人民意愿,不被人民擁有,不被人民享用的音樂事實和現象因此而未被“民族音樂”所采用。
這從《民族音樂概論》如何成就即可見一斑。
二、“民族”作稱,“民族音樂”如何成就?
據當年參加過《民族音樂概論》編寫工作的孫幼蘭介紹,1958年文化部批示,將中央音樂學院附屬的民族音樂研究所改為獨立的科學研究機構,并于當年5月1日劃歸藝術局領導。1959 年5 月1 日,文化部藝術科學研究院成立,民族音樂研究所改屬研究院領導,改名“中國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研究所在完成《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綱要》一至五編(未定稿)及參考資料15 種(約340 萬字)后,為向全國各藝術院校提供《民族音樂概論》教材,于1960 年8 月舉辦“民族音樂”研究班。該班由全國23所藝術院校和文化局等七家有關單位的音樂專業干部39人和音樂研究所二十多位研究、資料人員共同組成。最終完成《民族音樂概論》的編寫,于1964 年3 月由北京音樂出版社公開出版。《民族音樂概論》的公開出版,實現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零的突破,為在民族音樂理論建設方面立下了一塊新的里程碑,也為今后的繼續研究開拓了一個新起點。從最早的五十多人寫出的草稿,到八人的統修稿,再到四人的送審稿,《民族音樂概論》一步一步地從低到高、從粗到精、從松散到縝密、從不合出版要求到符合出版要求。《民族音樂概論》一書及12 本參考資料,不僅為全國音樂藝術院校提供了豐富可靠的教材,也為教授這一課程提出理論指導。同時通過研究班的舉辦,培訓了一批民族音樂理論的教學、研究人才,民族音樂理論的種子撒向了全國。這個重大的工作項目,應該說是開創時期的一次成功的實踐。?參見孫幼蘭《“民族音樂”研究班與〈民族音樂概論〉》,《中國音樂學》2013年第4期,第47—50頁。
毫無疑問,“民族音樂”的理論建構,是以《民族音樂概論》的問世為標志的。
《民族音樂概論》從理論基礎來講,間接地可聯系民國時期“國樂理論”“國樂觀念”。具代表性的理論資源為楊蔭瀏1942—1944年連載于《樂風》的《國樂前途及其研究》專論,1943年完成的油印本《中國音樂史綱》,以及《國樂概論》教材。較為直接的理論資源部分來自于延安“魯藝”的民間音樂研究成果。“民間音樂研究的命名直接來源于1939年開始的延安魯藝從‘民歌研究會’到‘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的歷程,當時,身任魯藝音樂系主任的呂驥給該系高級班講授新音樂運動史,針對抗戰之前對民間音樂的不夠重視,發起了民間音樂的研究與采集活動。其時正值抗日歌詠運動的高潮,因此該會的成立深具標志意義。”?蕭梅《中國傳統音樂研究述要》,《黃鐘》2009年第2期,第62頁。《民族音樂概論》具體參考、參照的文獻包括呂驥《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綏遠民歌集》《陜北民歌研究》;冼星海《為什么研究民歌》《民歌與中國新興音樂》等。?劉永昌《延安魯藝開辟民族音樂之路》,《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第57—58頁。尤其是呂驥《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將中國民間音樂分為民間勞動音樂、民間歌曲音樂、民間說唱音樂、民間戲劇音樂、民間風俗音樂、民間舞蹈音樂、民間宗教音樂和民間樂器音樂等八類?參見呂驥《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民間音樂論文集》,沈陽東北書店1948年版。的基本框架,對《民族音樂概論》產生直接指導作用,而且每類以“民間”作定性、定義,也為《民族音樂概論》之“民族”的界定起到指導作用。除此之外,1946 年3月31日,在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幼年班第三教室成立的“山歌社”,也為《民族音樂概論》的成就提供了部分資源。“山歌社”以集體學習方式收集及整理民間音樂,其具體影響主要有以下四點:為民族音樂學理論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礎;發掘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民歌;引領民族音樂走向音樂課堂教育;促進民族音樂走向大眾。?參見吳璨《中國民族音樂理論發展的奠基者——音樂理論家郭乃安先生》,《中國音樂學》2012年第4期,第72頁。“山歌社”的宗旨與實踐,應該說與延安“魯藝”的實踐目的是有一定重合的。
《民族音樂概論》的實際資源便是該書編寫過程中于1960年10月——1961年11月間完成的12本參考資料,即《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討論選錄與專題報告》《中國古代樂論》《中國近現代音樂家論民族音樂》《民間歌曲》《城市小調》《古代歌曲》《歌舞與舞蹈音樂》《說唱和曲種介紹》《說唱音樂》《戲曲音樂》《民族器樂》。?同注?,第50頁。除《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討論選錄與專題報告》之外,其余基本上就是《民族音樂概論》所含民歌、民族器樂、說唱音樂、民間歌舞音樂和戲曲音樂等的專項分冊。
綜上可以看到,《民族音樂概論》的理論概括與總結,有保留、有取舍地承接了之前“國樂”的某些理念和主張。相比較于其后建構的“中國傳統音樂”理論體系,卻又缺少“非民間”而不包含在“民族”范圍之內的一些內容。
原因何在?
據沈洽先生介紹,最早提出“民族音樂理論”這一術語,并把它用作一個獨立專業名稱的,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已故教授沈知白先生;接著,已故教授于會泳先生又提出了“民族音樂理論”專業最初的學術框架;而“民族音樂理論”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在學術上得以相對定型和推廣則可以《民族音樂概論》一書的出版為標志。沈知白先生在1956年提出“民族音樂理論”這個學科名稱。是年,上海音樂學院成立民族音樂系,沈先生為主任,即創設了“民族音樂理論”專業。沈知白提出的“民族音樂”概念比“民間音樂”要寬,它可以包括 “宮廷音樂” “宗教音樂”和“士大夫音樂”“文人音樂” 等。?參見沈洽《民族音樂學在中國》,《中國音樂學》1996年第3期,第10頁。很顯然,沈知白提出的“民族音樂理論”構想與其后《民族音樂概論》由“民歌和古代歌曲”“歌舞和歌舞音樂”“說唱音樂”“戲曲音樂”“民族器樂”共五章構成的框架是不完全一樣的,反倒是與當下“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相若。
《民族音樂概論》之所以沒有將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和宗教音樂等納入其中,書中引言部分已道明原委:“民間音樂,民主性的反封建的內容,是它的基本的主導的傾向。……其它的非民間音樂(如封建時代的文人音樂創作、宮廷音樂和宗教音樂等),它們雖不都是勞動人民的創造,而且從它們總的傾向上來看,主要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編《民族音樂概論》,音樂出版社1964年版,第4頁。在當時的編者們看來,“民間音樂”和“非民間音樂”“在總的傾向上有本質的差別”“滲透著兩種文化的斗爭”。因此,歷史上由“臭老九”創作的文人音樂、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宮廷音樂和宣傳“封建迷信”的宗教音樂當然不能包括在教材中。?杜亞雄《“五大類”還是“四大類”?——對中國傳統音樂教學改革的建議》,《中國音樂學》2013年第2期,第16—17頁。很顯然,編寫《民族音樂概論》時,是有十分明確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的。
1960年10月,《民族音樂概論》研究班編選、鉛印了學習參考資料:《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小冊子左上角特別注明“內部資料 請勿外傳”字樣),人手一冊。該冊子分“毛澤東同志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黨和中央負責同志對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的方針政策和指示”“文藝界負責同志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三部分,摘錄了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以及周揚、郭沫若、沈雁冰、茅盾、夏衍、呂驥和周巍峙等包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文學藝術中的關鍵性問題》《繼承和否定》等言論和文章68篇。小冊子摘錄的言論,具有旗幟鮮明的綱領性指導意義,對如何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有明確的主張。例如:
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的兼收并蓄。?《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1960年,第4頁。摘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871頁。
無產階級對于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他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態度。?《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1960年,第5頁。摘自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700—701頁。
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1960年,第8頁。摘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小冊子上錯寫為1942年3月,筆者注),《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857頁,第62頁。我們要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武裝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對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進行批判。?《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1960年,第12頁。摘自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1956年9月15日);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42頁。
對于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的接受它,以利于推進中國的新文化。?《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1960年,第8頁。摘自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84頁。
要繼承民族藝術的優良傳統,一方面必須廣泛地進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須首先對于目前在群眾中最流行的舊有藝術形式進行改革的工作。……在音樂方面,應繼續加強民間音樂的研究工作,并注意中國的戲曲音樂,說唱音樂及中國民族器樂的研究與改造。……我們整個文藝工作的任務,主要的不是保存民族舊文學、舊藝術,而是發展民族新文學、新藝術。?《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1960年,第17頁,摘自周揚《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在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講話,見《文藝報》1951年6月第4卷第5期,第6—7頁。
無論繼承傳統或學習外國,都必須有批判的態度。……繼承傳統,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加以保存,也不是無批判地模仿。保守主義,故步自封,只能使傳統陷于停滯和衰落。傳統只有經過創造性的發展才能得到真正的繼承。?《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1960年,第30頁,摘自《周揚同志的發言》,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510—516頁。
總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在《論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中表述得十分明確,即站在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批判地繼承”,“民族”之根本由此體現。具體于如何“取”“去”以及怎么“批判”“繼承”,《民族音樂概論》的立場和呈現出的樣貌已經有所體現。緣于特定的時代背景,編寫《民族音樂概論》時,我國正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社會上彌漫著極左思潮,音樂學界當然也會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同注?。
三、“中國傳統音樂”,承載著怎樣的歷史和現實之內涵與外延?
早年,楊蔭瀏先生曾說過:“國樂全部的事實,決不是某一點理論,某一種樂曲,某一種樂器,或某一樣技術所可以代表的。從縱的方面說,我國有史以來,凡有音樂價值的記載、著作、曲調、器物、技術等等,都是國樂范圍以內所應注意的事實;從橫的方面說,中原以及邊地各省各市各村各鎮的音樂材料,和曾與、正與、或將與本國音樂發生關系的他國音樂的材料,也都是國樂范圍以內所應注意的事實。”?楊蔭瀏《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中國音樂學》1989年第4期,第4頁。這是從全部互有關系的古今中外音樂中審視國樂問題。?魏廷格《再議楊蔭瀏的國樂觀》,《民族民間音樂》1994年第2期,第4頁。
在筆者看來,面對當今中國傳統音樂的事實,學者們仍然保持有楊蔭瀏當年倡導的對國樂進行研究的態度,正是“從全部互有關系的古今中外音樂中”“審視全中國”現象。在回答什么是“中國傳統音樂”的問題上,已經展示出這種精神和態度:“中國傳統音樂是指在中華民族大地上歷代產生并大多流傳至今和在古代歷史長河中由外族(包括現屬于我國的少數民族和國外民族)傳入并在我國生根發展的一切音樂品種。所謂‘歷代產生的’:既包括了古代的也包括了近、現代的(如某些樂種有上千年的—古代—歷史,也有些樂種只有幾十年的—近、現代—歷史,像某些地方小戲)。”?參見董維松《關于中國傳統音樂及其分類問題》,《中國音樂》1987年第2期,第41頁。具體到傳統音樂的實際包含,則大體將之分為四類:一是民間音樂,二是文人音樂,三是宗教音樂,四是宮廷音樂(當然都是“中國的”)。此外,有些品種可能還不能歸到這四類中去,那么,就只好籠統稱之為“傳統音樂”。?同注?。從這一架構、體系中可以看出,原本“民族”的概念和屬性仍然保留,沒有改變,整體以“民間”作歸納放置于其中,展示以廣大人民群眾為基礎而創造、流傳的民間音樂面貌。非普通民眾創造和享用的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與“民間”并列,共同列入“傳統”之中。于是,各有其所,本質、屬性相異的民間、文人、宮廷、宗教四大類別共存相容,形成傳統音樂學科調整后建立在宏大歷史、文化觀念上的新體制。
以《中國傳統音樂概論》?王耀華、杜亞雄編著《中國傳統音樂概論》,海峽出版發行集團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為例,在編著者博大深廣的視野里,中國傳統音樂,實際上是以歷史中國、傳統中國、文化中國來定義的一個概念和范疇。與之前的《民族音樂概論》相比較,增加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等內容而擴充了新體量的傳統音樂體系,不能說從根本上改變了原先民族音樂理論這一學科的基本框架、實質內容和理論觀念,但可以說一定程度上補充或改寫了民族音樂理論的歷史。“民族音樂”被“中國傳統音樂”取而代之,很顯然不只是簡單的易名改稱。如果說“民族音樂”是因為包含國家、民眾、民族諸關系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人民”屬性而有此稱謂的話,那么,改稱“中國傳統音樂”則是具體、實質性地以文化為主導,現象、事實為依據,以傳統概念作定性而規約、規范形成的學科或者說學術體系。我們看到,名稱的改變,不僅僅有上述實際指代關系和范疇的改變,改稱后的實體內容更有超出我們一般認知程度上的重大調整。《中國傳統音樂概論》總體將始于《民族音樂概論》作概括的民歌、民族器樂、說唱音樂、戲曲音樂、民間歌舞音樂統歸到“民間音樂”為一大類,與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另外三大類并列構成傳統音樂新體系,在《中國傳統音樂概論》編著者之一的杜亞雄看來,“全面了解我國傳統音樂,是建設中華民族新音樂文化的需要,為達此目的,我們應當加強對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和宗教音樂的研究,同時在教學中改變用民間音樂五大類代替傳統音樂四大類的情況,在教材中適當地增加有關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和宗教音樂的內容。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使下一代全面地了解我國的傳統音樂,使他們能夠繼承、利用和改造傳統音樂,為發展中華民族的音樂文化做出貢獻。”?杜亞雄《什么是中國傳統音樂》,《中國音樂》1996年第3期,第17頁。
建立起“中國傳統音樂”這一理論體系,應該說是改革開放政策落實,思想觀念、文化覺悟、文化態度發生改變、對傳統文化重新認識的體現。1978年開始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幾許相似于當年五四運動之后的社會狀態,而且影響更加猛烈。改革開放,一方面是要將國門打開,向西方開放,向全世界開放,另一方面要對國家自身舊有的體制進行改革。從部分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轉變,尤其是農村包產到戶等一系列農業政策的改革和實施,使得“民族音樂”的主要創造者和接受者——“人民”,不再以“勞苦大眾”的身份和狀態出現在國家、社會之中,而是逐步走出原本固有的生活模式,開始以多元、多樣化身份成為國家的主人。
所以,從民族音樂到中國傳統音樂這一轉變,首先是“人”的轉變。這里的“人”,即傳統音樂現象的觀察者和傳統音樂現象的當事者。觀察者有了新的覺悟,不再是帶有部分主觀色彩的“批判者”持“批判地繼承”態度,有取舍地看待或對待觀察對象;當事者有了新的姿態和身份,不再是“被壓迫階級”“勞苦人民”,而是享有同等社會權益的國家公民。“傳統音樂”因此而由被“批判地繼承”變為受“尊重地呈現”。其次是音樂體量有了調整、增大,而這一體量的增大,并不是因為傳統音樂理論誕生之時,傳統音樂實際狀態發生了改變,學者們將之增補進去的,而是某種程度上原本存在的現象得以再認識的結果。那么,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就在于,如果在我們的理論認知、文化覺悟以及我們對待傳統音樂的態度和方式有了改進、完善,對傳統音樂理論的體量做重新審視、規劃時讓上述傳統得以回歸的話,那么,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就是,被重新納入中國傳統音樂體量中來的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和宗教音樂這三大部分,在我們的傳統觀念和具體行為上到底處在一個怎樣的位置?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由此引發出來的是我們如何看待它,認識它,進而如何研究它的問題。
在認同傳統音樂“不僅包括在歷史上產生、世代相傳至今的古代作品,也包括當代中國人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創作的、具有民族固有形態特征的音樂作品”?同注?,第3頁。這一基本概念和界定的同時,在面對如何解釋“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屬性和特征時,仍然存在著是將它們當作“歷史”現象看待,還是當作“傳統”現象看待的實際問題。畢竟,歷史與傳統是兩個不盡相同的概念。
回到具體現象本身來探討。
先說宗教音樂。宗教音樂之前被排除在“民族音樂”之外,是因為它不是勞苦大眾享用的音樂,屬性上不吻合“人民”的概念、要求和標準。因為它唯心、迷信,是有悖于唯物主義世界觀而“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所以它從人民可以認知、受用的范疇中被剔除。當它再重新回歸到中國傳統音樂的視角之后,它的實際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毫無疑問,國家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有了憲法保障,應該說普通民眾開始對之有了重新的認識。在這一基礎上,對宗教音樂的研究這幾年迅速成為熱點。以道教音樂研究為例,對道教音樂研究的文獻進行檢索和統計不難發現,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關研究呈迅猛增長態勢,并一直持續至今。?參見拙文《當代道教音樂研究之定量分析(1957—2008)》,《音樂研究》2008年 第2期,第115—127頁。這一現象的出現,不僅僅是因為宗教音樂回歸到了傳統音樂理論的大家庭后被認同、被認知而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視,更主要的是有了被普通民眾接受的社會文化基礎和條件。所以,這一問題于學界看來,是中斷了以后,恢復、重構再繼續研究的狀態。
于文人音樂而言,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當下時代還有對應得上 “文人音樂”的現象存在嗎?回答這一問題,如何認定、理解和解釋“文人”是前提。
“文人”一詞,字面上可解釋為有著較高文化修養和底蘊的群體。它衍生于周王朝的“士”階層,最初是指為官之人。后來指有才能之人。而“文人”一詞的首次出現是在《詩·大雅漢江》中:“告于文人,錫山土田。”這里沿用了“士”的解釋,意指有才能之人。從后來的一些文獻中不難看出,“文人”就其字面義而言,一直用以指帶有文德之人。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人的身份卻處于一直變化的狀態中。五代以前,文人以王公貴族居多,社會地位較高,“養士”之風盛行。比如在《孔叢子》中就說道:“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到了五代,隨著科舉制度的確立,我們可以從當時的一些文獻記錄中看出,文人的身份發生了轉變。除原本帝王文人以外,這一時期出現了貧庶文人、僧道和女冠。由此可見,文人的身份出現了階層下移的現象。明清時期,科舉制度的取消徹底打破了原本“士、農、工、商”的階級排序,文人的身份再次發生變化。
到了現代社會,科技的發展和分工的細化,促使文人從眾星捧月般的位置,變身為百業之一,諸如科學家、工程師、教師、醫生等都是有文化的人,但他們從事的職業,已經與文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分界,顯見的事實就是文人的邊界已經模糊。
“傳統音樂”中所見的文人音樂仍然歸于古舊的文人概念。當今,如何看待文人音樂遭遇到的現實情形是,舊時的文人狀態、文人品格、文人修養以及文人所享用的精神和物質狀態,在當下已經不復存在。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便是,文人音樂已經走進“歷史”不再“傳統”,我們如何解釋和認知置之于“傳統音樂理論”之中的它呢?
再說宮廷音樂。帝王制度的滅亡和封建體制的消失,宮廷早已廢除,伴隨著宮廷而產生的宮廷音樂便隨之載入史冊成為歷史現象。當它被納入我們今天所認知和使用的中國傳統音樂理論體系的時候,我們該如何于傳統的角度、傳統的觀念將其當作傳統音樂現象來看待呢?必須肯定的是,今天大量存在的傳統音樂現實狀態中,可以窺見古代宮廷音樂之遺存。但無論遺存也好,還是部分轉換、變通到其他傳統音樂類別中保存至今也好,作為宮廷音樂之概念作解釋,從宮廷音樂獨有的特性、特質上來看待,這種形式,這種現象于今天體現在哪里呢?
值得一提的相關現象是,當今納入高等院校教學體系中的相關中國傳統音樂課程的教學,并沒有在已經從名稱到實際內容發生了改變的狀況下做應變調適。也就是說,中國傳統音樂的教學仍然還是以當年《民族音樂理概論》的理論框架和實際內容作為主體教學內容。其中增補的宗教音樂多見專題性講習或單獨開設課程,文人音樂和宮廷音樂則在音樂史課程中教授。出現這一現象,與其說教學安排上已經習慣舊有格式,改名而不變其實,還不如說中國傳統音樂理論這一概念和學科,仍然面臨一些實質性的無論是來自于理論體系本身,還是實際操行中的現實難題。
從“國樂”到“民族音樂”再到“中國傳統音樂”,從單一邏輯看,似乎是固有傳統音樂一個漸次發展的路向和軌跡。但通過三個階段的回顧與梳理可以看出,它并非如同我們想象那般,是歷史自然發展的順序和規律,而是在我們認知體系、認知覺悟以及對待文化的態度、觀念受制于特殊歷史、社會、政治和文化等狀態下,有人為取舍、干預甚或改變的事實記錄。
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音樂已自成體系。而對其進行系統而又相對獨立研究的理論體系,是否也已經形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