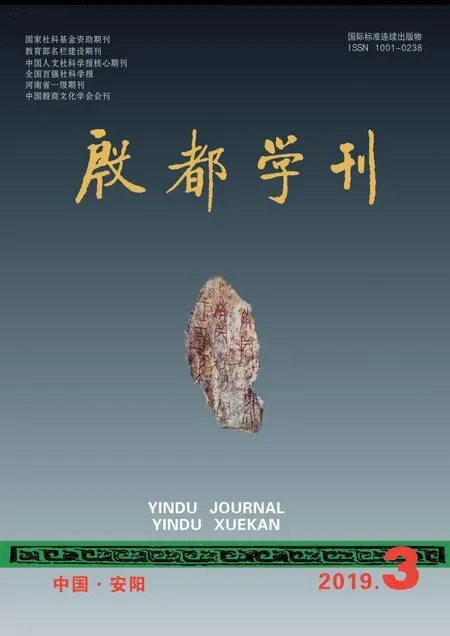皖系軍閥的對日外交策略
賈德威
(濰坊工商職業學院,山東 濰坊 262234)
在中國歷史上,皖系曾經作為北洋軍閥的核心登上了政治舞臺。在其統治時期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如對德參戰、府院之爭、張勛復辟、西原借款、中日軍事協定、直皖矛盾、南北議合、巴黎和會直至直皖戰爭,無不打有日皖勾結的烙印。從當時的社會狀況來看,日皖的所謂親善與合作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日皖之間對各自利益的維護,成了決定二者關系親疏的最根本的驅動力。所以,日皖的勾結,拋開人為的偶然性因素之外,我們還應看到這其中的許多歷史必然性的因素。
從皖系軍閥方面看:
首先,在皖系所處的外部環境中,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雖然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權,但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以及南方實力派等都大有問鼎中央的野心與實力。所以在暫時形成的南北統一政治局面的背后,正在醞釀著新的矛盾和斗爭,南北各派都在堅守著自己的實力和權益,圍繞著爭奪對中央的控制權而在不斷地進行組合與分化。所以,段祺瑞絕不可能像袁世凱那樣成為北洋軍閥的絕對權威和首領,他必須以保有強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實力為支撐,才能保持并穩定自己的統治地位。
其次,在帝國主義勢力遍布中國的情形下,尤其是在各個軍閥及派別或以英國,或以美國,或以德國為靠山的情況下,皖系軍閥為了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站穩腳跟,也極需一個強有力的外援做后盾。當時的歐美各國正忙于歐戰,不可能也沒有精力再去全力資助段內閣,當時只有日本有此經濟實力和政治精力,因而日本也就成了皖系最希望投靠的對象,這也為日皖的靠近奠定了基礎。
再次,從皖系軍閥的內部組成看,在段祺瑞的皖系班底中,核心骨干人物如徐樹錚、曲同豐、傅良佐、吳光新均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皖系結成聯盟的新交通系成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也于清末留學日本,他們都與日本有著無法割裂的淵源,同時他們又是皖系的決策和智囊團,而段祺瑞又對他們言聽計從,所以他們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皖系的外交視線轉向了日本,因而這些人就成了日皖合流的牽線人和催化劑。
從日本方面看:
歐戰的爆發,歐洲列強的勢力從遠東逐漸后退,列強對日本在華侵略的牽制與約束也隨之減弱。無形之中,這也就為日本推行其“大陸政策”提供了契機。所以日本方面才認為“目前是日本迅速解決中國問題最有利的機會,這樣的機會是千載難逢的”。[1]寺內內閣上臺后,雖然改變了大隈內閣時期日本軍閥、政客所慣于采用的赤裸裸的軍事威脅、攫取利權的做法,而換上了一幅“友善”的面孔,但其侵華的實質沒有改變,只是把邪惡的黑手掩藏在了身后。在以經濟援助為主要手段的侵華政策下,日本也同樣需要在中國扶植一個親日政權作為內應。而此時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由于袁世凱的死亡,北洋軍閥集團失去了維系的中心,各派之間勢均力敵,都覬覦中央政權,但又都缺乏控制全局的實力。鑒于“國民黨只有議論,毫無實力,段祺瑞既得國會之一致承認,又有相當力量,則援段較為賢明”[2],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理所當然地成了日本的寵兒,日皖的勾結與合作也就此拉開了序幕。靠著日本的支持,段祺瑞武力統一的政治雄心勃然而發,不斷排除異己,連年大打內戰。而日本從段祺瑞那里也使許多懸而未決的案件得以“圓滿解決”。
在日皖以“親善”為幌子的勾結與合作中,既有日本的積極拉攏,也有皖系軍閥的主動投靠,它是種種復雜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共同作用的結果。因為任何一種所謂的“合作”都是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展開的。不存在沒有付出的回報,也不存在沒有回報的付出。日皖的合作及相互勾結,其原因與動力也是“互惠互利”的,日本投之以桃,皖系軍閥就要報之以李,只有這樣,所謂的合作才會進行下去。
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對立的統一體一樣,盡管日皖之間有許多共同的政治使命,但日皖之間也同樣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雙方都是在固守著自己的政治利益與精神信仰,表面的、暫時的一致與趨同的背后,也有著雙方各自的計謀與籌劃。所以盡管段祺瑞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勾結”,有大量確鑿的事實可以證明,但孤立地看待事情結果,而忽略事情的經過,籠統地稱之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或“工具”,并不完全合乎歷史的真相,“因為其間往往是隨時隨地而有極多變化和復雜的內容”。[3]
近代中國的貧窮、動亂及帝國主義的侵入,使得中國的外交有種底氣不足的軟弱和急功近利的短視,所以皖系軍閥的對日外交開始的基準點就已經移位了,它不再是兩個國家平等的“互惠互利”,而是以皖系軍閥的“欲求”和日本的“予取”為特征的,是一種缺乏平等、尊重和互利的被扭曲了的外交關系。所以皖系軍閥在獲得一定的政治與經濟援助的同時,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日本的欲望和要求。
江蘇督軍李純在給馮國璋密函中曾說“日本近年以詭詐舉動,攫取英法各國的東方利益,又欲壟斷中國權利,置之保護之下,野心昭然”。[4]一個封建督軍尚能窺見日本的野心,作為一個久經沉浮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段祺瑞“無論從資歷上,從性格上,從手腕上”,“實為中國軍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對此任何人皆無異議”。[5]所以對于日本日益膨脹的政治野心段祺瑞又豈能不知,在必須依靠日本援助的同時,在“親善”與“友好”的面照下,無論是出于統治者的責任、個人的道義還是民族的尊嚴,他都必然要采取一些策略,這一點從日皖交涉的過程也是有跡可循的。
一、“親善”背后的利用
日本雖然一再以日華“親善”來標榜與粉飾他的對華政策,但其與皖系軍閥的合作與勾結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日本企圖借助皖系軍閥之手,使日本對華已提出而未落實或尚未達到目的的侵略要求得以一一兌現,并進一步擴大其在華利益,實現其“大陸政策”。而皖系軍閥也同樣想借助日本的力量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壓制直系、奉系及南方實力派,進而實現武力統一的野心。所以相互利用是日皖勾結的實質,日本與皖系的合作處處都打有相互利用的烙印。
皖系軍閥的政治命運是幾經沉浮的,而在這些升降沉浮之中,皖系幾乎都是依賴日本而使其黑暗的政治前途又數度重現了光明。以張勛復辟為例,段祺瑞為了重返政治舞臺,就曾以保障日本在華利益為誘餌,借助日本對黎元洪、張勛施加外交壓力,并在日本的經濟援助下而實現的。西原龜三“第四次中國之行,目的就是鎮壓張勛復辟和復活段內閣”。[6]段祺瑞的討逆軍費,甚至為收買駐守天壇辮子軍的8萬元開支,都是來自日本的資助。[7]所以段祺瑞在重新執政后,再次十分明確地向日本表達了如下意向:“中國政局幾經變化后,我再度出任總理,將來一切施政,當按預定方針進行”[8],頗有用完之后,為表感謝以示回報的意味。
中國封建軍閥統治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時局和社會總是處于風雨飄搖、瞬息萬變的情形之下,各種勢力的爭斗和較量都有一觸即發之勢。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為了能在這種角逐當中力主沉浮,離開日本的援助是絕然不行的。在一無錢款,二無供給的情況下,只能以逐步滿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為代價獲取援助,從而維持自己的統治。在經濟上,僅西原借款一項,其金額就達1.5億元,而寺內內閣期間的對華借款總額竟達2.1億日元以上;在軍事上,日本為其編練了參戰軍。參戰軍系日本軍械裝備,并由日本派出教官訓練的正規軍,其所需經費也來源于日本提供的參戰借款,受參戰督辦段祺瑞的直接管轄。雖然性質上相當于日本的駐防軍,但對于緩解皖系的統治危機,其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外交上,皖系也正是借助于日本來抗衡以英美等國為靠山的直系及南方實力派,使其免受外交的孤立與列強的威脅。所以皖系軍閥在滿足日本侵略要求的同時,也以利誘的形式換取了日本在經濟、軍事和外交上對自己的援助。也正是仰給于日本的援助,段祺瑞才得以不斷擴充自己的勢力、排除異己、破壞和談、武力統一中國的政治資本。
所以,日皖的勾結與合作是以相互利用為始終的。盡管二者的終極目標并不一致,但借助于或利用對方,他們都可以各取所需。直皖大戰失敗后,東京《朝野新聞》8月3日社論說:“無論如何,段派比之其它各派較了解日本所與中國的利益”“因彼派有利用日本的勢力,以固其立腳地的傾向,此系事實”。[9]所以當皖系軍閥一旦失去了日本的外援后,段祺瑞苦心經營多年的邊防軍及安福御用組織,雖然曾經貌似強大,但因為沒有了根基,在外力的沖擊下便轟然倒塌了。
二、“友好”之中的戒備
皖系軍閥統治在中國正式確立后,它所面臨的經濟形勢是十分嚴峻的。政府維持正常開支的費用“每月約二千萬兩,而財政部可靠之收入每月只余關余、鹽余、煙灑稅、印花稅等等,合計不足一千二百萬兩,尚短八百萬兩,則借款為彌補”[10]。誠如章宗祥所說:“借款非理財之根本策,此人人所知,然自民國成立以來,財政紊亂,整理需時,為維持現狀計,舍借款幾無他策”,“以西原之提議起,以無折扣為主義,輕其擔保,破除向來借款之苛例,又以實業為名,不涉內政”[11]所以僅以此點言之,中國如欲借款,自惟此種債主是趨[12]。所以盡管皖系極需而且必須要用借款,但鑒于日本以往的政治訛詐以及侵略野心,皖系軍閥也有一種本能的懷疑和戒備心理,也是經過了一番權衡與探詢的。西原龜三回憶錄中有曹汝霖對他的試探“寺內內閣所標榜的中日親善,遠東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綱領我已充分了解,并認為是十分良好的,但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償,是否還準備了第二種政策呢?”,“寺內首相的第二種政策是吞并東三省吧!”“寺內首相既有此意,我方當慎審考慮,有所抉擇”。所以在西原借款中,皖系軍閥對于日本的真實意圖與目的也是有所懷疑的,也是經過“慎審考慮”而做出的“抉擇”。
再以一向被中國人認為是皖系軍閥賣國、禍國罪證的中日軍事協定而言,雖然有日本駐兵東三省的野心,但其中也有著段祺瑞對于日本軍事實力的垂涎。在訂立期間,段祺瑞對于日本也存在著相當的懷疑和戒備。交涉過程中段祺瑞曾多次電告章宗祥“部意中俄接壤,關系密切,非至必要時,萬不可輕于用兵,第一步只能作為實行準備”[13],“此次共同防敵,乃一時的,若措詞稍一不慎,竟成類似攻守同盟條件,則責任異常重大,尤須審慎”[14]“惟此項文件,詞意必須明確,電內條文,若解釋微有出入,所關甚巨”[15]所以在皖系軍閥對日本的曲意迎合與屈從之中,其懷疑與防備之心也鮮明可見。
章宗祥在《東京之三年》中有記載:“自日德宣戰后,青島為日本占領,中國深慮日本有繼承德人權利之意,故關于德人在山東之權利問題始終不與日本開始交涉。當時膠濟鐵路本與津浦鐵路聯運,自青島戰后,津浦即將聯運停止,膠濟以客商不便,屢請復舊,中國不允,有戒心也”。[16]
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皖系軍閥雖然曾對日本表示了某種“大度”與“友好”,甚至有呼必應,但對日本的野心也不是毫無戒備的,而是處處存著提防之心,害怕“上當”。皖系軍閥對日本的這種閃爍不定的懷疑與戒備,既是由當時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決定的,也是出于弱者對于強權的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自衛的本能。
三、“追隨”之下的抗爭
皖系軍閥的對日外交表現,國人向來以“賣國”一言以蔽之。但仔細品讀這段歷史,也往往不難發現,皖系軍閥在不斷滿足日本侵略欲望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力求為中國爭回一些不必要喪失的主權和利益。盡管這種努力收效甚微,也絲毫不能改變日皖勾結的性質,但孤立地看待事情的結果,而割裂當時的社會環境,就無法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所以在日皖的種種交涉中,皖系軍閥的努力雖然效果不大,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它的存在。
在對德問題上,日本極力慫恿、勸說乃至利誘中國對德絕交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皖系軍閥雖然不敢違逆日本的方針,但鑒于日本的這種迫切心理,雖然在外交照會中一再聲稱“絕不含有交換利益之意”,但隨之也聲明“惟外交既有變動,則財政必生影響”,“如聯合國允我酌加關稅,及將庚子賠款緩解或延長年期,則于目下財政不無裨益”,并致電章宗祥“望先向日外部密探意見,并盼其(日本)助成此舉”等等。對于皖系軍閥的“據理力爭”,日本則斥責中國政府“雖表面聲言并非交換,而事實抱有交換之隱衷”,聲明“日本政府實愿真心與中提攜,中政府總宜將策略收起,方可誠意接洽”[17]。盡管弱國外交常常隨權勢而左右搖擺,但中國最終獲得提高關稅及緩交庚子賠款等利益,就是在皖系軍閥對日本的一再要求和反復交涉下而實現的。章宗祥在其所著《東京之三年》中有記載“在交通銀行借款中,就事論事,當局者破除舊例,竭力為國家爭回利權,當日亦費盡苦心也”。[18]
《中日軍事協定》的成立,暴露了日本侵占北滿及東三省的野心,它的成立完全出于日本的主動。在日本的威逼利誘下,皖系軍閥也表示了認同。但在行軍區域、換文方式等一再堅持自己的立場,同時力求以“山東問題及東三省懸案從速和平解決”為條件做交換。段祺瑞指出“關于山東問題的解決,并不僅止于撤退山東鐵路問題”“希望把青島建成中國的一個軍港”[19]。雖然結果未如人意,但皖系軍閥的“趁火打劫”的用心也是存在的。
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理應收回原本屬于自己的權利,而在日本的粗暴干涉和無理要求下,皖系軍閥最終也表示了“合作”的立場。但事實如果真如小幡酉吉所說,日皖之間已經達成了完全意義上的默契和一致,也即皖系軍閥堅決果斷地一定要賣國,態度明確而毫無游移,那么作為中國代表的顧、王二使就不會全然違背政府的立場。段祺瑞通電北京政府,主張放棄山東權利時說“歐約如不簽字,國際聯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條件,一切放棄,又恐如外蒙宣戰事,借愛國以禍國也”。[20]這雖是政客的詭辯,但其也聲稱“青島問題,顧、王兩使爭執直接交還,國家有利,未嘗不是”。由此可以看出,在不損害“日中親善”的大前提下,皖系軍閥也試圖并希望多爭回一些國家權益。一可平息民怨,二可增加政府的威信,其立場雖不堅決,卻也有此意愿。所以在日皖的勾結中,皖系軍閥也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附合,雖然雙方互伸橄欖枝,但由于其根源于不同的母體之中,所以也有矛盾,有爭奪,盡管他爭回來的相對于送出去的少之又少,但也確曾努力過。
四、屈從之中也有背離
皖系軍閥與日本的勾結,始終披著“日華親善”的面紗。在其政治方向一致時,表現出了無比親密的融合,但兩者的終極目標并不完全一致,它們各自都有著自己的企圖和野心,因而這種“親善”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礎上的,是暫時的,也是脆弱的,當外力松動了這種融合,使二者的政治方向發生偏轉時,其矛盾也就凸顯出來,雙方各自趨利避害的本性也就暴露出來。所以皖系軍閥在屈從日本的同時,當危及它自己的統治利益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與日本相背離的傾向。
在參加歐戰問題上,皖系軍閥雖然以日本的外交態度為導向,提出對德斷交。但從中日交涉的外交照會中可以看出,皖系軍閥對于是否參戰的游移態度。一方面,參加歐戰,害怕日本會借口加強中國沿海的防御而侵犯中國的領土;另一方面,不參加歐戰,又害怕中國在外交上喪失主動權。最后中國通過對德絕交案,其中雖有日本的極力慫恿,但主要的也有皖系軍閥尤其是段祺瑞對于歐戰時局的把握:“多維爾海峽連當年的拿破侖都未都渡過,英國陸軍雖弱而海軍強大,德國要想擊敗英國海軍,渡過海峽,看來是沒可能的。”[21]正如西原龜三所說:“如果俄國革命提前三四天,或者中國對德斷交推遲三四天,我的一場艱苦努力很可能化為泡影了”。[22]
對于南北和談,日本雖然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但考慮到自己的外交形勢和將來的在華權益,還是背叛了極需幫助的皖系,而做出了諸如:停止對華借款、參加五國對華和平勸告及禁止對華輸出軍械武器等措施。皖系軍閥在中國的統治權,對于維護日本的在華權益是有利的,但不是唯一的。對皖系軍閥而言,獲得統治權則是其最終目標,也是其存在的唯一前提。所以對于呈現兩面性、半推半就的日本,皖系軍閥對日本的態度也遠非我們所想像的那么堅決果斷。徐樹錚在其致皖系軍人的密電中“今日政局,和為必不可能,明眼人皆知之,而不許人言和又為情理所不宜,惟我輩主戰之人,只好估從默爾,切整軍實,專蓄戰力,預作扶危定傾之備”。[23]所以,在屈從日本不論出于何種動機的南北和談的照會下,皖系軍閥為維持自己的統治,仍然有著自己的盤算,即極力地破壞南北和談,企圖實現武力統一。
五、妥協的背后也有拒絕
皖系軍閥在中國的統治,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軍事上很大程度都依賴于日本,所以為維護并鞏固自己的統治,向野心勃勃的日本做出妥協與退讓是必然的。但這種妥協與讓步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因為既然妥協的前提是為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那么對于動搖或破壞他統治權益的不情之請,他也就不會也不能再讓步和妥協了,一定并必然加以拒絕,此即為妥協的最底限。
在西原借款中,日本曾欲在中國發行金本位紙幣,“關于金紙幣問題,前曾考慮由中國、交通兩銀行發行,由于段總理有異議,遂議定創設幣政局掌握發行”[24]。在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很行是全國最大、最主要的銀行,是管理中國政府國庫的重要的金融機關,它們都擁有紙幣發行權,是中國政府的機關銀行。日本想在這兩個銀行發行金紙幣,其目的是使中國貨幣與日元聯系起來,將中國貨幣變為日元的附庸,從而控制中國的金融和經濟命脈。但日本的陰謀最終由于段總理的“異議”而遂告破產。
再以中國人一向詬病的鐵路借款而言,滿蒙四路及濟順高徐鐵路借款,雖終簽字,但“此中曲折,固非局外人所能推測者矣”[25]。借款成立前,日本外務省一再堅持滿蒙鐵路運輸會計兩主任均用日本人,以便于日本對中國的控制。而段政府“堅持不允,答以從前京奉鐵路奉隴海路均許外國人辦運輸會計主任,侵害中國主權甚多,萬難同意”[26]。再后來,日本欲請早已下野的段祺瑞重新組織日本的偽政權,段祺瑞曾堅決拒絕。
從這些歷史資料和歷史活動可以看出,皖系軍閥對于日本的要求和企圖并非是有求必應的。當日本的野心觸及到他的心理承受的最底限時,他必然要拒絕。因而皖系軍閥的對日外交原則就成了,可以借款,但不能完全合流;可以割讓,但不能全盤霸占;可以追隨,但絕不做傀儡。在皖系所認定的某種限度之內,什么都可以讓,都可以給,但超越了他所能承受的程度,也就必然要拒絕,如段祺瑞所說:“利害關國家,胡可安緘默”[27]。
綜合以上各方面,從皖系軍閥與日本“勾結”的各種歷史活動和交涉中可以看出,皖系軍閥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對于日本,它曾經追隨、妥協、屈從甚至不惜出賣國家主權為代價,但此間也有皖系軍閥壓制日本,以求自保甚或自強的一些策略。在十分軟弱而且有著極度依賴性的對日外交中,也有戒備,有利用,有敷衍,更有力爭和拒絕。盡管這些這些策略無法改變其日皖勾結的實質,也并未扭轉歷史的最終走向,但結合當時具體的歷史環境,客觀地看待這些策略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皖系軍閥對日外交的失敗,錯不在于這些策略的有無與得失,而是其根本出發點發生了偏移。把個人或集團的利益凌駕于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處處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為準繩,甚至以出賣國家權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它的援助,只抓住了自己的點而忽略了國家的面。所以皖系軍閥在對日外交中的種種策略收效甚微,以致于讓許多人在其所出賣的巨大的國家利益面前,完全忽略了皖系軍閥曾經有過的掙扎、牽制與抗爭,但任何一個歷史活動和歷史事件的產生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種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評價皖系的對日外交,不應只注意到他的妥協與退讓,而回避其對日本所采取的一些策略。因為正是這所有要素的總和,才構成了皖系對日外交的全部內容,才能真正勾畫出日皖外交的歷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