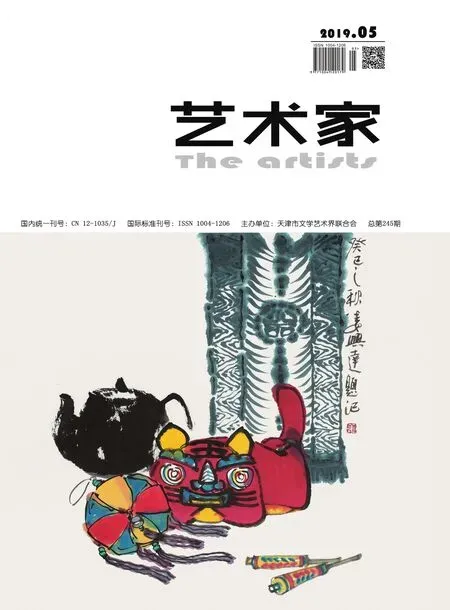《富春山居圖》作品賞析
□張 辰 魯東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
《富春山居圖》以浙江富春江為背景,全圖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當(dāng),墨色濃淡干濕并用,極富于變化,是黃公望的代表作,被稱為“中國(guó)十大傳世名畫”之一。
像《溪山行旅圖》這種鋪滿畫面的畫作,巨峰壁立,幾乎占滿了畫面,山頭雜樹茂密,飛瀑?gòu)纳窖g直流而下,山腳下巨石縱橫,使全幅作品體勢(shì)錯(cuò)綜,給人一種氣勢(shì)磅礴的感覺。而《富春山居圖》則給人以完全不同的感覺,《溪山行旅圖》的畫面具有強(qiáng)烈的震撼感,在畫面中,范寬把景色、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可《富春山居圖》卻有著大片的留白。空白的延續(xù)使畫面有趣了起來(lái),那種水平線延長(zhǎng)的感覺,追求的是一種水平的力量,從小土堆開始,慢慢地出現(xiàn)了樹木、小山丘,然后是高大的群山,群山過(guò)后,映入眼簾的又是一棵棵不算太茂盛的樹木……如此反復(fù),斷斷續(xù)續(xù),起起落落,有高潮,有低谷,仿佛是生命的過(guò)程,生命的最后就是留白的意境;又仿佛是在訴說(shuō)著一個(gè)故事,那一個(gè)個(gè)的小山丘就是故事情節(jié),或平平淡淡,或跌宕起伏,看的叫人深陷其中,無(wú)法自拔,這就是卷軸的力量。
《富春山居圖》用筆利落,黃公望雖學(xué)習(xí)借鑒了董源、巨然一派的風(fēng)格,但比之董、巨更簡(jiǎn)約,更少概念化,因而也就更透徹地表現(xiàn)了山水樹石的靈氣和神韻。畫作筆法中既有濕筆披麻皴,又加些許長(zhǎng)短干筆皴擦,在坡峰之間還用了近似米點(diǎn)的筆法,濃淡迷蒙的橫點(diǎn),運(yùn)筆勁道十足,表現(xiàn)力極強(qiáng)。除此之外,黃公望還極注意層次感,前山后山的關(guān)系改變了傳統(tǒng)屏風(fēng)似的排列,取而代之的是由近到遠(yuǎn)自然消失,虛實(shí)相生,過(guò)渡微妙。
山峰多用長(zhǎng)披麻皴,準(zhǔn)確地表現(xiàn)江南丘陵的特征;平沙則用淡墨勾勒,恰如其分地做到了文人畫所推崇的“惜墨如金”的審美要求。在布局上采用積樹成林,壘石為山的方法。基本上是對(duì)江南董、巨兩家的演變與傳承。但黃公望把宋人的“深遠(yuǎn)”以“闊遠(yuǎn)”代之。宋畫的構(gòu)圖,通常是由近景到遠(yuǎn)景層疊上升,正是這一“闊遠(yuǎn)”使宋畫成為元畫。在對(duì)宋人傳統(tǒng)的繼承上,還包括了“思”與“景”兩個(gè)方面的有機(jī)聯(lián)系。對(duì)黃公望而言,董源的程式語(yǔ)言和風(fēng)格特點(diǎn),使他自然地聯(lián)想到故鄉(xiāng)常熟虞山的景觀特征。從心理學(xué)角度來(lái)看,這是最能引起共鳴的。而富春江兩岸的風(fēng)光,又恰好進(jìn)入他以往的審美理想之中。所以,師傳統(tǒng)與師造化在這幅杰作中完美地結(jié)合在一起。
這幅畫中的山?jīng)]有棱角,也沒有鋒芒,給人以厚重的感覺。沿著水平線觀看,我們可以看到書法,這上面寫著“無(wú)用”二字,明顯是莊子道家的學(xué)問(wèn),講究隨心隨性。同時(shí),這也可以看得出中國(guó)山水畫的變化,之前的山水畫向來(lái)是畫得很工整,像《千里江山圖》《漁父圖》《瀟湘圖》之類的,而從《富春山居圖》這類山水畫之后都有著“隨意”的特點(diǎn),這得益于倪瓚所推崇的“逸筆草草,不求形似”,元代畫家倪瓚在《答張?jiān)逯贂分袑懙溃骸敖袢粘龀峭忾e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處,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diǎn)染,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為圖之意。仆之所謂畫者,不過(guò)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shī)识!逼渲校耙荨敝傅氖菚鴮懶刂械囊輾猓刂杏泻迫徽龤猓@樣才會(huì)真正不為外物所役使,行筆如蟲御木,自然脫俗。綜觀全畫,到處都是簡(jiǎn)練概括、清勁淡逸的點(diǎn)線,濃淡干濕,變化為妙而豐富,形象生動(dòng)而自然,充滿著簡(jiǎn)遠(yuǎn)、清幽的寧謐之趣。
清初畫家惲壽平在贊賞此圖時(shí)說(shuō):“凡數(shù)十峰,一封一狀,數(shù)百樹,一樹一態(tài),雄秀蒼茫,變化極矣。”這幅作品在元代文人眼中,的確是一幅從真山真水中提煉概括出來(lái)的杰作,因此被推為黃公望的“第一神品”。
從美術(shù)史我們可以得知,倪瓚隱居太湖,吳鎮(zhèn)《漁父圖》中的提拔中也寫到“只釣鱸魚不釣名”,這些都體現(xiàn)出老子的“功成而弗居”。這些思想構(gòu)成了元朝繪畫的新背景,在此心理背景下,畫面便自然不再出現(xiàn)“花紅柳綠”的色彩形式,畫面更多的變成了心境中淡淡然的表現(xiàn)。像枯藤老樹昏鴉這類詞,必?zé)o法用紅綠色彩搭配,所以整個(gè)元朝的繪畫風(fēng)格開始形成“淡墨”風(fēng),也有淡漠之意。黃公望的作畫形式被后人稱作淺絳山水,只用淡淡的赭石作畫。我們看到元朝以后的繪畫作品大部分只用赭石與花青,很少有其他顏色。黃公望把中國(guó)繪畫過(guò)渡成了水墨形式,更像是追求時(shí)間褪色之后的顏色,從唐到宋再到元,從夏天的艷麗、燦爛的色彩追求過(guò)渡到秋天的素淡、雅凈的淡墨風(fēng),更多是心境上的改變,將淡漠的、遼闊的、空靈的思想過(guò)渡到繪畫之中。
元代的繪畫開始發(fā)生變化,這與朝代有所關(guān)系,元代的統(tǒng)治者對(duì)文化并不重視,所以這些文人畫家并沒有很好的發(fā)展空間,這就使他們?nèi)ソo人寫戲曲,畫畫自?shī)识眩蚨覀兛梢钥吹贸鱿瘛陡淮荷骄訄D》這類的畫作,仿佛是不存在體制感的,也沒有什么規(guī)矩可言,反而成了意境深遠(yuǎn)的傳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