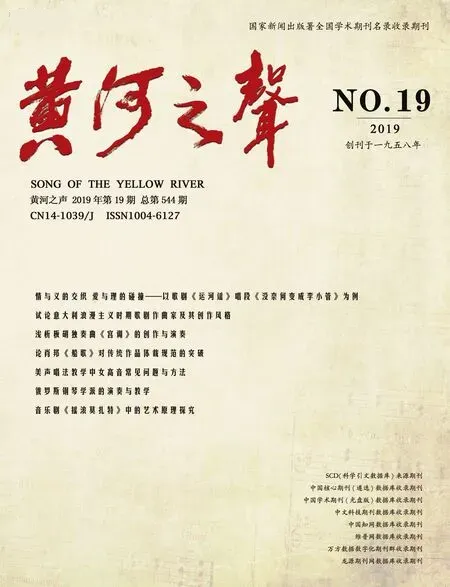黎錦暉兒童歌舞音樂創作綜述
張佳凝
(鄭州師范學院,河南鄭州450044)
黎錦暉音樂創作的黃金時期是1920至1929的十年,在這期間他共創作了兒童歌舞劇12部和歌舞表演曲24首,其中以《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可憐的秋香》、《寒衣曲》、《神仙妹妹》等作品尤為突出。因此筆者想借此文對黎錦暉兒童歌舞音樂創作進行綜述,可參考相關文章較多,共十四篇,其中六篇是筆者所選重要篇目。本綜述主要從黎錦暉兒童歌舞音樂的創作思想、創作特點兩方面進行概述。
一、黎錦暉兒童歌舞音樂的創作思想
在徐小平的《論黎錦暉的兒童歌舞劇》(以下簡稱徐文)一文中對黎錦暉的創作和思想形成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由于黎錦暉從小接觸民間音樂導致了其對民間音樂的特殊偏好,后因經歷了新文化運動使其產生“平民音樂”的思想,這也是其兒童歌舞音樂能脫穎而出的原因。
汪毓和先生的《黎錦暉兒童歌舞音樂的歷史意義——為紀念黎錦暉誕辰一百周年而寫》(以下簡稱汪文)、孫繼南的《黎錦暉兒童歌舞音樂的藝術經驗——紀念黎錦暉先生誕生100周年》(以下簡稱孫文一)、《黎錦暉音樂創作思想初探》(以下簡稱孫文二)、林萍的《論黎錦暉兒童歌舞劇的創作成就》(以下簡稱林文)、俞玉滋的《黎錦暉兒童歌舞音樂取得成就的原因——紀念黎錦暉誕生一百周年》(以下簡稱俞文)等文章也都提到黎錦暉兒童作品的題材內容都與“五四”時期科學、民主的新思想相符合,其創作思想積極向上且富有激情。同時這些文章還都分別通過對黎錦暉作品藝術特點的詳略分析與總結更加深化其創作思想的獨特性,雖然分類標準有所差異(筆者在下文會做簡略說明),但無不是證明其創作思想所具備的時代性。其中孫文二與俞文都還涉及到黎錦暉二十年代的音樂作品集中體現的其愛國民主思想,并通過舉例說明其作品所表現的歌頌正義、勇敢、團結等主題。
二、黎錦暉兒童歌舞音樂的創作特點
對于黎錦暉兒童歌舞音樂的創作特點,每篇文章的分類和劃分標準不同,故筆者在此將它們歸成五點,并一一敘述說明。
(一)音樂的教育性(以愛的教育為題材選取中心以及“美育”思想)
汪文與俞文兩文都把黎錦暉的美育教育思想做了重點的論述,不論是歷史意義還是藝術特色,黎錦暉為兒童的創作是為進行美育教育為目的,這在其創作思想上也有所體現。一方面致力于國語運動的推廣,一方面又追求一種富有情感、趣味的歌劇,因此其兒童音樂作品由于具有童趣與通俗的特點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關于愛的教育的內容,孫文一與林文都將愛的教育劃分在黎錦暉創作藝術特色下,徐文卻將其劃在黎錦暉音樂創作的新探索之外,獨立成章。標準雖然不同,卻可足以說明其對于黎錦暉音樂創作的重要性。在“五四”時期中國文學藝術界被廣泛采用的一個積極性的主題就是“愛”,而“愛的教育、美的追求”也是黎錦暉歌舞劇的思想內容,例如《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等,黎錦暉都將“愛”這一主題貫穿在這些作品中,且表達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它可以抒發對生活的熱愛,也可以與邪惡作斗爭。黎錦暉用“愛的哲學”喚起了人們對美的憧憬,同時也激發了人們對美的向往,更使孩子們自幼就受到了真、善、美的滋潤和熏陶。
另外,張清華的《黎錦暉兒童歌舞藝術的“人本主義”內涵》一文就黎錦暉兒童歌舞藝術的道德魅力、智慧啟迪、審美品質三方面論述肯定了黎錦暉“人本主義”教育觀,具有進步意義。
(二)音樂的童趣性(兒童個性鮮明,適合兒童心理特征)
孫文一、孫文二與林文三篇文章對黎錦暉音樂的童趣性特點都給予了不小的關注與肯定。黎錦暉兒童音樂的創作一直體現其以兒童為本的思想,由于有著音樂教育的經驗而使黎錦暉對兒童心理有著深刻的揣摩與研究,不論是從旋律流暢、易上口,劇情緊貼兒童性格還是藝術形式的設計便于孩子理解,都受到了兒童的歡迎。其中孫文一與孫文二還詳細舉出其歌舞劇《月明之夜》中的《招招月》、歌舞表演曲《吹泡泡》以及兒童歌舞劇《神仙妹妹》中的《老虎叩門》等作品為讀者增強說服力。可見,黎錦暉總能為兒童的心靈注入新鮮的活力,使作品漲滿了快樂的氣氛。
(三)音樂的大眾性(詞曲的口語化和通俗化)
孫文一、孫文二將黎錦暉兒童音樂創作的詞曲口語化與通俗化著重說明,在筆者看來這在當時是具有時代進步意義的,也與黎錦暉的新思想交相呼應,故應屬其創作特點之一。黎錦暉在音樂大眾性方面之所以做的成功,不僅由于“五四”時期新思想對其的影響,還跟其較多接觸民間、戲曲音樂以及熱心推廣國語運動有關。不難看出,黎錦暉的音樂大眾性的指導思想是以詞曲口語化和樂化句為基礎的。孫文一對于黎錦暉語言方面的造詣有著更為詳盡的論述,孫文二則舉出《小孩子乖乖》、《我要睡覺》兩首作品帶譜為例,雖出自同一作者,但各有千秋。
此外楊佃青的《在文學與音樂之間——黎錦暉和他的兒童歌舞作品》一文則是專門通過舉例來說明黎錦暉兒童歌舞作品中文字與音樂的聯姻所產生的巨大魅力,同時也指出其作品“明顯缺乏戰斗性”的缺點,像黎錦暉這樣兼跨藝術門類的兒童文學家,卻能有種全心全意為兒童服務的精神,實屬不易。
(四)音樂的民族性(對民族民間素材的借鑒與運用)
黎錦暉音樂創作的民族性不單單是其兒童音樂創作的特點,而是已成為其整體的創作風格,徐文、孫文一、孫文二與俞文對黎錦暉音樂的民族性都有著詳細的闡述。從小受到民族音樂熏陶的黎錦暉,擅于戲曲民間音調來創作音樂,其中俞文提到黎錦暉“創造性地繼承了民族音樂傳統中選擇曲調并‘依聲填詞’的技巧”,四篇文章共同舉出多個例子,如《麻雀與小孩》中部分曲調來自湖南民歌《嗤嗤令》、《打開門》來自民間器樂曲牌等。而他絕大多數的作品卻是在民間音樂的背景上進行富有民族特性的新創造,而不是上述的直接采用民歌的方法,例如《可憐的秋香》、《小小畫家》選段等。
而汪文和林文對于黎錦暉音樂民族性的闡述,更側重于中西音樂創作手法合璧這一方面。兩篇文章指出,黎錦暉的創作始終堅持借鑒外國的有益經驗,但又不忘繼承本國民族傳統,其大膽地移植了國外的兩種藝術表演形式,但在音樂、曲調、語言和歌詞的聲韻結合上處處體現了其對民族傳統的挖掘與繼承。其中汪文更強調黎錦暉的作品采取中西兼用的方法所取得的成功,林文則在吸收民族民間音樂方面有著更清楚的描述。不論側重點是什么,不可否認的是黎錦暉兒童音樂的創作對于民族民間素材的借鑒與運用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五)音樂的戲劇性(特指兒童歌舞劇)
音樂的戲劇性是徐文單獨所劃分的一部分,所以也就只是針對黎錦暉的兒童歌舞劇這種新穎的創作形式。文章從鮮明的性格音樂、人物性格發展的戲劇性、音樂布局的戲劇性三個不同角度論述黎錦暉兒童歌舞劇音樂的戲劇性。兒童歌舞劇不同于兒童歌舞表演曲,它有故事情節,矛盾沖突,但戲劇性是區分二者的關鍵。而黎錦暉的突出貢獻就是利用音樂手段完成戲劇性任務。對于鮮明的性格音樂,作者舉出《小小畫家》中三個教師各自鮮明的個性塑造;對于人物性格發展的戲劇性,仍舊以《小小畫家》為例,音樂與主人公的性格是緊密相連的;而對于音樂布局戲劇性,《小小畫家》與《葡萄仙子》也都運用的較為成功,戲劇性效果明顯。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對于黎錦暉兒童歌舞音樂創作的論述大致可以分為側重其“愛”、“美”教育;側重其音樂民族性;側重其思想(即人本主義)以及側重其歌舞劇戲劇性四個方面。雖然側重點各異,但在筆者看來,這些都是具有內在緊密聯系的。我們需要確定的是,從上述黎錦暉的五點創作特點看,其音樂的教育性決定了教育的對象是兒童,即需要針對兒童的心理需求進行創作,從而產生其創作的童趣性。而一部面向中國兒童的音樂作品,民族元素的采用是不可忽略的,黎錦暉音樂的民族性由此產生。所以,除第五點音樂的戲劇性外,前四個特點之間都建立著一定的因果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