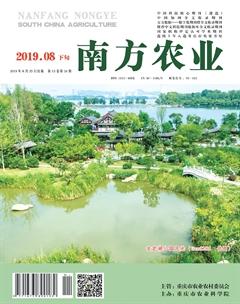丘陵山區耕地細碎化對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的影響
王鑫 陽利永


摘 要 采用數據包絡分析和線性回歸模型,深入研究經營耕地細碎化對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耕地細碎化對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有顯著負向影響;家庭務農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機械化耕作和家庭農業純收入、經營耕地質量分別對耕作純技術效率有顯著負向和正向影響。為提高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可從降低耕地細碎化水平、加大農業技術培訓力度和提高耕地質量三方面入手。
關鍵詞 耕地細碎化;農戶;純技術效率;丘陵山區
中圖分類號:F304 文獻標志碼: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9.24.039
糧食安全已上升為我國的國家戰略,糧食安全觀念也由過去的“藏糧于庫”向“藏糧于民”思維方式轉變[1]。要實現我國的糧食安全,就必須保證一定的農業生產效率[2];要保障糧食安全,根本出路在于科技[3],因為技術不僅可以優化資源配置,還可以突破資源環境約束并降低生產成本。然而,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卻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學者們分別從區域因素[4]、城鎮化[5]、產業組織模式[6]、生產性服務[7]、基礎設施[8]、農業保險[9]等宏觀因素和土地流轉[10]、土地細碎化[11]、收入非農化[12]、勞動力老齡化[13]、新技術采納行為[14]等微觀因素對農戶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
由于地形地貌與人多地少雙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國耕地細碎化現象較為突出。探討耕地細碎化對農戶耕作效率的影響,對提高中國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將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然而,關于土地細碎化對農戶生產技術效率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平原地區和發達地區,因而少見基于丘陵山區的相關研究。鑒于此,基于丘陵山區的農戶問卷調查,探討耕地細碎化對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的影響,以期為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提供決策依據。
1 數據來源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9年7月在云南省玉溪市開展的農戶實地問卷調查。調查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法,1)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在玉溪市分別優選2個近郊村(賈井村和東山村)和2個遠郊村(跨喜村和把者岱村)作為典型村。2)在這4個典型村分別隨機選取約60位農戶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問卷主要包括農戶家庭所有成員的基本情況、農地承包與經營情況、耕地投入產出情況等內容。具體調查采用“一對一”面談方式,每戶約
30 min。本次實地調查共調查250位農戶,獲得有效問卷237份,問卷有效率達94.8%。
1.2 變量設定
1.2.1 因變量
本研究主要關注農戶經營耕地的純技術效率,因而因變量選取的是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
1.2.2 核心自變量
本研究重點考察耕地細碎化對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的影響,因而耕地細碎化的指標是核心自變量。耕地細碎化具體選用地均面積和地塊數量兩個變量進行表征。其中,地均面積是指農戶經營耕地地塊的平均面積;地塊數量是指農戶經營耕地的地塊總數。
1.2.3 控制變量
借鑒相關研究成果,本研究分別從農戶家庭的勞動力、耕地稟賦和收入等方面選取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務農勞動力平均年齡、務農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農業純收入、農業收入比重、勞動力人均耕地面積、經營耕地質量、機械化耕作共7個控制變量。變量定義與說明如表1所示。
1.3 模型選擇
1.3.1 DEA模型
數據包絡分析(DEA)是一種評價效率較好的方法,常用的DEA模型有固定規模收益(CRS)模型與可變規模收益(VRS)模型。在農戶農業生產過程中,農業生產經營并不能夠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因此最適合采用VRS模型中的純技術效率[15]。DEA模型分析又分為基于投入或產出兩種角度,在規模收益不變的情況下,投入與產出角度下的效率測算結果是相等的[16]。基于投入角度來評價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具體采用DEAP2.1軟件,選取可變規模報酬假設下基于投入角度的DEA模型進行測算。投入指標包括土地投入、資金投入和勞動力投入;產出指標為農戶的耕地經營收入。
1.3.2 線性回歸模型
線性回歸是研究一個連續變量的取值隨著其他變量的數值變化而變化的趨勢,通過線性回歸方程解釋兩變量之間的關系能夠更為精確。因此,結合自變量和因變量的特性,本文適合選用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多重共線性檢驗
為檢驗解釋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本研究選用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脹因子(VIF)兩個指標作為多重共線性的表征。結果顯示,解釋變量間的容忍度值最大為0.169>0.1,VIF值為5.913<10,見表2。這表明,解釋變量間不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可以用于線性回歸估計。
2.2 模型運行
采用軟件SPSS23.0的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模型分析結果顯示:ANOVA顯著性P值=0.000,達到1%的顯著性水平;同時,偽決定系數R2=0.248。這些指標表明,該回歸模型擬合效果較好。
2.3 計量結果分析
2.3.1 地均面積對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的影響
從表2可以看出,在其他變量固定時,地均面積回歸系數為負數(B=-0.065,p=0.046),且達到5%的顯著性差異。這表明,地均面積對耕作純技術效率有負向影響,地均面積越大的農戶,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越低。這與許玉光等[15]針對小規模農戶的研究結果一致,但與他針對中、大規模農戶的結果不一致。可能原因是,本調研區位于丘陵山區,耕地零碎,且大多為小規模農戶,對于這些小規模農戶來說,在相對少的投入情況下也能獲得一定的產出;地均面積小的耕地,農業生產經營管理相對也更為容易。同時,在調查中發現,參加過農業技術培訓的農戶僅有61戶,僅占總體的25.7%,說明農戶在農業技術方面的掌握程度也不夠。
2.3.2 地塊數量對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的影響
從表2可以看出,在其他變量固定時,地塊數量回歸系數為負數(B=-0.017,p=0.001),且達到1%的顯著性差異。這表明,地塊數量對純技術效率有負向作用,地塊數量越多的農戶,農戶耕作的純技術效率越低。地塊數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耕地細碎化程度,地塊數量越多,耕地細碎化程度越大。對于地塊數量多的農戶,耕地零散而不便于機械化耕作,在經營管理上也更為不便,因而不利于提高農戶耕作的純技術效率。
2.3.3 控制變量對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的影響
控制變量中,家庭務農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機械化耕作的回歸系數均為負數,家庭農業純收入、家庭經營耕地質量的回歸系數均為正數。家庭務農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農業純收入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家庭機械化耕作、家庭經營耕地質量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且顯著性檢驗較強。說明家庭務農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對耕作純技術效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受教育年限越短,更早進行農業生產活動,在農業方面的耕作經營管理與農業技能經驗越豐富,純技術效率越高;家庭機械化耕作對耕作純技術效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在地均面積與地塊數量的雙重影響下,耕地細碎化比較嚴重,因此在地均面積大且地塊數量多、零散的情況下,使用機械化耕作會阻礙純技術效率的提高;家庭農業純收入與家庭經營耕地質量對純技術效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地均面積與地塊數量的影響下,農戶進行傳統的耕作中,耕地質量與農業純收入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兩者越高,則耕作純技術效率也就越高。
3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研究基于農戶實地調查數據,采用數據包絡分析評價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并采用線性回歸模型實證檢驗耕地細碎化對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1)耕地細碎化對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有顯著負向影響;地均面積對純技術效率有顯著負向影響,地均面積越大,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越低;地塊數量對純技術效率也有顯著負向影響;地塊數量越多,農戶耕作純技術效率越低;2)家庭務農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機械化耕作對耕作純技術效率均有顯著負向影響;家庭農業純收入、經營耕地質量對純技術效率則有顯著正向影響。
從上述結論可得出以下重要的政策啟示。1)降低耕地細碎化水平。通過農戶之間耕地“互換”等方式流轉耕地,使耕地集中連片,實現規模化經營。2)加大農業技術培訓力度,提升農戶農業經營的技術水平。3)提高耕地質量。通過土地整理與流轉進一步提高耕地質量與農戶家庭的純收入。
參考文獻:
[1] 郭小峰.新時期我國糧食安全問題研究及評價[J].生產力研究,2018(12):83-88.
[2] 吉小燕,劉震,藍菁,等.剝離環境因素和隨機因素的退耕戶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分析——基于陜西省吳起縣農戶調查數據[J].農業技術經濟,2016(12):76-83.
[3] 楊義武,林萬龍,張莉琴.農業技術進步、技術效率與糧食生產——來自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7(5):46-56.
[4] 郝曉燕,韓一軍,李雪,等.小麥技術效率的地區差異及門檻效應——基于全國15個小麥主產省的面板數據[J].農業技術經濟,2016(10):84-94.
[5] 何悅,漆雁斌.城鎮化發展對糧食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研究——基于我國13個糧食主產區的面板數據[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9,40(3):101-110.
[6] 李霖,王軍,郭紅東.產業組織模式對農戶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以河北省、浙江省蔬菜種植戶為例[J].農業技術經濟,2019(7):40-51.
[7] 楊萬江,李琪.新型經營主體生產性服務對水稻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研究——基于12省1926戶農戶調研數據[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5):12-19,144.
[8] 周曉時,李谷成,吳清華.基礎設施改善了農業技術效率嗎?——基于異質性隨機前沿模型[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7,16(2):191-198.
[9] 鄭春繼,余國新,李先東.農業保險對農業技術效率影響的差異性分析——基于動態面板數據的GMM估計[J].江蘇農業科學,2018,46(16):323-328.
[10] 曾雅婷,呂亞榮,劉文勇.農地流轉提升了糧食生產技術效率嗎——來自農戶的視角[J].農業技術經濟,2018(3):41-55.
[11] 田紅宇,馮曉陽.土地細碎化與水稻生產技術效率[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8(4):68-79.
[12] 吳天龍,趙軍潔,習銀生.收入非農化對農戶小麥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基于河北省的調查數據[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8(3):19-23.
[13] 張淑雯,田旭,王善高.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小麥生產機械化與技術效率的影響——基于地形特征的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8,23(10):174-182.
[14] 張瑞娟,高鳴.新技術采納行為與技術效率差異——基于小農戶與種糧大戶的比較[J].中國農村經濟,2018(5):84-97.
[15] 許玉光,楊鋼橋,文高輝.耕地細碎化對耕地利用效率的影響——基于不同經營規模農戶的實證分析[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7,38(4):688-695.
[16] 張蚌蚌,王數,張鳳榮,等.基于耕作地塊調查的土地整理規劃設計——以太康縣王盤村為例[J].中國土地科學,2013,27(10):44-50.
(責任編輯:趙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