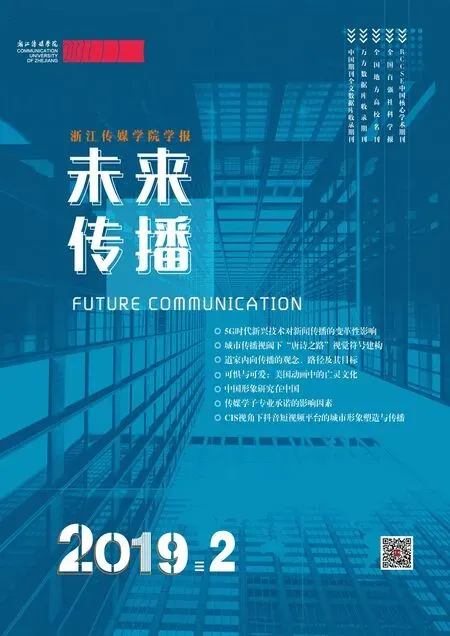“絲綢之路影視橋”的平等傳播姿態
——一種電視節目模式“共造”的機遇
陶 冶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先后出訪中亞和東南亞,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打造沿線各國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戰略意義重大。有許多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應該文化先行,以實現沿線各國的“民心相通”,“發揮文化的先行優勢,通過擴大人文交流與合作,大力傳播當代中國的價值觀,展示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正是彰顯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與策略”[1]。亦有學者認為古絲綢之路的建設“便有著文化先行的成功經驗”[2],甚至舉出了張騫通西域與鄭和下西洋的例子。2014年,作為推進“一帶一路”工作的配套工程,《“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2014—2020年規劃》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正式提出。在這一規劃的指導下,我們制作、翻譯了一批優秀的節目,開拓了新的傳播渠道,開展了中阿廣播電視節目交流項目,甚至培養了一大批固定的海外觀眾群體。然而,如何進一步推進和完善“絲綢之路影視橋”的建設,在真正意義上實現“民心相通”,顯然還有著更巨大的拓展空間。
另一方面,廣播影視在“一帶一路”建設戰略中扮演了“戰略解讀者、政策踐行者和文化傳播者”[3]三種角色,不僅要傳播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而且還要充分發揮廣播影視在“聯接中外、溝通世界”中的作用。其中,廣播電視節目在世界各國均是傳播力最廣的大眾通俗文藝形式,尤其是歐美國家近年來對世界各國廣泛輸出的電視節目模式,極大地改變了輸入地電視節目內容的面貌,同時也使得韓國、日本等電視節目模式輸出的后起之秀在經濟上獲益,并進一步提升了各自的國家形象。2013年起,我國電視熒屏上充滿了《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X音素》(X Factor)、《舞林爭霸》(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與星共舞》(Dancing With Stars)、《急速前進》(The Amazing Race)等各類節目模式的中國版。那么,通過“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建設的契機,是否可以推動我國電視節目模式創新進而“走出去”呢?
一、“盎格魯—美利堅”體系:“再造”的陷阱
眾所周知,在遠早于“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開始建設之前,電視節目模式作為文化產品的交易活動便長期存在。根據著名節目公司Granada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其實是當今最重要的電視節目模式輸入市場,英國則是最大的節目模式出口國,占據了所有模式節目播出時間的45%。[4]表面上看,是英國、荷蘭、瑞典等輸出節目模式給美國,其實,任何企圖向全球市場推廣的節目模式必然要接受美國收視市場的檢驗。換言之,各國研發的電視節目模式必須在美國市場上經過一次“美國化”的意識形態改造,方才具備向世界各地銷售的政治許可。倫敦城市大學教授滕斯拖爾(Jeremy Tunstall)將這套節目模式交易體系命名為“盎格魯—美利堅”體系。[5]這一概念于1999年一經提出,便成為英美兩國電視研究學界的共識。在大西洋東岸的英國建立了一整套以BBC為代表的“公共服務”為核心的模式,而西岸的美國則建立了一套完全基于商業自主的廣電模式。滕斯拖爾卻認為這兩種模式沒有本質區別,因為“國家并不是一個政體,而是一個市場”。[5](50)
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和歐洲已經完全占據了WTO、IMF和世界銀行的全部主導權,而這一切正是以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并因此推動以貿易自由化、生產國際化、資本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全球化[6]而建構的。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范疇內,“盎格魯—美利堅”體系表面上依然是一種在WTO框架下運行的商業交易體系,哪怕是接受方的觀眾發現這一體系帶來的節目是異質文化的“他者”,也很難確認這個“他者”到底是誰——特別是面對以荷蘭、瑞典、以色列為代表的諸多歐洲國家研發的節目模式的時候。但是,經濟的檢驗伴隨著意識形態的改造一并進入了“盎格魯—美利堅”電視節目體系,從而使接受方的受眾主觀上產生對英美文化的接受——如不經特別說明,絕大多數接受方的受眾均認為《XX好聲音》或者《幸存者》這些節目來自英國和美國,而完全不知其原創國其實是荷蘭和瑞典。另一方面,電視節目表面上存在作為文化“產品”來進行交易的經濟屬性,但卻無法從根本上鏟除其作為“文化”本身的意識形態屬性,故而輸入國不可避免會帶有警惕,并在引進電視節目模式的時候設置意識形態的把關人,此時通過WTO的體系打著貿易平等的旗號就成為了突破這道屏障的利劍。
就節目模式本身而言,其核心的概念是“再造”(Reproduce)——正如以色列學者波登(Jérme Bourdon)所認為的那樣,“盎格魯—美利堅”電視節目體系是一種“硬拷貝”且全世界范圍內都存在著對其的一種“離散的適配性”[7]。換言之,這種“再造”具備插即用的特性。如果我們將內容與形式拆分開來的話就會發現,本土內容其實已然包裹在一種意識形態上高度“美國化”的形式中。比如,我國引進節目模式的《中國好聲音》,其原版中椅子背后聽著歌聲選學員的明星歌手被稱為“coach”即教練,而隨著節目的深入是四個“教練”帶著自己的“隊員”與其他對手進行比賽。但是經由中國創作者本土化再造后,“教練”被改稱為“導師”,“隊員”也成了“學員”,這恰恰是因為在中國的主流價值觀中對一夜成名存在著普遍的不認同,同時又強調在“成才”的道路上“導師”的指導與幫助,討論的是中國的話題,唱的主要是中國歌曲。當我們拋開這一切本土化再造的內容后,驚訝地發現其被內容所掩蓋的形式依然是宣揚一夜成名的“美國化”意識形態,而版權方對于這種核心意識形態的捍衛更是要通過派出“飛行制片人”來予以監督的。因此,該體系對于節目內容創作權就可以有相當大程度的讓渡,而本土化的“再造”則以對接受方“表面上”的“充分尊重”與“平等傳播姿態”來呈現。經歷本土“再造”的電視節目模式下每一個節目參與者都是本土的主持人、本土的明星,討論的也都是本土的話題,這便會使受眾在接受過程中產生“本土性”的認知偏差與文本誤讀。
表面上這是傳播者與接受者達成的“雙贏”局面,本土的“自我”在“他者”的“模式”里得到了張揚,并為本土觀眾創作了許多喜聞樂見的節目。但是,從全球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懷疑這是一種“以退為進”的傳播策略,以至于在“異質”與“本土”沖突最為激烈的地方也照樣播出著《沙特好聲音》《卡塔爾達人秀》這樣的節目。[8]這種看似平等的傳播姿態表面上是讓渡“內容”的創作權,但卻通過版權的方式極盡所能地擴大“形式”的外延,以取得意識形態的控制權。這種平等傳播姿態的“假面”下,是“盎格魯—美利堅”體系高高在上且堅定不移的意識形態。
二、“絲綢之路影視橋”:借鑒的困境
在此,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盎格魯—美利堅”體系能夠進行如此“偽平等”的傳播,其前提還在于這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系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義桅將古代絲綢之路視為全球化1.0形態,而將當前以全球貿易、投資擴張并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核心的全球化視作2.0形態,同時,對我國“一帶一路”戰略建構全球化3.0形態充滿了期許。[6](10)“一帶一路”戰略的目標是一種包容性的全球化,是一種沿線各國老百姓能夠真切感受到的全球化,是一種“南南合作”而實現共贏的全球化,因而有學者將其視為“中式全球化”[9]。相較于起源自大航海時代而建立的以殖民體系為核心的全球化2.0形態,“一帶一路”戰略所建構的本質上是一種文明的共同復興,通過分享中國發展紅利而串聯四大文明,推動與我們一樣歷史上曾經十分繁榮的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因此,在此基礎上建構的“文化先行”與“民心相通”便顯得任重道遠,因為這本質上是一種“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進步超越文明優越感”[9](11)的文明融通機制。
對于“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而言,且不論“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國情、宗教、民族習慣的不同,即便我們依然按照全球化2.0形態的思維方式來思考該問題,所做出的一切都將不過是對“盎格魯—美利堅”電視節目體系的拙劣模仿,并會遭到該體系的既得利益者毫不留情的懲罰。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戰略規劃中,“文化先行”的策略無可厚非,并且“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本身也是“文化先行”的一部分,而“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的建設原則本身也是“一帶一路”戰略所秉持的價值觀,但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文化先行”?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文化傳播更加應該強調“平等的傳播姿態”[10]。同時,作為“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先期的理論準備,我國學術界一直在強調立足沿線各國的國情努力“講好中國故事”,然而,沿線各國國情復雜,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宗教信仰天差地別,如果一一滿足則會加劇“講好中國故事”的內容創作難度并付出高額的創作成本。那么“盎格魯—美利堅”體系“看似平等”的傳播姿態是否可以為我們所借鑒呢?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這種“偽平等傳播姿態”——對內容創作權的讓渡,很容易讓人誤以為“盎格魯—美利堅”電視節目體系是WTO框架下的一種惟利是圖而掙取版權費的節目交易體系,接受方則因為與直接引進節目不同而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內容再造權。殊不知在這種模式交易為主體的體系中,“內容”只是節目模式的枝節,而“形式”被經過各種商業測算和市場檢驗為“模式”才是意識形態和商業利益的根本內核。并且,這種方式成立的前提是英美國家對WTO領導權的控制,如果失去了經濟全球化的法律保障,交易都可能不復存在,又談何“傳播姿態”呢?而“絲綢之路影視橋”本來就是“一帶一路”戰略中的“文化先行”者,又何來這套完整的經濟基礎設施呢?
其次,我們拋開再造的內容“幻像”反觀近年來充斥世界各國熒屏的各類引進節目模式的電視欄目,會發現一些其模式中無法去除的原生規則,比如許多“類比賽”的電視節目——無論是競演類的節目如《XX偶像》,亦或是野外生存競技類的節目如《幸存者》——往往都會將參與者分組,在小組中強加入所謂的“同學”感情,然后隨著比賽環節的推進讓他們自相殘殺,甚至還要極度殘忍地讓“導師”在兩位“學員”中選擇其中一位“生還者”。這些比賽環節絕不是崇尚和諧、包容的沿線文明所鼓勵的意識形態,即便本土觀眾從本土創作者和表演者所提供的“內容”中不知不覺地對“模式”中提供的價值觀產生認同,也不可避免會帶來“文明的沖突”。沿線各國本身對我國“一帶一路”戰略一定程度上存有疑慮甚至戒心,[11]在傳播姿態上稍有不慎,后果難以設想。
再者,我們自主的電視節目模式尚處在引進、消化與吸收階段,真正意義上自主研發的電視節目模式少之又少,即便有,也主要是像《漢字聽寫大會》《中國詩詞大會》那樣帶有鮮明的中國本土特色的節目。這一類的節目尚未提煉出節目模式,更無法提供他國進行再造——我們很難想象,如若這些在中國國內有著非常高評價的電視節目輸出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從而“再造”出“《哈薩克斯坦詩詞大會》”或“《阿拉伯文聽寫大會》”之類的節目,這樣的“再造”對“一帶一路”戰略所期望實現的“民心相通”又有多大程度的支持作用呢?對文明的融通是否會起到相反的作用呢?
三、平等傳播姿態:“共造”的可能
時任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童剛強調:“‘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需要我們逐漸探索出有效的國際合作模式”。[3]“盎格魯—美利堅”體系的“偽平等傳播姿態”與我們對“一帶一路”戰略所期望的文明的融通顯然有著較大的差距。中國人民大學的陳陽教授曾在2009年便極為敏銳地發現了電視節目模式全球流動中的這種“文化混雜”與“本土改造”,并對“文化混雜”表現出一種意識形態的擔憂。[12]尤其是其包裹在讓渡內容再造權的外殼下,堅定的意識形態模式內核在根本上與“絲綢之路影視橋”的精神內涵不一致。然而,從微觀的技術層面來看,讓渡本土內容再造權確實是值得我們在建構自身節目模式創新時需要高度重視的。
那么我們又該如何拿出真正的“平等的傳播姿態”來實現與沿線各國的民心相通呢?我們能否打造一系列“中國形式”的電視節目模式從而讓沿線各國來“再造”本土化的節目呢?我們能否將“當代中國的價值觀”乃至共贏共榮的“中國夢”直接融入電視節目模式,從而讓沿線各國的觀眾在從他們本土表演者的臉上看到這種價值觀呢?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從經濟基礎到意識形態,乃至我國已開發的電視節目模式的“家底”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借鑒“盎格魯—美利堅”體系的核心創作理念——讓渡“再造”權。故而,我們認為應該歡迎沿線各國的創作團隊一起加入到電視節目模式研發的前端,將“再造”(Reproduce)改變為“共造”(Coproduce),進而從根本上打破“盎格魯—美利堅”體系的意識形態內核,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來實現對文明的共同進步,從而超越全球化2.0的西方中心主義藩籬。
這種“共造”必須是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共識,由各國創作團隊集體打造的“形式”(節目模式),然后再由各國根據自身具體實際來進行本土化的內容生產。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盎格魯—美利堅”體系的“再造”本質上是一種“我設計好游戲規則,你負責帶著你們家里人照著這個游戲規則來玩游戲”的過程;而“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中的“共造”則是“我們一起來設計游戲規則,然后各家玩出各家特色”的系統。對于捍衛貿易自由化的我國而言,將我們與沿線各國共同的價值觀——比如“自由、平等、公正、友善”——以“共造”的方式內化為其中的節目模式,并像其他原創節目模式一樣經受住市場的檢驗,便一定可以通過“絲綢之路影視橋”將這種價值觀傳播到世界各地。
“盎格魯—美利堅”體系中貫徹的“美國化”意識形態具備一種隨時可切換的動態性——美國最初是殖民地,因此其意識形態中具備第三世界殖民地斗爭的“解放性”;之后伴隨著西進運動的拓荒努力而具備邏輯自洽的“開拓性”;同時又是現代科技的領導者,這便使其又具備了無可爭辯的“現代性”,那么縱觀當今世界各國,或曰各電視節目收視市場,“解放性”+“開拓性”+“現代性”的動態平衡總能找到與當地觀眾“適配”的意識形態接口。因此,我們必須以極強的文化自信來面對“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建設中的機遇與挑戰。盡管橫亙在面前的“盎格魯—美利堅”體系已然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資本觀念統治了全球,但是我們也必須意識到今天的歐美發達國家內部或多或少地呈現出“逆全球化”的態度。若以“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的平等傳播姿態,在充分尊重沿線各國的歷史與文化的前提下建構節目模式的“共造”權,則對“民心相通”起到極大的建設性作用。
同時,相較于傳統意義上的“講好中國故事”而言,“絲綢之路影視橋”的“共造”體系可以發揮沿線國家創作者的主觀能動性,使得一種單向的傳播成為一種雙向乃至多維互動的關系,并將這種互動上升為“文明的互鑒”與“文明的共同進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自由、平等、公正、友善”具備向“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進行傳播的共同價值——作為今天貿易孤立主義思潮中自由貿易的捍衛者,我們熱愛自由;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者,我們自始至終平等對待沿線各國,并期望所有國家能夠共享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作為單邊主義貿易壁壘的受害者,我們捍衛公平的決心一以貫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國一貫奉行睦鄰友好的政策,并將這種友善的外交風范推廣到全世界。而如上的共同價值一樣可以實現動態平衡的適配。
“絲綢之路影視橋”的“共造”體系要求我們在節目模式研發的時候必須守住意識形態的底線,堅決與“盎格魯—美利堅”體系的“零和博弈”的競爭性價值觀切割開來,強調今天現代化中國互利共贏與和平友善的價值觀。同時,我們可以拿出在中國受歡迎的電視節目與沿線各國創作團隊一齊來探討,如何將這些節目“共造”成沿線各國觀眾都喜聞樂見的節目模式。筆者以為,我國原創電視節目《國家寶藏》具備這種模式“共造”的潛力。沿線各國幾乎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本民族燦爛的文化,至少在內容層面具備了各國對該節目進行本國再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各國博物館本身具備文化交流的功能,因而在“國寶”交流過程中就具備基于“形式”的情感表達——互相尊重彼此歷史,互相尊重彼此文化,中國的平等友好與和諧世界的價值觀可以在與沿線各國共造節目模式的時候貫穿始終。這種共同價值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廣泛傳播就具備很強的可行性,同時也賦予了沿線各國較高的創作參與性。
四、結 語
至此,我們不難意識到,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2.0的形態中,“盎格魯—美利堅”電視節目體系本質上是這一形態作用于電視節目模式交流(交易)的呈現形式。若不是冷戰結束,也不會出現“盎格魯—美利堅”體系一家獨大的局面——至少當時還存在著一種被稱為“蘇維埃體系”[13]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節目交流體系。換言之,“盎格魯—美利堅”體系并不是這個世界上電視節目交流的當然體系。
也因此,我們認為“絲綢之路影視橋”完全具備成為這個世界上另一種節目模式交流體系的可能性。這種依托于全球化3.0形態的電視節目模式交流體系本身就是不斷自我建構、不斷完善的動態演進體。它要求我們在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將“當代中國的價值觀”融入其中的電視節目模式。這不僅是為了展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形象,更重要的是以完全平等的傳播姿態讓沿線各國參與進來。此時,基于“絲綢之路影視橋”研發的電視節目模式便是我們“搭的橋”,而沿線各國通過“共造”創作的內容則是大家一齊“鋪的路”。今天,我國電視熒屏上熱播的《中國好聲音(新歌聲)》《急速前進》《奔跑吧!兄弟》《中國達人秀》等等可以視為“分享紅利”階段,而我們自身能夠研發出立足自身市場的《中國詩詞大會》《漢字聽寫大會》等節目則可以視為“紅利互動”的開始,那么“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的建設或者說以《國家寶藏》(《一本好書》部分具備)為代表的具有“中國氣派”的節目模式研發就應該為“給予世界更多紅利”的布局。這里要提醒的是,在“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的“共造”語境中,我們應該避免那種刻意傳播中國文化的內容模式,因為我們日常語境中的“中國文化”往往指向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然而恰恰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性反而使得接受方對于節目內容的前理解存在較大的隔閡。換句話說,如果試圖傳播中國文化則必定會在“內容”上反復著力,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形式”(節目模式)的重要性。
當我們回首“盎格魯—美利堅”電視節目體系的傳播策略時,對“形式”和“內容”的對立性傳統認知就十分值得重新審視。而當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意識形態的內容直接可以內化于電視節目模式這一“形式”的時候,我們需要做的就不是“讓渡”創作權,而是邀請沿線各國廣泛地參與創作,以實現沿線各國的“萬眾創新”,進而實現文明的共同進步。故而,在“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的建設過程中,內容再造權不是像“盎格魯—美利堅”體系那樣“讓渡”出來的,而是從根本上基于對接收方本土文化甚至文明的尊重而共同參與出來的。換言之,如果本土“再造”是“盎格魯—美利堅”體系的本質特征的話,那么“共造”就是“絲綢之路影視橋”的根本表現。與此共生的不僅是“平等的傳播姿態”,還有著“互利共贏的經濟姿態”,以及“共榮共進的文明姿態”。當經濟上的連通使我們成為“命運共同體”的時候,共同價值的傳播姿態便會在此氛圍中呈現得更加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