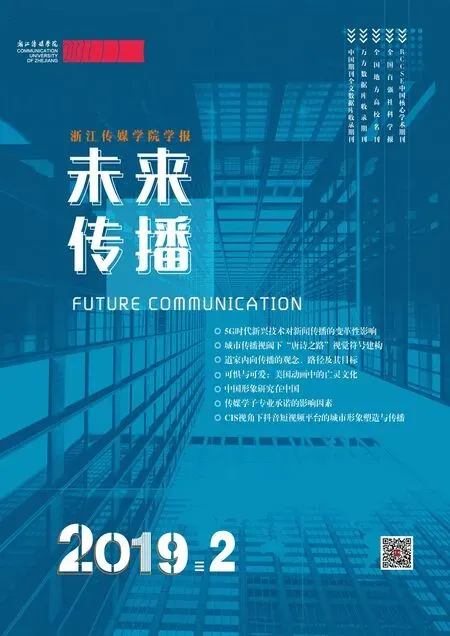視角、情節與結構:新世紀少數民族題材影片地域文化表現策略
唐克龍
新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現代化進程向生活世界的滲透,少數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人文景觀、民俗風情等地域文化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新世紀以來的少數民族電影在表現文化沖突方面投入了較多的關注,顯示出較大的實績,對于提醒整個社會關注少數民族地域文化的保留與傳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注]新世紀以來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生產總量,迄今未見有完整的統計數據。《中國少數民族電影文化》(烏爾沁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9月版,443-446頁)一書對2000年至2011年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數量進行了統計,據該書數據,這12年內,中國一共生產了66部少數民族題材影片,平均每年大概生產5-6部。按照這種算法,那么從2000年到2018年止,中國生產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總數大概在100部左右。這個數量并不算多。少數民族題材影片主題多樣,反映少數民族地域文化生存困境的影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數量也難以確定。
少數民族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的少數民族地區歷史悠久、特色鮮明、作用恒久的獨特文化傳統,包括特定地區的生態、民俗、傳統、習慣等自然、物質文化形態。而關于“少數民族電影”或“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等概念,學界一直存有爭議。王志敏提出了三個原則,即“一個根本原則”(文化原則)、“兩個保證原則”(作者原則、題材原則),以此來判斷一部電影是否可以歸類到“少數民族電影”或“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去。本文論及的“少數民族電影”,其編劇、導演或演員并非全為少數民族身份,但從文化、題材方面著眼,均屬“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為論述方便,概視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1]
新世紀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表現文化沖突時必然要涉及地域文化的呈現問題,這種呈現如何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可以從哪些方面優化其表現手段?本文嘗試從視角、情節、結構等幾個方面,探討它們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各自的表現和功能,對其可能性和限度進行分析,以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少數民族題材影片中地域文化的表達策略。
一、視角:呈現客體、挖掘其隱含的“療救”功能
視角——或者說視點——是每一部影片觀照其表現對象的獨特眼光和角度。視角無處不在:“視角具有往往不作明言,卻又無所不在的普泛性,假如你帶著視角意識去讀作品,就會感覺到無處沒有視角。”[2]就電影而言,總是存在著兩種視角:基本剪輯角度的物理視角和敘事意義上的視角。[3]所謂“帶著視角意識”去觀察,即是指從敘事視角去讀解一部影片,分析其內在視角,認識其表現和功能。
敘述視角有繁復的類型。根據托多羅夫的分類,整體而言,敘述視角可分為三類:全知視角(敘述者>人物)、內視角(敘述者=人物)、外視角(敘述者<人物)。[4]全知視角的敘述者總比他的人物知道得更多:某個人物的秘密愿望、幾個人物的想法、不為人物所感知的事件等。這種視角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從后面”的觀察方式;內視角的敘述者和人物知道得一樣多,如果人物沒有找到對事件的解釋,則敘述者也無法向讀者提供。內視角有時采用第一人稱,有時采用第三人稱,它是一種(敘述者和人物)“同時”觀察的方式;外視角可以看作是對全知視角的反動,在這種視角里,敘述者比作品中的任何一個人物都知道得少,他只能向讀者敘述人物的行為和語言,而對內情一無所知,沒有進入任何意識,屬于一種(敘述者)“從外部”觀察的方式。[4](511)外視角的特點或優點是富有戲劇性和懸念,有利于調動讀者進行再創造,但不利于全面刻畫人物形象。相對于全知視角,內視角和外視角都是“限知視角”。
少數民族影片具有獨特的自然生存環境、民俗風情和歷史文化傳承特征,對觀影者而言,這都足以引起新奇性、震驚性體驗。影片采用什么樣的視角讓觀眾去觀看、去感受、體驗到這些獨特的民族地域文化,將直接影響到傳播效果。
就視角而言,電影是一種影像藝術,和文學主要作用于認知性視角不一樣,它的視角主要是一種感知性視角,也即它主要作用于觀影者的視覺、聽覺等感覺器官,從而達到傳遞信息的目的。透過這種視角獲得信息,具有直接、直觀、全面的特點,但同時也受制于感覺器官的局限性,比如呆在屋里,若不借助門窗,就不能看到外面的景觀。在這種情況下,采用全知視角來進行敘述,可以令少數民族地域文化得到更全面、具體的呈現。實際上,在新世紀以來的少數民族電影中,全知視角也是采用最多的一種敘述視角。
少數民族的地域文化主要包括自然風光、歷史人文遺存和民俗風情等。在電影中,通過全知視角,這些文化形態都能得到全面和饒有意味的表達,取得較好的傳播效果。比如在電影《婼瑪的十七歲》中,哈尼族層次分明的梯田景觀在影片中多次以全景的形式呈現,有時是以長鏡頭+空鏡頭、有時是以背景的方式,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還有哈尼族的“開秧門”農耕儀式、“擲泥巴”選情人、給受驚嚇的人“叫魂”等,都是以類似于全知視角的方式,向觀眾展示哈尼族的民俗文化;在電影《鍬里奏鳴曲》中,地筍苗寨的自然風光、民俗風情和民族文化(歌鼟)等地域文化樣式,也是在全知視角的支配下,或作為背景,或作為前景,一一呈現出來的,對影片的歷史、文化增量的生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影片《我們的嗓嘎》中,侗族傳統民間音樂侗歌的傳承是影片著力表達的主題。侗歌的特色,也是在全知視角的引領下,通過黃月嬌在學校的教唱、潘依蘭的奶奶的演唱、黃正宇跟著潘奶奶學唱等形式得以展示出來;在電影《靜靜的嘛呢石》中,藏族寺廟的日常生活、傳統藏戲的排練、演出等民族文化樣式,也是通過全知視角傳達給觀眾,能夠較好地讓觀眾熟悉藏族地域文化的特色;還有電影《爾瑪的婚禮》中,理縣羌族地區濃郁的民族文化風情和民俗(如婚禮),也是通過鏡頭的轉換,通過爾瑪所在的民俗園的表演,在全知視角的控制下傳達出來。
除了全知視角,還有一類影片采用了限知視角敘事,例如《云上太陽》《天上草原》等。《云上太陽》表面上看是采用了全知視角,但與純粹的全知視角不同的是,它引入了一個“他者”視角即第三人稱視角——即影片中作為故事重要參與者、旁觀者的法國畫家波琳的視角——形成了一種限知敘事。透過波琳這個限制性的“他者”視角,影片所要表達的少數民族地域文化(貴州某苗鄉的優美的自然風光、獨特的造紙技藝、苗家人純樸的人性和善良仁愛的品德)得到了全面、細致又不失個性化的呈現。在《天上草原》中,這個“他者”則是由漢族小孩虎子充當的。虎子在影片中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者出場,通過他的限知視角,蒙古草原的奇異風光、風土人情、牧民純樸寬厚的人性都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呈現。
有意味的是,如果僅僅只是考慮民族地域文化信息的傳達,那么,透過波琳或者虎子的“他者”視角呈現出來的苗族或蒙古族地域文化,其實際傳播效果與采用全知視角,其實是沒有什么差別的。但這種限知視角還有一種功能卻是全知視角不具備、或者說其效果不如限知視角的,那就是限知視角將民族地域文化的“療救”功能,意外地透過“他者”視角而挖掘了出來。具體而言,就是少數民族地域文化信息(自然生態、民俗風情等)進入“他者”視角后,又對“他者”的精神和心靈世界產生沖擊,甚至重塑了“他者”的信仰與精神世界。從美學角度而言,這類似于外在對象的自然之美、民風之美對主體產生了“喚醒”作用,通過“外射”和“移情”機制,主客體在精神上融而為一,主體最終重塑了自己的精神世界。[5]波琳在影片中身患怪病,是一個需要“療救”的“他者”。在苗寨的經歷“喚醒”了她的心靈,健康、純樸的苗族地域文化成為醫治她的怪病的“良藥”。此后她從疾病中康復,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苗鄉地域文化的治療功能;虎子進入蒙古草原世界,一直有一種不適應感,也是在精神上“有病”需要療治的“他者”。是草原壯闊的風光、蒙古族樸素真誠的民風、牧民仁慈寬厚的胸懷“喚醒”了他的人性,滋養了他的成長。最后,一直沉默的他在贏得賽馬比賽的瞬間,終于用蒙語喊出了“騰格里”,恢復了正常人性。
就此而言,影片以“他者”限知視角呈現地域文化,比單純的全知視角之展示,更能挖掘出民族地域文化隱含的“療救”功能,而不僅僅只是一種“奇觀”化呈現。這是全知視角無法達到的效果。因此在影片中設置什么樣的視角,不但關系到客體的客觀呈現問題,而且也關系到客體的功能發掘問題,并不僅僅只是借助一個簡單的“觀看”角度看到“什么”而已。
二、情節與民族地域文化的表達
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表達民族地域文化,還需要借助故事和情節。故事(story)“是所有呈現給我們的事件或我們可以推斷出的事件”,情節則是“以某種形式或結構對一系列事件的安排或建構”。[7]電影是一種敘事性藝術,講述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是一部電影的根本任務。根據福斯特的定義,廣義而言,故事就是按照時間順序對一系列事件的講述,情節同樣也是對事件的敘述,不同點在于,情節特別強調因果關系。例如“國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是故事;而“國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傷心而死”就是情節了。[7]相比小說等敘事藝術而言,電影的故事時間有限,而且相對明確,因此更注重情節的安排,力求在有限的時間里,推動故事的發展,最終抵達結局,完滿表達創作者的意圖。
對一部分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而言,對豐富多彩的民族地域文化的宣傳、展示是影片最重要和根本性的任務。但這種宣傳和展示又不能像紀錄片那樣過于直接。因此,創作者大抵都會通過講述一個故事,在情節的有機發展中,讓民族地域文化自然而然地隨情節的發展而展現出來,讓觀眾在欣賞、體味故事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接受少數民族地域文化的熏陶,了解其相關知識,創作者的主觀意圖也因此得以實現。
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這種“意圖倫理”既然主要是藉由情節的巧妙安排而實現,那么,情節如何設置才能使其得到更充分的表現,便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了。
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的情節設置及其表現效果大抵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情節線索比較明晰,影片故事被情節推動向前發展,地域文化的展示不具備連續性、主體性;另一種則是情節線索相對隱晦,故事的推進略顯滯澀,但地域文化的展示卻占據了主體性地位,連續性較強。
在第一種情況即情節線索比較明晰的影片中,觀眾看到的是一個人物性格鮮明、情節跌宕起伏、有較為完整的發生—發展—高潮—結局的生動的故事。比如在電影《爾瑪的婚禮》中,爾瑪跟漢族英語教師劉大川學習英語,逐漸產生了感情。但兩年前她已和本族青年多巴訂婚,多巴家屢次催著他們結婚,爾瑪不愿意。在多巴家和自家父母的強大壓力下,爾瑪還是堅持退婚,經過一番波折,最終如愿退婚。情節發展到這里是一個小高潮,也是一個轉折。之后,爾瑪和劉大川正式相戀,按理,這以后的發展該是平平順順了。但天有不測風云,平地也起波瀾。到談婚論嫁的時候,兩人又為婚禮該按羌族習俗在羌寨舉辦還是在縣城舉辦較上了勁,兩人都不愿妥協,僵持到甚至要分手的程度。情節發展到這里,可謂吊足觀眾胃口:究竟故事最終怎樣收場呢?最后劉大川的姑媽出場,達成妥協:婚禮先在羌寨辦,然后去縣城辦。緊張解除,故事收束。
《爾瑪的婚禮》人物形象豐滿,故事一波三折,較為典型地體現了敘事學意義上的情節發展過程,有效地調動了觀眾的注意力,創作者所要表達的民族平等、融合的主題,也在情節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生動傳達。那么,給觀眾講述一個曲折的愛情故事是否就是這部影片的最終目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通過情節的編排、發展,創作者還有一個隱含的、也許是終極的目的要傳達給觀眾,那就是讓觀眾了解、熟悉羌族地域文化。通過“情節化”而不是“導游式”的潛移默化方式,將羌族地域文化的一些因素巧妙地編織進情節的發展過程中,讓觀眾在跟蹤情節的同時,不知不覺感受到民族地域文化的魅力。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羌族民俗園的歌舞表演、羌寨的自然風光、羌族的婚禮儀式等,都是這樣有機鑲嵌在情節鏈中的。而且,像其他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要表達民族地域文化面臨的危機一樣,《爾瑪的婚禮》也在爾瑪和劉大川爭執究竟是不是要按羌族儀式舉辦婚禮這個情節上,暗示了羌族民俗如結婚儀式等處在危機中的狀況。這樣,影片最終就超越了愛情故事的俗套,引導觀眾思考少數民族地域婚俗文化的生存問題,擴展了影片的格局,提升了主題。
《鍬里奏鳴曲》是由瀟湘電影制片廠和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合作拍攝的一部少數民族題材影片,主要目的即為推介、宣傳該縣苗族地域文化,包括苗寨風土人情、自然風光,還有地筍苗寨獨特的苗歌多聲部合唱形式——歌鼟等。與《爾瑪的婚禮》的敘事策略差不多,在情節安排上,《鍬里奏鳴曲》也是通過苗族婦女潘秋子和漢族修路男子梁三金之間的愛情故事來結構全劇的。在潘、梁相戀直至最終結合的過程中,經過了一系列波折,最后的結合也隱喻了民族團結、融合的主題,與《爾瑪的婚禮》中的類似結撰并無二致。同樣的,苗族地域文化也通過這樣的情節化方式傳達給受眾,很好地貫徹了影片的主旨。
但在影片《婼瑪的十七歲》中,雖然同樣還是在講一個愛情故事,但情節模式卻有變化:影片的主人公、哈尼族少女婼瑪并沒有和她心儀的漢族男子阿明締結婚姻,但這并不重要。因為在婼瑪和阿明交往的過程中,哈尼族地域文化(哈尼梯田、“開秧門”、“擲泥巴選情人”民俗、叫魂等)已經通過情節的發展而呈現出來。觀眾即使對婼瑪和阿明未成眷屬而抱憾,但也一定會對觀影過程中感受到的哈尼地域文化感到愜心。這其實就是影片要達到的目的,婼瑪和阿明的結局究竟如何,倒不是最重要的了。
在第二種情況即情節線索相對隱晦、情節鏈并不十分完整的影片中,因為沒有一環扣一環的故事可以有效吸引觀眾的注意力,那么影片的其他組成因素,像民族地域文化的表現,就能吸引觀眾的部分注意力,凸顯其特征。比如在影片《云上太陽》中,波琳更多地只是被設定為一個異質性的觀看視角,她和當地的苗民始終存在一種疏離感。在她和當地苗民之間,除了幾次因生病而產生的劇情波瀾外,從敘事角度而言,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清晰的情節鏈,更類似于“散文化”的敘述,不足以在劇情上吸引觀眾。這樣,她的作用便類似一位異域觀光者,透過她的發現、“觀看”,觀眾跟著她領略了一番苗鄉的自然風光和人情、人性、民俗之美。電影《靜靜的嘛呢石》也與此類似,影片描寫了小喇嘛在藏歷新年三天里從寺廟到家里、又從家里到寺廟的日常生活,在宗教儀式和世俗生活的場景中轉換,中心情節是圍繞觀看電視劇《西游記》光碟,暗示世俗生活和現代文明對宗教世界的沖擊。電影《我們的嗓嘎》的地域文化傳播意圖則更明顯,影片中黃月嬌、黃正宇姐弟的命運都與侗歌的傳承緊緊聯系在一起,影片的目的即在表達侗歌這一侗族傳統音樂形式在當代的命運。與其說是黃氏姐弟的故事串起了地域文化的珠子,不如說是他們的命運被侗族地域文化所左右。他們的個體命運只有與他們的民族文化聯系起來才有意義。在影片里,他們更多地充當了民族地域文化呈現的工具。故事雖然是完整的,但構成故事的事件并沒有明確的時間性節點,這樣,情節安排也便不那么明顯、緊湊、連貫,不再占據主導地位。
情節在影片中的地位和功能一直是電影史上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起源于亞里士多德的傳統情節觀認為,對于敘事藝術而言,情節比性格、主題或語言都更重要。因為情節是對生活的模仿,而藝術的對象是人,所以情節的主要作用,在于確立一個供人物作出重要抉擇(反應)的局面(環境)。[8]但技術的進步、表現手段的豐富和電影觀念的變化對上述觀念提出了挑戰,“非情節化”對觀念和實踐方面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其核心觀點是:“電影的表現手段非常豐富,運用電影中的非情節因素渲染情緒,制造氣氛,創造意境,就可以達到刻畫人物的思想感情的目的,構成一部完整的影片”,[9]因此情節并不重要。
實際上,關于“情節化”和“非情節化”的爭論,都應該針對具體對象、在特定的語境里展開,一般性的討論很可能是不會有結果的。這涉及到電影類型、受眾市場、傳播媒介等因素。就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而言,生產動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新世紀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的生產動機,主要是為了表現現代化背景下少數民族地域文化的生存危機。在這樣的框架里討論影片情節的設置問題,顯然應該與其生產動機聯系起來。這樣,我們分析具體影片中情節的設置,也就能看出它是否有利于地域文化的表現。分析表明,情節線索的隱顯、連貫與否,對地域文化的表現關系甚大。簡略說來,當情節連貫而富有戲劇性時,觀眾的注意力會被有效吸引,被情節控制,暫時疏于注意其中的文化呈現。但這并不表明少數民族地域文化的呈現就被忽略了,不能達到預期效果。相反,這種呈現會以滲透的方式隨情節一起進入觀眾的意識,留下較深印象,獲得較好的傳播效果;而當情節線索不連貫、沒有明顯的情節發展過程、因果關系時,觀眾的注意力則不容易集中,較易分散。這樣,在沒有好的“故事”吸引人和扣人心弦的情節控制觀看節奏的情況下,觀眾會轉而被影片中的地域文化牽扯較多的關注。但因為對情節的關注受挫,對地域文化的關注也可能會心不在焉,從而難以留下深刻印象。因為觀眾畢竟是來欣賞一部劇情片的,是否有“抓人”的故事情節,將直接決定其觀影感受。這與欣賞紀錄片時的期待心理顯然大不一樣。因此,劇情片中的情節線索應該明顯、緊湊一些,要強化故事性,在情節的推進、轉換過程中,將地域文化因素有機融入,達到“潤物無聲”的傳播效果。一般性地依賴“原生態”展示、去情節化鋪展,恐怕難以取得理想效果。當然這與觀眾的個體審美差異也有很大關系,但這不會影響情節在影片中地域文化的表現上所能發揮的整體作用。
三、結構:線性因果性、散文式結構與民族地域文化表達
結構在少數民族題材影片中也是一個重要的地域文化表現手段。結構的一般意義是指事物各個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組織安排,是一切事物的基本屬性和存在形式,是一種事物據以區別于他種事物,顯示和保持其整體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組接模式。電影中的結構與現實生活結構具有某種同構性,因此其形態和生活本身一樣,也是復雜多樣的,難以納入到某種單一、固定的樣式中去。但是,高度凝練的藝術結構畢竟不同于生活結構。在多樣化的結構形式中,主導性的結構其實也只有幾類。例如從時空角度看,有順敘式、倒敘式和時空交錯式等主要類型;而從邏輯角度看,又有戲劇式、變奏式、小說式、散文式等類型。而且,在一部影片中,某種單一的結構形式雖然會發揮主導作用,其實也不排除還有其他結構形式參與故事的編織,形成混合式結構。
在電影中,最常采用的結構方式有傳統的線性因果式結構、小說式結構、散文式結構等幾種。線性因果式結構又被稱為戲劇式結構,指的是以戲劇沖突為結構的基礎,遵循因果律,富有戲劇性,有一個矛盾沖突發展的過程,即一條包括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等結構要素在內的情節線索。[9](397)但戲劇式結構也有多種形式,并不限于因果式。尤其考慮到電影和舞臺劇的差別,“戲劇式”和“因果式”更不能簡單地劃等號。因此有學者主張,電影中的戲劇式結構應該明確為“線性因果式結構”。[10]小說式結構在時空轉換上較為靈活,不追求強烈的戲劇性,注重結構因素的漸變性。散文式結構也被稱為紀實性結構、主題變奏式結構,其特點在于實錄性,由一個主題統攝全片故事和情節,類似于音樂的主題變奏,不追求戲劇沖突,也不采用隱喻、聯想、倒敘、閃回等藝術手法。
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的結構呈現出較為多樣化的形式。總的看來,采用線性因果式結構、散文式結構的較多。不同的結構形態,對地域文化的呈現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爾瑪的婚禮》是比較典型的采用線性因果式結構的一部影片。影片以羌族姑娘爾瑪和漢族英語教師劉大川的相識—相戀故事為主線順序展開,以兩家關于“婚禮在哪里舉辦”構成矛盾沖突,最后在劉大川姑媽的調解下達成舉辦方案作為結束,是一個較為典型的線性因果式結構。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在這個結構框架里,民族團結、民族融合的主題得以凸顯;另一方面,羌族濃郁的民族文化風情和地域特色也“順便”得到了完美呈現。與此類似,《鍬里奏鳴曲》以苗族姑娘潘秋子和漢人梁三金的相戀—結合為情節線索,啞巴叔子吳學拉則充當潘、梁情感障礙的角色,最后以吳的退出緩解沖突、潘、梁結合結束全劇。影片也是以線性因果式結構統一全劇,也同樣反映民族團結、民族融合的主題,而有關苗族民俗風情、自然風光、民族文化等民族地域文化,或作為背景,或作為前景,也藉此結構一一呈現,傳播效果非常不錯。影片《婼瑪的十七歲》也是采用按照時間順序發展的線性因果式結構。與前述兩部影片一樣,也是講述少數民族少女婼瑪(哈尼族)與漢族男子阿明相識、相戀的故事。但婼瑪和阿明最終沒有結婚,結構的最后一環出人意料。但這只能說明故事模式產生了突變,結構模式其實沒有變化。同時更重要的是,民族地域文化如哈尼梯田等也在這個結構中得到自然完全的呈現。三部影片的結構功能都是相似的,那就是既表現了民族團結和融合的主題,同時也呈現了民族地域文化。至于爾瑪、潘秋子、婼瑪與漢族男子相愛而終成眷屬或未成眷屬的故事,原本就脫胎于中國傳統的“大團圓”結構模式,符合或者超出觀眾的心理預期,都應算是這個結構的題中應有之義。
采用散文式結構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也比較多,這或許與導演懷抱的“原生態”呈現意圖有關。散文式結構的特點是主題明確,但故事性不強,這意味著情節之間的因果關系不明顯,或者沒有因果關系。職是之故,情節作為推動劇情發展的結構性力量,也就顯得很不充分,缺乏緊湊、連貫的戲劇性張力,偏向散文化、詩化一路。比如在電影《靜靜的嘛呢石》中,雖然還是按照時間的推移進行敘述,似乎算得上是線性結構,但全劇并沒有一條可形成戲劇性沖突的清晰的情節線索,情節、場景之間的因果關系都很松散。全劇寫小喇嘛三天的日常生活,情節無明顯發展過程,沒有強烈的戲劇沖突性,像一篇鋪敘性的散文。但影片表現文化沖突的主題卻是明確的。因此,類似于散文“形散神聚”的特點,影片雖然沒有明確、強烈的戲劇沖突,但各個情節、場景、段落卻都統一在主題之下,承擔起闡釋主題的功能,并非可有可無。同時,在這種結構中,“故事”既然不再是主要的看點,那么,有關藏族地域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宗教儀式、藏戲等就會凸顯出來,很大程度上代替人物的活動,成為另一種結構性力量;在《我們的嗓嘎》這部影片中,黃月嬌、黃正宇作為兩條平行的情節線索,都缺乏環環相扣的沖突性事件,整個情節鏈顯得斷續、拖沓、不可信,缺少緊張感。這樣一來,作為影片的結構性要素,就不能很充分地推動故事的發展。創作者只好直接把侗歌的傳承問題作為影片的結構力量,但這樣又顯得生硬,難以從感性上說服觀眾,打動不了觀眾。其實,如果換一種思路,強化黃氏姐弟的故事,增強沖突性,將其作為情節結構,而把侗歌傳承問題稍微弱化,作為背景線索處理,影片無論在“講故事”或者在呈現民族地域文化方面,應該都會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在影片《云上太陽》中,基本上也看不到因果式的戲劇性情節,波琳的“他者”視角所看到的,都是充滿陌生感、新奇感的苗鄉文化,詩意彌漫在整部影片中,而那種緊湊、環環相扣的戲劇性情節卻付之闕如。這樣,透過波琳的眼光而呈現出來的苗族地域文化,就成為結構影片的重要因素了。
實際上,由于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特殊性,結構要素在其中往往呈現復雜的樣態。在一部影片中,純粹單一、固定的結構方式往往并不多見,而混合了兩種以上結構方式的倒很常見,例如前述《靜靜的嘛呢石》,還有像《碧羅雪山》《天上草原》《開水要燙,姑娘要壯》等。單獨論述某一種結構樣式的表現與功能,更多是出于論述方便之考慮。這是應該提請注意的。
就本文分析的兩種結構方式來看,在采用線性因果式結構的影片里,民族地域文化的呈現隨結構的生成、展開而展開,它不是推動故事發展的結構性力量,但卻是結構里至關重要的因素,是結構里隱含的表達對象;而在采用散文式結構的影片中,情節之間因果關系松散、斷裂,戲劇性不強,劇情整體趨向散文化、詩化,則情節難以成為影片的有效結構性力量,地域文化卻凸顯成為影片的中心結構因素,使影片表現出某種“類紀錄片”風格。對于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而言,究竟哪一種結構方式更有表現力,更值得采納,實難判斷。這主要決定于具體影片的創作意圖、傳播動機等因素,不能一概而論。
四、總 結
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生產,一直與特定的民族文化表達、身份認同等密切相關。新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和現代化步伐的進一步加快,這種文化沖突和身份認同焦慮也愈加凸顯。在影片中呈現全球化、現代化背景下少數民族文化的當下命運,并揭示其與全球化、現代化的緊張關系,已成為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一個重大主題。有關這一主題的討論,可以從多方面展開。本文通過對影片中視角、情節、結構運用的分析,從敘事藝術的角度,重點探討了少數民族題材影片中的民族地域文化呈現問題。提出影片在視角、情節、結構等方面的匠心經營,對民族地域文化的成功傳播是有很好的促進作用的。這是一個技術分析的路徑,關系到影片最終的傳播效果,因此值得創作者和學界加以重視。應該強調的是,少數民族地域文化的影像呈現雖然對技術性因素依賴性很強,但其呈現機制、策略卻需要整體性考量,需要注意視角、情節、結構這幾個手段的綜合運用,以及和主題、內容、語言、剪輯等影像要素的有機匹配,這樣才能釋放它們的綜合效益,同時也能令單獨的表現手段發揮出最佳功能,使劇情和民族地域文化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最終達到“潤物無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