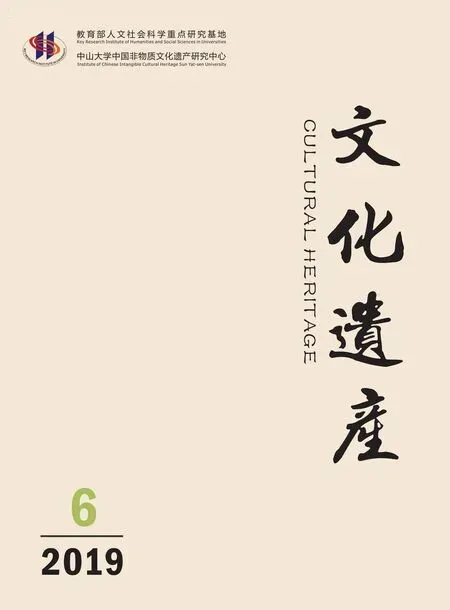上黨梆子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張愛珍訪談錄*
姚佳昌
張愛珍簡介:女,漢族,1959年出生,山西高平人,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演員,晉城市上黨戲劇研究院副院長。自幼熱愛戲曲藝術,13歲考入高平縣青年文藝培訓班,主攻青衣、小旦。畢業之后,進入劇團,排演新戲《蝶戀花》,并于“文革”之后在晉東南地區首次排演古裝戲。對上黨梆子進行了唱腔上的有益改革與創新,陸續推出《姐妹易嫁》《皮秀英打虎》等,并在1991年,憑借《殺妻》《兩地家書》兩部折子戲,榮獲第九屆中國戲劇梅花獎。其唱腔“甜圓、純美、如詩、通透”,被廣大專家和戲迷親切的稱為“愛珍腔”。演出戲曲的同時積極開展上黨梆子的傳承工作,于2009年,評選為上黨梆子國家級非遺傳承人。
上黨梆子,主要流行于山西省東南部古上黨郡地區。清道光末年官方稱它為“本地土戲”,民國二十三年(1934)赴省城太原演出,曾叫“上黨宮調”,當地群眾稱“大戲”,1954年山西省首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定名為上黨梆子(1)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志·山西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志·山西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0年,第95頁。。上黨梆子在清代中期興盛,并傳播于今山東菏澤和河北永年地區,形成了山東棗梆和永年西調兩個姐妹劇種。上黨梆子以朝代大戲為主,粗獷豪放為主要特點,融合了“昆梆羅卷黃”五種聲腔,于2006年評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18年2月8日筆者前往山西省晉城市城區,對上黨梆子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張愛珍進行了口述訪談。訪談主要包括了張愛珍的個人從藝史,她對上黨梆子的認識以及劇團管理和戲曲傳承等方面內容。
一、結緣戲曲,苦練青訓班
“文革”期間,上黨梆子同樣遭遇了摧殘,戲曲教育難以正常開展。在上世紀70年代初,一些地方恢復了戲校,但都以“樣板戲”為教材。張愛珍老師的學藝階段正是戲校剛剛恢復的時期,艱苦的環境造就了她對于上黨梆子戲曲藝術的特殊領悟,以下就對張老師的學藝經歷以及切身體悟等方面進行請教。
姚佳昌(以下簡稱姚):張老師好,我老家是長治市的。奶奶是上黨梆子戲迷,自己從小耳濡目染,對上黨梆子也很是喜歡。現在就讀于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希望通過對您的訪談,了解一下您的從藝經歷、劇團管理、戲曲傳承等方面的內容。您在十三歲的時候就進入到高平縣青年文藝培訓班(以下簡稱“青訓班”),當時為什么選擇進入青訓班學習呢?
張愛珍(以下簡稱張):自己從小就喜歡聽歌、哼唱戲詞。記得我媽媽曾說過“你看你這個閨女天天嘴里哼唱,長大后去唱戲吧。”她這么隨便一說,結果還真說中了。高平在1970年成立青訓班,1972年我哥哥馮來生作為高平人民劇團的樂隊成員到鄉下招生,于是在哥哥的鼓勵下報名參加考試。記得當時的考試內容,一個是一段毛主席語錄《我們的文學藝術》,一個是歌曲《雄偉的喜馬拉雅山》,還有一段阿慶嫂的說白以及《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然后再看你身段咋樣。后來500多個人錄取了不到25個,其中只有7個女生。所以說就是這個機會,領進門的就是我哥哥。
姚:您也正好趕上了青訓班這個機遇,我們知道在“文革”期間,全國上下樣板戲“一統天下”,對于上黨梆子來說,也不例外。當時在青訓班學習期間是如何學戲?又是怎樣處理傳統戲和樣板戲之間的關系呢?
張:我們當初學的都是樣板戲,傳統戲還沒有開放。特別是學唱腔的時候,把上世紀50年代,像郭金順的《徐策跑城》《兩狼山》,王東則的《皮秀英打虎》,吳婉芝(2)吳婉芝(1933-1999),女,上黨梆子戲曲名家,師從段二淼、郭金順,其表演以唱功見長。其唱腔古拙中亦有新意,高亢中不乏委婉,如行云流水,剛柔并濟,韻味甚濃。廣為上黨地區人民所喜愛,其優美唱段亦廣為傳唱,代表劇目為《皮秀英打虎》《秦香蓮》等,張愛珍老師是其唯一弟子。的《闖宮》等唱片拿來,反復聽,重復唱,當時啟蒙的就是這幾段,所以說開門的唱腔就是學的上黨梆子的傳統唱腔。但是古裝戲沒有開放,你就不敢唱古裝戲那個詞,還得把那個詞改成現代的詞。在樣板戲流行期間,上黨梆子丟失了好多傳統,像當時的打擊樂,都用京鑼、京镲,總的來說得靠近京劇。我們這一代演員在學校學習樣板戲,沒有系統學習傳統的東西,欠缺的也是這個,像唱腔中【四六板】【大板】等,是傳統戲開放以后才在劇團系統學習的。當時就請上郭金順、劉喜科等劇團以前的老演員教我們,所以對傳統的東西還需要進一步的挖掘、認識,化成自己的東西。
姚:當初在青訓班您主要是跟從誰學習的?您有拜過師嗎?
張:當初青訓班總共有十幾個老師,有天津京劇團來這里插隊的傅鳳英老師,她教我們武功。還有武鳳英老師,是自己唱腔的啟蒙老師,她聽吳婉芝老師的唱片,再教給我們,當初都稱她為“假婉芝”。所以說我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起步,比較門正,路子比較對。吳婉芝老師的唱腔啟蒙,“假婉芝”武鳳英老師給我們親口傳唱,這樣的話自己沒有走彎路。再后來自己又親自拜吳婉芝老師為師,成了她唯一的弟子。吳婉芝老師對我的要求主要就是認真演戲。演戲要樸實自然、唱腔要注意韻味,把握人物身份、個性。在生活上她關心我比較多,有件事記憶特別深,有一年,她不知從哪聽說了我胃不好,便弄上姜配紅糖的偏方托人捎到鄉下讓我服用。吳老師就經常對我講,你要按自己的理解大膽往前走。
姚:“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特別是對于學戲來說,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您能講講在青訓班學戲的經歷嗎?
張:我們當初學校是在高平定林寺,那以前是個寺院,環境差。夏天我們就在外邊松樹下跑圓場練功。到了冬天,就在殿內練功。寺院有好幾進院,彩排戲就在最高的一院,那時候開練腿功,身上練的是青一塊紫一塊的,腿腫的厲害,上下臺階都困難,那是比較艱苦的幾年。當時老師們要求非常嚴格,每天我們練功后,都要進行總結。自己學的比較慢,笨鳥先飛。我比較規矩,不走范,老師教什么,自己就怎么來。青訓班期間我們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邊學習一邊演出實踐。在練功期間排練一些歌頌那個年代的小節目,那時候就是來了新戲就學,像我們學的《育新人》《審椅子》等,都是那個年代比較流行的劇目。那時農村都有業余劇團,我們宣傳隊編上這些節目去農村演出,然后傳授給農村大隊的演員,那是全國性的活動。
在青訓班學到最重要的就是做人,要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唱戲,腳踏實地的能吃得了苦,要把基本功打好。其次就是各位老師都特別關心自己,覺得我有一副好嗓子,是培養的對象。但是剛開始自己并不出眾,也就是別人有特殊事情,如一部戲分A、B角,我是B角,或者就不是B角。由于A角有特殊情況,因為自己在課下擠時間學會了,到時候救場如救火。記得有一次在高平鄉下演出《杜鵑山》,主演病了不能上場,由我頂上女主人公何湘就上場了,一上場老師們認為還挺不錯,就開始重點培養自己了。所以說一定要等待機遇,人一生中的機遇擦肩而過,你如果這次把機遇弄丟了,那就永遠來不了了。況且我們這是綜合性藝術,一個演員遇到給你排一部戲的機會太難得了。我認為天時地利人和,哪一門不成你都做不成。
姚:在畢業期間,正面臨著全國戲曲改革,這對于您來說也是很大的機遇與挑戰吧?
張:是的,當時畢業后到了高平人民劇團,最幸運的是去北京學習李維康的《蝶戀花》,在這期間李少春的《逼上梁山》,還有《望江亭》《英臺抗婚》等幾個折子戲也開始上演了,這就面臨著古裝戲的開放。所以說我們就一邊看古裝戲,一邊看《蝶戀花》的排練、演出。這一年的后半年,又上北京學《闖王旗》,是趙燕俠主演,還有李和曾、袁世海。我看到了京劇演員們排練場上的那種認真。我當時就想,我太幸福了,小時候不知道多會能去北京,想不到現在一年去了兩次。
進京學習完《蝶戀花》之后,我們就抓緊排演,這是我畢業后出節目單的第一個戲,當時在高平連演半個月,座無虛席。晉東南地區文化局組織三團一校來看演出,最后晉東南戲校把《蝶戀花》移植走了。那一年我們高平人民劇團在晉東南十分火爆,可以說把好多電影、劇團都比下去了。當時古裝戲開放了,因為咱們知道的消息早,就排演《秦香蓮》,我們抓住這個機遇,在長治蓮花池演出。因為古裝戲剛開放,人們感覺非常新鮮,蓮花池上萬人的劇場,一毛錢一票,觀眾滿滿的。我們隨后還排演了《英臺抗婚》《姐妹易嫁》等,當時人民劇團太火爆了,可以說這就是我們的戰功。
二、從觀眾中走出來的“愛珍腔”
張愛珍老師在上黨梆子演出實踐中,積極加以有益的探索創新,逐漸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唱腔風格,被專家和戲迷親切的稱為“愛珍腔”,廣為觀眾們所喜愛。以下對張老師的藝術風格以及“愛珍腔”的探索過程進行了訪談。
姚:在您的演出實踐中,對上黨梆子唱腔進行了有益的改革創新,從您的《皮秀英打虎》(下稱《皮》劇)到《吳漢殺妻》(下稱《殺妻》),再到《兩地家書》,這三部經典劇目廣為流傳,您能講講這些劇目在唱腔的運用上有哪些獨特之處嗎?
張:首先《皮》劇,原來就是按恩師吳婉芝老師的原稿全部排練下來的,也不算是很大的改革,基本上還是延續。第二稿是我在演出實踐中對聲腔的應用,特別是人物的性格表現上做了些變化。其中男女主角談情說愛的那一段【四六板】“藤蘿架上藤花開”就改成【一串鈴】(3)【一串鈴】,上黨梆子曲牌體唱腔。分兩種形式,一種為長短句,一種為七字句,適用于武旦。了,以此來表現皮秀英心直口快、活潑開朗的性格。即使有些和老師的唱腔一樣,因為理解不同,唱出來肯定有區別。
《殺妻》這個戲從1986年到現在,久演不衰,每個臺口都演,而且現在已有四代演員都在傳唱,只要是旦角演員能夠演的了《殺妻》,就給她奠定了很大的基礎。其中“窗前梅樹”那一經典唱段,原來是說白,在觀眾中演出也是很感人。后來導演、音樂設計根據我個人的條件,把說白改成了唱。之后通過在觀眾中演出實踐,我覺得把這一段改成唱腔,能夠更好發揮我的優勢,同時豐富人物心理的發展。《殺妻》是在傳統唱腔的基礎上,根據人物的個性而設計的,里邊幾個最經典的叫板,掀起了整個折子戲的高潮。特別是在人物稱呼轉換的時候,如“夫君那”“駙馬”等幾個叫板,運用的是花臉的唱法,感覺特別的揪心。“窗前梅樹”這一段,前邊是【一馬三箭】(4)【一馬三箭】,又名“幺三五”“一根錘”,上黨梆子板腔。該板式唱腔剛勁、穩健,特別是老生、須生、老旦、大花臉行當演唱時更顯粗獷、豪放。。我覺得【一馬三箭】是上黨梆子最美的、最經典的板式,慷慨激昂,把王玉蓮那種控訴、委屈、無奈的心情,以及最后成全丈夫那種大義凜然的氣度表現的淋漓盡致。之后再轉入叫板,對比抒情的“窗前梅樹是我友”。在這之后的五十多句吧,如果說都用咱們傳統的老剁板,就像“老爹爹且息怒”的唱法一樣,也能唱得過去,但是對表現人物來說,她的“三次請求”,從平靜到最后的高潮、哭訴,只是傳統的剁板唱肯定無法表現。所以我想怎么能夠像《洪湖赤衛隊》中韓英死的時候“娘……啊……兒死后”的那種感覺。之后馮來生老師,就按著這個感覺,寫出來的唱腔,其后吳寶明院長又在一些尾音上進行了修飾,珠聯璧合,出來之后,觀眾們非常喜歡。
姚:我第一次在鄉下看您的演出就是《殺妻》,現在仍回味無窮。特別是整部戲的唱腔上,已經形成了屬于您自己的風格特征,“愛珍腔”應該也是在那時候形成的吧?
張:是的,是在《殺妻》廣為知曉之后,當時有一篇文章是《看愛珍戲,四五夜不睡;聽愛珍腔,四五瓶不醉》,好多年輕人連看六七場,有的在劇場就掉淚了。所以說《殺妻》吸引了好多年輕觀眾,而且是以前不喜歡看戲、不喜歡上黨梆子的年輕人。1988年的《兩地家書》就更加成熟了,特別是在唱腔的運用以及刻畫人物的深度上,比原來講究多了。當年的馬科(5)馬科,戲曲導演、上海京劇院國家一級導演,于1988年執導上黨梆子《兩地家書》,其代表作有《曹操與楊修》等。導演,他強調刻畫人物時應該如何更加傳情。比如以前排每本戲,有個習慣,對句詞只對說白,之后到唱腔部分了,好了,把它跳過去,因為有音樂設計寫唱腔,寫出來咱們再唱。這個是不科學的,應該是你把句詞都朗誦下來,按人物感情把它讀好,讀出語氣的輕重緩急,這樣再去唱,那就不一樣了。他還強調做“小品”,讓演員每天去做“小品”,回憶你從家里邊起床以后是怎么來的排練場,回想原來的這些生活“動作”,再去思考如何演戲。有人說演戲都是假的,說你為什么不感人,不感動觀眾?是因為你表演的都是假的。通過做“小品”這些基本功來練習,出來的人物是活生生的,而且特別的感人,這就是《兩地家書》整個音樂唱腔的迷人之處。
1993年的《柴夫人》是對我的唱腔上的又一次提高。1996年還排演了《塞北有個佘賽花》,是我和郭孝明兩人主演,整場戲兩個人唱,有三百多句唱詞,那個也是在“愛珍腔”發展中的又一部作品。特別是之后的演唱會使“愛珍腔”更上一層。2017年4月,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與山西省戲劇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山西戲曲“新流派”創造經驗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對“愛珍腔”進行了廣泛深入地探討,可以說“愛珍腔”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往前走,也就是走來了30多年吧。
姚:您的“愛珍腔”,有專家認為“有繼承,有發展,融清麗于激揚”,您對于戲曲唱腔方面的繼承與創新是如何理解呢?
張:創新,我覺的本身就是“老腔新唱,新腔新唱”。“老腔新唱”,比如說我來唱一段《秦香蓮》中的【四六板】,我理解的和他們唱的就不一樣,主要體現在刻畫人物上,我這個人就需要這樣行腔。記得有一次在高平演出這部戲,幾個鄉鎮干部看完之后上臺第一句話就對我說“張老師,這唱腔改的真好聽。” 我回復說“這是傳統”。對于《秦香蓮》這部傳統戲來說,上黨梆子的老藝人也一直在創新,包括吳婉芝老師對于其句詞唱法的改革。上黨梆子《三關排宴》中也有創新。聲腔三十年一變,你每個人的嗓子,唱法出來就不一樣。我覺得有的人說一點不能動,那就把它保存到庫房算了,它就成死態的了,有的不能動的就是不能動。現在都有些摳字眼,比如說又一個流行趨勢就是講究方言。地方語咱就是地方語,非要唱成老不唧唧的(指土話),我都覺得難聽。有了唱腔的美化,有縮有放,才好聽。應該把非遺的東西包裝美給了新時代的人去欣賞,那是不是更好?
姚:是的,有繼承有創新,才能夠更好地弘揚傳統戲。作為一名戲曲演員,在您的藝術之路中,您感覺什么是需要堅持的呢?
張:首先你應該愛這個行業。堅持二字,說出來好聽,做起來難。那如果說不愛的話,肯定堅持不下來。不管是打把子,還是當宮女,首先要有這份敬業精神,你才能堅持。我覺得心里邊應該認定了這份工作,我死活要干它。我覺得有這種毅力的人,才能把上黨梆子劇種傳承下去。
作為一名演員上舞臺要認真,不管什么環境,天陰下雨還是臺下只有幾個觀眾,每場戲都應該一樣對待,不能說有一場戲馬馬虎虎演過去,在我這是行不通的,也是我帶團所不允許的。如果說舞臺上整場演出出現瑕疵,比如音響沒放開音或道具誤上了或伴奏錯了。下來之后,我不管你是多大身份,我會毫不客氣地批評你。另外如果我身體不好,嗓子不好還非得演,戲退不掉,但是唱的達不住自己要求的水平,感覺心里愧對觀眾,心里難受。所以說干啥都得認真,你如果不認真、不嚴謹,藝術就要出瑕疵。
姚:這也是您師父吳婉芝老師所教導的。您從縣級劇團一路走來,一直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可以說您是從老百姓中走出來的。
張:是的,我覺得剛畢業之后的實習演出很關鍵,我十七歲就出名了,當時已經被觀眾認可,能夠擔任大戲的主角了。而20歲到30歲這十年的成長很重要。演員沒有十年在舞臺上滾打,你是沒有功力的。必須有十年的時間,四個晚上的戲,是你一個人唱到底的角色,給觀眾唱十年,這樣才比較扎實,才能稍微成熟一點。我覺得一個是學習一個是實踐,自己就是在觀眾的口碑中紅的,是老百姓捧出來的。那時候沒有什么宣傳文章,見到一篇報道自己還嫌不好意思呢。為什么在老百姓心里扎的深,原因就是每年在鄉下演出,演出三四百場,所以說我覺得這就是我的身份。
十年磨一劍,什么東西成功都得有一個時間。對于戲曲來說,你得和老百姓融合,再加上自己的反思,直至觀眾們喜歡了,也認可了,那么就堅定不移地往下走,這樣就形成了精品段子。一個戲排出來之后沒有一年多演出實踐是不行的,需要和觀眾們產生共鳴,不斷摸索經驗。我總覺得藝術無止境,就在這。
三、美不過家鄉戲五種聲腔
上黨梆子以演唱梆子腔為主,兼唱昆曲、皮黃、羅戲、卷戲,俗稱“昆梆羅卷黃”。從現存舞臺題壁可知,至少在十八世紀中葉,上黨梆子已經是一個擁有五種聲腔的成熟劇種。無論是其聲腔類型、劇目種類、音樂特色,還是傳承脈絡、傳播范圍等都有其獨特性,以下就這些內容對張老師進行了訪談。
姚:有一句話叫做“高不過太行山與天同黨,美不過家鄉戲五種聲腔”?可以談一下您對于上黨梆子五種聲腔的認識嗎?現在上黨梆子的“昆梆羅卷黃”五種聲腔,還都有保留和傳唱嗎?
張:“高不過太行山與天同黨,美不過家鄉戲五種聲腔”這一句是吳寶明院長的經典詞,這是在我的演唱會上主持人白燕升運用的。提起“昆梆羅卷黃”這五種聲腔,不得不說自己的演唱會(6)2010-2012年,上黨梆子名家張愛珍演唱會分別在山西晉城、太原、長治、陽城皇城相府、臺灣新竹舉辦,演唱會上的唱段主要有《殺妻》《兩地家書》、上黨時調《浪子踢球》、傳統曲目《殺四門》、上黨昆曲《長生殿》、上黨二黃《打金枝》、新編現代曲目《李雙雙》《塞北有個佘賽花》等。,你看為什么演唱會中,一個是我的經典段子,這是必有的,另外是傳統戲和現代戲要全,其次是板式上要全,再次是五種聲腔要全。當時我就要求這方面的內容,咱們的上黨梆子,比如說《殺四門》,那些戲也都快失傳了。《殺四門》那段唱是咱們上黨梆子打擊樂最豐富,最精彩的。另外,我把上黨昆曲《長生殿》、上黨二黃和反二黃加入。我特別喜歡反二黃,加入《虹霓關》那一段。最后演唱會彩排了總共十段,其中有四段是我以前沒有親自唱過的。之后我就抓緊學習,遵循吳寶明院長所強調的根據塑造的人物個性來演唱。在晉城澤州會堂的演唱會結束后,好多老年觀眾激動地說,“今晚才嘗到了小時候的《殺四門》、上黨昆曲《長生殿》的味道。”
姚:您演唱會當時很成功,可以說上黨梆子的五種聲腔中有些已經失傳了,比如說卷戲、羅戲,亟待保護傳承。就您所知咱們的上黨梆子是否有一個傳承譜系?您是第幾代傳承人?
張:應該是趙清海最早,其次是段二淼、郭金順、申銀洞等,再下來是郝同生、郝聘芝、吳婉芝等,再下來是馬正瑞、高玉林等,再下來是我們這代,張保平、吳國華、郭孝明等。我們再下一代就是陳素琴、杜建萍、成靜云、索偉琴、張敏麗、宋晉梅等,再下來是李丹、邱亞萍、魏璐穎等,再下來就是高平中專我們培養的這一代。一般一代相隔是10到15年左右的樣子。
姚:上黨梆子的藝術特色是粗獷豪放的,因為它演出的多為朝代大戲,如《岳家軍》《楊家將》等,那還有細膩抒情的地方嗎?
張:咱上黨梆子演楊家戲、岳家戲多,在咱這個地方沒楊家戲,就不過癮。一個劇團如果沒有蟒、靠,就覺得你小家子氣。特別是下午場,熱鬧!上黨梆子細膩的,也就是抒情的方面比較少。因為咱們上黨梆子中閨門旦、小旦、小生這樣的行當比較少,所以這些生旦戲就少,只有青衣、老旦和須生這樣的楊家戲。小生、小旦肯定要委婉細膩的多,因為談情說愛嘛。但是包括《殺妻》《兩地家書》中也很少表現談情說愛的。咱們現在的板式在原來基礎上已經發展了很多,包括剁板等好多種,以前也就是兩三種。現在可以根據句詞的長短,能出來不同的唱腔。根據你的人物,寫出不同人物的個性唱腔。
姚:上黨梆子過去分為州底派和潞府派,州底派主要流行于原澤州府,行腔較穩健、平緩,注重聲音的藝術表現力。潞府派主要流行于原潞安府和沁州,行腔高昂而常大起大落,注重情緒的強烈表現,現在這兩派還有區分嗎?
張:兩派之間肯定相互學習,他們的東西在咱們(州底派)里邊,咱們的東西他們又吸收上了。通過演員之間相互的串班演出,相互學習,它就有一種融合。另外就是咱們州底派,本身在唱腔的地方語言上就不同,像咱們這兒就分成高平音、陽城音等。都說高平的上黨梆子正宗,我覺得主要是在語言上。高平說話位置靠上,鼻音大,唱出來的味道好。你看吳婉芝老師的唱腔就都在鼻音上。大家有時候議論,人家唱的這個味真是好啊,這就是強調的唱腔這個味。再一個唱腔要有個性,包括演員的個性、聲音的個性、表現的人物的個性。
姚:上黨梆子在清光緒年間傳到了山東菏澤和河北永年地區,并發展成為了棗梆和西調兩個姐妹劇種,現在咱們相互之間還有交流嗎?
張:這些都是過去老藝人逃荒傳過去的。應該感謝那些藝人,咱們的地方戲傳出去以后,又在那個地方生根發芽,發揚光大,我覺得他們為上黨劇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以前山東棗梆、永年西調,每年都在咱們這演出。最近幾年演員互相往來,交流也增多了。看他們的戲,和咱們一樣的地方很多,只是落腔、尾音等,有時候不同。我感覺一是咱們的方言不同,另外就是咱們老藝人,傳的時候有可能就唱成這樣了。永年西調,那就是咱們給出的孩子。老藝人在其他地方傳播的時候,還保留了一些傳統的唱法。咱們上黨梆子中的《潘楊訟》,就是移植的人家永年西調的。
姚:戲曲作為一門綜合藝術,除去唱腔之外,表演動作也是重要的內容。對于上黨梆子來說,有哪些講究的地方呢?
張: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哪樣都離不了,當然我是以唱功為主,還有水袖,但比較少。現在好多話劇導演排戲劇,對“手眼身法步”不講究了。大部分和話劇一樣,舞美、燈光,舞臺上豪華的不得了,把表演程式的東西都丟失了。一個演員必須打好童子功,必須學開腰腿、拿頂、翻功、把子功、扇子功等。現在有些沒有基本功,出來之后就完成不了這個任務。當然用技巧表現人物,但如果為技巧而技巧,離開了人物也不行,應該把技巧很合理的運用到人物中。
姚:上黨梆子的音樂也很有特色,包括各類板式、花腔、曲牌等等,其傳承和發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張:小時候學譜子,當時的觀念就是樂隊好好學,演員學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因此演員在這一方面比較欠缺。如果說譜子你都讀不準,你也就不懂如何把唱腔唱好,如何唱出感情。所以樂隊和演員都應該好好地學習樂理知識。
吳寶明院長的《上黨梆子音樂》最近就要出版了,這本書比較全面,包括了上黨梆子曲牌等打擊樂以及各種唱腔的浪頭等,但是咱們戲里邊不可能用全了,有些不用的就慢慢丟失了。現在新創劇目的作曲中,吳院長就運用了好多傳統音樂。但是咱們年輕人,因為學的少,他老感覺是移植過來的。其實是在上黨梆子原有音樂的基礎上,把它拆開或者整合而成的,所以還是在傳統方面了解的不透徹。另外現在非遺傳承人就沒有戲曲音樂這一塊,可以說演員都是作曲的捧出來的。以前是沒有音樂設計,也沒有導演,由拉頭把的和演員來設計唱腔。現在有了音樂設計,但沒有編入非遺傳承人當中,全國都沒有,就沒有設立。我感覺應該設立,戲曲沒有音樂不行,演員不靠音樂設計能成功嗎?
四、從管理到傳承,從未停步
從戲校畢業之后,張愛珍老師分別進入高平和晉城上黨梆子劇團工作,先后當任縣、市劇團的領導,為扭轉劇團的經營狀況,她肩挑重任、銳意進取、改革創新。在離開劇團之后,又積極開展了一系列的戲曲傳承工作,提攜后輩、言傳身教,對上黨梆子藝術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故以下對其劇團管理、傳承工作以及對上黨梆子未來發展的思考等方面進行了訪談。
姚:在劇團管理方面您曾經大膽創新,特別是您當二團團長(7)考慮到演員個人發展和劇團經營狀況等原因,晉城市上黨梆子劇團曾經有過分團和合團的情況,時間分別在1990年和2002年。后就確定了“真正改革、慘淡經營、如履薄冰”的十二字建團方針,具體有哪些舉措呢?
張:說起改革,我夠大膽了。因為當初分團時分為第一和第二演出團。分人的時候,比如說兩個花臉,就是一家一個,如果是只有一個,就給一團。為什么這樣做呢?上級覺得我在縣里邊當過領導,有經驗,不擔心。我這里是年輕化,可以到社會上去招聘,但必須保證一團的。所以說當時對我比較嚴格,給的任務比較艱巨。改革主要是打破原先的工資制度,也就是不管是中專生還是臨時工,按打分制來定崗。如果誰不上了,你給誰救場了,那就賺他的一份。所以就有了獎勵激勵機制,這種機制還是挺好的。但是打破了以前的制度,就需要做一些工作,因為好多人不太情愿,慢慢的大家就理解了。這種機制也為后來合團的改革奠定了很大的基礎。
姚:只有真正的改革才能更好地促進劇團的發展,這也是您對于劇團管理的經驗總結,對現今劇團的管理改革仍有很多借鑒意義。我們知道后來在合團之后,您退出劇團,并從那時起開始了上黨梆子的傳承工作?
張:當時按我的年齡正是唱戲的時候,也是觀眾希望一直看到你創作新作品的時候。但是合團之后,就出現了對我藝術發展不利的一面。我退下來已經十幾年了,你想一個人能有幾個十年。因此,說遺憾也算遺憾。遺憾的是自己在舞臺上應該展示的時候,不在舞臺上,不遺憾的是你能親自做一些傳承工作。這幾年,就傳承來說,主要是培養杜建萍,把她一步步推到梅花獎的獎臺上。在順其自然能夠做什么的情況下,做了一些工作,思維一直沒有停下來。也為觀眾演出戲曲,因為高平上黨梆子青年劇團是我當年創業的地方,是因我而成立的,所以他們叫我,我就過去輔導他們。他們的戲價低,打上我的名就能漲高戲價,演職員就能多發工資。我想這也行,只要我的名字能夠給大家帶來富裕的收入,這也值得。只是大家想看我的新作品的時候,不好遇到機會了。但也沒有什么遺憾,你早點退出舞臺,讓年輕人展示,這也是咱們應該做的。因為我們上一輩,高玉林老師就是四十多歲退出舞臺,把我們捧出來的。所以說我們也應該捧下一代,這是一個演員的責任。
姚:這十幾年您也在不斷思考,如何更好地傳承上黨梆子這一劇種。特別是在您被評為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之前,就已經開始籌備建立自己的傳習工作室?當時為什么要建立傳習工作室?傳習工作室的主要工作有哪些?
張:為什么要搞傳習工作室?其實我原計劃在沒有平臺的時候,就想成立一個自己的工作室,更好地傳承咱們的上黨梆子。后來經過各種努力終于建起來自己的戲曲傳習工作室,在全省可能也是第一個。這個傳習工作室掛牌之后,正好趕上去臺灣開演唱會。因為出境的話需要辦手續,如沒有這個工作室,就沒法辦理手續,你還去不了臺灣。所以說剛成立起來,就做了這件大事。這之后,傳習工作室的新聞一播出,高平中專張春生校長就找我談,想招生辦個戲曲班,由我負責戲曲專業教學,這樣就和高平中專辦了一件大事,培養了一批戲曲后備人才。他們中專六年制,今年(2018)就要畢業了。這一批學生是一個完整的班子,女演員小四十名,男演員是27名,樂隊38名。我一直想培養一個好樂隊,因為當時我團里樂隊就是最棒的。由此培養了上黨梆子歷史上第一代女鼓師、女琴師,而且反響很好,咱們已經連續五年上晉城市春晚。其次是在2016年參與“非遺文化上黨梆子”戲曲進校園系列活動,走進晉城10余所中小學。在這期間我培養的孩子們積極參與其中,他們演出已經很有經驗了。
姚:這也是您在反哺家鄉,為上黨梆子培養后備人才。除此之外,您還積極培養上黨梆子小演員,并且有多人獲得小梅花獎,咱們這個小梅花獎也是傳習所來培養的嗎?
張:小梅花獎是中專和傳習所一起培養的。小梅花獎拿了四朵了,計劃2018年再拿上一朵,他們的年齡也就到了,因為有年齡限制。所以說這幾年也很費心,真的,雖說沒有唱戲,我就一直在做這個。為什么兩年多我一直沒有上臺呢?一方面嗓子一直生痰,其次杜建萍去拿梅花獎,還有這批學生費心。所以說,我的身體有些透支了。家里的事務也顧不上照顧,包括孫子也顧不上照看,自己家人幫著承擔、付出了很多,家庭成為了自己堅強的后盾。自己一心撲在上黨梆子上了,同時又想達到所想要的結果,所以這幾年比較辛苦。做這些也就是給上黨梆子培養了傳承人,作為我一個年齡這么大,話說就是太陽要落山的一個演員,能做的事也就是發揮我最大的余熱,從未停步,一直在做。
姚:作為非遺傳承人,您在自覺地傳承著上黨梆子藝術,這也是您文化自覺的表現,由此您身上的責任確實會比較大。
張:對于傳承來說,我也是不斷思考如何把咱們上黨梆子精華的東西運用到所演出的戲曲人物上,讓他們更豐富飽滿,我感覺這樣才有價值。現在,我這個“愛珍腔”基本確立了,但“愛珍腔”不是我個人的,它是劇種的財富,那徒弟就得把“愛珍腔”傳承下去。如果這個徒弟有能力傳承下去,他們也可以超越。這不是死的,你只要把這個唱腔把握了,你去運用它,出來的味道不一樣了才漂亮呢。但是必須遵照四聲,不能倒字,吐字就是地方的普通話。其次,對于上黨梆子來說現在需要整理改編一些傳統劇目,讓各個劇團唱,才能傳承下去。上黨梆子傳統劇目有300多,經常唱的只有二三十個。比如有的劇本還需要修改豐富,現在的劇本都是干巴巴的,沒有肉,這些需要加強。
姚:為了更好的傳承上黨梆子和您的“愛珍腔”,您也有正式收過徒弟嗎?
張:我正式收的有四個,杜建萍、索偉琴、邱亞萍、魏璐穎,還有幾個學生是我內部收的,總共八九個吧。我在收徒的認識上是,徒弟首先具備基本條件,再一個是做人。另外你收上徒弟,老師就有責任對他負責,如何培養將自己的藝術傳承下去。
姚:現在咱們劇團的發展有沒有困境,有沒有青黃不接的感覺?您感覺咱們上黨梆子發展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張:怎么沒有,縣里邊就不行,中層力量太差。包括須生,男角色很缺,小生就更別提了。你要說人才有沒有?是有,你看市里邊人才濟濟,但是輪不上唱。我覺得上黨梆子的發展還是需要有人才,其次還得讓這些人才有平臺。現在培養出來了,如何來保護他們是個大問題。所以說這就需要有個好領導,一個寬宏大量,有文化情懷、遠見卓識,并全面考慮劇種未來發展的領導。
姚:上黨梆子的傳承和發展確實有很多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各界的共同努力。您也為此付出了很多,在近幾年的看似沉寂中,您也從未停止過思考實踐。
張:我甚都不關心,就是操心唱戲多,干甚太認真,要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的漂亮。現在我覺得,咱做的事無愧于組織的培養就可以了,能做的盡量做,一生想做完是不可能的。只是覺得有時有力出不上,不是很圓滿。遺憾的是自己感覺缺一部戲,現在要是有一部新戲,有一個好角色,你看,給觀眾們過癮的發揮發揮,那多好!
姚:謝謝張老師接受我的訪談,自己對上黨梆子藝術和您的從藝經歷有了更為深入地了解,希望上黨梆子藝術廣為流傳,也祝您的藝術之路常青。
后記:拜訪當天是2017年農歷臘月二十三。上午張愛珍老師還在忙著指導學生,接近中午才得以相見,在她家中訪談近一小時,后被住在同一家屬樓的吳寶明夫婦邀請共進午餐,共度小年。餐桌上吳寶明夫婦和張愛珍、張建國夫婦談及上黨梆子的現狀以及未來發展,表現出很多憂慮同時又有更多的期盼。期間我給他們敬酒以表謝意,真切地感受到了家庭的和睦對于個人發展的重要性。飯后,在張愛珍老師家中繼續訪談至傍晚時分,張老師在訪談過程中感情投入,情深至極常常心有所動而盡情的回憶往事。上黨梆子作為自己的家鄉戲,我為有張老師這樣的藝人的堅守而感到驕傲,也更愿為其傳承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