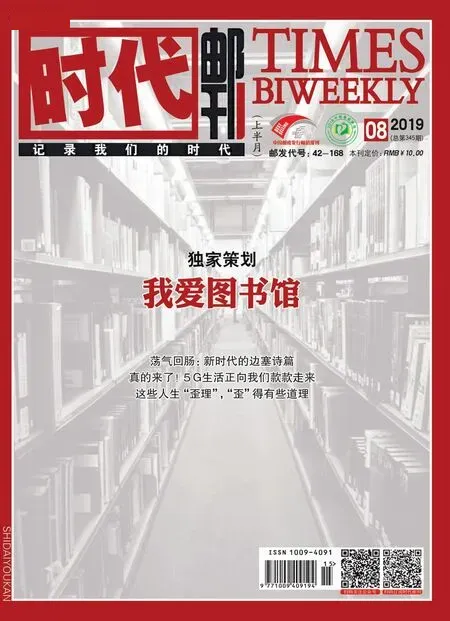放生
■郭震海
山下,有一條寧?kù)o的小河,晨風(fēng)輕輕走過(guò),寧?kù)o的河水泛起粼粼波光。
他自山中來(lái),一身布衣,頭戴一頂寬邊草帽,一只手里提著兩個(gè)空魚簍,在晨風(fēng)中搖搖晃晃,一只手里拎著漁網(wǎng)。
他來(lái)到小河邊,放下魚簍,先是站定目測(cè)水面,然后手劃水面,隨后雙手一揮,漁網(wǎng)拋向空中,就如瞬間綻開的巨大花朵,落入水中。
每天早上,他不多也不少,只下一次網(wǎng),就要兩簍魚。大魚也好,小魚也罷,他都要。
他捕魚不食魚,也不拿到集市上去賣。倘若你問(wèn)他捕魚用來(lái)干什么?他長(zhǎng)滿胡須的嘴微微一動(dòng),吐出兩個(gè)字:“坐等。”
日升三竿,沿河的一條大道,熱鬧起來(lái),一輛輛車,三三兩兩的人,沿著大道,來(lái)來(lái)又去去,消失在山中,山后就是一座城,一座繁華的城。山上有一座廟,廟里香火很盛。
網(wǎng)已收,魚滿簍。他悠閑地坐在河邊的一塊青石上,確如他所言,是在坐等。陸續(xù)有香客沿著高高的石臺(tái)階走下山來(lái),有的會(huì)來(lái)到他面前,買魚。
他賣魚不論斤,論條,一條10元,高高豎起的紙牌上明碼標(biāo)價(jià),不討價(jià),當(dāng)然來(lái)者也不會(huì)還價(jià)。來(lái)者買魚后,不會(huì)帶走,而是來(lái)到河邊,虔誠(chéng)地一條條放入水中,名曰“放生”。
午后,兩簍魚全部賣光。一條條小魚兒來(lái)自小河,又重新回歸小河,他又如早上來(lái)時(shí)那樣,一只手提著兩個(gè)空魚簍,搖搖晃晃,一只手拎著漁網(wǎng),優(yōu)哉游哉地回家。路過(guò)集市,他會(huì)買二斤牛肉,打二兩散酒,也會(huì)為妻子買條絲巾,或?yàn)?0歲的老娘買點(diǎn)愛(ài)吃的糖酥點(diǎn)心。
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他每天早上來(lái),中午回。總是那般悠閑,那般自在,似乎和山上的廟,與河里的魚達(dá)成某種默契。有了山上的廟,才會(huì)有虔誠(chéng)的信徒來(lái)祈禱、來(lái)“放生”,有了“放生”,就有了他的每天捕魚,形成一個(gè)完美的供需“鏈條”。
買魚者說(shuō),他們買魚,是為了“放生”,是行大善,是為自己或家人祈求幸福安康。
賣魚者說(shuō),他捕魚不殺魚,僅供“放生”,也是行善。他靠賣“放生魚”養(yǎng)著一家老小,小日子過(guò)得蠻滋潤(rùn)。
每一次途經(jīng)小河邊,我總會(huì)忍不住駐足,靜觀許久,也靜思很久……或許,在這個(gè)世界上,有許多事情一旦形成某種平衡,就很難用簡(jiǎn)單的對(duì)與錯(cuò)、是與非去衡量,就像這“放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