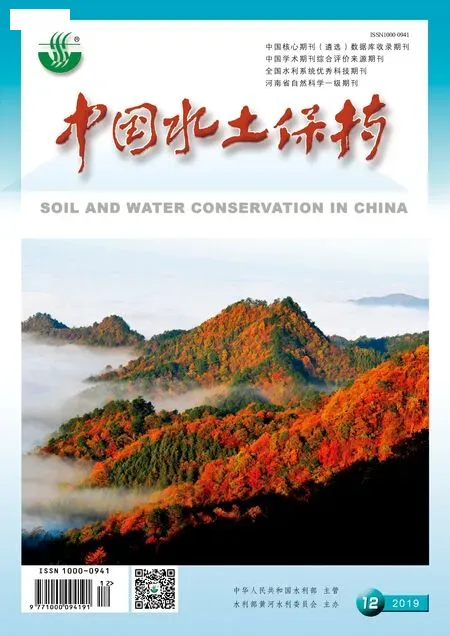江西省2018年度省級重點監測區水土流失動態監測中存在的問題與建議
劉桂成,李相璽,萬小星,田魏龍,卿 娟,廖元群,徐丹巧,劉子銘,齊述華
(1.江西師范大學 鄱陽湖濕地與流域研究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地理與環境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2.江西省水土保持監督監測站,江西 南昌 330009)
土壤侵蝕是陸地表面在水力、風力、凍融和重力等外力作用下,土壤、土壤母質及其他地面組成物質被破壞剝蝕、轉運和沉積的全過程。土壤侵蝕造成土地退化、土壤肥力降低、河流淤積等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20世紀50年代美國農業部根據1萬多個徑流小區試驗資料,歸納統計提出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1997年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修正模型RUSLE。20世紀70年代被引入我國,目前已經得到廣泛應用[1-4]。
筆者按照水利部印發的《區域水土流失動態監測技術規定(試行)》的要求,利用CSLE模型開展了江西省2018年度省級監測區的水土流失動態監測,對監測成果進行野外復核,并對區域水土流失動態監測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總結,提出改進建議。
1 研究區概況
江西省地處長江中下游南岸,屬東亞熱帶季風氣候區,降雨季節性明顯,疏松的紅壤地表、多山的地形條件及頻繁的生產建設活動等造成水土流失易發、多發的特點,是我國南方紅壤丘陵區水土流失嚴重省份。根據全國第一次水利普查結果,江西水土流失面積26 496.87 km2,水土流失依然是制約江西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8]。
根據《江西省水土保持規劃(2016—2030年)》,江西的省級水土流失監測區有76個縣(市、區),面積113 964 km2,其中省級重點監測區和一般監測區分別有39和37個縣(市、區)。根據全國第一次水利普查結果,省級水土流失重點監測區的水土流失面積為15 605.71 km2。
2區域水土流失動態監測方法
按照水利部2018年印發的《區域水土流失動態監測技術規定(試行)》,區域水土流失動態監測中水力侵蝕采用CSLE方程計算
A=R×K×L×S×B×E×T
式中:A為土壤侵蝕模數,t/(hm2·a),表示單位面積坡面多年平均年土壤流失量;R為降雨侵蝕力因子,MJ·mm/(hm2·h·a),表示雨滴及降雨形成徑流對土壤顆粒的分離與輸移能力,該因子具體取值由水利部水土保持監測中心分發;K為土壤可蝕性因子,t·hm2·h/(hm2·MJ·mm),表示土壤抵抗雨滴和徑流分離土壤顆粒的能力,與土壤理化性質有關,該因子具體取值由水利部水土保持監測中心分發;L為坡長因子,無量綱,是指其他條件(降雨、土壤、坡度、土地利用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等)一致情況下,某一坡長的坡面土壤流失量與坡長為22.13 m的坡面土壤流失量之比,反映了坡長對土壤侵蝕的影響,監測區1∶5萬地形圖生成10 m分辨率DEM并輸入符素華等研發的LS模型計算[9];S為坡度因子,無量綱,是指其他條件(降雨、土壤、坡長、土地利用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等)一致情況下,某一坡度的坡面土壤流失量與坡度為5.14°的坡面土壤流失量之比,反映了坡度對土壤侵蝕的影響,監測區1∶5萬地形圖生成10 m分辨率DEM并輸入符素華等研發的LS模型計算[9];B為植被覆蓋與生物措施因子,無量綱,是指有植被覆蓋的坡面土壤流失量與同等條件下(降雨、土壤、坡度、坡長、工程措施和耕作措施一致)清耕休閑地土壤流失量之比,反映了植被覆蓋對土壤侵蝕的影響,通過收集前3年監測區范圍內23期Landsat和MODIS影像,融合法或參數修正法計算得到24個半月30 m分辨率NDVI數據;E為工程措施因子,無量綱,是指采取某種工程措施坡面土壤流失量與同等條件下無工程措施坡面土壤流失量之比,反映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作用,根據各工程措施的因子賦值查表確定;T為耕作措施因子,無量綱,是指采取某種耕作措施的坡面土壤流失量與同等條件下傳統耕作的坡面土壤流失量之比,傳統耕作指順坡平作或壟作,T因子反映了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的作用,根據耕作措施和輪作措施查找表獲取耕作措施因子值。
在獲取土壤侵蝕計算各因子的基礎上,利用ArcGIS軟件進行柵格運算,獲取土壤侵蝕模數,并依據《土壤侵蝕分類分級標準》(SL 190—2007),評價土壤侵蝕強度。
根據江西省2018年度省級防治區水土流失動態監測成果反映的情況,重點針對水土流失強烈及以上侵蝕地塊和植被覆蓋度高但發生侵蝕的地塊,在上饒縣等16個縣(市、區),對60個土壤侵蝕地塊進行了野外復核。
3 結果與分析
3.1 土壤侵蝕因子空間分布
按照耕地、園地、林地、草地、建設用地、交通運輸用地、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和其他土地8個一級地類進行面積統計和面積占比統計。省級水土流失重點監測區土地總面積113 964 km2,其中:耕地面積為26 323.57 km2,占總面積的23.10%;園地面積為1 661.88 km2,占1.46%;林地面積為68 366.42 km2,占59.99%;草地面積為527.03 km2,占0.46%;建設用地面積為7 305.40 km2,占6.41%;交通運輸用地面積為848.55 km2,占0.74%;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面積為8 731.31 km2,占7.66%;其他用地為199.84 km2,占0.18%。
降雨侵蝕力為5 300~9 900 MJ·mm/(hm2·h·a)之間,降雨侵蝕力較高。贛東北是暴雨集中區,侵蝕性降雨強度大,降雨侵蝕力明顯高于其他區域。地形坡度以小于5°的為主,占總面積的36.54%,廣泛分布在中部平原地區,其次是8°~15°和15°~25°坡度范圍的土地面積分別占15.41%和22.26%。坡長小于100 m的土地面積占監測區總面積的60.6%,坡長為100~200、200~300 m的土地面積分別占總面積的24.06%和12.34%。高植被覆蓋區占監測區總面積的48.87%,以園地、林地、草地為主,而園地、林地和草地的78.94%為高植被覆蓋區。受衛星影像空間分辨率的限制,解譯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為水平階和梯田,分布在東北部和中西部多山的縣(市、區),并以梯田為主。
3.2 監測區水土流失空間分布特征
2018年度省級水土流失動態監測結果為:江西省級重點監測區水土流失面積為14 359.73 km2,占省級重點監測區面積的12.60%,其中輕度侵蝕面積為11 625.90 km2,占總侵蝕面積80.96%;中度侵蝕面積為1 537.89 km2,占10.71%;強烈侵蝕面積為663.25 km2,占4.62%;極強烈侵蝕面積為436.44 km2,占3.04%;劇烈侵蝕面積為96.25 km2,占0.67%。平均土壤侵蝕模數為338.17 t/(km2·a),總土壤侵蝕量為0.385億t。相比于第一次水利普查結果,水土流失面積減少了1 245.98 km2,水土流失面積減少比例為7.98%,其中輕度侵蝕面積增加2 597.42 km2、中度侵蝕面積減少2 875.91 km2、強烈侵蝕面積減少1 014.52 km2、極強烈侵蝕面積增加4.77 km2、劇烈侵蝕面積增加42.26 km2。
受侵蝕性降水強度大等因素的影響,盡管贛東北地區的植被覆蓋度較高,但水土流失較為普遍。由于地勢平坦且城鎮化發展快,鄱陽湖平原和吉泰盆地的水土流失面積較小,并以輕度侵蝕為主。此外,坡耕地廣泛分布,在坡耕地梯地化改造等工程措施下,土壤侵蝕強度顯著降低,坡耕地主要以輕度侵蝕為主。生產建設和農業開發等原因造成強烈及以上等級的土壤侵蝕面積占總水土流失面積的8.33%。強烈及以上等級的土壤侵蝕區主要土地利用類型為建設用地和耕地,分別占總水土流失面積的29.92%和52.02%。侵蝕面積統計結果見圖1。

圖1 按照土地利用方式、高程分帶和坡度分帶的土壤侵蝕面積分布
3.3 區域水土流失評價中存在的問題
針對水土流失強烈及以上侵蝕地塊植被覆蓋度高但發生侵蝕的情況,在上饒縣等16個縣(市、區),對60個土壤侵蝕地塊進行了野外復核,其中54個復核地塊的監測結果與實際情況相符。監測結果與實際情況不一致的地塊主要發生在建設用地和林地,造成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數據的現勢性難以滿足準確評價的要求。城鎮擴張過程中存在削山造地、填湖造地等對陸表地形和土壤覆被條件的改變,都沒有在動態監測中所采用的土壤圖和地形圖中體現,造成土壤侵蝕評價的偏差。例如景德鎮市昌江區如意湖公園在2017年的高分影像中處于施工狀態,復核時項目已建設完工,部分為荒草地,地勢平坦;贛州市龍南縣在稀土尾礦治理中將所有山地填平,并已將其開發建設為工業園。
部分采石場等在持續開采過程中,已經對區域土壤類型產生顯著的影響,表層土壤喪失,巖石暴露,由過去的疏松紅壤覆被退化為裸巖,所采用的土壤圖沒有反映這種變化,導致評價中土壤侵蝕模數計算結果不準確。
(2)生產建設項目中的水土保持措施解譯缺失。在對部分縣(市、區)核查中發現,大部分生產建設項目都采取了邊坡復綠、竹節溝等水土保持措施,這些措施都能夠有效地減少水土流失,但目前技術規程中對這類措施因子的水保效益評定缺少明確的修訂參數,忽略了這些小型水土保持措施發揮的效益。此外,受衛星影像空間分辨率精度的限制,難以有效提取水土保持措施。各地區對生產建設項目的水土保持方案編制審批進度和實際落實情況也不一致。在生產建設項目開展的過程中,水土流失主要發生在施工階段,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天地一體化”中生產建設項目的水土保持監管可以加入水土流失動態監測,尤其是對批復的重點工程項目的監管,獲得更全面的監測數據基礎上反映真實的水土流失情況,對水土保持方案中規定區域預測的水土流失量、強度及動態變化進行監測[10-11]。
(3)在計算果園、其他園地、有林地和其他林地土壤流失比例時,技術規程中要求喬木林的林下蓋度按實地調查或經驗取值,范圍為0~1。實地核查經驗取值或者取NDVI曲線中值,使得每個縣(市、區)的林下蓋度值都會不同,對該地類的輕度侵蝕面積造成一定影響,林下蓋度取值越高,該林地的侵蝕模數就越低。可以在各個監測點中建設林草樣地,進行24個半月林下蓋度的拍照,得到多樹種、多地區的全年林下蓋度曲線,為今后的監測工作提供數據基礎。
(4)土地利用解譯圖斑中存在少量目視解譯錯誤,比如將有林地解譯為灌木林地,根據植被覆蓋與生物措施因子計算公式會導致該圖斑的植被覆蓋與生物措施因子值偏大,從而造成侵蝕模數增大。
(5)降雨侵蝕力因子通過收集全省站點多年平均1至24個半月降雨侵蝕力數據插值得到。由于年代、技術和站點數量的限制,全省范圍的降雨量數據不夠全面精確,造成一定偏差。暴雨集中區的降雨侵蝕力偏大造成該地區的總體侵蝕強度增加。
(6)植被覆蓋度計算方法的不統一,造成植被覆蓋度的差異較大。技術規程中提供了2種24個半月植被覆蓋度計算方法,即融合計算方法和參數修正方法。不同的技術單位計算植被覆蓋與生物措施因子的過程難以統一,從而造成評價結果的不一致。
4 結 語
按照水利部印發的《區域水土流失動態監測技術規定(試行)》的要求,利用CSLE模型開展了江西省2018年度省級重點監測區的水土流失動態監測,得到以下結論:
(1)總體上,CSLE模型適用于區域水土流失動態監測,特別是在我國存在大量坡耕地和水土保持措施的情況下,CSLE有其獨特的優勢,但有必要進一步開展土壤可蝕性因子、降雨侵蝕力的率定,以及地形因子的尺度效應等基礎性研究。
(2)江西省2018年度省級重點監測區的水土流失面積為14 359.73 km2,占省級重點監測區面積的12.60%,平均土壤侵蝕模數為338.17 t/(km2·a),總土壤侵蝕量為0.385億t。
針對水土流失動態監測中存在的問題,建議從以下幾方面修訂《區域水土流失動態監測技術規定(試行)》:①統一植被覆蓋度遙感獲取的方法;②針對礦山、采石場等對地形和表層土壤的破壞,明確界定這些區域為強烈侵蝕區;③加強南方典型水土保持措施的水土保持效益的定量評價;④加密使用雨量站觀測資料,完善降雨侵蝕力的計算。
水土保持信息化監管的順利開展,需要強化基礎性工作,這就要求進一步強化各縣(市、區)水行政主管部門的水土保持信息化人才隊伍建設。盡管服務于水土保持信息化的衛星遙感影像空間分辨率顯著提高,但水土保持措施的準確解譯仍然存在困難。江西省歷來重視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治理成效非常顯著,但是由于水土保持信息化人才缺乏,水土保持措施的信息化工作比較薄弱,水土保持措施“上圖”工作不到位,導致水土保持工作成效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