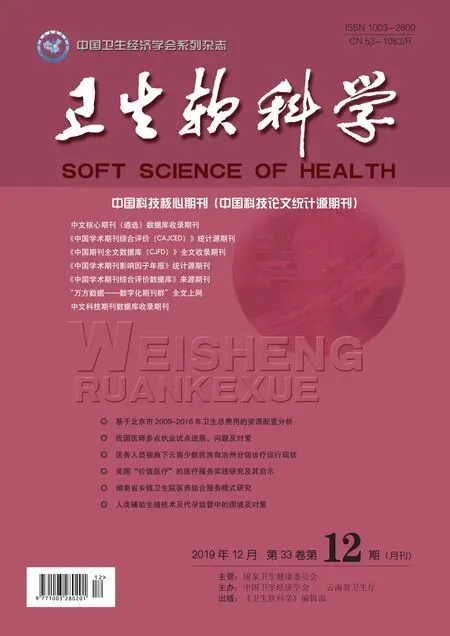大數據背景下健康辟謠現狀研究述評
魏海斌,蘇菁涵,吳一波,鄭智源
(1.廣西中醫藥大學,廣西 南寧 530200;2.廣西醫科大學,廣西 南寧 530000;3.北京大學藥學院,北京 100191;4.福建醫科大學,福建 福州 350004)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并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衛生健康領域則集中體現為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與人民健康需求之間的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我國實施并持續推進“健康中國”戰略,人民群眾的健康意識大大提高,健康觀念也由治療疾病向保障健康轉變,健康信息成為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
2015年9月,國務院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系統部署大數據發展工作。大數據具有5V特點(IBM提出):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alue(低價值密度)、Veracity(真實性)。《綱要》的頒布以及大數據工作的開展無疑將極大地助推“健康中國”建設。但不可否認,在大數據背景下,健康信息良莠不齊、真假難辨。
目前,與大量健康信息產生與傳播形成對比的是我國居民健康素養狀況不容樂觀。根據2017年最新監測結果顯示,我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為14.18%,比2016年的11.58%增長了2.6個百分點,而2008年首次監測數據僅有6.48%,且存在“城鄉居民差異大”“與文化程度密切相關”“低齡、高齡兩級素養低”和“知識理念與行為之間存在差距”等問題。我國公民基本健康素養情況不容樂觀。
基于上述情況,健康謠言肆意傳播,對人民群眾的健康權益、衛生(健康)部門的正常運轉以及健康事業的有序發展形成了極大阻礙,大數據背景下的健康辟謠相關研究亟待開展。
1 對象與方法
健康辟謠的對象是健康謠言,而在大數據背景下“健康謠言”又是“網絡謠言”的一種專業性細分議題。因此,“網絡謠言傳播與治理”的相關文獻能夠為“健康辟謠”所借鑒和引用。故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網絡謠言”和“健康謠言”有關的文獻材料。
通過查詢萬方數據庫,分別以“網絡謠言”和“健康謠言”為關鍵詞,以關鍵詞的模糊匹配與組合方式,對近20年(1998-2018年)的期刊文獻進行檢索。并通過查詢人民網、搜狐網等權威媒體官方報道,借助Nvivo 12.0軟件,對近5年(2014-2018)“十大健康謠言”內容進行定性分析。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經檢索,共得到 “網絡謠言”相關文獻5115篇,“健康謠言”相關文獻746篇,并通過梳理得出了近20年(1998-2018年)的文獻檢索對比,結果網絡謠言與健康謠言的研究大致都可以分為4個階段:一是萌芽階段(1998-2002年),期間相關概念和理論剛剛引入,二者年均文獻數量均不足5篇;二是初步發展階段(2003-2008年),期間受互聯網普及以及“非典”事件等因素影響,網絡謠言年均文獻數量逐步突破了100篇,健康謠言近20篇,二者開始拉開差距;三是快速發展階段(2008-2011年),期間因互聯網的持續發展及福島核事故事件,二者文獻數量猛增,前者年均達到200篇,后者逼近40篇;四是穩步發展階段(2012-2018年),期間受國家相關政策影響,二者文獻數量總體保持穩定增長態勢,前者文獻數量峰值突破800篇,后者達到120篇。
2.2 “網絡謠言”相關文獻梳理
明確謠言概念內涵是開展相關研究的前提。在《康熙字典》(1716)中,謠言是指沒有事實存在而捏造的話[1]。《韋伯斯特英文大字典》(1828)指出,謠言是一種缺乏真實根據或未經證實、公眾一時難以辨別真偽的閑話、傳聞或輿論[2]。
2.2.1 謠言傳播危害
Benjamin(1983)[3]、藺秀云(2005)[4]認為謠言傳播危害嚴重,消息傳開后將產生明顯的社會負面影響力,容易造成社會恐慌、社會秩序混亂、經濟的衰退。
2.2.2 謠言傳播機制
謠言傳播機制由謠言傳播動力、謠言傳播特點和謠言傳播控制策略等組成。對謠言傳播機制比較科學和系統的研究始于1944年,Knapp以馬薩諸賽州的謠言為例,初步研究了謠言產生的原因、后果和控制策略[5]。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1986)在《風險社會》中首次提出了“風險社會”的理論概論,隨后成為謠言傳播機制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6]。近年來,趙洪涌(2015)[7]、陳華(2016)[8]等學者對偏泛函微分方程理論、謠言傳播外部環境等方面開展了實證分析和仿真研究。
2.2.3 謠言傳播公式
在謠言傳播機制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為了提升其普遍適用性,廣大學者開展了謠言傳播公式的相關研究。1947年,奧爾波特認為,謠言=(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指出了謠言的產生和事件的重要性與模糊性成正比關系。1953年克羅斯對上述公式進行了完善,其認為謠言傳播與公眾的批判能力有相應的關系。國內學者對謠言傳播公式進行了修正和改進,具體包括郭小安(2014)[9]引入“敏感度”變量等。
2.2.4 謠言傳播模型研究
謠言傳播公式為構建謠言模型奠定了基礎。基于前人研究基礎,Daley和Kendall(1965)[10]提出了謠言傳播經典的數學模型,后來被稱為DK模型。Maki和Thomson(1973)[11]對DK模型進行了修正,并提出了MT模型。隨著對謠言傳播研究的不斷深入,Zanette(2002)[12]、蘭月新(2012)[13]等學者相繼進行了小世界網絡建模、演化博弈建模等相關研究。
在進入大數據時代后,信息傳遞呈現了新的特點,謠言傳播模型相關研究也出現了新的趨勢,擴展模型順勢而出。王彥本(2016)[14]、范純龍(2017)[15]、等學者提出了SIR-CO、SIR-TV等擴展模型。
2.3 “健康謠言”相關文獻梳理
從文獻檢索結果來看,“健康謠言”相關文獻746篇,文獻總量遠遠少于“網絡謠言”,同樣也是從2011年開始至2017年保持了持續遞增的發展態勢。然而,從《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No.7(2016)》和《2017騰訊公司謠言治理報告》等調查結果來看,作為一種專業性細分議題,健康謠言是網絡謠言的重災區。同時,在眾多的網絡謠言中,最具典型性的兩次重大謠言事件均為健康領域謠言:一次是2003年非典時期由于“板藍根能治療非典型性肺炎”的謠言引起市民瘋搶板藍根事件;另一次是2011年日本核泄漏時由于“食用含碘物質可以防輻射”的謠言引起許多國家的民眾搶購碘鹽事件。可見,因與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益密切相關,健康謠言往往能夠瞬間引起極為廣泛的關注度和極為嚴重的不良反應。反而觀之,“健康謠言”現有文獻數量卻相對過少。
2.3.1 健康謠言內容與特點
大多數學者認為“健康謠言”主要包括健康養生類、食品安全類和人身安全類等內容。隨著研究的深入與發展,彭曼(2007)[16]、劉岱淞(2010)[17]、茹倩倩(2012)[18]等學者認為健康謠言還應該包括醫患關系謠言。結合健康謠言的內容,羅政鋒(2017)[19]等學者研究發現,健康謠言具有貼近生活、以偏概全、圖文并茂、危言聳聽、來源模糊、新瓶舊酒等特點,見圖1。
通過對近5年十大健康謠言的主要內容進行概括和整理,并運用Nvivo 12.0軟件對近5年(2014-2018年)的十大健康謠言文本內容進行編碼,形成了15個節點。從節點的內容來看,基本驗證了學者們對于網絡健康謠言內容與特點的觀點。從圖1中可以發現,食品、癌癥、細菌病毒相關的健康謠言信息出現頻次排名前三,分別為19次、16次和10次。同時,從圖中還可發現,諸多健康謠言在多個年度的健康謠言中都有出現,屬于新瓶裝舊酒的現象,尤其是在食品、癌癥、細菌病毒這些出現頻次較高的健康謠言信息更為明顯。例如“低鈉鹽就是送命鹽”就分別曾在2016年和2018年的十大健康謠言中出現。
此外,如圖2所示,除了食品、癌癥、細菌病毒等健康謠言的經典主題外,健康謠言的內容也隨著年度熱點事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具有一定聯系。例如霧霾等一系列的生態環境惡化引發了社會的關注,于是吃豬血鴨血能除霾、霧霾不散是因“核污染、霧霾顆粒堵死肺泡等相關健康謠言便順勢而起。

圖1近5年(2014-2018年)十大健康謠言編碼節點分析圖

圖2 近5年(2014-2018年)十大健康謠言節點關系圖
2.3.2 健康謠言傳播動力與原因
業內學者主要從傳播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對健康謠言的傳播動力與原因進行了探討。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李寧(2018)[20]等學者的研究發現,在健康謠言傳播的過程中“沉默的螺旋”“意見領袖”“把關人”起著關鍵作用,同時受近期熱點公共衛生事件影響較大,而中央級官方媒體的辟謠作用較為明顯。從心理學的視角來看,宋文淵(2016)[21]等學者的研究表明,健康謠言傳播是由“社會風險”議題的應激回避心理、醫學知識缺乏和“群體意識”下的跟風從眾心理、“首因效應”和面子因素等多種社會心理和情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鄧勝利(2018)[22]認為社交媒體附加信息對用戶信任與分享健康類謠言具有重要影響。
2.3.3 健康辟謠理論與觀點
在掌握了健康謠言的基本動力和原因后,健康辟謠理論與觀點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熱點。謝志強(2011)[23]提出了政府公信力學說,認為辟謠成功的關鍵在于政府有公信力。李彪(2012)[24]稱微博辟謠是偽命題,進而提出了自凈理論說,并認為網絡會把真相還原達到“無影燈效應”。此外,阮鵬(2013)等[25]還認為公眾的科學素養或謠言判斷力是謠言傳播的天然阻力。李瑞芳(2017)[26]認為健康辟謠,需要基于文化關注和回應公眾,才能避免辟謠的負面結果。胡文嘉(2018)[27]認為在新媒體環境下,食藥安全領域辟謠需要聯合開展多主體辟謠、平臺化辟謠以及互動式辟謠。
2.3.4 全面看待健康謠言
有學者認為健康謠言并非一無是處,同時辟謠過程應當注意規避“塔西佗陷阱”問題。胡獻忠(2011)[28]提出任何網絡現象都不是空穴來風,虛擬網絡中的很多現象是因為在現實社會中無法普遍實現的緣故。由此,健康辟謠過程中容易產生“塔西佗陷阱”“羅賓漢情節”等問題,這引起了楊妍(2012)[29]等學者的注意,他們認為重塑政府公信力是應對“塔西坨陷阱”的關鍵,為健康謠言相關研究提供了更為全面的視角。
從更廣泛的層面來講,健康謠言的治理從屬于健康傳播范疇,國內外學者進行了相關探討與實踐。健康傳播最早見于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的流行病學研究,正式見于1971年美國的“斯坦福心臟病預防計劃”,現今較為通用的概念是美國學者羅杰斯(Everett M Rogers)在1994年提出的界定,即健康傳播是一種將醫學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易讀的健康知識,并通過態度和行為的改變,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個社區或國家生活質量和健康水準為目的的行為。中國健康傳播研究始于1987年的全國首屆健康教育理論學習研討會,1993年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醫科大學主編的健康教育教材《健康傳播學》,隨后第一屆中國健康傳播大會于2006年召開,這標志著健康傳播研究已經獲得廣泛關注。近年來,我國羅毓琪(2016)[30]等學者認為健康傳播研究議題涉及廣泛,既包括以艾滋病預防為龍頭的疾病預防,也包括抑郁癥、藥物濫用預防、醫患關系研究、戒煙等內容,從而豐富了健康辟謠的領域與內容。
3 討論
3.1 研究內容
“網絡謠言”相關研究的內容更為廣泛,不僅涉及傳播學、心理學、社會學、計算機與網絡信息技術等多個領域,同時更加系統化和理論化,基于成熟的理論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健康謠言”相關研究的內容雖然也呈現出了多學科的特點,但其研究不夠聚焦,因而相對只形成了較為分散的各類學說,未能形成系統化的經典理論。因此,健康謠言研究內容需要集萃聚焦。就健康辟謠研究而言,應集萃健康辟謠的學說和觀點,即明確辟謠主體和途徑,同時聚焦健康辟謠的內容,形成系統化的理論。
3.2 研究方法
當前的研究中,“網絡謠言”相關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加多元,除了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外,還應用了計算機技術的模擬仿真等方法。“健康謠言”相關研究的研究方法仍然較為單一,基本為獨立應用定量或定性的研究方法。因此,健康謠言研究方法需要多元創新。就健康辟謠研究而言,應當采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同時尋求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尤其需要引入大數據技術。
3.3 研究層次
“網絡謠言”相關研究已經相對成熟,當前已進展到第五個層次,即模型構建層面,基礎模型、改進模型以及擴展模型已經出現,但缺乏相應的實證數據來佐證和評價。而當前“健康謠言”相關研究尚處于第三個層次,即觀點創新和理論建構層面,尚缺乏公式及模型相關研究,但既有研究表明公式及模型下一步研究發展的趨勢。因此,健康謠言研究層次需要及時提升。就健康辟謠研究而言,應當適時、科學、合理地提出健康辟謠基礎模型并進行實證研究和評價,進而提出改進模型。
4 小結
綜上所述,無論“網絡謠言”相關研究還是“健康謠言”相關研究,二者的終極目的在于客觀地認識各自領域謠言的本質,即謠言表象背后的真相,并科學地對謠言進行治理,盡可能地減小其危害。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文獻分析,可以認識到大數據背景下健康辟謠模型的相關研究呈現出以下3個發展趨勢:一是衛生主管部門公信力、醫療機構解釋力、受眾群體判斷力是健康辟謠研究內容的3個關鍵因素,同時應當聚焦健康促進、食藥安全、醫學治療和醫患關系4個重要內容;二是在大數據的時代背景下,用戶行為挖掘、文本內容挖掘、多智能體模型等適宜技術與方法能夠為健康辟謠研究提供方法論層面的有力支撐;三是健康辟謠模型的理論建構及其實證研究有助于提升健康辟謠的研究層次,同時也將會是未來的發展方向。